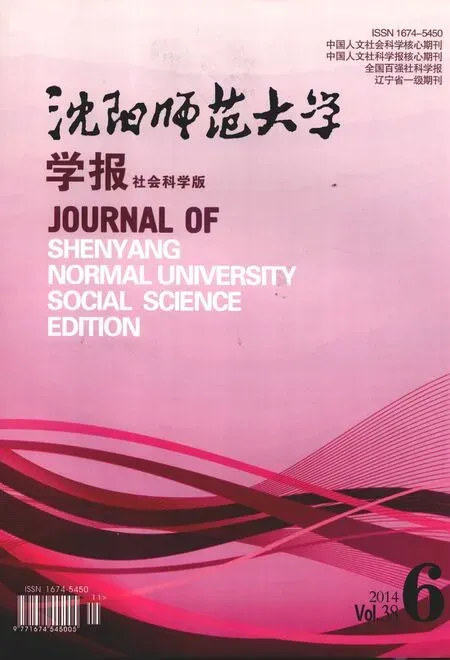满语文保护抢救的意义与现存问题
2014-04-11曹萌
曹萌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
满语文保护抢救的意义与现存问题
曹萌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保护抢救满语文的价值意义主要是保护抢救一个民族“物种”,而使之不至灭绝。同时,也是盘活珍贵历史文献、认识和解读清朝历史的需要,以及打造和传播满族聚集区最有影响力文化品牌和提升该区域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前保护抢救满语文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面对处于濒危和亟待保护抢救的满语文,我们应该在满语文保护抢救意义的感召下,针对满语文保护抢救工作诸多问题,努力构建科学的保护抢救战略和机制并予以实施,从而将满语文的保护抢救推向一个新阶段。
满语文;保护抢救;现存问题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了不起的民族。从宏观的视角看,满族的历史贡献有三:一是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久的中央统一政权。清王朝在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在极力维护中国大一统的基本格局;二是满族开拓进取、善于学习的精神值得称道。满族建立中央王朝后,出于巩固和发展本民族统治地位长远利益的需要,能够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和吸收汉文化,不断推动民族自身的发展。他们虽然丢失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但得到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其三,满族荣辱不惊、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境界令人敬佩。满族作为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辛亥革命后,社会上对满族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使满族在政治上感到压抑。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民族的兴衰沉浮,满族人民能够顾大局、识大体,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因为这样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满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体现出一定的优秀品质,传承发展优秀满族文化也成为当代的责任和使命。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根本性、核心性要素,是满族文化传统和资源的根本性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满语文在经过特定历史时期的辉煌之后,逐渐走向了退化和式微,到今天,满语文已经进入濒危语言文字行列。抢救满语文是传承发扬满族文化的基本方面和根本保证,因此本文拟就满语文保护抢救的意义与现存问题作一定的描述和说明,以期对当今满语文的保护抢救提供特定的学术支持。
一、保护抢救濒危满语文的价值意义
濒危语言文字是指使用人口比较少并且在许多的社会适用领域中没有发挥其社会使用功能的语言文字。其濒危标准有5个指标: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母语使用者的年龄;母语使用能力;母语使用范围;民族群体的语言观念。弱势语言文字一旦消亡,其中积存和蕴藏着的文化现象也将随之消失,到时候再想收集、整理那些民族语言文字将成为一件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憾事。这既是使用该语言文字的群体的损失,也是人类财富的损失。一位著名的国际语言学家说过,语种的消亡与物种的灭绝一样可怕。因此,保护抢救
濒危的满语文实质是保护抢救一笔特定的文化遗产。这样一来,该工作和相应的努力就不单单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研究具有特定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为此,我们将保护抢救满语文的价值意义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抢救保护满语文相当于保护抢救一个民族“物种”,而使之不至灭绝。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语文是该民族族众思维活动和思想成果的载体,是该族族众表达生活发展愿望和进行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一般说来,某一民族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创造、使用与发展的文字,总是与该民族的文化进步、文明进展和民族传统习俗等密切相连,亦即有着深刻的民族烙印,反映着使用该语言文字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生产及生活方式的特点。因此,语言文字不仅成为识别民族种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族“物种”的标签,对于使用这一语言文字的民族而言,语言文字还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并且能贮藏和传播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满族语言文字是满族民族“物种”的根本性特征。这样,在国家层面上,保护抢救满语文是体现满族民族特色、促进民族团结、合理处理民族关系的必要之举。如果满族将来没人会讲满语、写满文,没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物种”,也就是灭绝了。因此,抢救保护和传承满语文是抢救保护和民族“物种”不灭绝的需要。
第二,抢救保护和传承满语文是盘活珍贵历史文献、认识和解读清朝历史的需要。满族文字创始于1599年,之后,满族就主要用满文记录本民族的历史、政治、军事、文化宗教和生产生活,积累了厚重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典籍。如今,这些文字资料已成为考察和研究当时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的珍贵资料;同时,清朝还将一大批汉文的经典名著译成满文,以促进满汉文化交流。这样,在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文字历史发展中,在数量上,满文就成为仅次于汉字留存于国内的文字资料。不仅如此,在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发展中,满语文还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作为官方的语言和文字而使用与流行:政府文件、官员报告、地方记录和民间交流都曾经使满语文有过短暂的扩展和辉煌,并因此留下了大批的满文文献档案和其它记录。根据估算,目前,全世界的满文档案文献存量多达500多万件(册)。其中,至少有200多万件(册)保存在我国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20余万件(册)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有约60万册保存在黑龙江省,有1万余件(册)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现在已经破译的一些文献档案可知,这些满文文献档案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地理、宗教等各个方面。从学术价值,尤其是历史文献价值上说,它们对于清代历史文化的再现、对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了解和研究这些文献档案的前提是必须精通满语文,因此,如果不保护抢救满语文,不加快培养精通满语文的专家学者翻译解读这些文献档案,这些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将成为一堆废纸。
第三,保护抢救满语文是打造和传播满族聚集区最有影响力文化品牌和提升该区域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满族现有一千多万人口,国内分布有多个满族聚集区。他们大多是辽宁省、河北省和吉林省的满族自治县,尤其以辽宁省东部最为集中。在这些满族聚集区域里,满族文化成为最突出和典型的地域文化,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资源;满族文化是这些区域文化软实力的一张名片。满语文则是这张名片上最根本的符号和图标:因为人们只有通过满语文的引导,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认识和肯定这张名片。因此,保护抢救满语文,必将极大地提升满族聚集区域的文化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支持该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展。
二、当前满语文保护抢救存在的问题
尽管满语文的保护抢救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或者表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景况,但是,从调查和考察的结果看、从满语文的濒危程度和已经展开的满语文保护抢救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看,目前满语文的保护抢救仍然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将这些问题归纳起来,表述为以下8个方面。
一是与满语文保护抢救相关的研究机构多,但规模小、层次低、满语文专业研究人员匮乏或老化。当前,国内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满族文化为宗旨、与满语文保护抢救有密切关系的满族文化研究机构几乎遍布全国,在东北三省和北京市尤为密集。但是,如果从保护抢救满语文功能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来评价这些研究机构,可以明确地见出这些机构的不足或阙失,即规模小、层次低、满语文专业研究人员匮乏或老化。这里仅以辽宁省现存的满族文化研究机构与满语文保护抢救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机构作一说明。辽宁省共有这类研究机构9家: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清史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辽东学院满族服饰研究所、大连民族学院东北民族研究院,以及辽宁省档案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清前史研究中心和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上述研究机构,除沈阳师范大学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大连民族学院东北民族研究院具有5名以上专业研究人员外,其他的研究机构大都是由1-2名该领域专家牵头搭建,或由2-3名专家构成,而机构中的满语文研究专家大多早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如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关嘉禄研究员、辽宁省档案馆的佟永功研究员、孙成德研究员,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武斌研
究员、佟悦研究员,以及抚顺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波研究员。他们或者已经退休多年,或者即将退休。这种情况在北京市也有所表现。该市与满族文化研究、与满语文保护抢救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机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以及《民族文学》杂志社、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其中的主要专家学者分别是赵展教授、赵志忠教授和戴逸教授,以及关纪新研究员、赵志强研究员,以上罗列的专家中,赵展教授、戴逸教授年事已高,赵志忠教授临近退休,最年轻的专家赵志强研究员也已经57岁。满族文化研究机构中的这种满学专家、满语文专家空缺状态,直接导致了所在研究机构不再直接地进行满语文的保护抢救工作,亦即研究平台的满语文保护抢救功能弱化或衰退。
二是国内用满语文研究满学的专家学者非常稀缺,仅有的几位精通满语文的专家学者大多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学界,满语文人才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情况异常突出。因为,满族是一个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民族,具有开放性,对外来文化积极主动吸纳,尤其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对汉文化积极吸取。同时,作为清朝的统治民族,需要尽快学习掌握先进的汉语文。所以进入清朝中期以后,满族在语言文字使用上就从满语单语进入到满汉双语,最后大多转用汉语。发展到今天,满语只有极少数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一代已经失传,仅有的懂得满语的满族人对母语也是只有听的能力而说的能力极低,有的根本就没有说的能力。满语文作为交流的功能已经严重衰退,并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濒危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满语文研究满学的专家学者也非常稀缺,而且既有的专家学者大多年事已高,退出工作岗位并逐渐淡出学届。以辽宁省为例,辽宁省是满族和满语的故乡,现在省内能用满语研究满学的专家学者只有关克笑、关嘉禄、佟永功、邹兰新、康尔平、李荣发、鲍明、李云霞、何荣伟、张丹卉等人,其中前六位都已经年过七十或年近七十,早已退休。他们在满语方面的专长在社会上已经衰退,或者已经被学界逐渐淡忘,其余几人也都年近50岁,而且也很少有人坚持用满语文研究满学。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市也有体现。现在该市仅有的几位能够用满语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赵展教授、关纪新研究员、赵志中教授,也分别为80多岁和60多岁,因为年龄偏大,其淡出满学界已是在所难免。放眼国内,目前能够用满语文研究满学、而且正在进行该类研究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
三是满族民间社团组织数量多,但绝大多数与保护抢救满语文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从理论上说,满族联谊会一类的民间社团也应该在满语文的保护抢救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提供直接的支持。但是,从保护抢救满语文工作的角度看,目前分布在全国大约30多个城市的区域满族联谊会,以及与满族联谊会主旨近似的社团组织,如满族经济文化促进会、中国满族音乐研究会等,这些民间社团组织尽管大多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满族文化、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联谊活动为宗旨,大都未把保护抢救满语文列为其工作目标或努力方向之一,只有个别满族联谊会,如抚顺市、承德市满族联谊会做了一些满语文普及工作。
四是专家学者、政府部门或社会人士提出的满语文保护抢救建议或方案多,但付诸实施的少。满族已经走过了400多年的历史,满族文化已经呈现为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很多领域,有很大的精华部分成为今天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遗产:有的供人们学习研究,有的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满语文作为该类资源和遗产的重要组成和核心要素,其保护抢救价值和意义已经被许多专家学者、政府部门或社会人士认识到,且达成共识,并因此提出了很多保护抢救满语文的呼吁性方案和建议。如苏珊的《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从族语认证做起》(《中国民族报》2014.5)借鉴台湾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方面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认证考试体系,提出为挽救濒危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也应积极尝试、建立少数民族语言认证考试的制度;刘正爱在《“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民族研究》2010.4)中指出国家制度对民族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新宾满族自治县就国家、地方、个人三者之互动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刘思波《满语文行走在遗失路上》(《抚顺日报》2010.12)提出民间地区在挽救满语文方面应该作出贡献;孙成德《满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兰台世界》2014.1)提出借由计算机等高科技软件及政府在政策上的主导,对满语文的保护抢救具有重要作用;于凤贤的《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语文的不断发展——黑龙江省民族语文工作30年》指出:有关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制定才能更好地保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发展;栾福鑫《满语保护和发展的政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6)指出:保护满语文还需要大力借助国家的政策力量、上升到一定的国家政策观照的高度才能更有利于满语文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在满语保护过程中应完善政策意见表达渠道,获取专业看法、主动访谈专家学者,提升满语政策方案编制主体素质等;曹萌教授也提出过《非馆藏满文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数字化系统建构》(《沈阳师范大学》2013.6)和以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辽宁建设满学研究院等建议。应该说专家学者、政府部门或社会人士针对满语文保护抢救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大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也大多合理或可行,但这些意见很少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也很少有付诸实施。
五是满学界缺少满语文领域的研究成果,语言学角度的满语文研究成果甚少,满语文理论建构阙失。满学在我国同汉学、藏学、蒙古学合称四大显学,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科与学术热点。近百年来,经过许多满学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研究,满学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果丰硕。纵观满学界的研究成就,我们却不难发现,学者们在满族历史研究、满族文化研究、满族人物研究和宗教习俗研究、甚至饮食服饰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著作颇丰,但是,在满语文研究方面却成果寥寥,从语言学理论角度研究满语文的论著更为罕见。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的《满语语法》(民族出版社,1986年),赵杰的《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89年),以及关嘉禄、佟永功的《简明满文文法》和鲍明《辽宁满汉混合语调查》,佟永功《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六是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满语文保护抢救缺乏高等学校教育层次的有力支持。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人口在1000—500万人之间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土家族、彝族、藏族、蒙古族。在这九个少数民族中,壮族聚集区有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回族聚集区有宁夏大学;维吾尔族聚集区有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蒙古族聚集区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藏族聚集区有西藏大学;苗族、土家族聚集区有西南民族大学。上述高校均设有院系专门对于该聚集区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研究。满族聚集区域则没有高等学校专设的满语文院系,这使得满语文的保护抢救缺乏高等学校教育层次的有力支持。
七是满族文化载体多,满语文在满族文化载体上的展现不够。目前,国内满族文化载体甚多,尤其在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和北京市内,到处可见满族文化的遗址、遗产和其他载体。仅以辽宁省为例。该省就分布有省级以上满族物质文化遗产18处,其中还包括4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布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此外,还有13项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观地说,满族文化载体在辽宁省无论是数量还是品位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些载体也绝大部分被作为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的内容开发出来,展示于游客眼前。但是,统观这些展现在游客眼前的满族文化载体,其上很少有满族文字的标识或满语文的介绍,也很少在汉语、英语、日本语、韩语介绍的同时配备满语文介绍和解说。这种文化载体介绍说明方面的语言文字上的缺位,也是保护抢救满语文工作中呈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负面问题。
八是满文文献档案资料甚多,而翻译利用极少,绝大多数即将成为死档和“天书”。在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文字历史上,用满语文记录书写而留存下来的文献档案的数量是仅次于汉文记录书写而留存于国内的文字资料。在有清一代的满族统治期间,满语、满文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作为通行的国语而被广泛应用。在“国语骑射”的政策实施中,当时的政府文件、官员报告、满族上层社会的交往,以及满族青年人的学习内容,都主要是满语文。满语文作为清朝一定时期广泛应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书写记录了清王朝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的满文档案文献和古籍。据专家估算,目前,全世界存贮的满文文献档案多达500多万件(册)。从现在已经破译的部分满文文献档案看,这些汗牛充栋的满文文献档案所记载和书写的内容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地理和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它们对于了解认识满族的历史发展,考察清代社会实况,对于社会科学特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当前我国现有的1000多万满族人口中,精通满语文并能够翻译和阅读这些满语文文献档案的只有关嘉禄、佟永功、鲍明、王硕以及何英伟、程大鲲、张虹等几个专家学者。浩如烟海的满语文文献档案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满语文专门人才的缺乏而逐渐成为死档和无法破译的天书。
综上所述,面对当今处于濒危和亟待保护抢救的满语文,我们应该在上所归纳、揭示的满语文保护抢救意义的感召下,从上所分析描述的满语文保护抢救工作诸多现存问题中,努力构建科学的保护抢救政策和机制,认真落实或实施保护抢救方面的举措、行动和战略,从而将满语文的保护抢救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
[1]李世举.辽宁满族文化资源现状及开发对策研究[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2).
[2]王焯,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护模式探究[J].文化学刊,2009 (6).
[3]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传统与创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7).
[4]闫晓敏,黄愉强.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语言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9).
【责任编辑 詹 丽】
H313
A
1674-5450(2014)06-0013-04
2014-08-22
国家语委项目《保护抢救濒危满族语言文字的战略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013011009);日本住友财团项目助成番号(138053)
曹萌,男,辽宁建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学报主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传播学、跨境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