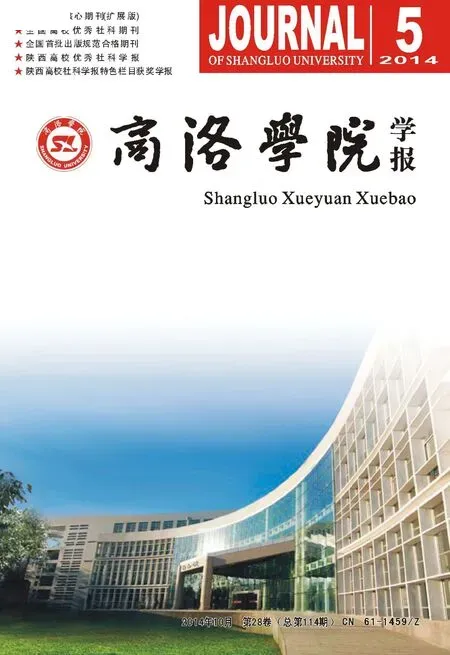文学四要素视阈下的余华创作转型
2014-04-10冯超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文学四要素视阈下的余华创作转型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自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历经了两次转型。余华的这两次转型,评论界历来莫衷一是,褒贬不一。借助艾布拉姆斯有关文学活动要素的理论,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等四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试图对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创作转型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文学四要素;余华;创作转型
从1985年开始,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先锋小说,这批作品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陈思和先生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关照之后发现,对叙述方式、语言形式和人生存状态等三个层面的解剖与审视成为实验期先锋小说的创新所在。不同于马原、洪峰、孙甘露等先锋作家对小说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的极大关注,余华作为第三个层面的代表,向我们展示的总是普通人的生与死、泪与笑。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初登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皆影响出众,好评如潮。其中尤以短篇小说《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和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2005年推出的《兄弟》引人注目。尽管余华的创作仍在延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创作生涯进行阶段性划分,在客观而又审慎的观察之后,我们试图将他的创作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7-1992):代表作品为《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第二阶段(1993-1995):代表作品有《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三阶段(1995-2005):代表作品是《兄弟》。这三个阶段也可以分为两次转型,即由“先锋文学”到“温情现实主义”的转变,再由“温情现实主义”向“通俗文学”的发展。对于余华的转型,大多评论文章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积极肯定的评价,并称之为“胜利大逃亡”[1]。但纵观各种评论后发现,由于缺乏整体评价体系和客观评价标准使得各类意见略显武断或绝对。那么本文首先对余华的创作历程和转型作一简要评析,然后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角度对余华转型的是非成败进行分析,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其做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一、创作转型:从先锋文学到温情现实主义再到通俗文学
首先,先锋文学的代表。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初登文坛的第一篇作品,之后的《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等一批作品的涌现,使得1987年至1992年成为他创作的集中爆发期。从县文化馆走出来的余华,在西方现代思想的熏陶下,开拓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中救了出来”[2],余华的自述不仅是他文学灵感的追根溯源,更是他的作品在先锋文学中独占一角的原因所在。
十八岁本是个青春的故事,但“我”却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见识到了一个充满荒诞与混乱的世界。虚伪、丑陋、欺骗,世间所有的恶像弥漫无边的黑夜一样猛然袭来,少年心中的善良与真诚瞬间粉碎。滚落满地的苹果、哈哈大笑的司机、疯狂抢掠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撼动少年未谙世事的心。十八岁的第一次出门不仅是一次探险,更是一个青春少年的成人礼。《现实一种》则讲述了一家人相互仇杀的故事,山岗的儿子皮皮不小心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即山峰的儿子,先是山峰踢死侄子皮皮接着山岗又杀死弟弟山峰,最后山岗因杀人罪被枪决,而正是山峰的妻子导致山岗的尸体遭到肢解。作品是以一种极端的叙事对伦理文化及人性本质实行了彻底的颠覆,其先锋性是突出的。《古典爱情》则是对旧式才子佳人小说的反叛。才子归来,本想重续因缘,但昔日的美景佳人在颠覆性的反转之下,已沦为供人食用的“菜人”。撕心裂肺的惨叫,血肉横飞的肢体,古典爱情的期待与美好在余华笔下被撕的粉碎。
新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总是伴随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决裂,此时的余华已成为先锋小说家的代表。不管本期作品的主人公是谁,他们大都经历了人性暗陬中最丑陋最阴暗的部分,余华在“去谎言”的基础上慢慢揭示着人性的弱点。罪恶、酷刑、死亡、欺诈、暴力、犯罪……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之间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异化关系,而遮蔽在真实生活表层之下的世界末意识和生存危机感更让人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悲观和虚无中。读者对于人性真实的思考,对于自然的存在疑虑成为作品的主题。此期的余华与其说是故事的讲述者,倒不如说是神秘的预言家,他在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编码中告诉每一个试图走进他的人:生存虽然伟大,但同时又很可怕,生存于世的任何人在兽性本能的驱动下总是显得过分无力和苍白。“余华的世界在虚伪的面纱之下是混乱而荒诞的,常识即是荒谬,人类的欲望是苦难的根源,人被欲望支配着无可救药的成为摆在解剖台上的冷冰冰的尸体。”[3]于是,操起手术刀,像一个解剖世人精神世界的医生一样,用比现实还要冷酷、残忍、真实的刀法,酣畅淋漓地划开那带血的“现实”和“人生”就成了余华先锋时期的一抹亮色。
其次,温情现实主义的转变。虽有痛苦的挣扎和深度的解剖,但已经丧失了持续解决现实难题能力的先锋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和思想震荡中逐渐式微。余华的强大之处正在于此,他并没有像马原、孙甘露、格非一样渐渐隐退直到淡出人们视野,而是从实验回归传统,在一个“温情的转身”之后,从一个冷酷、残忍、无情,甚至“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4]的先锋号手,转变成了一个善良、悲悯的温情现实主义作家。于是,《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陆续推出,成为余华本期转型的丰硕成果。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故事“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小说,通过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讲诉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诉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诉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诉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5]4福贵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诸多重大事件和所有亲人的接连死亡后,依然活着,坚强的活着。或者正如余华在前言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5]2,他的活虽在人生存本能的驱动下,但却超越了生命的存在,具有了不苟且、不残喘、不放弃的精神尊严和象征价值。《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卖血的故事。12个月为一年,12年为一个轮回,12次卖血组成了许三观看似卑微实则伟大的一生。普通人维持个体生命存在的血液,在许三观的血管已经变质,“血——钱”交易之下潜藏着他生存下去的渴望和动力。此时的余华,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观感摆脱琐碎的日常和冷酷的现实。较之前期应对现实时的紧张态度,疏离与缓和成为他解决问题的一种新尝试。或许正如余华自己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5]2。新创作观念的确立,总是伴随着新人物的成长,而对残忍、虚伪、冷酷等人性恶的剥离,使得凝固在余华血管中的“冰碴子”开始融化,变成了有温度、有感情的新鲜血液。于是,苦难如山的福贵在灾难一次次袭来的时候并没有一蹶不振,怨天尤人,而是坚强、从容的面对,呼喊出“我就是死了也要活着”的生存悖论。同样,被生活压不垮、折不断的许三观除了生存下去的坚韧,骨子里透出来的是与家庭、伦理、血缘缠绕在一起的感动与美好。缺失了多年的温情伴着余华深邃的审视重新复苏,大地之子的同情与怜悯让他由先锋转向了温情。
最后,通俗文学的发展。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发表后,引起文坛一片称赞,被认为是一部从没有被指责过的佳作。在经历了漫天遍野的称赞后,余华一度陷入了沉寂与等待。终于在十年后的2005年,他带着号称“十年磨一剑”的《兄弟》重新归来。
《兄弟》中异父异母的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在重新组合的家庭里,承受着“文革”的狂热与改革的浮躁,生活的裂变夹杂着悲喜与苦难让两个人的命运同这个嬗变的时代一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波澜,恩怨交错的他们伴随着家庭的崩溃离析渐渐走向了毁灭。故事中的人物既现实又虚妄,场景即滑稽又残忍,性饥渴以致变态的李光头父亲,殴打宋凡平两眼血红的红卫兵,宋凡平下葬时因棺木过短被迫折断的双腿,孙伟的父亲用大铁钉三次砸入脑袋而碰裂出的脑浆……一个个人物、一幕幕场景一起构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奇特风景画。在小说的上部,所有人物都处于一种血红色的癫狂状态中,但在残忍的表象下还有李光头与宋钢之间的兄弟深情能够安慰读者的心灵。而到了小说的下部,充盈其间的感动在余华后现代笔触的浸淫下消失的无影无踪,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在现代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下侵袭着读者的视线与神经——无聊近乎于无耻的处美人大赛,坐飞船上太空的闹剧风波,满城充斥的洋垃圾西服……那个先锋小说时期冷静的近乎残忍的余华,那个温情现实主义时期善良的近乎悲悯的余华,在狂轰乱炸的市场助推下改变了。余华的改变不同于非典型意义上外部疏离,而是在急剧的跃动中表现出极强的彻底性和决绝性。虽然在文字选取和语言组织上,余华依然钟情于死亡、暴力、鲜血、尸体等“零度词汇”的使用,但是在失去了直抵人心的思想批判和耀人眼球的写作技巧后,那些冰凉的让人窒息,冷酷的让人疼痛震撼已经不复存在。“十年磨一剑”而成的《兄弟》只是一个有趣的、喧闹的,外表深刻实则通俗的“故事”。当然,商业营销的胜利也是成功的一种,不过为了获得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也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的勒索,来赚取那些廉价的眼泪”[6]。本期的余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通俗小说家。
二、转型的是非成败:文学四要素下的多维透视
到了2005年,已是不惑之年的余华,终于完成了他的创作生涯中两次华丽转身,从先锋文学到温情现实主义,再到通俗文学,两次转型都在读者和批评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讨论乃至争议。最后的结果无非只有两个,一曰成功,一曰失败。前者文章不可胜数,后者著作寥寥,但无论赞扬还是批评,各类评论家似乎只是从几个单一的角度对其两次转型做了一些并不全面的评价,而某种个人情感因素的渗入使得本该理性、严肃的文学批评沾染了嘲笑、辱骂、污蔑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色彩。因此,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角度对余华的转型做出分析就有了存在的可能与必要的意义。
从“世界”角度而言,余华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做出的两次转型,失却了对文学精神品格的坚守。《镜与灯》中的世界作为一个大范畴,是“文学活动所反应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7]30在这里,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我们研究当代文学中不能回避的独特背景,也是横向比照余华转型成败的度量衡。诚然,20世纪世界文学是在对异化人性的批判与普遍人性呼唤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除了“十七年”和“文革”将文学本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从而使其走上另一种极端外,总体上说是以“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贯穿全部”[8]的。文学正是人学,所有的文学活动归根到底都指向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终极价值与20世纪世界文学殊途同归。
以此为背景和参照系,我们不难发现,先锋时期的余华是何其的“先锋”。《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少年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喻、充满伤害和阴谋的世界;《古典爱情》中的美丽邂逅转瞬即逝;《死亡叙述》中的司机终究无法逃脱死亡阴影的追随;《现实一种》中的骨肉相残……先锋时期的余华作品,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暴力伤害,不可预知的命运捉弄。在看似阴森、恐怖的氛围中,透漏着心灵的惊厥和颤栗,但余华本质上不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他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非理性的暴力世界,更向世人表明了一种面对暴力的非理性态度。在作品中他以极端另类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思考,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颠覆实现其对精神本质的揭示,从而引起读者的惊奇与思索。但是他要向读者表达的却是一种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想给我们传达的是一种渴望,一种对正常的人生、人性的渴望。但是到了温情现实主义时期和通俗文学时期,余华作品中的渴望不见了,或者说变得模糊了,渺茫了。理性的思考与批判在极端艳丽、异常刺激的词汇中消失殆尽,只留存下来“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的福贵;为了躲避苦难而数次卖血为生的许三观;以油滑、暴力、色情为噱头的“兄弟”。到这儿,余华已经彻底改变,变得面目全非以致难以识别,他的身上淡去了对精神本质的揭示,淡去了对正常人生、人性的渴望,最终沦落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摊作家”,从这一点来说,余华的转型无疑是失败的。
从“作者”角度而言,余华作为创作主体在自我建构中做出的自觉、不自觉的调整与改变,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现实所指,人们匆忙的脚步是对这个多变时代的最好注解。时代在变,思想在变,世界在变,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中发展、前进。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作者“不单是创作作品的人,更是创作文学规范并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8]31,主体也并非总是食古,难免会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从而做出自己的调整和改变,因此从作家自身来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只是一批文学实验者。然而在探索面对现实的禁锢表现出反抗的无力时,潮头之上的作者就开始思考创作观念、创作风格的走向与未来。当然,不论如何选择未来的路,对于作者来说,读者的兴趣就是他们奋斗的方向,而时代的接受与认可则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的关键。两次转型的余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说:“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年轻的作家不明白一个道理,你写的作品在你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人接受你,以后永远也没有人接受。尽管现在很多例子证明作家死后获得了盛名,如卡夫卡,但他死后的盛名也是他同一时代的人给他的,并非他死了以后过了五百年被人像挖文物一样挖出来,他死了没几年其作品就风靡了欧洲。他死后的几年和活着的几年是一个时代,不是两个时代,他的作品是被共同的时代所接受。”[9]这两次转型对于余华来说,只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做出一些的选择和调整。因此,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余华的转型无可厚非,也理所应当。
从“作品”角度而言,余华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在转型过程中有得有失。作品即“作者创造出来的对象和读者阅读的对象”[7]32,先锋时期的余华小说,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和冷漠而又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构造了一种“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们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10]。他拒绝那些关于现实共享的结论,以他的体验和想象力来挣脱“现实世界”的围困[11]。冷漠是他的态度,残忍是他的方法,死亡和暴力是他的内容,而这正是余华先锋小说的本质特征。然而到了温情现实主义阶段,这一特征不复存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流露出的日常经验与他先锋时期所追求的本质的真实之间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时的叙述正如余华自己所说,“书中的人物经常开口自己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上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12]。对于事实我们不可置疑,但此时余华作品风格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死亡仍然是他小说中的主体话语,但其中流露出的些许温情和理解已经冲淡了他以往的冷漠。后来到了“通俗小说”的阶段,这些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当年血管里流着“冰碴子”的余华,此时流淌着的却是沸腾的热血。而这正是一种进步,叙事态度及风格的转变使得余华摆脱了先锋小说“独语式”的自我建构,从而在故事人物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条相互沟通连接的对话通道。
在语言艺术方面,余华先锋时期的小说语言是冷静的,或者说是冷漠的、无情的。余华只是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为我们讲述一幕幕他所知道的人间世界。因此,充塞他文字之间的比喻、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使得死亡、暴力、尸体、鲜血等新奇而又时髦的词汇混杂成繁复冗长的句子,其中蕴藉的先锋性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致敬。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时期,余华开始使用一种中国化、生活化的简单文字,且都具有口语色彩,句子较短,句式简单,修辞极少,叙述多于描写。可能有人会认为,简单的文字也能托起沉重的思想,对此我们不会否认,但是无法回避与忽略的是,简单的文字本身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作家文学才情的退化与丧失,而此时的余华正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中。当简单变为干瘪,苍白的语言已无力支撑庞大的思想躯体,他只能用干瘪的句子写出干瘪的人和干瘪的事。而到了《兄弟》时期,他的语言、文字更是毫无文采,虽有近乎疯狂的狂欢和看似豪华的盛宴,但文字却像白开水一样苍白、无力与重复,让人在索然无味的咀嚼中,丧失了仅存的阅读快感。此时的余华已经彻底地沦为了一个“码字者”,靠着庸俗的情节,苍白的文字,无力的思想堆砌出一部多达50万字的超长篇《兄弟》。虽然《兄弟》大卖,余华在商业价值上胜出,但作品低劣的艺术水平则让他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从“读者”角度而言,余华的两次转型都实现了作品视界与读者视界的重合与统一,这是作者书写策略的成功之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读者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有着重要作用。作为普通受众,有选择读与不读,也有选择读这个与读那个的自由,而这些却决定了作家及其作品的命运。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早已不是漂浮在普通民众之上的人造幻影,而变成了一种联通你我的商品。自此,严肃的、纯正的、精英的中国文学从大众聚焦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电影、电视等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网络、电子游戏、卡拉OK等娱乐形式在普通市民生活中的侵略与扩张,导致文学出现了消解与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的传播媒介在将文学推向边缘的同时,也给新时代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以余华的《活着》为例,正是因为小说在被知名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推向市场后,才引起了人们的密集关注和系列好评。从这一点来说,余华在感谢读者接受他的同时,更应该感谢的是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
当然,无论现代传播媒介如何发展,在余华创作的三个时期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先锋时期被人认识,名声大噪,余华在人类的“生存困境”方面开拓进取,成为先锋小说的旗手,而当先锋小说由于内在原因逐步走向式微,大多先锋作家已经渐渐地淡出了人们视野的时候,余华作为一个旗手却改旗易帜,放弃了先锋小说中对语言、形式和结构的过分关注,延续了自己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走向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大泽。此时的作品,更是受到了读者大众的青睐。据资料统计,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首版三万余册告罄,4月份重印。《活着》除了香港和台湾的大量发行外,还被译为英、法、德、意、荷、韩、日等国文字,余华也凭借该作品多次获奖,蜚声海外。1995年《收获》推出《许三观卖血记》后,199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立即出版单行本;1998年南海出版公司再度出版单行本,当年就创下七万册的销售记录……到了2005年《兄弟》出版时,在上海书展上,《兄弟》不仅名列上海各大出版社订货量榜首,而且作者余华还举行了三场长达两个小时的签名售书:9天的书展单本销售近6000本,成为近年来小说类图书单本销量的第一。很显然,余华的三个时期,两次转型,都完美的实现了作品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的相一致。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无论怎样,余华都在凌空高蹈的先锋舞台谢幕后引发了庶民的狂欢。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转型,不仅是极其成功的,而且对当今文学产业的发展和文人作家的生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结语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死守成规,灵活变通,几乎是艺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不变就没有创新,没有成果,也成就不了大业。但是说归说,做却又是另一种样子,要变不容易,选择怎么变,往哪里变却更难。尽管变革之途何其坎坷震荡,好在作家们都已达成了一个共识,正像余华所说的“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敢于不断地否定自己,重新出发,不断重复自己的作家只会较早的奔向坟墓”[13]一样,优秀的作家正是在否定之中,不断前进。
但是,作家终归是作家,他不同于追名逐利的地摊作者和一身铜臭的文化商人。作家除了通过文学创作来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还是要尽一些作家份内的责任,也要保持一些理性和道德。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各种文学思潮却像走马灯一样处于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反复与迷狂中。在过去的三十年,文学有焦灼,有浮躁,有勤勉,也有勇气,乃至悲壮。作家,有的被记住,有的被遗忘。不错,作家有时确实应该跟紧时代的步伐,走在潮流的前沿,但是潮流毕竟是暂时的,前一天的时髦,或许在明天就被新生者打下浪头,从此暗无天日,永不再被人记起。作家,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责任的作家,不应该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潮流的传声筒,不应该亦步亦趋的紧紧赶在时代和潮流的身后,而应在一个价值失范,人心浮躁的时代,摆脱现实的沉沦,坚守精神的家园。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2.
[2]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M]//我的写作经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3.
[3]何滢.余华小说创作转型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3.
[4]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M]//陈思和.2002年文学批评.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31.
[5]余华.活着·前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4.
[6]黄惟群.读《兄弟》,看余华[J].山西文学,2005(11):72-76.
[7]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5-41.
[8]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6.
[9]余华,张英.不衰的秘密文学[J].大家,2001(4):122-130.
[10]余华.虚伪的作品[M]//吴义勤,王金胜,胡健玲.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6.
[1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300.
[12]余华.灵魂饭[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210.
[1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154.
(责任编辑:罗建周)
Yu Hua's Novels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Elements of Literature
FEN Chao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
A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vanguard fiction,Yu Hua has gone through two transformations,after Long Travel at the Age of Eighteen since 1987.For Yu Hua's two transformations,the critics always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literary activities elements raised by Meyer Howard Abrams,we prepare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the world,writers,works,readers,trying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for Yu Hua's vanguard creation.
four elements of literature;Yu Hua;creation transformations
I206.7
:A
:1674-0033(2014)05-0032-05
10.13440/j.slxy.1674-0033.2014.05.07
2014-06-11
冯超,男,河南鹤壁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