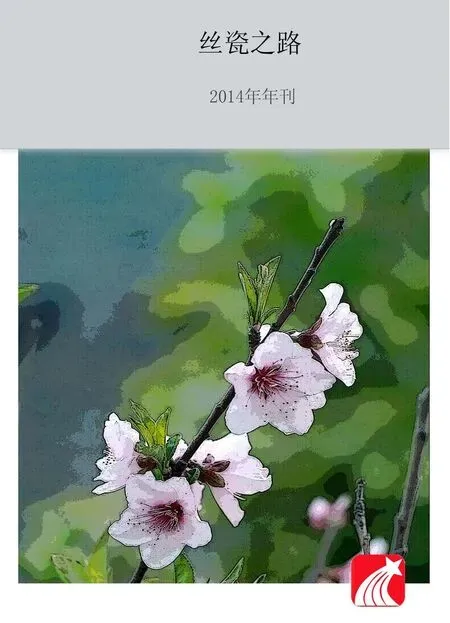“屯田”與“積穀”
——西漢在西域的農業活動拾遺
2014-04-10李豔玲
李豔玲
“屯田”與“積穀”
——西漢在西域的農業活動拾遺
李豔玲
學界對西漢在西域的屯田問題多有論述,對“積穀”事宜則鮮有涉及。關於屯田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屯田管理機構、屯田地點、方法及意義、屯田人員構成等方面。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屯田地域的變遷、屯田土地的來源及生產規模、積穀活動等問題做一些補充,以進一步考察西漢在西域的農業活動。不當之處,謹請方家賜教。
一
西汉政權最初屯田於何處?《史記·大宛列傳》稱漢伐大宛之後,“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1]《漢書·西域傳上》稱“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下》載“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漢書·鄭吉傳》記“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2]“使者”和“校尉”是“使者校尉”的略稱。[3]引文中記述的初次屯田地點並不一致,學界一般綜合兩書記載認爲武帝時期初屯輪臺,後又屯田渠犂。[4]按《史記·大宛列傳》由太史公撰述,其稱最先屯田輪臺當可信從。輪臺屯田是趁破大宛之威而設置的,當時漢破大宛雖獲得了向西域推進勢力的好時機,但尚無力量顛覆匈奴在這一地區的霸主地位,所以衹能屯田於被漢軍屠滅的輪臺以便觀察西域各國的動向,並宣揚漢之威德,同時積穀以爲漢之奉使西域者提供糧食。該屯田的設立時間當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5]
至於鄰近輪臺的渠犂屯田,當並不始於武帝時期。《漢書》記征和中,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向漢武帝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6]桑弘羊等就此提出了在渠犂屯田積穀的具體策略,但武帝並未採納。這一建議到昭宣時期纔得以實施。或以爲:桑弘羊對輪臺至渠犂一帶的情況比較瞭解,應正是太初、天漢間屯田的結果;奏言稱“益通溝渠”、“益墾溉田”,可以理解爲由於原有的屯田,輪臺一帶溝渠已通,溉田已墾,而桑弘羊不過請求增益而已,即他上奏時,輪臺、渠犂的屯田尚在進行;桑氏提出“置校尉三人分護”,是擴大原有屯田規模的需要。[7]分析奏言內容,可以發現,“益通溝渠”是用以描述輪臺以東渠犂等地優越的自然條件的。再者,即使存在已通的“溝渠”,也可能是當地土著居民修建的簡易的水利設施,其並無已有屯田的含義;後面的“通利溝渠”正是針對初次屯田而言,“益墾溉田”則是指校尉領軍屯田之後的募民墾殖活動,衹是一種設想。所以,桑弘羊的建議並未透露任何關於渠犂已有屯田的信息。
另外,《漢書》稱“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8]。意即設校尉屯田,坐鎮原已被開墾的輪臺,並以其地爲中心而實施桑弘羊征和四年之議開墾輪臺以東渠犂等地。[9]若早在武帝時期置校尉屯田輪臺以東的渠犂,又何須稱“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所以,桑弘羊的奏言恰說明輪臺以東渠犂等地在武帝時期不曾設校尉領護屯田,也無所謂當時渠犂屯田一度中止。[10]
因龜茲王殺賴丹,輪臺屯田再次結束。“輪臺”之名亦不復見於有關此後的漢代文獻記載。根據《漢書》中把桑弘羊等人建議與昭帝屯田輪臺及其以東事系於“渠犂條”,以及渠犂的道里四至記载了西到龜茲的距離,可推測昭帝屯田輪臺失敗之後,這一地區成爲渠犂的一部分,“輪臺”地名消失。如此,我們可以理解《漢書·西域傳下》與《鄭吉傳》所謂(初)置校尉屯田渠犂事,實指武帝田輪臺,即班固在記述時以廣義的“渠犂”指代原來的輪臺。[11]至於《西域傳上》稱“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應爲狹義的“輪臺”、“渠犂”,是班固連後事通叙之,其中渠犂有田卒是指昭帝時期校尉賴丹屯田事,而非言武帝時輪臺、渠犂已皆設校尉行屯田。
桑弘羊等人建議屯田輪臺以東,與破大宛之後西漢在漢匈交戰中損失慘重密切相關。特別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廣利兵敗降匈奴,影響着西域諸國對漢匈兩方的傾向性,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旨在使之不因漢軍不利而動搖。奏文中特別提到“輔烏孫爲便”,意在保證漢與烏孫的聯繫不被匈奴破壞,以免西漢斷匈奴右臂的努力前功盡棄。衹是因武帝面對內外形勢的變化,決定改弦更張,頒輪臺“哀痛之詔”[12], 桑弘羊等人的意見未被采納。漢與匈奴在西域的力量對比隨之有所變化,匈奴勢力轉甚。如匈奴扶立的樓蘭王因受匈奴反間,多次發兵遮殺漢使。匈奴還曾在征和五年(公元前88年)離間羌與西漢,言:“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13]這無疑會威脅漢通西域的大業。有桑弘羊等人輔佐的昭帝在即位初的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派賴丹領軍屯田輪臺[14], 並稱是“用桑弘羊前議”,當正是對這種狀況所做出的反應,其目的仍是爲對抗匈奴以維護漢在西域的威望。但西漢僅任命扜彌太子爲校尉行屯田事,並且對於龜茲王殺校尉上書謝罪,“漢未能征”,可知昭帝初期仍承武帝末年堰兵休士的策略,亦足見當時西漢的影響力已不比初破大宛之時。
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西漢屯田鄯善國的伊循。西漢經過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在始元、元鳳間有所恢復。匈奴內部自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則因爭單于位發生分裂而勢衰,對西漢北方邊境的威脅減輕。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本欲襲擊匈奴的漢軍大敗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15]。匈奴在寇漢北邊不利的情況下,又將戰爭矛頭指向與漢聯姻的烏孫,加強在西域的活動。傅介子使大宛,受詔責詰曾經殺害漢使的龜茲王和樓蘭王,說明當時西漢也有意重新增強自身在西域的影響力。傅介子從大宛還至龜茲誅殺從烏孫歸來的匈奴使者,回中原後又提出斬殺龜茲王,稱“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16],其最終按霍光令就近以樓蘭驗之。西漢欲再次樹立在西域諸國中的威望,也意味着要重新與該地匈奴的勢力對抗。漢殺親匈奴的樓蘭王而立親漢的尉屠耆,樓蘭更名鄯善。新立的尉屠耆懼被前王之子所殺,請西漢遣將在“地肥美”的伊循城“屯田積穀”,使之“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其後更置都尉”。[17]這樣既防前王之子反叛,更防匈奴勢力在樓蘭地區捲土重來,從而爲西漢控制西域南道,進一步經營西域奠定基礎。但西漢遣屯伊循人數少於武帝初屯輪臺時期,當與“鹽鐵會議”確定堅持與民休息之策有關。可能至地節二年或三年(公元前68年或前67年),伊循才更置都尉,擴大屯田規模,並由敦煌太守領屬。[18]
地節二年,宣帝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19], 以討伐親匈奴的車師。這緣於車師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而其親向勢力已衰的匈奴,威脅着西漢與烏孫的交通。[20]立足於渠犂屯田,西漢一度攻取車師地。面對匈奴發兵,宣帝“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21]。除爲穩固自身在西域諸國中的地位,西漢首次明確提出在西域屯田積穀以驅逐匈奴勢力爲目的。鄭吉聽從詔令,分渠犂田卒三百人別田車師。但終因車師地近匈奴而遠渠犂,西漢田卒無法應付匈奴爭奪車師,衹得罷車師屯田盡歸渠犂,由三校尉領護該地屯田,車師地重歸匈奴。
隨着匈奴勢力的日益衰落,主管西方的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降漢,車師亦附漢。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漢在鄰近渠犂屯田區的烏壘設立西域都護府,並新辟比胥鞬屯田。即如《漢書》所記,“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都護治烏壘城”。[22]懸泉漢簡證實,文中“北胥鞬”爲“比胥鞬”之誤,並且該地屯田設有比胥鞬校尉。[23]西漢將渠犂的部分屯田士遷徙到比胥鞬,至於其在現今何地,學界意見不一。[24]我認爲在莎車國境內的觀點更爲合理。[25]或以爲西漢將匈奴勢力逐出車師地,不隨即在該地或附近屯田,於理不合,所以比胥鞬應在車師境內。考慮當時情勢,車師附漢,經由車師的交通開始暢通。匈奴設在焉耆、危須、尉犂間的僮僕都尉撤銷,西漢取代匈奴控制西域,在烏壘設府施政,“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匈奴已無力威脅西漢對西域的統治。當時並無立即屯田車師之絕對必要。這時,烏孫和康居成爲西域最大國。烏孫在神爵二年以匈奴外孫泥靡爲昆彌卻沒有扶立西漢外孫元貴靡,康居原先亦羈事匈奴而輕西漢,若兩國再與衰落的匈奴勢力聯合,則必嚴重威脅漢在西域的統治。兩者自然開始成爲西漢防備的對象,上引文所述都護職責特別提到“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也說明了這一點。從渠犂分出一校尉屯田莎車附近,將西漢屯駐勢力向西推進,可增強西漢對南道及西部諸國的控制。《光明日報》曾報導在圖木舒克市北面的絲綢之路古道荒漠中發現一處屯田及官署遺址群,主要遺址是一座較大型椎形建築,建築物由紅柳、羅布麻、麥草泥分層築成,周圍遺存有民居、水渠和防禦性建築,地面遺留有大量燒灰及漢代陶片。建築周圍尚能分辨的屯田遺址約有萬畝以上。文中認定該遺址爲“北(比)胥鞬”屯田處。[26]這或可作爲西漢曾屯田莎車附近的佐證。由都護的職責及“屯田校尉始屬都護”可知此時屯田目的不再主要針對衰弱的匈奴,而是改爲鎮撫監察以烏孫、康居爲首的西國。位處西部的比胥鞬屯田與中、東部的渠犂、伊循屯田相互輔助,可以穩固西漢對西域的統轄。
甘露年間,西漢爲平息自己所分立的烏孫大小昆彌之間的矛盾,一度屯田烏孫赤谷城,爲大小昆彌劃分人民地界。該地屯田當始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或至多持續了兩年[27], 並最終達到了分化削弱烏孫和扶植其親漢勢力的目的。曾在烏孫屯田的辛慶忌“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28]他“屯焉耆國”的原因,以及這一活動是屯田還是僅限於軍事屯守,無從考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本近匈奴而輕漢,及至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漢朝正月,“咸尊漢矣”[29], 漢在西域的聲威日隆。西漢屯焉耆可能是順應這一形勢加大統治西域力度的結果,同時可保障西域都護府至焉耆及經由焉耆至車師的交通。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西漢設立戊、己兩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30], 即屯田交河地。兩校尉的前身當是渠犂校尉和比胥鞬校尉,從而以直屬中央的正式武職取代臨時性的職官——屯田校尉,渠犂、比胥鞬屯田規模隨之縮小。[31]這次屯田重心的轉移或與匈奴郅支單于在西部擴張勢力有關。宣帝末年,居於西部的郅支單于見西漢待呼韓邪單于甚厚,其向西移,欲聯手烏孫小昆彌。在被拒絕後,郅支單于破烏孫,兼併堅昆、丁令等國,之後又多次侵襲烏孫。這種局勢下,西漢屯田駐守車師孔道以防備郅支勢力,自在情理之中。屯田車師亦當與車師日益凸顯的交通樞紐地位不無關係,因經由該地通往西域其他諸國較自鄯善地區爲易,西漢駐屯車師可以保障愈加頻繁的東西往來。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己校尉徙屯田於姑墨。[32]此次屯田起因於匈奴外孫日貳殺烏孫小昆彌後逃至康居。而勢力較強的康居“自以絕遠,獨驕嫚”。[33]西漢屯田姑墨無疑是防備日貳一如匈奴郅支單于聯手康居襲掠烏孫等周邊政權而威脅漢對西域的統治。日貳被小昆彌安日刺殺後,己校尉當撤回原駐地。但日貳被殺的年代不明,對刺殺日貳人員進行獎賜的都護廉褒的任期也不確定,或至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或至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34]姑墨屯田結束的時間最晚也應在這兩個年份。
至遲到平帝即位,戊己校尉治所已從交河東遷至高昌壁。[35]屯田中心動遷的原因或正如王素所述:高昌正當通道,離通往敦煌的“新道”尤近。[36]
另外,西漢在今土垠遺址設置居廬(訾)倉,遺址所出漢簡及附近的柳堤、灌渠遺跡表明該倉附近極可能存在過屯田。居廬倉的設立,或以爲早在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漢列亭至鹽水時期,王莽時期仍在使用。[37]但傅介子刺殺樓蘭王,西漢屯田伊循之前,主要由當地樓蘭人負責迎送接待漢使,即《漢書》稱“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38]。所以,居廬倉的設置及其附近行屯田當不早於伊循屯田。考慮到這一地點也位於東西交通要道,居廬倉附近屯田或在伊循設置屯田後不久。
西域屯田一直持續到王莽時期,在車師受到匈奴與投降的車師後王國人的聯合襲擊,戊己校尉史等攜衆入匈奴後,車師屯田當無從繼續。隨着西域政權重新亲匈奴而叛漢,西漢與西域的關係斷絕,西域屯田活動亦當終止。
二
關於屯田土地的來源,文獻中沒有記載。趙充國奏請在河湟屯田時提到,“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田事出,賦人二十畮”[39]。可見他意將羌人沒有耕墾的“故田”和“公田”作爲屯田土地使用。武帝時期初屯被屠滅的輪臺,以及桑弘羊建議屯田輪臺東的捷枝、渠犂等,都是故國,無疑存在“故田”。與前引《漢書》所載不同的是,明王褘在《大事記續編》卷一中記“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牧圉,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40]; 《水經注》卷二記桑弘羊等人奏言爲“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41]兩書都未稱渠犂等國爲“故國”,按此理解,桑氏建議屯田的土地则是沒有開墾的公田。另外,應鄯善王請求在國中伊循城屯田的土地當屬於“公田”。因此,西漢在西域用以屯田的土地很可能主要是當地無人墾殖的“故田”和“公田”。
至於屯田規模,在此衹從人口數量上進行粗略考察。姑墨屯田因時間較短,略而不論。前引《漢書》稱輪臺、渠犂的屯田最初衹有田卒數百人。根據《漢書》記載,地節二年宣帝重開渠犂屯田,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發西域城郭諸國兵,並“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車師降漢,鄭吉曾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面對匈奴發兵襲擊田車師者,鄭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但最終漢“罷車師田者……(鄭吉)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42]可知在漢匈爭奪車師期間及撤銷車師屯田後,渠犂田卒增加,達到1800人。按一校尉領兵滿編是一千人左右[43], 那麽在渠犂屯田的三校並不滿編。後來渠犂屯田人數是否增至滿員,不得而知。但神爵三年一校尉徙屯比胥鞬,另一校尉跟隨都護移駐烏壘轉化爲西域副校尉,當致使渠犂屯田人數減少。隨着渠犂校尉與比胥鞬校尉遷往車師轉變成戊己校尉,渠犂屯田衹留有下屬官員負責,規模較以往縮小。[44]比胥鞬屯田在設置一校尉時,田卒人數至少應有數百人,校尉遷走後,該地屯田是否繼續及屯田人數,無從考察。
前述元鳳四年伊循屯田衹有吏士40人,地節二年或三年更設伊循都尉,又稱“伊循城都尉”,另有多枚漢簡記載弛刑士被送往當地,屯田活動一直持續到西漢撤離西域之前。[45]這一地區的屯田應頗具規模。
戊、己校尉屯田車師之初,所將屯田卒不知是否滿編。但王莽時期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史、司馬丞、右曲侯等“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之後“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46], 說明西漢末期車師屯田規模已在兩千人以上,且有舉家甚或整個家族遷移到當地者,这已具有民屯性質。
另外,一枚懸泉漢簡記載: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別之,如詔書。(Ⅱ0115②:16)[47]
該簡年代爲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文中的“部都尉”包括伊循都尉。[48]按大扁書多公佈在人群集聚、流動性強的較大的驛站、客舍,以及居住人口數量較多的鄉、亭、市、里、官所等要鬧處。[49]所以,當時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及伊循都尉轄治的人口當不在少數,這些地區或已有設鄉里組織加以管理者。
黃文弼先生根據土垠遺址的一枚簡文“庚戌旦出坐西傳日出時三老來坐食歸舍”,指出鄉官“三老”的存在說明該地已實行鄉村制度。[50]則居廬倉附近已有較大的平民聚落,當地的屯田人員也不再單純由戍卒構成。
伊循、居廬倉附近,以及車師的大規模屯田,與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相對應。車師、居廬倉等地的屯田由軍屯發展成較大規模的民屯,當正是應用了桑弘羊提出的先遣田卒“田一歲,有積穀”,再“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的策略。屯田活動的進行,使西域出現新的農業生產區,無疑能夠推動屯田所在地區的經濟開發。
西域屯田使用犁等鐵制農具,並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使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提高。[51]但屯田是西漢一手造就的獨立於當地政權的再生產組織[52], 以政治、軍事防禦爲首要目的,當無改善當地政權農業生產條件,向其推廣先進技術的意圖。而屯田生產規模有限,也制約着屯田開發對西域農業整體生產水平的影響。考慮到時代較晚的尼雅遺址,雖出土了鐵鐮,但大部分生產工具仍是木制的[53],或可推測西漢屯田時,西域諸國土著民的農具以木質爲主,與屯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存在明顯差距,以致西域的農業生產技術總體發展極不平衡。
三
屯田區設倉以積穀,土垠遺址出土的漢簡中出現了“居廬訾倉”、“交河曲倉”等倉名。[54]至於倉的形制,可參考居廬倉遺址的相關資料。黃文弼在該遺址考察時,發現一“長方形土台,高八英尺許,長十九英尺。寬五英尺五寸。上豎立木竿五……在竿之四週,尚有許多四方井穴,用柳條滲以木屑,編織爲,覆於井口,約四尺建方,彼此相通爲甬道。……在竿之兩旁,曾掘二井,內滿儲沙子,無一他物。……復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類似高粱之穀粒,已腐化結爲乾餅”[55]。關於那些井穴,孟凡人指出應是用於儲存糧食的窖穴。[56]中原地區以窖穴儲存糧食的方法起源甚早,洛陽西郊漢代居址有方形倉窖,窖內鋪木板或草,上面再撒鋪一層穀糠,以防糧食受潮發霉。[57]居廬倉遺址井窖上的柳條褡摻以木屑或也是爲了防潮,井穴相通爲甬道,則或爲了加強窖內通風散熱。這種地下倉窖與西域極爲乾燥的自然環境相適應,但不排除當地有地上倉儲設施的可能。
前文提到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鄯善王請求西漢在伊循“屯田積穀”等,似乎“積穀”僅限於屯田收穫。但屯田生產能力有限,需要內地轉運穀物。[58]此外,屯田地區的“積穀”作爲一種經濟活動,還存在購買的方式。
土垠遺址出土的一枚簡文記曰:
關於屯田區購買西域土著居民糧食以積穀的可能性,可利用前引桑弘羊等人的建議進行分析。桑弘羊等建議屯田輪臺以東的捷枝、渠犂地區,言:“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顏師古注曰:“言以錐刀及黃金彩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即把“錐刀”作爲換取西域諸國穀物的物品之一。吳仁桀則認爲:“‘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戔爲佳耳。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犁旁國少此,故貴黃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61]吳說相對合理。況且新疆諸多史前考古文化遺存常見金屬制小刀和錐等工具,並不缺少錐刀之物。[62]因而,桑弘羊等所言意在說明當時西域諸國不流行使用貨幣,商品經濟尚不發達,屯田區可以利用當地民衆喜好黃金和漢地綵繒的風尚,用黃金、絲織品換購土著居民的穀物。
或以爲屯田區周邊政權糧食供給能力有限,雙方開展糧食貿易的可能性不大。但西域政權間的“仰穀”貿易[63], 說明綠洲政權有餘糧出售,完全具備與屯田區進行糧食貿易的基礎。
另外,《鹽鐵論·輕重十四》中文學對開發邊地的看法,曰:“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64]表明邊屯戍士的衣物由中原內地提供。居延漢簡則證實,政府向屯戍人員發放衣物的同時,還會將布、帛等實物作爲俸祿給屯戍區的官吏;除政府發放的官服外,還有私人攜帶至屯戍區者;絲織品及其他衣物進入當地商品流通領域。[65]土垠遺址也有絲織品殘片出土[66], 可見西域屯田區也不例外,有大量絲織品輸入,爲絲織品—穀物貿易提供了條件。根據班固《與弟超書》稱:“竇侍中令載雜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氐馬、蘇合香、毾。”[67]知東漢時期,西域屯駐區同周邊政權存在用內地攜來的絲織品換購馬匹、香料、毛織品的商業活動。較東漢經營西域深入的西漢時期亦當如此。綜合考慮,在屯田的基礎上,西漢屯田區與西域土著政權之間完全可能存在用絲織品換取穀物的積穀活動。[68]屯田區與西域土著政權間的積榖貿易關係當以屯田區爲中心,需要西漢向屯田區輸送錢帛作爲保障。因而,這種貿易同屯田活動本身一樣,往往隨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勢力強弱變遷。西漢勢力一旦退出,屯田積穀活動中止,積穀貿易關係也會隨之瓦解,具有不穩定性。
屯田生產爲積穀活動提供糧食來源,積穀活動也保障着屯田的順利進行。兩者在發揮重要經濟功能的同時,也是西漢向西域擴展勢力、樹立威德,對其進行統轄的重要策略。西漢首屯中部輪臺地區,將自身勢力楔入西域,以對抗匈奴勢力並宣揚漢之威德。在屯田一度中斷後,西漢重新屯田於靠近漢地的東部地區——伊循(還可能包括居廬倉附近),扶植親漢勢力;進而再次推進到中部渠犂進行屯田,以驅逐匈奴勢力。隨着汉匈力量對比發生轉折性變化,西漢以西域中部爲中心鎮撫諸國,屯田地域進一步向西擴展,田於比胥鞬,以戒備西方勢力較強的烏孫、康居叛亂或與匈奴勢力聯合,後來又重點發展東北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車師前國屯田。間或根據西域事態發展變化,進行臨時屯田。西漢藉屯田,牢牢控制着東部與東北部的戰略要地,經中部向西深入,對西域進行全面管轄。從而西漢在督察西域諸國,防備匈奴勢力捲土重來的同時,保障東西交通的暢通。
西漢在西域屯田利用無人墾殖的“故田”和“公田”進行生產,多有發展成爲民屯聚落者。生產中採用中原的先進技術,推動了當地農業的開發,但也造成西域農業技術兩極分化。而爲彌補屯田生產能力的不足,屯田區從土著民手裏購進穀物,亦能夠刺激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藉助屯田積穀,西漢在穩固自身對西域的統治的同時,使土著政權,特別是位於屯田區附近的政權在政治、軍事上有所倚重,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經濟上得到發展。諸政權的綜合實力對比因此有所變化,進而對西域政治格局變遷產生一定影響。
■注釋
[1] 《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179頁。
[2] 《漢書·西域傳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73頁;《西域傳下》,第3912頁;《鄭吉傳》,第3005頁。
[3] 余太山:《兩漢西域都護考》,載氏著:《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57頁。
[4] 有學者結合桑弘羊等人建議屯田渠犂的奏言(詳見後引文),認爲武帝時期衹是提出屯田輪臺(即侖頭)和渠犂的建議,並未實際推行。如勞榦認爲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至七年纔屯田於輪臺和渠犂,《漢書》的記載是一種大致叙述,否則武帝的輪臺之詔不可通。見勞榦:《漢代的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28本上(1956年),第485—496頁。張維華指出西域屯田始於昭帝時期,即扜彌太子賴丹在始元年間屯田輪臺,大規模的屯田經營是宣帝時鄭吉以渠犂爲中心的屯田,其地域似當包括西面的輪臺。見張維華:《西漢都護通考》,載氏著:《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245—308頁。李大龍則提出西漢在輪臺、渠犂屯田,首議於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而推行於昭帝時,兩地的大規模屯田卻是在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見李大龍:《西漢西域屯田與使者校尉》,《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第119—122頁。另外,曾問吾認爲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初屯渠犂,昭帝時期才屯田輪臺。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0—51頁。
[5] 關於輪臺屯田的背景,參見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3年),第27—110頁。至於設立輪臺屯田的時間,參見注3所引文。另外,施丁認爲屯田輪臺在天漢年間(公元前100年—前97年),但他認爲初屯地不是輪臺,可能是樓蘭。見施丁:《漢代輪臺屯田的上限問題》,《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0—27頁。
[6] 《漢書·西域傳下》,第3912頁。中華書局標點爲“輔烏孫,爲便”,今改。
[7] 同注3。
[8] 《漢書·西域傳下》,第3916頁。
[9] 參見張春樹:《試論漢武帝時屯田西域侖頭(輪臺)的問題》,《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4輯第3冊,大陸雜誌社印行1975年版,第89—92頁。
[10] 李炳泉曾指出渠犂屯田始於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或三年之間。他根據桑弘羊等人的奏言,認爲渠犂屯田在征和四年或前一年停止,昭帝時期也未恢復。見李炳泉:《西漢西域渠犁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7頁。
[11] 劉光華認爲既然《漢書》稱昭帝用桑弘羊前議,則賴丹屯田輪臺不確,“輪臺”應爲“渠犂”之誤;而《漢書·鄭吉傳》中“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的記載是昭帝時期的事,非武帝時期。見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76頁。
[12] 關於桑弘羊等人提出奏議的背景及武帝頒佈“輪臺詔”的原因,參見田餘慶:《論輪臺詔》,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0—62頁。
[13] 《漢書·趙充國傳》,第2973頁。
[14] 關於賴丹屯田輪臺的時間,參見薛宗正:《西漢的使者校尉與屯田校尉》,《新疆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第105—110頁。
[15] 《漢書·匈奴傳上》,第3785頁。
[16] 《漢書·傅介子傳》,第3002頁。
[17] 《漢書·西域傳上》,第3878頁。
[18] 對於伊循屯田擴大規模的時間及原因,參見李炳泉:《西漢西域伊循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1—9頁。
[19] 《漢書·西域傳下》,第3922頁。
[20] 有關西漢遣鄭吉等屯田渠犂的原因,參見注11劉光華書,第78—79頁。
[21] 《漢書·西域傳下》,第3923頁。
[22] 《漢書·西域傳上》,第3874頁。
[23] 張俊民:《“北胥鞬”應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89—90頁。
[24] 参见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ソ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3—24頁。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6—337頁。錢伯泉:《北胥鞬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第116—122頁。蘇北海:《別失八里名稱源於北胥鞬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4期,第169—176頁。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4頁。殷晴:《漢唐時期西域屯墾與吐魯番盆地的開發》,載殷晴主編:《吐魯番學新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2—565頁。劉國防:《西漢比胥鞬屯田與戊己校尉的設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23—29頁。
[25] 參見周軒:《北胥鞬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第215— 221頁。
[26] 王瑟:《西漢在西部最大屯田區被發現》,《光明日報》2009年7月5日第5版。
[27] 參見李炳泉:《屯田與兩漢對西北邊疆的經略》,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第31—32頁。
[28] 《漢書·辛慶忌傳》,第2996頁。
[29] 《漢書·西域傳上》,第3896頁。
[30] 關於西漢戊己校尉分置的論述,見孟憲實:《西漢戊己校尉新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第128—135頁。
[31] 賈叢江:《西漢戊己校尉的名和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第33—42頁。
[32] 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附錄》,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85頁。
[33] 《漢書·西域傳上》,第3892頁。
[34] 有關廉褒的都護任期,參見注3所引文。
[35] 余太山:《兩漢戊己校尉考》,載注了所引氏著,第258—270頁。
[36]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頁。
[37] 關於土垠遺址與居廬(訾)倉的對應關係及其性質、興衰時間,見孟凡人:《樓蘭新史》,光明日報出版社、新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0—83頁。王炳華:《“土垠”遺址再考》,《西域文史》(第4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2頁。至於居廬倉附近曾存在屯田的論述,見王先生文。
[38] 《漢書·西域傳上》,第3878頁。
[39] 《漢書·趙充國傳》,第2986頁。
[40]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91,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頁。
[41]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9頁。
[42] 《漢書·西域傳下》,第3922—3923頁。
[43] 賈叢江:《關於西漢時期西域漢人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1—8頁。
[44] 關於渠犂三校尉的轉徙變遷,見注31所引文。
[45] 同注18所引文。
[46] 《漢書·西域傳下》,第3926頁。
[47]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
[48] 注18所引文。關於伊循都尉為部都尉的論述,另參見賈叢江:《西漢伊循職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15頁。
[49] 參見馬怡:《扁書試探》,載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83頁。
[50]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1948年版,第189—191頁。
[51] 參見殷晴:《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十二世紀前新疆開發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4—78頁。法國學者童丕根據古代中亞和西亞灌溉技術發達的情況,以及克里雅河流域圓沙古城的考古成果,認爲西域早在西漢屯田經營之前,已存在相當規模的灌溉工程。他還指出,桑弘羊等提到輪臺東部捷枝、渠犂故國“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若按每人耕作20畝計算,則需要25000人經營,這應是一個或幾個當地政權全部居民的數目,亦表明漢族到來之前渠犂等小國居民已依賴於灌溉。見E. Trombert, “Notes pour une Évaluation Nouvelle de la Colonisation des Contrées d’Occident au Temps des Ha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299, n°1(2011), pp.67-123.但根據《漢書》記載,渠犂有1480人,周邊分別與龜茲、烏壘、尉犁、且末、精絕相接。除龜茲人口達8萬之多,其他諸國與渠犂人口總和爲17250人,較25000人相差很多。況且,在地廣人稀的西域,幾國共同開發一地建設水利工程的可能性不大。殷晴也在書中提出《水經注》中的“可溉田五千頃以上”比較合乎情理(同書,第67頁注①)。另外,張波提到,《水經注》記載索勱橫斷注賓河,“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第37頁),可證明西域土著民不曾進行攔截河流發展大規模灌溉的水利建設。目前屬於西漢進入西域以前的較爲密集的灌溉渠道除在圓沙古城發現外,並不見於西域其他地區。鑒於西域總體人口數量較少,推測在西漢屯田建設大規模水利工程之前,當地居民實行的灌溉技術主要是“撞田”,即利用地形和水勢等條件進行泛灌,有時修築簡易堤防疏導或堵截流水。參見張波:《綠洲農業起源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期,第137—154頁。
[52] 〔日〕尾形勇著,呂宗力譯:《漢代屯田制的幾個問題——以武帝、昭帝時期爲中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96頁。
[5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新疆民豐大沙漠中的古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3期,第119—122,126頁。
[54] 注50所引書,第192頁簡16。
[55] 注50所引書,第106頁。
[56] 注37所引孟凡人書。
[57] 余扶危、葉萬松:《我國古代地下儲糧之研究(中)》,《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第268—269頁。
[58] 參見注11劉光華書,第155—158頁。
[59] 注50所引書,第189頁及木簡摹本19。簡文內容釋讀得淩文超學長指正,在此表示感謝。
[60] 于振波:《從糴粟記錄看漢代對西北邊塞的經營——讀〈額濟納漢簡〉劄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3—107頁。
[61] (清)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見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76頁。
[62] 參見陳戈:《關於新疆地區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頁。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的青銅文化遺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0—77頁。
[63] 關於西域政權間的“仰穀”貿易,參見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號(1984年),第32—65頁。拙文《“寄田”與“仰穀”》,載羅豐主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頁。
[64]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0頁。
[65] 陳直:《西漢屯戍研究》,見陳直著:《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74頁。楊劍虹:《漢代居延的商品經濟》,《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60—166頁。
[66] 注50所引書,第108頁。
[67] (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上),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47頁。
[68] 至於屯田區與土著政權間是否存在用黃金換取穀物的貿易模式,若按前注引陳直文,“邊郡錢幣,運輸困難,有時用黃金代替貨幣”,則西域屯田區也可能有黃金輸入,進入流通領域。但其所引簡文並未寫明黃金,理解或有誤。現有文獻多見西漢政府賜予西域政權統治階層黃金的記載,而不見黃金輸入屯田區的記錄。所以,因資料缺乏,在此不做過多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