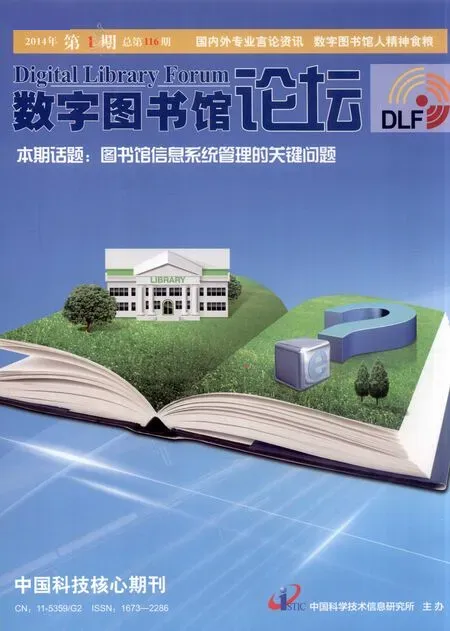“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发展与特征*
——以1980-2012年关键问题研究报告的内容分析为基础
2014-04-10陈定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广州510006
□ 陈定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发展与特征*
——以1980-2012年关键问题研究报告的内容分析为基础
□ 陈定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始于1980年的“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研究在管理信息系统学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模式。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世界范围内29次最具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将其32年的发展历史概括为奠基期、改良期和重塑期,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重要特征。
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管理,关键问题,研究模式
“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下称“关键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各类企业的信息主管进行调研,以确定未来3-5年内企业在信息系统管理方面的需求和信息技术主管关注的焦点。事实证明,该项研究有助于信息主管和系统厂商了解目前行业的信息化布局和发展重点,制定明确清晰的信息化战略规划。
关键问题研究始于1980年的美国[1],随后扩散到英国、爱尔兰、德国、希腊、塞尔维亚、挪威、波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国港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三十余年来多个国家研究者的逐步推动,其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都有了一定的扩展,在管理信息系统学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模式。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着力于检讨方法论的利弊,对关键问题方法论发展的专门论述还很少,鲜有针对关键问题研究方法论的梳理和全面分析。为了更全面地解析关键问题研究的历史内涵及其研究模式,研究团队从国家分布、研究行业、样本数量等多个维度考虑,挑选了世界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29次“关键问题”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其研究模式,逐步梳理出世界范围“关键问题”研究的模式演变。
根据分析的结果,下文将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演变分为奠基期、改良期和重塑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分界如下:奠基期始于1980年美国信息管理协会(Socie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IM)的首次研究,止于1984年前后Dickson等人发布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关键问题研究理论;改良期紧接Dickson等人奠定的关键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止于2000年前后Petter Gottschalk对关键问题研究模式弊病的总结;重塑期则是2000年前后至今,并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直到形成相对稳定的新兴研究模式为止。
1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奠基期(1980年-1984年前后)
关键问题研究始于SIM主持的一项针对该会会员的调研,调研一开始并没有严谨的方法论支撑,所以对“关键问题”这一命题所秉持的更多仅仅是“了解”而非“研究”的态度,但由于这一调研引起反响比较热烈,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而对“关键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在美国蔓延开来。在这一段时间,有三次代表性的研究奠定了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基本流程和研究底基。
1.1 1980年Leslie的研究:原始的框架
1980年,SIM抱着“了解意见”的态度开始了一次针对SIM成员的调查,这次号称“关键问题研究之肇始”的调研,在方法论上比较简陋,研究者采用一份六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调查问卷,针对该会会员展开研究。
Leslie在1983年的报告中对这次调研作出说明:“我们并没有声明研究结果代表了整个信息系统行业;也没有声明这些研究可以准确地反映所有协会内部成员的需求和情况;所有的关键问题反映的只是417名独立的、参与了本次调查问卷的研究者的想法,他们的主业与信息系统相关,他们也同时是协会的成员,仅此而已。”[2]可见这次研究并没有以“科学的调研”为目的,仅仅是以“了解意见”为切入点,但这次调研以其广泛的范围和新颖的“信息系统管理”的切入角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2 1982年Martin的研究:关键因素和多轮调研
第二次是1982年,E.W.Martin将John Rockart的关键成功因素法用来确定关键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3],虽然关键成功因素法主要适用于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但Martin认为这一方法论也可以有助于信息系统管理/数据处理(MIS/DP)主管的工作,关键因素的种子由此深深扎根在后续的所有相关研究中。
此外,这一次研究中,研究者对15位首席信息系统主管开展两轮的调查,被调研者拥有一次机会去修改他们的选择,最终得到了与1980年研究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多次反复确认并逐渐“接近真相”的思路,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演变成更具有理论性和更为系统化的德尔菲法。
1.3 1983年Dickson的研究:奠基期的最终形成
第三次代表性研究发生在1983年,并由此确定了德尔菲法作为该项研究的基本方法。Gary W.Dickson等人在1984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时尚未有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关键问题研究,为了规避1980年的调查中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对关键问题不同的词汇表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调查结果”,而决定采用4轮德尔菲调查法。多轮德尔菲法将给被调研者反馈的机会,让研究人员去修正不恰当表述。
为了达到“修正不恰当表述”的目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四轮德尔菲调查法的基本情况如下:
(1)第一轮:参与者被要求提出5到10个他们心目中未来5到10年的关键问题,还必须给出每个关键问题的理由。这些关键问题被汇集形成一份完整的问卷。
(2)第二轮:发放第一轮汇集的问卷,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选择十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并给出具体序次。
(3)第三轮:发放第二轮的整体排序结果,参与者有机会重新排序,如果对某一关键问题的排序有“根本上”(这里的“根本上”指次序与第二轮相比调动3个序次以上,如原本第六的关键问题被调到第二,即已经调动了4个序次)的变动,则参与者需要给出理由。这些理由将会在第四轮的调研问卷中给出。
(4)第四轮:对第三轮的问卷进行缩短,关注前两轮排序都比较靠前的关键问题。对参与者发放了第三轮的排序结果和调动序次理由,要求参与者作出最后的决定。
除了德尔菲法,本次研究还开创了“排名前十的关键问题”、“业界信息主管对关键问题的认可程度”等分析和研究主题,这些成为了后续关键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4]。
这三次调研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模式是逐层递进的,从最简单的探索性的“摸底了解”到“关键因素法”和“德尔菲法”的逐步应用,虽然这阶段的研究比较简单粗糙,但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却由此确定下来,Dickson的研究更成为SIM在2000年以前持续开展各类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模板。
2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改良期(1984年前后-2000年前后)
1983年的研究之后,关键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进入较为保守的时期,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如何改进原有的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模式,并继承其研究流程、分析手段和分析内容,侧重对方法论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良。
2.1 1985年Curt和Martin的研究:实践因素的加强
1985年,Curt Hartog和Martin Herbert在基本依循83年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由于新的关键问题不断出现,旧有的某些关键问题越渐显性化,因而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列表进行了改动;
(2)进一步排除了学术研究中热点问题的影响,全面关注实践领域的关键问题;
(3)将预期时间缩短为未来两年内。
其中的第二点影响最为深远。从这时开始,关键问题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实践领域,使得该项研究与学术界的“热点研究”有所区分,成为关键问题研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值得强调的是,此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依然是以德尔菲法为主,但增补了定性资料的研究,Curt等人针对14名感兴趣的被调研者,进行了30到40分钟左右的电话访谈,访谈内容分为一般问题(针对每一名参与者)和特殊问题(针对某些参与者)[5]。
2.2 1986年到90年代中Brancheau的研究:侧重体系与历史的继承
这一阶段关键问题研究的分析主题,继承并完善了1983年Dickson的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针对不同行业探讨关键问题的不同排序、针对关键问题进行因子分析以及与之前调研结果的对比研究[5]。SIM主导的“美国派”研究依然在世界范围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三个主题中的“对比研究”也是SIM研究体系中最有力的一项传承。
Dickson的调研之后三年,1986年SIM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开展了第二次合作,由Brancheau等学者主导。这次研究在方法论一节中即声明,“本次研究方法论构建的基本目标是,能够和1983年研究中形成的基本框架进行对比研究”,可见本次研究的方法论仍是以“传承”和“改良”为主。从本次的调研采用的三轮德尔菲法中,这种倾向显得更为明显[6]:
(1)第一轮:被调研者都收到了1983年产生的关键问题列表,他们只需要从中选出并排列未来3到5年的信息系统管理关键问题;研究者鼓励他们加入新的关键问题。本轮的参与者有90人。
(2)第二轮:被调研者收到了第一轮的调研结果,并重新排列、给出理由。本轮的参与者有54人。研究者同时请求参与者(主要是信息主管)将关键问题测量工具转交给各自的总经理或其他上层负责人,最后得到了21份来自这些负责人的有效回复。
(3)第三轮:第二轮信息主管和最高管理者的意见被附在调查问卷中,参与者作出最后的排序。本轮参与者包括68名信息主管和12名总经理。
而这次研究的分析主要包括十大关键问题的分析、对比研究(与近期研究的对比、与之前研究的对比)、历史趋势等[6]。基本的研究框架还是和1983年的研究保持一致。此后,SIM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又在90年代开展了两次合作研究,总的来讲,也没有跳出这个研究框架。
2.3 地域传播带来的反馈:改良、反思与质疑
同样在这个阶段,关键问题的研究开始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相关研究虽然有细枝末节上的变化,但也主要是依托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方法体系。例如斯洛文尼亚Dekleva等人的研究所采用的同样是四轮德尔菲法,但从第二轮问卷发放阶段开始,其采用的问卷是用十级量表而非四级,这是为了使得数据差距能够更加明显[7];而中国的陈国青团队,是在沿用德尔菲法问卷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了单轮的问卷调查法[8];再如中美洲的研究团队,则在研究前设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两大“研究假设(Research hypotheses)”,并在调研过程中着力求证[9]。而像Blake Ives、Sirkka L.Jarvenpaa等学者那样,放弃德尔菲和问卷调查法,而采用结构化访谈等定性方法论者,终究属于少数[10]。
但无法否认的是,随着该研究方法在地域实践上的扩大,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逐步对美国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反向影响(这也得益于大部分的调研报告最终都以英文写就)。例如,澳大利亚的Watson等人在1989年作出的两项修改[11]就被Fred Niederman在1990年的SIM研究中沿用,这两项修改是:(1)对德尔菲法每一轮的问卷答题方式进行改造,从原有的排序(Rank)变为打分(Rate),这样能够减轻参与者的脑力负担,也可以为后续研究的横向对比提供参照;(2)在德尔菲法的操作中,对上一轮没有回复的参与者也同样发给新一轮的问卷,以提高回复率。又如斯洛文尼亚的研究中,对信息主管地位的考量(包括信息主管是否直接向最高主管汇报等)[12],也在2003年以后Jerry团队的研究中被考虑。
随着多轮德尔菲法在关键问题研究中的使用日渐增多,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逐渐在反思这一方法论的缺陷。1994到1995年的SIM研究,提到了调研方法论的弊端,包括某些问题难以清晰表达的问题和不同关键问题有时候会互相交叉重叠的问题[13]等等。由于方法的缺陷和调研本身的难度等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SIM的关键问题研究逐渐转为非正式项目,该项持续多年的研究暂时退出了信息系统管理研究者的视野。
2.4 Gottschalk的总结:四大弊端
2000年前后,以Gottschalk为首的几位研究者较为全面地对全球范围内的关键问题研究进行了总结[14,15],这份总结报告首先发布在夏威夷第33届系统科学国际会议上,其后又修改发布于《信息管理国际杂志》,是目前对关键问题方法论进行较为深入反思的重要综述性文献。该文总结前人观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质问关键问题研究使用德尔菲法的弊端:
(1)一致性:德尔菲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中意见的研究方法,但是有些意见本身也不可能被集中。
(2)联系性:关键问题之间应当是互相联系的,甚至是因果关系。但是德尔菲法在让多个关键问题进行排序的过程中,常常使得某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被忽视——这些关键问题虽然本身看起来并不重要,但它们往往是另一些关键问题的驱动因素。
(3)理论性:对关键问题的研究,缺乏底层理论的支持和论述。
(4)差异性:许多研究的数据差异并不明显,例如很多关键问题之间只有零点几的差别,而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更是没有想象中的巨大数据跨度。
以这四个问题为基础,重新观察改良期的关键问题研究发展,会发现这段时间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历史沉淀的积累和细节的改进上,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方法体系依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Gottschalk提到的四大问题使得该研究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理论底层的矛盾并没有阻止各个地区和行业积极投身相关研究,所以随着方法论的低落和研究兴趣的高涨,双方矛盾必然不断累积终至爆发,这最终使得关键问题研究在2000年前后逐渐进入一个重塑时期。
3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重塑期(2000年前后至今)
2000年前后,由于关键问题序次常年变动不大、信息系统管理学科体系的日渐完善和信息系统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等原因,包括SIM在内的关键问题研究者,都开始重新思考、探索并重塑关键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而思考、探索和重塑的主线则是对“德尔菲法”的批判和思考。
3.1 Jerry Luftman主导的SIM研究之一:方法论的变革
改革的关键在于从定量研究向定性研究靠拢。1999年,Morgado等人就建议,应当引入一些新的方法论来改进关键问题的研究,他们所提倡的新方法论,主要是Q方法论(Q-methodology或Q-sort)①Q方法论(Q-methodology或Q-sort),即通过给受试者出示一组关于某一话题的陈述或命题,让他们按自身的偏好、判断或感觉给这些语句排序。通过这种排序,人们将自己的主体意见添加到这些命题中,然后对这些个人排序进行因素分析,来找寻和证明存在于这些观点中的论述模式。和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②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即通过提取研究问题的构成要素,将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以有向图、矩阵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信息进行处理,并用文字加以解析。通过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16]。虽然采用访谈法等定性性质的关键问题研究在之前并非没有,但在改良期,定性往往是作为定量的补充,而在重塑期,无论是调研阶段还是分析阶段,定性研究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经过7年左右的暂停,2003年SIM决定重新启动正式的关键问题研究,而从这时候开始,在SIM2003年至今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以批判德尔菲法为主线,关键问题的研究与其往常的纯定量思维渐行渐远,它所关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焦点也越来越集中。虽然SIM的团队并不声明其所用的是定性研究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其方法论也日渐趋向于定性。这一年,SIM委托Jerry Luftman等学者开始新的研究,他们在较大程度上展开了方法论的变革。
Jerry等人认为,以前以多轮德尔菲法为中心的研究,有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调研的时间、人力成本较高,而且容易使调研对象产生抵制心理;二是虽然在德尔菲的调研过程中,各项问题有变动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其变动的趋势不大,并不能体现出“意见集中”的功效[17]。这两项思考和举动,从操作难度和实际效果两个角度对德尔菲法作出了一定的批判,他们转而采用单轮的问卷调查法以便更广范围地调查、获得更高的回收率。
当然,单轮问卷调查所回馈的信息必然不如原有的德尔菲法,Jerry等人更侧重以其他定性资料或调研资料为基础,对调查结果展开解释和分析。例如2004年,团队调查了各个被研究组织的预算情况;而2005年更将调查范围扩展到“组织因素(包括CIO报告结构、职员总数、组织结构、预算等方面)”[18],强调了对企业情况的客观审视。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中,2009年额外加入了来自欧洲的27个组织和中国的174个组织的资料[19]。2010年更将中国地区扩展到亚洲/澳洲地区[20]。
3.2 Jerry Luftman主导的SIM研究之二:核心关键问题成为焦点被放大
Jerry主导下的SIM研究,除了对基本调研方法的扬弃,还对一些核心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放大,以展开细致的分析,其中最典型的“核心关键问题”是“技术和业务的融合问题”(IT-Business Alignment)。
由于“技术和业务融合”这一问题从1983年开始就常常登上“十大关键问题”的首位,这一结论本身对实践已经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因而研究团队决定针对这一主题细化深入,从而开始了“阻碍技术和业务融合的因素”和“推动技术和业务融合的因素”的研究[17]。2004年,对“技术和业务融合”这一问题的微观聚焦进一步强化,Jerry的团队在“阻碍因素”和“推动因素”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业务-信息系统融合成熟度调查”,依据“沟通理解成熟度”、“竞争力/价值评估成熟度”、“治理成熟度”、“伙伴关系成熟度”、“范围与架构成熟度”、“技能成熟度”等六个维度,划分出五个级别,让企业进行自我评价,最终发现企业自评的成熟度多在2-3级之间[21]。
3.3 实证研究的世界化倾向:德尔菲法的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关键问题研究继续在世界范围的扩展,虽然研究方法体系在美国本土有被质疑和重构的倾向,但观察其拓展过程,即便带有一些转型期的特征,德尔菲法依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例如2011年,关于加拿大医疗领域信息主管的关键问题研究,已经表现出细分研究的特征,并对行业内部进行分层探索,但基本方法依然是三轮德尔菲法[2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的扩展深度无法赶得上其扩展的速度。许多国家展开的关键问题研究的次数不多、延续的时间跨度也有所不足,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采用德尔菲法这种研究方法会更为稳妥。例如2011年塞尔维亚的研究,也不可脱俗地继续沿用相关方法论体系,以便与国际的相关研究实现对比和对接[23]。
进入重塑期以来,关键问题研究方法论显现了两大趋势:首先,越加强调定性思维,对纯粹的定量研究有所补充;其次,对客观材料的重视,如财务报表、企业结构的基本资料。这两大趋势表面上似乎是对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冲击,可事实上,与其说团队抛弃了德尔菲法的研究体系,不如说是以德尔菲法积累的历史成果为基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实践领域,日益强调对关键问题研究的实用度和可信度。
4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整体特点
从整理的历程演变看来,关键问题研究模式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1)关键问题的“关键”二字,强调的是实践领域的关注焦点。从一开始SIM所强调的“了解意见”,到后期研究的“实用性”,我们都可以发现,相关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在实践领域,这和许多学术调研强调的“学界热点”和“研究热点”之类有着显著的差异。
(2)关键问题调研的本质是主观意见的汇集。无论是德尔菲法还是访谈法、甚至Q方法论,基本都是对实践者的主观意见进行汇集,并得出相关结果,而且,由于每次参与关键问题研究的专家团队组成成分不同,每一次意见汇集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见解。
(3)营利性企业对研究方法论和内容所施加了持续性的影响。1991年,Sharon L.Caudle首次开始了针对公有领域关键问题的研究;1995年,John W.Swain等人又延续了1991年的研究框架,作出了进一步探索[24]。但从整体情况看来,来自公有领域的研究极为稀缺,且对方法论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决定了现有的关键问题研究框架基本都是由营利性企业主管为主的团队构建起来的,而由于“关键问题调研的本质是主观意见的汇集”,使得相关的方法论本身有着难以消除的营利性组织烙印。事实上也可以发现,公有领域信息系统管理的一些特点在现有研究中从未展开过探讨,例如“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作”、“民众对公有单位信息化的态度”等等。
(4)重视整体性研究,鲜有对专有领域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一国的整体信息化情况来开展,这些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行业特点各有不同的众多企业开展实际的工作呢?这是值得提出疑问的。由于这个倾向,关键问题研究模式也很少体现专有领域的特点。
倘若要将关键问题研究引入新的领域,如图书馆学领域,建立适用于该领域的关键问题方法论,上述四大特点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对于这些特征的思考,如果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般逐一着手解决,则可能导致新的方法论走入新的误区,因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思考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也许是更合适的道路。
从以上这些特点切入,以认识论的视野来分析,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认识论筑基是偏重建构主义的,这一方法论摒弃了独立客观的知识体系,而更进一步强调被调研者的主观创造力。在这一情境下,建构主义所要求的方法论,往往是阐释的、辩证的,其“系统的数据搜集”多指向定性的资料搜集。在关键问题研究的早期,缺乏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探索,导致了早期研究对定量的重视、对定性的漠视,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对应建构主义的认识基础,无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何会出现一番重塑关键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的浪潮③2003年前后,Jerry的团队重新开始了SIM官方“正式”的关键问题研究,此次研究改进了以往纯粹关注粗粒度“关键问题”的模式,开始针对“技术和业务融合的阻碍因素”和“技术和业务融合的推动因素”等单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并更注重定性研究,是为关键问题研究方法论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00年以后,关键问题的方法论转向,正是在尊重20多年定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建构主义认识论的肯定和迎合。
本文在整体上回顾整体的方法论变迁,即是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和基调,将这套研究模式尝试性地引入图书馆学领域、为国内图书馆技术管理的实践发展提供必要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在这一背景和语境下,更需要重视关键问题研究的认识论底层和近年来该项研究的整体特征与转向。
[1] BALL L, HARRIS R.SMIS Members: A Membership Analysis [J].MIS Quarterly, 1982, 6(1): 19.
[2] BALL L, HARRIS R.SMIS Members: A Membership Analysis [J].MIS Quarterly, 1982, 6(1): 19-37.
[3] BALL L, HARRIS R.SMIS Members: A Membership Analysis [J].MIS Quarterly, 1982, 6(1): 1-9.
[4] DICKSON G W, LEITHEISER R L, WETHERBE J C, et al.Key information systems issues for the 1980's [J].MIS Quarterly, 1984(3): 135-159.
[5] HARTOG C, HERBERT M.1985 Opinion Survey of MIS Managers Key Issues [J].MIS Quarterly, 1986, 10(4): 351-361.
[6] BRANCHEAU J C, WETHERBE J C.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J].MIS Quarterly, 1987(3): 23-45.
[7] DEKLEVA S, ZUPANCIC J.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a Delphi study in Slovenia [J].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996, 31: 1-11.
[8] 石赟,陈国青,蒋镇辉.信息管理中的关键因素[J].中国管理科学,2000(3):63-69.
[9] MATA F J, FUERST W L.Costa Rica and Guatemala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ssues in Central America: a multi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1997(6): 173-202.
[10] IVES B, JARVENPAA S L.Applications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 Issues for Management [J].MIS Quarterly, 1991, 15(1): 33-49.
[11] WATSON R T.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 1988 [J].Australian Computer Journal, 1988, 21(3): 118-129.
[12] DEKLEVA S, ZUPANCIC J.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a Delphi study in Slovenia [J].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996, 31: 1-11.
[13] BRANCHEAU J C, JANZ B D, WETHERBE J C.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1994-95 SIM Delphi Results [J].MIS Quarterly, 1996, 20(2): 24-25.
[14] GOTTSCHALK P.Studies of key issues in IS management around the world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0, 20(3): 169-180.
[15] GOTTSCHALK P, WATSON R T, CHRISTENSEN B H.Global Comparisons of Key Issues in IS Management: Extending Key Issues Selection Procedure and Survey Approach [C/OL].[2012-03-13].Proceedings of the 3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 2000.http://ieeexplore.ieee.org/ stamp/stamp.jsp?tp=&arnumber=926910&tag=1.
[16] MORGADO E M, REINHARD N, WATSON R T.Adding value to key issues research through Q-sorts and interpretive structured modeling [J].Communications of the AIS, 1999, 1(3): 1-24.
[17] LUFTMAN J, MCLEAN E R.Key Issues for IT Executives [J].MIS EXECUTIVE, 2004, 3(2): 89-104.
[18] LUFTMAN J, KEMPAIAH R, NASH E.Key Issues for IT Executives 2005 [J].MIS EXECUTIVE, 2006, 5(2): 81-99.
[19] LUFTMAN J, BEN-ZVI T.Key Issues for IT Executives 2009: Difficult Economy's Impact on IT [J].MIS EXECUTIVE, 2010, 9(1): 49-59.
[20] LUFTMAN J, BEN-ZVI T.Key Issues for IT Executives 2010: Judicious IT Investments Continue Post-Recession [J].MIS EXECUTIVE, 2010, 9(4): 263-273.
[21] LUFTMAN J.Key Issues for IT Executives 2004 [J].MIS EXECUTIVE, 2005, 4(2): 269-285.
[22] JAANA M, PARé G, TEITELBAUM M.Key IT Management Issues in Canadian Hospitals: A Delphi Study [C/OL].[2013-03-11].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rticleDetails.jsp?reload=true&arnu mber=5718550&contentType=Conference+Publications.
[23] BULATOVIC J.Key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A Serbia's Perspective (Delphi study) [DB/OL].[2013-11-18].https://globaljournals.org/GJCST_Volume11/6-Key-Issues-in-Information-Systems-Management.pdf.
[24] SWAIN J W, WHITE J D, HUBBERT E D.Issues in Public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J].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5, 25(3): 279-383.
Research Model of Key Issues of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Reports of Key Issu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udies: 1980-2012
Chen Dingquan/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The study of "key issues of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was started as a sophisticated research pattern in 1980.The history of key issues study is scanned, and 32 years of its history has been divided into 3 phases: prehistoric era, matured era and reform era, and based on the study of its method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ey issues study is also summariz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Key issues, Research models
2013-09-11)
10.3772/j.issn.1673—2286.2014.01.002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整合性图书馆系统的应用与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编号:09CTQ004)的资助。
陈定权(1974- ),男,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chendq@mail.sy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