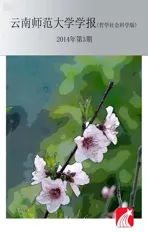族群、环境、地方知识与灾难
——以1786年四川大渡河地震为例*
2014-04-10郭建勋
郭建勋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四川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一、引 言
西方人类学将灾难研究的碎片化趋势转到整体事实的研究路径上,为整体、全面及历史地理解灾难的成因和后果提供了新思路。具体而言,人类学从整体论和过程论入手,探讨灾难多维性及其与环境、社会文化复杂互动过程,将环境、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因素纳入到灾难研究中,体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价值和特点。其中,人类学对脆弱性概念的讨论和细化*目前,使用较多的布莱基(Blaikie)的定义,他认为,脆弱性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预期、应对、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和特点。这里涉及的是一套组合因素,它们决定在自然和社会中分立和可区分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参见Piers Blaikie,Terry Cannon,Ian Davis and Ben Wisner( 1994) ,At Risk: Nation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and Disasters.New York: Routledge.P.9,使得研究视角从灾难本身向灾前社会转移,关注灾难中的自然、社会与人的因素及相互作用及其过程。
2008年汶川大地震激发了人类学家积极应对灾害的学术与社会参与精神,国内人类学界开始重视对灾难的研究。[1]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最多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研究,主要内容有:地震期间的人类学关怀;地震灾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变迁;产业恢复和重建以及地震灾害史。[1]这些成果体现了国内人类学界的现实关怀和参与度。*这与国外早期灾害研究相类似。研究者关注灾难的客观属性,并着力对其影响层面进行事实描述,研究内容涉及多方面,如灾难的时空分布、灾难中的行为表现、灾难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灾难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灾难救援与灾后重建、心理恢复、社会组织调整与适应、社会变迁等。目前,如何将灾难包括地震的研究回归整体事实,从“非常态”事件转向正常的社会结构分析,将应急、现实关怀与历史过程相结合,分析具体灾难发生前后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拆解灾难背后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寓意,以便揭开深埋于自然环境造成灾难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根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做出贡献。这是目前人类学灾难研究中需要继续深化和探究的内容。
1786年6月1日(清乾隆五十一年5月6日),在四川泸定大渡河一带发生一次7.75级*对于此次地震的震级,地震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大地震。这次地震是四川有地震资料记载以来震级仅次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一次,引起的水灾波及长江中游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之大、影响之远,在四川地震史上也不多见。[2]据说,此次地震引发的水灾,让今天的四川乐山、宜宾、泸州、重庆一带漂没之人不下十万之众。[3][p.106]关于本次地震资料丰富,有60多种地方志,另外还有碑刻、私家笔记等多种类型的材料。*据江在雄介绍,经过1955年到2005年的发掘整理,有关此次地震的史料丰富、类型多样。这些已收入《四川地震全记录》一书中。
川西泸定大渡河流域处在北东、北西和南北向三大断裂带交汇的区域,发生的地震往往强度大。[4][p.6]自雍正三年(1725年)有地震史料记载,该区域共发生破坏性最大、损失惨重的强震三次,即雍正三年、乾隆五十一年和1955年。同时,这一区域在明末清初时人户就相对集中、经济较为繁荣。西炉未开之前,(泸定)冷碛为西徼唯一之商场。[5][p.208]化林坪在清康熙时,为川边第一重镇。乾隆时,尚能成为川边第二重镇,控制番夷。[5][p.219-220]泸定的人口,一半居住在大渡河谷平原,一半在低山和高山;一半是来自川西北和川南移民,一半为当地土著。[5][p.6](泸定的)冷碛、沈村、咱里、烹坝、县城附近,人口稠密、市肆发达,为县境精华所荟。[5][p.3]而打箭炉(今康定)俨然国都,和方供役,纳贡之夷,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蚁聚,炉城市肆所由繁昌,商业所由兴盛,专在于此。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一二为工人。[5][p.14-15]到现在,该地区也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分别建有猴子岩、长河坝、黄金坪、泸定、硬梁包、大岗山电站。这些电站既在生态敏感区,也在强震高发区。水电开发、小工业基地建设,新城建设等形成的移民安置点也多集中于大渡河谷地带,脆弱的地质生态和人为因素,大大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风险。

二、文献中的地震和水灾*本部分资料主要来自以下两书: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壹),地震出版社,2005;孙成民主编《四川地震全记录》(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目前学者所用的资料绝大部分出于此。官方记载主要来自当时亲赴震灾区进行震灾调查和抚恤的四川总督保宁在震灾调查后写给当时朝廷的奏折。有关这次地震造成灾害的奏折保宁共写有两个。一个是五月初六地震发生后保宁从成都出发途经双流、新津、邛州、名山、雅安、荥经、清溪而至泸定、康定对灾害进行全面调查后,于五月二十五写给乾隆皇帝的第一个奏折。另一个是保宁在震区调查过程中接到越营参将、越厅通判和宁越营都司有关越西一带震灾情形的禀报后于六月初二写给皇帝的奏折,后收录在清廷档案中。
1786年6月1日午刻,打箭炉突然地震,至酉刻势方少定,第二天又有数次地震,以后连日都有轻微地震,到18日才停止,城垣全部倒塌,文武衙署仓库兵房等全部倒塌共169间,歪斜、脱落、墙壁倾颓有384间,其完善者十止一二。压死勒休千总陈荣1员,兵丁2名。城内店铺房屋倒塌了727间,压毙内地商民35名。查在炉贸易商民,本系有力之户,其无业食力贫民共51户,倒塌土房54间,压毙民人5名。明正司除土司官寨和大小头人的锅庄外,倒塌番民碉房177座,压毙番民男妇大小193名口,倒塌喇嘛寺,压毙喇嘛21名。[3][p.95-96]
沈边、冷边、咱里三土司地方共倒塌了贫民瓦土房127间,压毙男妇大小4名口;倒塌671间穷番碉房平房,压毙男妇大小181名口。震塌、震倒化林坪的营城衙署、兵房、药局307间,其余都司千总衙署及仓房、库房、兵房均有墙壁坍卸、间架欹斜。泸定桥御碑的亭墙被震裂,脊瓦脱落,护崖羊圈坍卸十二丈,桥东巡检汛弁廨署、兵房也有轻微坍损。清溪县间段倒塌城身34丈,垛口连墙壁226丈,建在平地上的官民房屋也有墙壁倾圮,屋宇歪斜。[3][p.94]今越西厅城又震塌116丈,北门城台城楼震塌;倒塌46间通判、照磨、儒学、廨宇、仓监;倒塌26间兵房,坍损19间,倒塌39间军粮府衙署;民居瓦草房,压毙4人。宁越营(今甘洛县海棠镇)震塌9间都司衙署,62间营汛兵房中25间坍损,倒塌71间居民瓦草房。*孙成民主编《四川地震全记录》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8页。富林白岩岗、炒米岗巡哨楼地震倾圮。此外,天全城市乡村田水上岸,屋脊皆折;[3][p.100-101]今四川、重庆全境内、贵州部分区域、湖南的芷江、黔阳等地,均有程度不等的震感。*此根据孙成民主编《四川地震全记录》上卷第99到106页所录方志资料统计而来。地震发生前,泸定大旱。地震发生时,伴有地声和有多次余震。
本次地震,沈边所属之老虎崖(摩岗岭)地方大山裂坠。清人张邦伸在异闻*张邦伸写道,书中异闻据其在蜀中所见所闻写成。事虽离奇,实非诞妄。所记之事,为世所不常有者始书之,以志不忘。中,以“泸河水患”为题写道:临息时,成都西南大响三声,合郡皆闻,不解其故,越数日传清溪县山崩。清溪去成都五百里而遥,其声犹巨炮。[3][p.9]在今天泸定得妥的大渡河岸边,尚有一巨石,当地人称“花石包”,据泸定地名办测量体积有7324立方米。地震时由对岸的摩岗岭抛来。得妥铁桩庙墙壁上有一小碑,记载了这一经过:
永垂万古
乾隆伍十一年大限(旱)*地震发生前,该地的气候表现出不正常的迹象。地动山崩石立作(坠)山一皮金洞子*表明乾隆以前,此地有人开挖黄金。
节(截)水九日五月十四鸡明(鸣)出水
铁桩土主太保娘娘尊神土地庄患金身
会首吴德玉 吴应龙 李宗
四川雅州府沈边长官余为[5][p.253]
山崩壅塞了大渡河,沈边等土司沿大渡河边的大部分田地被淹。泸定民间曾有传言,当时大渡河的回水漫至泸定桥,人们可以坐在桥上洗脚,言水位之高。积水高20余丈,至十五日塞处冲开,奔腾迅下,田地又被冲刷。下游为清溪县过大渡河赴建昌大路,该处原野绵连,村堡相望。在强余震作用下,大坝溃败,高十丈的水头奔腾而下,沿岸的田地和房舍,大多被冲毁。
大渡河北岸清溪县境,冲没万工堰、娃娃营、杨泗营等塘汛、衙署、庐舍和田稼。冲走11间万工堰汛弁、衙署,66间兵房,甲仗、塘汛、卡房冲去无存;冲没385户万工堰等处居民瓦草房,淹毙大小21名兵民、男妇,受灾1297人。居民奔避山上,日食无资。冲没娃娃营社食一所,贮藏的193石谷荡然无存。冲走大田、松坪二土司境128间草房,淹毙23人,受灾378人。大渡河南岸越西厅境,冲没海螺坝、马厂、桂皮罗、临河堡、水打坝等处317户居民的瓦草房,淹死36人,受灾1343人。冲去松林地、野猪坝二土司境470间瓦草房,淹死19人,受灾1170人。沈边土司境内除冲塌房屋、淹毙人口外,478名番民受灾。[3][p.97]大渡河下游峨边厅沿岸的罗回、归化、沙坪、万旋等分溪场市一洗尽净。[3][p.103]激流到达嘉定(今天四川乐山),浪头高数丈,如山行然,[3][p.100]府城西南临水冲塌数百丈,丽正门崩入二百余丈,城上惊观水势落江者不计其数。[3][p.102]高出水面丈许的堵水铁牛亦随流而没。水至嘉定府城壅遏,沿河沟港水皆倒射,府江亦逆水十里,民居亦多淹没。叙州、泸州以下山材房料壅蔽江面,同行筏、舟船遇之,无不立覆,至湖北宜昌水势始渐平息。大渡河、岷江下游沿岸漂溺者以万家计。[6][p.2]
据上述灾难的粗略统计,地震及水患震中地区共倒、塌各类房屋共2527间,冲毁各类房屋共1377间,压淹死545人,水灾人数4666人,直接发放恤银3686两。*根据保宁奏折做的统计数据。这对当时有限的生态空间里的各族民众而言,地震及水灾的影响巨大。此次地震的震中虽在偏远的康区东部,但由于地震及水患影响到长江中游地区,水灾致死十万之众虽有夸张和不实,但给大渡河中下游、岷江下游及长江中游沿岸百姓带来的灾难后果和社会震动,在今天看来也是巨大的。加之地震发生地在出藏南路要口,为川茶输藏的要冲之地,清廷控制康藏的前哨。*本次地震发生后,运茶驿道阻塞不通,造成西藏茶叶供应短缺。参见孙成民主编《四川地震全记录》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地震及水灾引起了清廷高层的高度重视。乾隆收到灾情奏折后立即作了朱批,并于29日上谕要详查、确估和抚恤。[7][p.99]
三、灾难的前因与后果
对于这次影响深远的灾难的成因分析,地震专家认为是自然因素,因为川西泸定大渡河地区处在三大断裂带交汇的地带,发生强震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人类学家看来,许多归咎于自然原因的灾难,至少在部分上更像是由人类行为积累造成的,而人类行为积累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结合,产生了脆弱性状况。人口、社会经济或生态特性不断增加的压力,自然灾害就会变成灾难。[8]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分析此次地震。
从自然因素而言,地震、水灾的发生可以说是天灾,灾难总是一而再地回到我们的身边,人类没有能力阻止它们的到来。[9][p.10]若从人口、族群及与环境的关系而言,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田地被毁,则可视为由文化观念、生计方式、房屋选址、建筑技术和贫富差异等因素造成的人祸,而汉人与当地人在灾难的成因和承受的后果上不同,这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总结。
(一)清代对康区控制力逐渐增强,导致康东人口激增、户数增加,且多居住在大渡河谷底;新的环境观念、生计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是地震引发水灾且后果严重的重要因素。
康东大渡河流域历来是汉藏等多族杂居之地。任乃强认为:“大渡河沿河土著,泸定以上,昔皆番人;河道以下,昔皆倮倮”。[10][p.287]清代是汉族移民进入康区的高潮,一是由于王朝对康区实际控制力的增强,二是由于四川战乱、人口太稠。清初,清廷政治军事力量尚未到达康区。顺治九年(1652年),现泸定县境内的沈边、冷边两土司归附清廷。但当时清廷政治、军事力量尚未到达康区,没有对归诚的土司以册封。[11][p.29-30]清廷在化林坪设汛兵。康熙二年(1663年)化林坪改汛为营,三十四年(1695年)添设参将。[5][p.219]三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与土伯特划雅砻江为界,河口以东属西炉,以后官书,称此地为西炉,藏人则呼此带地方为“卡拉”,犹言中国领土也。[12][p.44]四十年(1701年)在打箭炉设置监督1员,以榷课税。[11][p.80]四十三年(1704年)化林营改为化林协、设副将,下设各营分驻打箭炉、泸定和宜东等地。[5][p.219]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铁索桥建成。[5][p.203]雍正七年(1729年)设打箭炉同知1员。[11][p.80]
总之,历史上因时因事而来的军士、商贾、工技、杂色人等,以及负贩、苦力、虞牧、农国之人,或沿大渡河谷南下北上,或沿碉门岩州的小路越岭至泸定桥,过瓦斯沟之大路的茶马古道,辐辏而至。随着清廷对康区控制力的增强,尤其是乾隆近三十年的金川之役,带来大量官兵夫役及逐利之商贾。当时汉人赴边之众,可以想见。[5][p.186]移植川边的汉人在大渡河岸泥石流形成大小不等的冲积河坝如兴隆、沈村、冷碛、安乐坝、烹坝,瓦斯沟等地形成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村落和市镇。汉人能在河谷定居,与汉人在河谷地带新建排霜沟,引进新作物有关,使得当地人放弃不耕的河谷坝子,成了汉人新居所,而当地人大多仍把耕地和村落选在附山的台地和山坡。
由于大渡河流域干湿两季分明,雨季集中,且多大雨,加之断裂带发育,两岸多是童山,林木绝少,岩石裸露,风化严重,泥石流灾害频发。基于生产技术、生计方式、交通线路和文化观念因素,汉人在大渡河谷地带形成新的市镇和村落,而当地人则爱护地力,以神山神谷,禁人扰动。[12][p.428]任乃强在总结泸定得妥陈氏家族发展时说道,“汉人到此地经商,终为地著。且善利用一般认为无用之地的荒山老林,并将当地土著视为无用之物开发利用”,[10][p.6]给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同时,川西、青海南部和西藏全部,是世界注目的黄金产地。进入康东的汉人,除了经商、农耕外,另一重要营生就是在大渡河沿岸山间开采黄金,或在河边淘金。汉人开挖山中黄金,对当地脆弱的生态更是雪上加霜。汉人开挖山间黄金,与当地人的观念相左。当地人对地表与山间的黄金作了区分,生活中所用黄金乃地表拾得,认为山间黄金为护神之物,对汉人开挖深恶痛绝*藏传佛教禁取地下黄金。当时在藏传佛教边缘的大渡河流域,采金很盛。。相异的生态观对于环境的影响自然不同,当地人将地表所得黄金主要用于寺庙、房屋建筑、家具或服饰上的装饰,以显神圣或尊贵;汉人则无视黄金的出处,均视其为生存资本和财富象征,无止无休攫取。随着黄金的物质财富观念和清帝国的需要,使得当地黄金开发愈演愈烈,后来一些当地人也参与其中。在今天,大渡河两岸都还有许多仍未完全坍塌的开挖黄金后废弃的山洞,当地俗称“金洞子”。上文所引铁桩庙所载文字,“坠山一皮,金洞子截水九日”,虽不敢断言大渡河水在此地被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阻断完全是挖金所致,但至少与之有关系。因为开挖山洞寻找黄金的方式,淘一成金,弃万倍土,造成地面坍塌和大量弃土。[10][p.645]此地一旦发生地震,带来的不仅是屋塌人亡,更有次生的滑坡、堰塞湖和水灾叠加的灾难后果。因而,可以说1786年强震及其后果,是人为建构的,因为地震及水灾发生在人的生产环境中。
从族群文化角度看,汉人由内地进入川边,视山地为不可耕种的蛮夷之地而居于平坝。*任乃强说,汉人概居河谷区域,从事农业,行汉语,守汉俗,有学校教堂,不奉喇嘛教;番人之纯粹者皆住高原,事牧畜,行藏语,守番俗,奉喇嘛教红教者多,无学堂教堂。其汉番杂配者之子孙,则处主原和河谷间,兼营农牧业,每能兼通番汉语,奉喇嘛教黄教者多,虽从番俗,而亲汉写,多喜自称汉人,即称番民,亦慕汉化。见任乃强著《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220页。他们处在日益脆弱的环境中,面临更多的自然灾害风险,但自身的文化观念让他们安于现状。他们相信生活在这些地带是文明的,人们还认为只要诚心信仰铁桩土主,即使灾难来临,神也会护佑。加之地震并不那么频繁,风险并不会时时出现,以至于当地人会将灾难发生的时间拉长*2013年6月,我在四川泸定得妥花石包处访谈当地一位老婆婆。她说,这是一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了。,甚至遗忘,以此淡化居住此地的风险和威胁。
(二)汉人带来的建筑技术减少了地震中汉人伤亡损失,而当地人建筑技术之不足、不佳的经济状况是平民伤亡较多的重要因素。
破坏力极大的强震导致的后果有多方面,原因也有很多。若从人员伤亡角度来看,房屋的选址和技术是导致损失的重要因素。据保宁奏折,山谷之间的损失要重于平地。打箭炉建在清溪平地的房屋,屋宇歪斜之处,尚属无多。这里仅就房屋本身的技术与减少损失角度进行讨论,因为在强震面前,再坚固的建筑都会完全倒塌。*1923年炉霍地震,虾拉沱天主教堂,建筑最坚,亦同崩圮。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据资料记载,本次地震时,打箭炉与化林坪等地的民居主要是藏区碉(平)房和汉区穿斗式建筑。*关于两者的类型,可以参考中国的地震烈度表。地震中,两者造成的损失也不尽相同。
康区碉(平)房是藏族的传统民居,以毛石为墙,一般为3到4层,墙体承重,也无承重的隔墙。*这里要区分的是,这里的碉房与嘉绒藏族地区的高碉建筑,在抗震性能上是有重大差别的。主要体现在墙壁的坚固上。高碉建筑中,棱愈多,则更难倒塌。任乃强在丹巴林卡南街见到一方碉高28丈,已修数百年,历地震数次而不圮。而此技艺,产于以茂州者多。包砌工价,每方丈约银4两。任乃强著《西康视察报告》,《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据地震专家评定,抗震类型属于Ⅱ类。[4]任乃强写道,西康建筑房舍,虽楼高七级,广厦千间,木匠无须如何设计,但只自下而上,一间一间依次叠砌之,随意增减,并无限制。恰如幼稚生为积木戏然。其各间修法,颇似内地装仓:用巨木作架,较小之木骈列装壁,另以木骈列盖顶后,再从上方如式修之。上下木柱,并不衔接。任随横拓若干间,上砌若干层亦然。故一经震荡,即全倒塌。而官寨子坚碉房,在房舍之外,筑坚厚土石墙包围之,墙壁坚牢不倒,借以支持木屋,故能耐久。[12][p.226]汉式庙宇、汉民住居的街房等建筑的主体部分以汉式穿斗的木结构为主。[4]
打箭炉城内店铺房屋倒塌727间,压毙内地商民35名。其无业食力贫民共51户,计倒塌土房54间。明正司除土司官寨大小头人锅庄外,计倒塌番民碉房177座。倒塌喇嘛庙,而汉式庙宇未提到有倒塌和破坏情况。*这里,座与间是不同的计量单位,房屋的间的数量多于座或户。也就是说,碉房的乱石墙有一定的抗震性,但房屋整体结构不如汉式穿斗房屋的抗震性强。而汉式房屋,整体抗震性强,较之藏族碉房不会出现整体倒塌的情况,易出现局部房间出现墙壁倒塌的情况。相对而言,出现人员伤亡的可能性减小了。泸定桥的桥头亭是飞檐翘角的木结构,地震后墙裂缝、脊瓦脱落。护崖羊圈坍卸12丈。而桥墩、桥亭和铁索等,没有受到损坏。建在平地的桥头巡检汛弁署、兵房有轻微倒塌。化林坪未被破坏的兵丁住房有206间,演武厅、都司署、千总署及兵房有的墙壁坍塌、有中等或轻微的间架欹斜。
可见在康巴农区的碉房,并不十分适应康东横断山地的地质条件,其抗震性不如汉式建筑,地震造成的死亡率也较高。*同样,现在道孚全木的崩科房抗震性最好,也是例证之一。因而,汉族移民的进入,一方面增加了人口密度,且多居住于河谷与低山,加大了地震破坏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汉族移民,尤其是来自四川名山的木匠,带来的汉式建筑技术,补充了原有地方文化之不足,*任乃强认为,番中古无木工。乱石彻墙,横架木条,铺薪填土,以为居屋;……现在康地所有华美住宅,皆四川名山木匠所造……(名山木匠)遇有大工程有三种:一为建筑喇嘛寺,二为建筑头人之官寨,三为建筑大桥梁。见其《西康图经·民俗篇》之168“名山木匠”。提高了当地建筑的抗震性,一定程度上又减轻了地震带来的财产损失,尤其减少了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保宁奏折中写到,在沈边、冷边、咱里三土司地方,当时共有751户。沿途有开馆小贸,及负戴食力之内地民人,共倒塌贫民瓦土房127间,但压毙男妇大小仅4名口,而三土司内的穷番碉平房,共倒塌671间,压毙男妇大小达181名口。官寨子之坚固,与名山木匠的参与关系密切。名山木匠不到康区前,番中房屋之柱,不施斫削;桥梁叠木为之,不施穿斗;今则一切已居改良。虽其工作仍为汉人所擅,番人亦不无相当进步。[12][p.429]
除了技术外,我们还应从社会层面对上述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同样的灾害和事件,除了族群因素外,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所承受的风险度和受灾情况也不同。如果从房屋坍塌的后果看,无论族别,社会底层的平民建筑,破坏都很严重,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而官方的建筑或当地土司、头人的建筑则倒塌较少,对他们而言,灾难的后果就不甚严重了。
四、结 语
总之,当地较少的土著人口及良好的生态观,对原有环境压力较小。清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和控制力逐渐增强,大量移民进入康东,带来新的观念和生计方式,使得环境压力加大,灾难风险大大增加;*今天有如此多的历史文献,我们才能对此次地震有如此详细的讨论,也缘于清代对这一边缘地带的日益重视,而地震及应对表现是将边缘地带纳入国家管理和体现国家权力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移民带来的技术在提高当地人防灾减灾能力方面亦有贡献。汉式建筑在减少人员伤亡上效果显著,当地人在山间台地建房,地震引发水灾的影响较小。汉人村落又多在河谷地带,避不开地震引发的滑坡和水灾,当地人房屋建筑技术的不足,使得地震中人员伤亡较多。地震中汉人与当地人在伤亡人数和受水灾影响方面的差异,显示了汉式建筑技术、当地人的生态观念在应对地震及次生的滑坡、水灾方面,各有优势,这为之后共居于此地的各族民众取长补短,应对灾难提供了新的经验和生存智慧,丰富和发展了地方知识。而同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与当地人的房屋倒塌情况严重,与上层官员、土司、头人相比,灾难损失也最大。对社会上层和富人而言,这可能算作文献及当地人所谓“地动”而非灾难。灾难中的主观感受和社会经济因素也不可忽视!
1786年大渡河地震再一次提醒我们,自然环境既是生养我们的大地母亲,同时,也可能是人与环境共同建构的魔鬼。防灾减灾既要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灾难中社会、文化和人的因素,在族群接触的背景下,地方知识本身也会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多元生态环境、多族群的活动及地方知识与灾难的相辅相成关系,是理解西南地区不同类型灾难过程的又一思路,值得关注、细化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李永祥,彭文斌.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3).
[2]江在雄.1786年大渡河地震、水患及救灾[J].四川地震,2006,(3).
[3]孙成民.四川地震全记录(上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4]王新民,裴锡瑜.康定-泸定地区强震活动与地震宏观破坏研究[J].四川地震,1998,(1).
[5]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6][清]张邦伸撰.锦里新编(卷14)[M].
[7]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壹)[Z].北京:地震出版社,2005.
[8](美)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纳日碧力戈译.彭文斌校.灾难的理论研究:自然、权力和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
[9](美)苏珊娜·M·霍夫曼.赵玉中译.魔兽与母亲[J].民族学刊,2013,(4).
[10]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11]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2]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