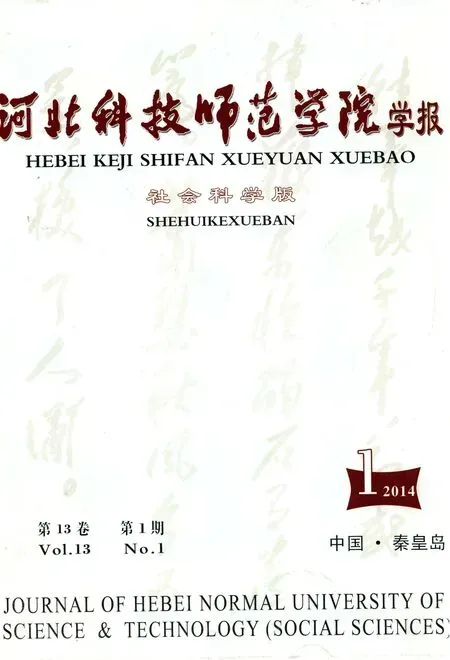唐诗中的冀东地理意象考释*
2014-04-07马吉照杨湘江
马吉照,杨湘江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河北秦皇岛 066100)
一、唐代冀东战事
边塞诗是唐诗大宗。从理论上说,一切地处边疆的军事设防之地固然皆可称边塞,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唐代边塞诗是写北方边塞。唐河北道北部,大致沿燕山山脉自西徂东分布的妫(今河北怀来东)、幽(今北京)、檀(今北京密云)、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营(治今辽宁朝阳,辖河北秦皇岛部分地区)五州,为唐朝的东北边塞,相当于今京津两市、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南部的大片地区,而燕山山脉正是隋唐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以南属农耕区,以北是半农半牧和游牧地区[1]83。唐朝时这一地区以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和奚,即杜甫“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后出塞》)、张祜“长驱千里去,一举两蕃平”(《采桑》)所说的“两蕃”,唐朝分别设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加以羁縻,但他们有时臣服,有时对抗,唐朝在东北边塞的战争就多是与这“两蕃”展开,唐诗中对重大战事亦多有反映,其中不少重大战事在今冀东地区展开。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举兵杀文翙,并据营州反,进攻河北。七月,以梁王武三思为渝关道安抚大使,防御契丹,著名诗人崔融随军东征,杜审言、陈子昂皆有诗赠别,崔融此行有《塞垣行》、《塞垣寄内》等篇,十一月还京时,陈子昂有《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九月,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以讨契丹,陈子昂为参谋,河北籍诗人卢照邻有《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曲父老》。陈子昂在军期间作有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及《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等十数篇。十月,契丹兵攻破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又攻瀛洲,河北震动。
神功元年(697年)三月,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大败于平州东,契丹攻掠幽州,屠赵州。陈子昂、张说时俱在河北,子昂作《国殇文》哀之,张说向朝廷详陈王孝杰忠勇敢死,因后军不继而败亡之状。后常建有名作《吊王将军墓》亦咏此事:“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2]93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常建诗多警策之句,独于此诗评价甚高,谓为“一篇尽善者”,“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
睿宗延和元年(712年)五月,幽州都督孙佺率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等,将兵十二万伐奚。临行朝中大臣有诗相赠,今存沈佺期、李乂诗,皆题《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是役,孙佺在冷陉山大败,遭擒后被杀,殁师八万。
开元二十年(732年)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受诏征讨契丹,储光羲有《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正在边塞漫游的大诗人高适在河北谒李祎,有《信安王幕府诗》,高适此行自幽蓟沿燕山南麓东下,出卢龙塞,到达营州,作有《蓟门五首》《塞上》《营州歌》等一系列边塞名篇。二十一年,幽州长史薛楚玉、副总管郭英杰等五将率精骑一万与契丹战于渝关,结果大败,士卒六千人被杀害。高适在归途中闻讯,《自蓟北归》咏及此事:“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此后,张守珪经略幽州,军事上一度取得成功,但二十四年,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二十六年(738年),部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高适有感于自幽州南归的朋友对边塞战事的讲述,结合自己的出塞经历见闻,写下一生最著名的代表作《燕歌行》,堪称唐人咏东北边塞战争的扛鼎之作。
天宝十载(751年)八月,范阳节度副大使安禄山及契丹战于吐护真河,败绩。是年,储光羲有《次天元十载华阴发兵,作时有郎官点发》:“鬼方生猃狁,时寇卢龙营。帝念霍嫖姚,诏发咸林兵。”描述战前大兵出发时的场面,题目中“天元”应为“天宝”之误。
几次最重大的对抗皆发生在唐前期,中唐以后,唐朝与东北诸蕃战时防御、和平时沟通中转的重任落在控制这一地区的幽州藩镇身上。幽州镇相对于唐朝有较大独立性,可以说既面临唐中央和周边藩镇的压力,又要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因此不会像前期热衷邀功的镇将那样动辄轻启边衅,东北边塞相对初盛唐反而平静,但战事还是时有发生,如《新唐书》刘济本传记载其镇幽州时期“奚数侵边,济击走之,穷追千馀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3]5974刘济是中晚唐河朔藩镇中著名的儒帅,权德舆所作墓志铭中称颂其“饮马滦河之上,扬旌冷陉之北”[4]5930。此一时期多位著名文士入幕或游历幽州,王建《塞上》、张籍《渔阳将》等诗篇皆是当时边塞之真实记录。
除了以上提到的唐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唐初的太宗东征朝鲜,亦以今冀东一带为重要基地,太宗君臣在戎马倥偬之余的群体唱和,也都广泛地写到这一带的地名和代表风物。正是由于在唐前期屡次成为边境战争的重要战场,东北边境成为唐代诗人关注的焦点,冀东地区的地名因而屡屡进入边塞诗,成为唐诗中的典型地理文化意象,作为诗人们笔下边塞的象征,与诗人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以及征人思妇的边愁闺怨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卢龙
唐代平州(北平郡)治卢龙,属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管辖,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二年(743年)还曾是安东都护府的所在地。城内驻卢龙军,管兵万人,马三百匹,后又增设柳城军,境内还有西狭石、东狭石、紫蒙、白狼、昌黎、辽西等十二戍所和多处镇城。平州处幽州与营州之间,把幽燕和辽西联系起来,使唐朝更有力地控制东北地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7引黄道周语谓:“失营州,渝关之险犹可恃,失平州,则幽州以东,无复藩篱之限矣。”[5]750
除了平州治所卢龙县,卢龙县城西北二百里(《通典》卷178“北平郡”条)有卢龙塞(今唐山迁西县北),属蓟州,唐曾于此置静塞军。静塞军驻地史书记载不一,《通典》卷172和《新唐书》卷38“地理一”皆载静塞军在蓟州城内,《新唐书》卷39谓在蓟州“南二百里”,《唐会要》卷78谓:“渔阳军在幽州北卢龙古塞,开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为静塞军。”严耕望先生考证认为静塞军在卢龙古塞,开元末至天宝间已移至蓟州[6]1732。出平州经渝关通辽东道可至营州,出卢龙塞往东北可达奚和契丹衙帐。因此,无论是平州的卢龙,还是平州以西并不遥远的卢龙古塞,均为唐东北军事、交通要地,而有些时候,古人也有卢龙塞代指临渝关或古北口,“盖幽州以东迄于海滨之长城塞,皆泛称为卢龙塞。”[6]1710
这一带曾留下不少诗人亲历的身影,唐诗中也不乏诗人送同僚好友赴“卢龙”从军的篇章。唐初,太宗伐高丽,“翠野驻戎轩,卢龙转征旆,”唐太宗驻军平州,有《于北平作》纪行写景。万岁通天元年,陈子昂写下《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为诗人崔融随渝关道安抚大使武三思东下防御契丹送行:“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开元二十年,高适漫游东北边塞,有《塞上》:”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曾入幕府幽州的杨巨源有《卢龙塞行送韦掌记》:“雨雪纷纷黑山外,行人共指卢龙塞。”中唐诗人于濆《边游录戍卒言》记述了一位“二十属卢龙,三十防沙漠”的老兵的征战人生。另外如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不卖卢龙塞,能消瀚海波”,李涉《奉使京西》:“卢龙已复两河平,烽火楼边处处耕”等提到“卢龙”,虽然均非诗人或诗歌题赠对象亲往卢龙,但仍然都与实际地理意义上的卢龙有关,因平州(卢龙)和营州、幽州等地同为“安史之乱”中安禄山的老巢,是唐东北边塞的战略要地,始终牵动着中晚唐诗人的爱国情怀和关注的目光。
除了亲至边塞的诗人的吟咏,卢龙(诗歌中亦称“卢龙塞”、“卢龙戍”、“卢龙碛”)同下文的渝关、辽西等地名一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理文化意象,在众多的边塞诗中代称边地,几乎没有具体地理方位的意义,如中唐诗人戎昱《塞下曲》:“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戎昱一生未有入边经历,《塞下曲》亦为传统乐府古题,此诗感慨边塞战争自古有之,边关将士长年背井离乡戍守在外的劳顿、凄苦命运,而非专咏特定时事,卢龙塞在这里就是遥远边关的象征,只要一提到卢龙塞,便无须再进一步描写、介绍戍守之地如何偏远,如何苦寒,边关将士的征戍之苦以及他们与家乡、亲人、思妇间的距离顿时不言而喻。刘长卿《月下听砧》:“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其二:“卢龙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芜晓不飞。乡国近来音信断,至今犹自著寒衣。”也都是同样性质的用法。
应当指出的是,以卢龙代指边地,在北朝人诗文集中已经出现,如庾信《思旧铭》有“坟横武库,山枕卢龙。思归道远,返葬无从”,王褒《从军行》有“康居因汉使,卢龙称魏臣”,前者是羁留北方的庾信抒写自己南归无望的痛苦,举卢龙代表极北极偏远的边地;后者代表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是总的来说,北朝时还不多见,更没有像在唐诗中这样广泛、典型地用以表现征戍之苦的主题,尚不足以构成有代表意义的诗歌意象。
三、榆关
渝关,即临渝关(今山海关),因形近亦多写作“榆关”。今人多以为旧渝关在抚宁榆关镇,明初徐达以其地非控扼之地,而移至今山海关,实则今山海关完全符合《通典》、《新唐书》等所记距平州、营州里程,今山海关即隋唐渝关故地,唐时设渝关守捉,管兵三千人,马百匹,属平卢节度使管辖,严耕望先生于此有详细辨证[6]1747-1751,故唐诗中的“榆关”仍在今山海关附近。
到过榆关的唐代诗人最著名的莫过于高适,《燕歌行》之“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之“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降胡满蓟门,一一能射雕”,皆雄奇佳句,卢照邻《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曲父老》“灞池水犹绿,榆关月早圆”则以榆关代指家乡河北。唐诗中以榆关代指边塞也很常见,如:
寒沙榆塞没,秋水滦河涨(按:此为唐诗中唯一咏及滦河者)。(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
朔风萧萧动枯草,旌旗猎猎榆关道。(刘长卿《疲兵篇》)
春风昨夜到榆关,故国烟花想已残。(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其一)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有两个“榆关”,一在东北,一在西北,相去甚远,需结合具体语境格外留意。唐诗中的“榆关”、“榆塞”,有的是指今陕北榆林的榆林塞,唐代属胜州。如白行简《归马华山》“冰生疑陇坂,叶落似榆关”,以榆关与陇阪(今甘肃陇山)并提,温庭筠《塞寒行》“晚出榆关逐征北”,同诗写到白龙堆(在新疆罗布泊)、河源(在青海)等西北地点,唐末喻坦之《代北言怀》“困马榆关北,那堪落景催”,代北在今山西北部,地近胜州榆林塞,皆是唐诗中咏陕西榆关的例子。
四、碣石
唐诗咏及碣石者有三十余首,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和高适《燕歌行》“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无疑是其中两个最著名的例子。这实际也是碣石这一地理意象在唐诗中两种较常见的意涵。
关于“碣石”的今地,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此不备引,概言之:《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的碣石,指今秦皇岛一带的燕山余脉,包括自昌黎碣石、北戴河金山嘴至辽宁绥中“姜女坟”的广大地区;秦皇、汉武、曹操所至碣石,当即《水经注》所说没入大海之碣石,即山海关外之“姜女坟”,今属辽宁绥中;北魏、北齐皇帝所登碣石,当为《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右北平骊成县西南”之“大揭石山”,即今昌黎碣石山[7]。唐人边塞诗中提到碣石,多指榆关一带的东北边塞,包括今冀东辽南大片地区,区分具体地点反而不妥,故本文概称为榆关附近之碣石。
“碣石潇湘无限路”,以碣石、潇湘并提,把碣石视为当时人心目中极北、极辽远之地的地理标志,又如卢照邻《明月引》:“荆南兮赵北,碣石兮潇湘。澄清规于万里,照离思于千行”,同样视碣石、潇湘两地为中国北、南两个地标,形容月光之普照,杨巨源《上刘侍中》:“曙华分碣石,秋色入衡阳”,也是类似的应用;武平一《奉和幸新丰温泉宫应制》“秦王登碣石,周后袭昆仑。何必在遐远,方称万宇尊”,则将碣石与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并举,都是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以及高适《别冯判官》“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之碣石,与其附近的“榆关”一样,皆可视为东北边塞一带的代称,比之张若虚等诗中的碣石作为极北之地、极僻远之地的地标意义,更多了几分边塞的烟尘气。不过有时碣石所代指的地域更大,可指属古燕国所在的河北北部广大地区,如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说安史叛军“复自碣石来,火焚乾坤猎”,言“碣石”实指幽州,姚合赠《卢大夫将军》:“碣石应无业,皇州独有名”,也是说料定卢将军在朝为官,声名显赫,而在故乡当已无产业,唐代卢氏人物多望出范阳,因而碣石此又代指范阳。碣石与范阳实际距离并不很近,但在外人或旅居异乡的河北人眼里,都属燕地,感觉并不遥远,这与卢照邻《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曲父老》“灞池水犹绿,榆关月早圆”,以榆关代指家乡范阳,道理是一样的。
古代“碣石”有多处,唐诗中以咏榆关附近之碣石最多,除上文提到者,又如唐太宗《春日望海》“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韦应物《石鼓歌》“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钱起《送上官侍御》“碣石春云色,邯郸古树花”,独孤及《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驷马上太行,修途亘辽碣”,《海上寄萧立》“驿楼见万里,延首望辽碣”等,皆是。
《山海经》卷三《北山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二东流注于河。”谭其骧先生引《史记正义》:“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认为绳水即《水经》圣水,“碣石山应指圣水上游所出大防岭,即今房山县大石河所出大房山,亦有可能指圣水东源广阳水所出西山,即今小清河所出北京西郊潭柘山。”[8]49今按,著名诗人贾岛籍贯在今北京房山石楼乡,而贾岛自称“碣石山人”(《题青龙寺》),并自云“故山思不见,碣石泬寥东”(《晚晴见终南诸峰》),又其从弟著名诗僧无可亦称其“孤高碣石人”(《吊从兄岛》),诸诗中之碣石,可为谭其骧先生的前一种说法即《北山经》之碣石为北京西南的大房山提供有力佐证,而房山有碣石,也为范阳贾岛、无可以碣石为故乡提供了更为合理可信的解释(榆关附近之碣石以东便是茫茫渤海,范阳贾岛的“家山”何以会在“碣石泬寥东”,前人是说不通的)。由此,唐诗中多次出现的与燕昭王相关的“碣石宫”、“碣石馆”也可确信在房山碣石附近,如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高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夜归碣石馆,朝上黄金台”,皆是。燕国都城“蓟“在今房山琉璃河,燕昭王时所建燕下都在南面紧邻的河北易县,燕昭王招贤所建碣石馆在这一带是顺理成章的(今河北定兴县境内距易县燕下都遗址不远犹有传为黄金台的巨大土丘)。至于后来秦始皇东巡在海隅碣石曾命李斯刻碣石铭,附近之行宫当然也可称为“碣石宫”,但那是另一回事,在唐诗中,凡与黄金台、燕王台连用的碣石典故,所欲寄托的心绪是颂扬前代君王求贤若渴,人才各尽其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忧伤和建功立业的渴望,与榆关附近之碣石代表极北、极远之地以及东北的烽烟边地,其文化意涵是不同的。
除了榆关附近之碣石和房山碣石,《通典》卷186:“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迹犹存。”[9]5015乐浪是西汉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汉四郡”之一,秦汉长城东起点在其境内。唐诗对此朝鲜碣石亦有涉及,如许敬宗《五言辽东侍宴山夜临秋同赋临韵应诏》“岂如临碣石,轩卫警摐金”是唐初群臣随太宗东征朝鲜时的奉和之作,高适《信安王幕府诗》“云端临碣石,波际隐朝鲜”、常建《客有自燕而归哀其老而赠之》“碣石海北门,馀寇惟朝鲜”,均与朝鲜并提,然高适赠诗的信安王李祎当时为北征契丹、奚两蕃,实际远没有到达朝鲜境,常建诗中“自燕而归”、“寸心渔阳兴”等也皆涉冀北地名,故两诗又未必不是指当时已在东北边塞的榆关附近之碣石。其实,碣石既非一处,学者争论又多,咏及碣石的唐诗除亲历之作外,有些情况诗人自己未必有清晰认识,今人就更不可能也无必要去做具体界定了。
五、辽西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
这首小诗细腻体贴地写出了独守空房的少妇对出征边塞的夫婿的思念心情,极其短小,却堪称绝唱。唐时已无辽西郡,唐诗中之辽西亦为东北边塞之泛称。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包括今唐山迁安、乐亭以东,秦皇岛大部,三国、西晋至北朝,在今辽宁境设置昌黎郡(治所仍在今辽宁义县西),辽西郡辖境面积随之缩小,基本上全境都在今冀东地区,郡治也先后迁到了令支(今河北迁安南)、肥如(今河北卢龙北),直至北齐时废辽西郡并入北平郡(今卢龙北)。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当时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以东有辽西城故址,并指唐代《通典》谓此为汉辽西郡治之说不确,而当为北魏以后之辽西郡[5]752。唐代边塞诗人憧憬汉代边功,具有浓郁的汉代情结[10]31-70,边塞诗也往往借用汉代人物、典故和地名,故唐人观念中的辽西当为汉代的“大辽西”,然无论是汉代还是三国以后的辽西,始终包含今冀东的大片地域(三国以前是“包含”,之后是以这一地区为主体)。
辽西与卢龙、渝关、碣石同为象征唐东北边塞的地理文化意象,不同的是其他几个虽有的地点有过变迁但均为唐朝的实际地名,而辽西当时就已消失在前代的地名沿革中,因而唐人在诗中咏到“辽西”时,基本上完全不具有实际登临的地理意义,而是寄托了更多关于边塞的追忆和想象,突出表现为,写到辽西的唐代边塞诗,首首皆与征人思妇的相思联系在一起,其中不乏和金昌绪《春怨》近似的五绝小诗,如以下几首: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令狐楚《闺人赠远二首》)
海上清光发,边营照转凄。深闺此宵梦,带月过辽西。(顾非熊《关山月》)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满泥。佳人持锦字,无雁寄辽西。(崔道融《春闺二首》)
其中令狐楚诗与金诗意境最近,同是梦见到辽西探望戍边的丈夫,一个是还没有走到辽西,好梦便被黄莺啼惊醒,一个则是已经梦见在辽西团聚,天亮了醒来才无奈与夫婿分别。唐诗中的“碣石辽西地”(高适《别冯判官》),如此集中地体现了征人思妇主题,而今天这里恰有著名的“孟姜女庙”和“姜女坟”来纪念传说中的孟姜、万喜良这对无数征人思妇中的代表,应该说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化巧合。
六、冀东地理意象群
“卢龙”、“榆关”、“碣石”、“辽西”等冀东地名,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并成为边塞、边地的象征,或与衡阳、潇湘等南方地名并称,作为北方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已经超越了其实际地名意义,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文化意象。由于均为今冀东一代的古地名,又代表着相近的文化意涵,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古典诗歌中“冀东地理意象群”。
这一意象群之所以在唐诗中集体出现,首先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有关。这一系列古地名中,除榆关创设于隋代外,卢龙是夷齐故地,辽西是秦汉古地名,碣石在《尚书·禹贡》中就是东北方向的地理标识,加上秦皇汉武的登临、曹操的吟咏、《水经注》的记载,更是早为唐人所熟悉,只是这些地名在唐之前,还很少和战争烟尘、离愁闺怨联系在一起(南朝诗文中有个别篇章)。唐代频繁发生在今冀东地区的战事吸引了诗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从唐初东征朝鲜的唐太宗群臣到从军、任职或漫游至此的初盛唐诗人崔融、陈子昂、张说、高适,再到中唐以后曾入幽州幕府的李益、张籍、王建、杨巨源等,对到边塞的实际任职或漫游为诗人们增添了对东北边地的直接认识,冀东地名首先是通过这些人的诗文以及当时边关送出的表章奏记集中地进入唐人视野,随着边塞诗的大量创作,这些冀东地名逐渐被赋予或者加强了作为边塞象征的意义,习惯性地与边关塞漠、征人思妇、战争烟尘以及行旅、离别联系在一起。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冀东一带之成为边塞,是在魏晋以后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直接控制的疆域较之汉代大为收缩以后的事,在汉代,长城(即中原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分界线)远在今赤峰、阜新、铁岭以北,今冀东之地虽然相对于中原地区空间上已属僻远,却并非边塞,自然不可能广泛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征戍主题。
“冀东地理意象群”在唐诗中形成并获得了象征边塞和北方极远之地的特定意涵,日本人遍照金刚所撰《文镜秘府论》“九意”篇是收罗唐人作诗习用典故、词藻而成的类书性质的文字,其中就有“卢龙惆怅,碣石呼嗟”条,并备注“从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1]198。唐诗以降,这些地理意象在后代诗文中被反复使用——即使到了清代,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已经牢牢纳入了国家版图,卢龙、榆关等所在的冀东地区已成京畿腹地时仍然屡见不鲜。例如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有《姑山草堂歌》:“卢龙叶堕边霜来,江南林涧还秋苔”,以“卢龙叶落”作为边地寒秋的表征,与江南秋景对题;郁植《乌夜啼》:“卢龙碛里征人在,多恐闻时也白头”,陈子升《昔昔盐》:“愁见晓鸿征塞北,不知天将定辽西”,严我思《闻砧曲》:“平沙猎猎吹枯草,碣石霜飞寒信早”等等,则皆沿袭了典型的表现“征人—闺怨”的边塞诗传统。显然,当冀东地区在地理上成为内地,完全不再具有边塞意义时,卢龙、碣石等冀东地名在文学作品中仍不言而喻地作为北方边地的象征,这就更加充分说明,此一意象群已经超越了原初的地理意义,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地理文化意象。
[1]李鸿宾.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C]//李鸿宾.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2]傅璇琮.常建考[C]//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周绍良.全唐文新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华玉冰.论秦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J].考古.1997(10):81-86.
[8]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C]//谭其骧.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杜预.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