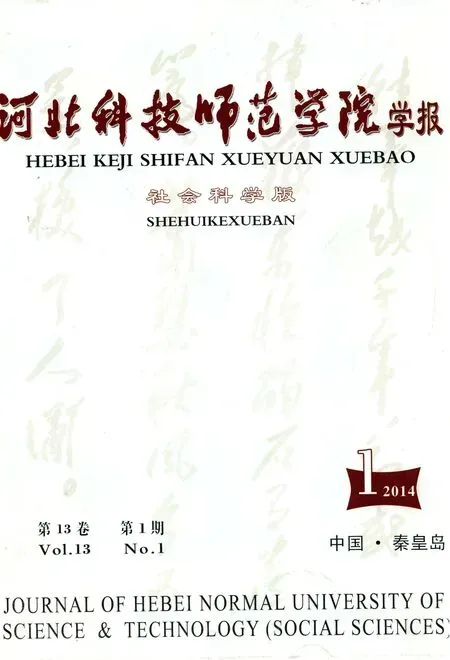孤竹国的农业文明探讨*
2014-04-07李强华韩国春郭艳红
李强华,王 芳,韩国春,郭艳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千载存续的孤竹国,诞于夏、兴于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1],是中国古代历史存续最久、疆域最为广阔的国家。其繁盛时期的疆域最大包括现今河北的秦皇岛、唐山、承德,及辽宁和内蒙古南部等地区。孤竹国的经济与文化,在商朝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生活在青龙河、滦河中下游的孤竹国居民多数过着定居生活,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对加强北方与中原地区文化融合,促进古幽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学界对孤竹国农耕文化的论述
孤竹文化是多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但在孤竹国的社会经济的研究方面,是以农耕为主还是游牧占主导,学者们各执己见。
(一)“游牧民族”说
持“游牧民族”观点的学者认为,孤竹国乃四荒之地,当地居民的生活随水草迁徙。李学勤在《试论孤竹》中论述道:“孤竹虽有国君,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的民众定居的地点”,他认为孤竹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并有国君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商周时期虽已传入中原文化,但仍有一部分人民处于游牧状态[2]。
(二)“定居民族、农耕文化”说
更多学者从考古和文献记载的角度,证明孤竹国民属定居民族,经济生活以农耕为主导。据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研究,商周时期很重视农业的经营,农作物已进行大规模耕种,并开始使用青铜农具,他解释《逸周书·克殷解》中“武王克商,发鹿台之钱,散锯桥之粟”的“钱”是青铜农器、“发鹿台之钱”是耕种工具、“散矩桥之粟”是粮食,都是属于农业方面的[3]。王士立认为孤竹国时期农业已很发达,人们不仅种植谷物,还大量饲养驴马等家畜,并已拥有“通河井”和“渗水井”等农耕灌溉技术[4]。康群认为孤竹的生产为“游收与农耕兼作”[5]。孟古托力认为商代的孤竹国有大量的华夏族人口世代居住,并与其他民族共同开发着当地的经济,并且无论从“距虚”(驴骡)的批量饲养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上,都证明“孤竹人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其农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孤竹国文化,虽有游牧人成分,但整体言不属于游牧类型”,“孤竹人口大体完成华夏化过程,变成华夏共同体”[6]。苗威认为:“孤竹是殷族的一支,殷族是不同于彼时周边少数民族的华夏族,而华夏族不是游牧民族,这就说明,孤竹是华夏族的一支,应是定居的农业民族而不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7]刘子敏认为从孤竹国封侯来说(《史记》索隐:“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所封”),孤竹国君为殷王的臣属,忠实地服务于殷王朝,孤竹国的主体民族应是殷族,殷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非游牧民族,因此孤竹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即使到了周代,孤竹人“以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定居状态并没有改变”;刘子敏还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孤竹居民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较长时间的定居生活,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而不是游牧民族[8]。王玉亮认为商周时期,无论王室抑或各诸侯国,辖域之间都有大量山林、沼泽、湖泊、闲散土地,都可以开垦、畜牧、渔猎,在山地丘陵可发展畜牧、狩猎,盆地发展农耕,靠河靠海则发展渔猎[9]。朱玉环认为孤竹国的农业文明对华夏农业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孤竹君家族及其所统辖的国民,多善开发、经营农业,在3 000多年前的冀东和辽西元荒之地进行了艰苦的开拓垦殖,并将野生植物栽培驯化为农作物。”并且当时孤竹国境内丰富的水域、平坦肥沃的土地、湿润温和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10]。
笔者认为,孤竹国主要存在于商周时期,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是农业,从事农业生产是人们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社会活动。孤竹二君子夷齐“兄弟让国”,来到周地,又因武王带兵伐纣,兄弟“扣马谏伐”,反对周武王的以暴易暴而“耻食周粟”,采“薇”充饥,最后饿死。从夷齐的事迹分析,二人不吃周朝的粮食,足以证明当时已有大量谷物种植,并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食源。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等方面也证明孤竹国时期农业文明已有了相当高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应以农耕为主,而非游牧。
二、孤竹国的农耕环境
《帝王世纪·第四卷》云:“封孤竹国:成汤十有八祀,乙未二月丙寅,王至东郊论诸侯功臣之后,封墨台氏。”因此孤竹国是商的同姓诸侯国。商代孤竹国最为鼎盛时期的辖域,北界大体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东界在辽宁大凌河、牤牛河一线,西界在北京市西山,南为渤海。随着商朝的灭亡,孤竹国逐渐衰弱,西周末年,孤竹国管辖范围只剩下滦河下游至朝阳的狭长地带。孤竹国所辖地区,背山面水,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温和,丘陵、盆地、平原等多样地貌有利于发展农耕、畜牧和渔猎等多种经济。
古代的大凌河水势磅礴,其流经地区水草丰腴,林木繁盛[1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濡水》云:“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魏土地记》云:“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经孤竹城西,右会玄水。”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云:“卢龙有玄水,今名青龙河。”施丁主编《汉书新注》云:“玄水:今青龙河。濡水:今滦河。”所以在孤竹国地域内,滦河及其第二大支流青龙河成为给养当地人民生存的重要河流。特别是青龙河,其发源于承德市平泉县抬头山,流经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秦皇岛,在卢龙县城西南汇入滦河,贯穿了孤竹国大部分疆域,为当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水源。
三、孤竹国的农业文化
孤竹国时期农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不仅开垦土地,改良培植农作物,研究农业灌溉技术,同时还大量驯养野生动物,畜禽养殖也具有一定规模。
(一)耕种文化
大量出土文物,如辽宁喀左县北洞青铜器窖藏、河北卢龙阚各庄商代晚期墓、天津蓟县张家园、北京平谷县刘家河等,均证明孤竹国早期已经是定居的农业。周文王时期,经济上实行“康功田土(开垦耕地)”、“耕者九一(九分而税其一)”等惠民政策,推动了耕种文化的发展[12]。
1.主要作物
冬葱、菽。《东周列国志》记载,菽和冬葱是孤竹人栽培成功的。菽,即大豆;冬葱,即大葱。《吕氏春秋》中对“菽”的形状进行了描述:“得实菽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为簇,多枝数节。”《春秋考异邮》云:“菽者稼最强。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菽者,众豆之总名。然大豆曰菽,豆苗曰霍,小豆则曰荅。”菽是孤竹国特产,是夏商时期孤竹人由野生豆类培育而成。《管子·戒》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即齐桓公伐山戎,灭孤竹,把菽和冬葱的种子从孤竹国带回了齐国耕种,从此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成为中原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山戎迅速强大,侵占了孤竹国北部大部分领土,最后孤竹国沦为山戎的附属国,孤竹特产就成了山戎特产。
桑麻棉。从古代的人物绘画或雕刻中,可知夏代已用丝绸、麻布作衣料,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商周时期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卢龙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的几种商代纺轮(石纺轮、陶纺轮等)、辽宁朝阳早期西周墓发现的织锦残片等,都证明在孤竹国早期纺轮就已出现。纺轮是用作纺线制作衣服的工具,说明当时孤竹人已具有纺织技术,同时桑麻棉的种植也非常普遍,孤竹人收获桑麻棉后,用纺车织成粗布,剪裁缝制成宽袖大衣。
2.主要农具
金属农具(如商代青铜器“钱”和“铸”等都是用来除草的农具)在商朝早期的使用为数不多,因其便于携带和保存,又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金属农具逐步演变成为稳定的金属铸币。从出土的文物看,商时期的孤竹人农业生产主要使用的农具是石器,也有骨器和蚌器。石器中有石斧(伐木开荒工具)、石犁(犁地打拢工具)、石刀(收割、砍伐、防身工具)、石镰(收割、除草工具)、石铲(翻地工具)、石锛(木料加工工具)等。北京地区最早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遗迹发现于今房山段拒马河右岸的镇江营一带,在这里出土了夏商时期鹿角镢等农业生产工具,证明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木器和骨器等。西周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木器为主,在今房山区刘李店、董家林村出土了殷周时期的石镰和石杵。春秋时期,犁、镢、镰、铲、耙、镐等铁制农具开始用于农业生产,出现了畜力犁。孤竹国历经了夏、商、周、春秋四个历史朝代,每一朝代的农具在孤竹人中都有广泛使用。
3.农业灌溉排水技术
关于农作物的灌溉与排水,当地居民除充分利用滦河流域和青龙河流域的有力水源外,在距离河流较远地区和干旱季节,人们发明了农耕灌溉技术,在水涝地区发明了排水技术。据《卢龙县志》记载,孤竹人在父丁(孤竹国第七任国君)时代就发明了通河井和渗水井。通河井是在河边挖的井,井水是地下的河水渗透而来,经过沉淀过滤后变成饮用水,同时用于灌溉。在低洼容易积水的地面发明了渗水井,将排不出去的水渗到地下,并在透层中填充砂石、陶瓷碎片等进行过滤,成为饮用水,也用于灌溉。在卢龙县沈庄龙虎寺、东阚各庄和八里塔等殷商遗址均发现有水井遗迹,及汲水工具陶罐和木桶。卢龙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的拥有3 000多年历史的商代木桶被称为“世上保存年代最久、最完整的一对商代木桶”,也证明孤竹国农业灌溉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二)畜牧文化
孤竹时期的畜牧业已比较发达,居民大量饲养牲畜。《逸周书·王会第五十九》记载:正北“……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孤竹国向周王朝进贡的方物是“距虚”,说明距虚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地方特产。距虚不仅仅是贡物,也用作商品交换、驮运和农耕生产。孤竹国民间大量饲养距虚,距虚是马和驴的后代,说明当时马和驴也有大量饲养。同时,在卢龙、滦县、昌黎、迁安等地孤竹国遗址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其他畜禽的骨骼,如牛、羊、鸡、犬、猪等,孤竹人饲养猪、羊、犬、鸡,主要是肉、蛋等食物来源,也用于祭祀。
在迁安市于家村汉墓出土的成套的生产生活用具和畜禽的陶制模型,如陶楼、陶房、陶仓、陶井、陶磨、陶碓、陶马、陶牛、陶羊、陶猪、陶鸡、陶鸭、陶盆、陶碗、陶酒杯等,生活所用一应俱全,充分反映了当时孤竹大地畜禽养殖的繁盛[10]。
(三)渔业和采摘文化
孤竹国南临渤海,境内又有诸多河流,在原始的青龙河上游、滦河下游地区,保存着很多的原始森林、草地、河滩、沼泽,生长繁衍着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和水生生物,为人们提供了优良的生存资源,也为渔猎经济和采摘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场所。在1974年卢龙县城南阚各庄村的滦河沿岸发现的“商朝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石器,青铜器上的鱼龟纹、石器渔网坠等,都证明当时渔业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周列国志》中记载了齐桓公为救燕而伐山戎、孤竹时,孤竹国军民在“濡水”以水抗拒齐军的战事,众横竹排,用于战争,竹排在不战时用于渔猎。
总之,孤竹国时期,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物种植、畜牧生产及渔业等都有较大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农业生产技术。随着农业的发达,逐步出现了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为华夏文明的萌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宋坤.中国孤竹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李学勤.试论孤竹[J].社会科学战线,1983(2):202-206.
[3]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2):10-34.
[4]王士立.古域唐山与儒学流布[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50-53.
[5]康群.孤竹与朝鲜[J].河北社会科学论坛,1996(3):61-63.
[6]孟古托力.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J].学习与探索,2003(3):117-123.
[7]苗威.关于孤竹的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6-80.
[8]刘子敏.孤竹不是游牧民族[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27-30.
[9]王玉亮.孤竹地望试析[J].廊坊师专学报,1998(4):6-10.
[10]朱玉环,田军民,洪娟.试论孤竹文化[J].中州今古,2002(6):50-56.
[11]王禹浪,孙军,王文轶.大、小凌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历史文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83-88.
[12]王士立.伯夷、叔齐评说[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11):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