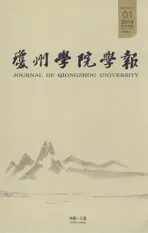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2014-04-07于国华
于国华
(1.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134002;2.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期的判断,以古诗产生于桓灵时代的观点最为集中,梁启超①梁启超“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见梁启超著《中国美文及其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 页。、罗根泽、袁行霈②袁行霈认为“《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参见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 页。、李炳海均持这一观点,而木斋先生的著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经过详尽考证,明确地将《古诗十九首》归入建安时期作品,并进而提出其为曹植甄后作品的结论,引起学界的震动。③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 页。对此,张朝富在肯定木斋先生学说价值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考:“五言诗在曹魏这里大兴,借鉴比独造说似乎更为可能些。”并进而认为,“最为可能的是,它们还处在五言诗的早期阶段——汉代”[1]据此,若想探讨《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考察建安之前的汉灵帝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五言诗创作的状况便有了必要。
汉灵帝统治时期之前虽有五言诗作出现,如班固的《咏史》,然其质木无文,不符合五言诗成立的基本特征。④根据木斋师观点:五言诗成立是成立则是群体的、必然的写作,其中的本质特征是“穷情写物”,外部特征是逐渐摆脱散文写法,虚词渐次退出,由单音词为主渐次转向双音词为主的句式,五言音步初步形成。参见木斋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 页。古诗十九首被称作“五言之冠冕”,是否能在汉灵帝时代产生,灵帝时代文坛盟主蔡邕具有标志性作用,因此,本文以蔡邕为中心考察汉灵帝时期产生五言诗的可能性。
一、蔡邕在汉末文坛的地位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精通辞章、天文、音乐等。蔡邕在当时文坛地位极高,实际上处于当时文坛盟主的地位,至少应该承认当时整个文坛没有人的地位能够超过蔡邕。这可从以下得到印证:
(一)蔡邕文学创作丰富
根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创作了“诗、赋、碑、诔、铭、赞”等文学作品“凡百四篇,传于世。”[2]1980其中仅存世的碑铭就有约50 篇,涉及当时的名士、贤达、师友等人,所作碑铭,在当时声名最著。刘勰赞美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3]
(二)蔡邕在当时文化传播中作用显著
蔡邕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从《论衡》与熹平石经二事中可见一斑。首先看《论衡》的传播。《论衡》最初在中土并无传播,蔡邕入吴一见倾心,大加称赏,带入北方,由此才传播开来①根据《后汉书》记载:“(王)充所做《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宋]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又据《太平御览》:“王充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见[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次,为了避免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蔡邕与杨赐、马日磾等人,一起校定六经文字。蔡邕亲自书丹,镌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2]1990观视及摹写者能达到每天千余辆,一方面是因为刻写内容的重要,另一方面应该有蔡邕书法的影响。同时,此次事件,扩大了蔡邕在士人的影响也是势所必然。
(三)蔡邕在当时士人中的地位
正因为蔡邕对当时文士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当时的儒士典范陈蕃、李膺竟然依据其品评而定高下。据《世说新语·品藻》中记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4]蔡邕对当时文人多有交游和提携之处,后来在建安文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曹操、孔融、王粲等人均受其沾溉。蔡邕死后,“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当时大儒北海郑玄听说“旷世逸才”蔡邕死了,感叹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2]2006既是对他史学成就的肯定,又是对他在当时文人领袖地位的认可。
由于蔡邕在当时有着文坛领袖的地位,虽一生经历四朝,汉灵帝(168 -189)在位,蔡邕卒于192年,可以推断蔡邕的主要成就在汉灵帝统治期间已经取得,因此以蔡邕为中心便可探知汉灵帝时期五言诗创作的环境、文学创作成就等情况。
二、从蔡邕对鸿都门学的批判看《古诗十九首》创作的环境并未成熟
(一)鸿都门学的设立
出于自身的爱好,同时也是为了培养自己独立于士人集团的政治势力②张新科认为“鸿都门学并不是一个文学集团,实质上它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政治集团。”见张新科《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文风的转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 期。,汉灵帝设立了鸿都门学③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千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2 页。,鸿都门学发展迅猛,人数“至千人。”官职“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1997甚至后来“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2]2499
(二)蔡邕等人对鸿都门学的反对与《古诗十九首》创作的环境
作为与经学无关与教化无关的纯文学艺术集团,鸿都门学从设立就被士集团激烈反对④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千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2 页。,其中蔡邕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后汉书·蔡邕传》载《上封事陈政要七事》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非以教化取士之本”。因此对鸿都门学中诸生颇为不满,认为其中很多人“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主张“上方巧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宜且息心,以示忧惧。”“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蔡邕传》载《对诏问灾异八事》)由此可见,即使在文学成就斐然,书法音乐等艺术皆为一时之俊的蔡邕看来,文学的地位仍然是“小能小善”无法与“通经释义”相提并论,甚至“有类俳优”,主张“宜且息心”,而在《古诗十九首》中所表达的内容为男女相思、离愁别绪、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或早建功业,均无关教化,有的诗作中甚至出现了“空床难独守”这样的女性心理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渴望建立功业的诗作中,也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式的儒家理想无关,与“匡国理政”无关,而是在人生如寄背景下,不甘贫贱的“先据要路津”。
由鸿都门学在当时所受到的反对可以看出,在灵帝时代,经学仍处于统治地位,一切以“匡国理政”为准绳,蔡邕在对比了文学艺术与经学之后得出“通经释义,其事犹大”的结论,由此可见,即使像蔡邕这样热衷创作且大有成就的人,亦未完全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境况下,是不会大量出现以个人体验为中心,与教化疏离的诗作,如果出现了这类诗篇,必定会被赞扬或被批判,作为特出于时代的作品,不被人关注是不可能的。
三、从蔡邕的文学创作看灵帝时期五言诗创作尚处于发生阶段
(一)蔡邕诗赋创作的比较
从整体上看,蔡邕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是广泛的,但从具体文学体裁来看,蔡邕诗歌的内容与赋的内容相比题材内容狭窄的多,蔡邕的赋作,根据佘红云的统计可分为7 类,包括言志、述行、爱情婚姻、山水景物、咏物、人物、乐舞游戏。①言志:《释诲》《九惟文》《吊屈原文》;述行:《述行赋》;爱情婚姻:《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山水景物:《汉津赋》《霖雨赋》;咏物:《笔赋》《团扇赋》《玄表赋》《蝉赋》《伤故栗赋》;人物:《短人赋》《警师赋》;乐舞游戏:《琴赋》《弹棋赋》”。见佘红云《蔡邕思想及其辞赋碑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22 页。这是符合汉末赋发展的潮流的,尚学锋认为:“从汉末开始,赋家的注意力逐渐由政治转向人生,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在心灵。赋中的思想由儒家的群体意识转向道家的个体意识。人的情感、欲望、个性以及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成为作品的核心内容。审美视角由客观世界转向主观感受,由表现类型化的情感转向个性化的内心体验,由描写形象转向创造境界”[5]蔡邕的个别赋作更是如此,正如刘桂华所说:“汉末文坛巨匠蔡邕的恋情赋独树一帜,蔡邕在赋中热情地歌颂爱情,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蔡邕的恋情赋对美女的描写细腻生动,对爱情心理也刻画得淋漓尽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赋中以常人的口吻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丝毫不带道德教化的色彩。”[6]
然而,在蔡邕的诗歌中,却紧守着对友人和官员德行的赞颂,(《答对元式书》《汉酸枣令刘熊碑诗》)表达隐逸之情要依靠辞赋《释诲》中说出。诗歌形式虽有五言六言,但是仍以四言为主。体现出对从形式到内容的节制,这种自觉的节制来源于对诗体经典的敬畏,通过统计蔡邕搜集的琴诗,高长山认为“汉乐府琴曲歌辞以四言和骚体为主,基本见不到五言。无论是四言还是骚体,都是沿袭原有的诗歌样式,没有参与诗歌形式的演变。汉乐府琴曲歌诗对于诗歌样式的演变没有发挥推动作用,相反,倒是一种阻碍。”[7]
(二)蔡邕时代诗歌创作的特征
在蔡邕时代,诗歌形式的大规模演变并未发生,诗歌抒发与教化疏离的个人情感的传统也并未形成。
在两汉时期,诗歌创作对文人来说是重要的、庄重的、甚至是神圣的,“作诗在中国古代,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诗的本质在于,作诗者都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诗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学。”[8]其主要的原因是在汉代,《诗经》被完全经典化了。《诗经》的作者被认为是圣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9]王式“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也被时人认可,当时,人们普遍“以《三百五篇》当谏书”[10]。因此,“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11]。美是美教化,刺为托诗以讽谏。均指向了社会政治,与自我生命欲望表达无关。因此,整个汉代儒士众多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很少,进行诗歌创作的更是微乎其微,很难得到技术上的训练和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产生“五言之冠冕”是不符合逻辑的。
(三)从蔡邕的五言诗创作看汉灵帝时代的五言诗成就
具体从五言诗创作情况看。考察灵帝时代,仅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诗》(其内容不出托诗以怨,美刺二端,且借助赋体打破诗的经典束缚而写出)与蔡邕《咏庭前石榴》。(蔡邕另有五言《饮马长城窟行》,是否为其作品,被人广为质疑,兹不论。)而《咏庭前石榴》具体如下: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12]
该诗在历史上地位很高,《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蔡邕的《咏庭前石榴》诗应该是我国咏物诗史上的第一首五言咏物诗。”[13]诗歌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颇具《诗经》风味,绿叶丹荣、翠鸟时来,仅仅是刻画了安闲美好的眼前之景,环境并未对翠鸟的生存形成压迫,最容易拨动心弦的“幸脱虞人机”之情表现得苍白无力,虽为“托物寄怀”但自我情感的抒发极为收敛,其音步第一句1112、第九句11111 仍为散体,体现出五言诗未成熟时期的青涩。
与之相近的诗篇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14]
在《庭中有奇树》中,“奇树”“华滋”并不仅是情感发生的环境,而是直接参与了抒情,“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庭树之花成为思念与深情的象征,然而却遇到了阻隔,“路远莫致之”而那“盈怀袖”的馨香,形象地传达出思念之情的浓烈与美好,最后一句再增一层转折,“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在抑扬之中,点出长久别离这一思念之因,而别与花相连,也使花与情的发生、发展的关联充满了想象的空间,耐人寻味。虽有散句,但是形成了偶对偶,散对散的整齐结构。由此可见,《咏庭前石榴》与《庭中有奇树》相比,艺术上是不成熟的,与之同时稍后的孔融《临终诗》也采用了五言的形式,但其被称为“类箴铭”,由此可见当时五言诗的艺术成就仍然较低,处于创作技巧的摸索阶段。由此导致的是,作家对这一诗体不重视,不仅试做作家作品数量少,诗作产生后,几乎无人回应,很少有文人进行仿作,因此,仅仅是五言诗的发生,而不是成立。①木斋先生认为“发生仅仅是个人的、偶然的写作,成立则是群体的、必然的写作。”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任何一种诗体的成熟必然经过大量的练习,经历一种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在汉灵帝时代,写作抒发个人情感的五言诗并没有成为风尚,五言诗创作技巧也过于粗糙,具有探索期的明显特征,而与《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之冠冕”的特点有着明显地区别。
四、从蔡邕时代的文人出处看作者不可能怀玉自弃
《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在当时是特出于世的,虽然《文选》在选录《十九首》的时候,只是标明是“古诗”表明已经无法考知作者。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五言之冠冕”等评价,体现了人们对其抒情性、以及艺术成就的直观感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在五言诗已经充分发展的南北朝时期的评价,假设《古诗十九首》真的产生于经学尚未完全坍塌的汉灵帝时期,其震撼更是可想而知。且《古诗十九首》为整个汉魏时期五言诗的冠冕,必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提升,产生于整个汉魏时期中五言诗写作的最巅峰时代。同时,其作者也必然为最巅峰时代之最巅峰之诗人。因此,是《古诗十九首》如果产生于汉灵帝时代,其作者姓名很难被掩盖的。理由如下:
(一)察举制度的网罗
东汉时期仍然察举制度,重视对士子文人的网罗。②“公卿等也都以辟士相尚,一般名士还有以不即时应命为高的风气。”也就是说,十九首若是东汉后期下层文人所作,其名声是难以逃脱的,因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视名声的时代,即便是作者有意避名、避世,也是毫无可能的,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关注着每个士人的品行,以便推荐。推荐得当,则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否则,则有失察之论,而郡望谱牒的重视,又使每个士子文人都在谱牒的网罗之中。”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具体到汉灵帝时代,在鸿都门学设立的时期,能创作《古诗十九首》之类五言诗文人,因其文辞,必在举荐之列,这在鸿都门学中仅通一艺便被荐举,甚至短时期内发展为千人规模可见一斑。如若在其它时期,也会因其内容不合经学之时宜而被批判,或者会因其艺术成就而被称赞,湮没无闻的可能微乎其微。况且,蔡邕作为文学家同时有“继成汉史”之志。被时人称赞为“旷世逸才,多识汉事”[2]2006。就连当时大儒北海郑玄听说蔡邕已死,不禁感叹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借用梁启超证明《古诗十九首不可能》产生于西汉的话:“枚乘、苏、李若有这种好诗,刘向似不容不见,见了似不容不著录。”[15]若汉灵帝时代有如此好诗,蔡邕似不容不见,见了似不容不著录。
(二)文人激扬名声的风尚
从文人本身来讲,两汉魏晋时代,激扬名声成为风尚。“士人的集团形成之后,处士的声誉已远超过实际的禄位。”(王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创作《古诗十九首》这样高水平的诗歌,无疑也是得名的一种快捷方式。即使是羞与当权者为伍的“士子”,也同样注重得名。激扬名声是当时士子的普遍行为①《后汉书·党锢传序》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激扬名声,名与诗必然相伴,不会遗失姓名而被目为“古诗”的情形。况且在《古诗十九首》中,有的作品有着建立功业的思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有“策高足”“据要路津”思想的文人,若创作出古诗十九首这样有着五言冠冕成就的诗作,又怎会失其名姓呢?
(三)文人交游的自由
即使不被朝廷认可,不入儒士品题,尚可以自荐于名士之门,比如蔡邕这样大文学家参与奖掖后人,“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16]495“建安七子”中年纪稍大的孔融也曾受过蔡邕的影响,蔡邕长孔融20 岁,《后汉书·孔融传》中说孔融“与蔡邕素善”。蔡邕与建安时期的曹操交好,《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曹操素与邕善。”“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阮隅、路粹是他的弟子。蔡邕只是当时文士交往的一个代表,乔玄、许邵都有与未成名士人交往的事例。综上,以《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其作者无论士庶,必然会名显于世。
五、汉灵帝时期的文化状况为《古诗十九首》的发展所做的准备
汉灵帝时期虽然没有产生《古诗十九首》的可能,但是为五言诗的繁荣以及《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做了大量的准备。
(一)汉末乱政为五言诗的“穷情写物”的个性化抒情打破了束缚
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爆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党锢列传序》)。杜洪义先生说过:“党锢之祸将汉末政坛上的士大夫精英殄灭殆尽,‘海内涂炭,二十余年’,使至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传统经学走向衰落,士人干政的势头亦由此转向。”[17]同样使当时士人以经学干政的热情大受挫败的是汉灵帝的西邸卖官和鸿都门学,根据《灵帝纪》记载:“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西邸卖官使为官不再神圣,有时甚至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同时,鸿都门学使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依靠尺牍、书法等与德行无关的本领入仕。使传统的儒学士大夫对不再神圣的统治体系无比失望。
“在对政治和自己曾经倾心的经学失望之余,汉末文士开始尝试着在个性情感的自由舒放中寻找精神的愉悦。”[18]其中,著述成为抒发个人情怀、实现自我超越的常见方式。“及党事起,(应)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2]1069一斑窥豹,当时文人选择的主要还是熟悉的传统文体,骚赋为主,但是随着情感的解放,诗作为经典地位的动摇,对诗歌创作的敬畏、对四言诗形式、对美刺二端的坚守都变得脆弱起来。诗歌在魏晋时期的抒情传统的确立也就呼之欲出了。孙明君发表了《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一文,认为“魏晋时代建安士人不仅突破了两汉经学家的诗教说,使原始儒家所提倡的“诗言志”这一诗学理想得以落实,而且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实现了人的再发现与自然的再发现,其诗歌写出了生命主体对社会政治之情,以及生命主体对自然世界之情,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亲情与友情,为中国文人诗苑开垦出一片片沃土,使中国诗歌体类之建构宣告完成”。[19]而个人情怀的抒发,必然会促进诗歌由板滞的四言、向更富于变化的五言的演进,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二)纸张对简帛的逐渐替代促进了五言诗的勃兴
在汉灵帝时期,正处于简帛与纸张的转换过程中,文人仍以简帛为主,来记载知识。以蔡邕为例,《博物志》卷六记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万卷中的部分即需要数车,可见蔡邕的藏书仍是以简帛为主,但纸与简相比的方便实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到了建安年间,纸已经成为公文中的用具,曹操曾下《椽属进得失令》命令诸椽属侍中、别驾用纸函进得失,当时也有了专门抄书的职业,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16]1249虽然史书中仍有简帛应用的记载,但更多地体现一种尊贵。《三国志·魏志》中记载曹丕用素书《典论》和诗赋给孙权,而同时给大臣张昭的却是以纸为材质。素贵纸贱,说明当时的纸已经有了很大的普及。有了更加便利的纸张作为载体,文学的发展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此査屏球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书信体发达的创作趋势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一个高潮,文人书信明显增多。这种创作活动给文坛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的抒情性大大增强了。纸的流行带来了文字交往的方便,具有书信功能的交往诗也随之流行起来。如建安七子间交往诗及同题之作尤多”[20],而当时的书信与同题诗作,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大量地采用五言诗的形式,成为时尚同时得以相互借鉴,积累五言诗的创作经验,使其得以在短时间内得到飞跃。
总之,汉灵帝时期并无产生《古诗十九首》的可能,但其时经学衰微,使诗的尊崇地位得以打破,个性化抒情得到推崇,纸张的运用逐渐广泛又使文学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文人之间的学习与借鉴更加便利,在加之曹操主持下清商乐的兴起,共同促成了诗歌由四言向五言的转换,从而五言诗快速走向成熟,在此基础上,作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才有可能出现。
[1]张朝富.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J].中国韵文学刊,2013(2):57 -62.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
[4][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尚学锋.汉末赋风新变与道家人文精神[J].中国文学研究,2000(3):22 -27.
[6]刘桂华.汉代赋史上的一朵奇葩一浅议蔡岂的恋情赋[J].济南大学学报,2003(3):50 -52.
[7]高长山.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2):68 -71.
[8]王志宏.刘项为何要作诗[N].中华读书报,2011 -11 -16(03).
[9][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300.
[10][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90.
[11][清]程廷祚.清溪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36.
[12][汉]蔡邕.翠鸟[O]//[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光绪善化章经济堂刊本.
[13]于志鹏.宋前咏物诗发展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4][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中):卷二十九[M].[唐]李善,注.韩放,主校点.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302.
[15]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19.
[16][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54.
[18]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21.
[19]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J].北京大学学报,1996(6):43 -50.
[20]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153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