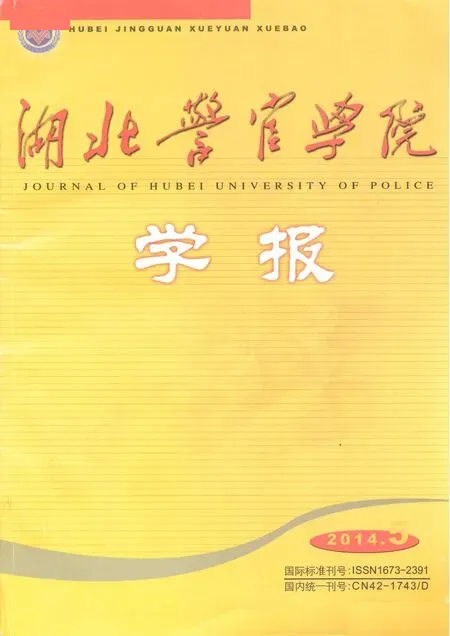媒体与司法二元侦查问题探究
2014-04-06孙琳琳
孙琳琳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媒体与司法二元侦查问题探究
孙琳琳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因各自的职能分化在言语竞争方面存在相互排斥性,但基于司法透明、公正的需要,司法机关又不得不借助媒体的力量拉近与社会公众的距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媒体言论层次升级的媒体事实侦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其与司法机关的侦查在维护国家法治秩序的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现有的法律侦查体制内仍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规制。
媒体侦查;司法侦查;二元侦查
新闻媒体是当今信息传递最广泛、最迅速、最灵敏的途径,是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最有效的渠道。[1]媒介传播呈现出高度快捷性和广泛参与性,使得新闻媒体无处不在。在“信奉自由,忠于真像”的职业追求之下,媒体工作者大多能本着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对实时新闻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但也存在为吸引公众眼球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刻意无中生有或者歪曲事实制造假新闻的现象。
媒体参与刑事侦查活动的报道已属常态,但慎重思量一番后,有许多问题令人深感忧虑:媒体应如何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以及在不泄露侦查秘密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如何将涉案情况向媒体公开?两者之间采取怎样的处理原则,才能做到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功能与保持警媒关系良性互动之间的理性平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但当下对此并无统一而权威的定论。
一、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一)内在功能上的附着与排斥
媒体与司法机关在内在功能层面,既具依赖性亦具排斥性。媒体绝非一个单纯运作的主体,其具有广泛的信息传播功能。姑且不论新闻传播主体有着怎样的企图,媒体在任何时候都率先专注于信息的新闻价值。正因如此,媒体界对司法体制内的新闻异常感兴趣,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反响强烈的热门案件。侦查公开一般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实现,报道犯罪活动的动向、犯罪的形态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都可以为民众了解犯罪动态,防止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报道侦查信息,也有利于对不稳定分子起到威慑的作用。它们相辅相成,具有一定的附着性。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媒体报道规定的缺位,及大量刑事案件在媒体的过度披露下呈现出的“司法未决、舆论先判”现象,成为学术界竭力声讨媒体权利扩张的理由。司法机关对此忧心如焚,以致在利用媒体时倍加防范。首先是对媒体监督职能的防范。司法机关总是对过度的媒体监督感到惶恐不安。在正常的侦查体制下,公权力机关出于侦查效率的考量,往往更愿意保守程序秘密。[2]尤其对实务中一些影响广泛的案件,需要以专门的司法程序、独立的法律逻辑进行权衡判断,所作的裁断虽符合法律准则的要求,但未必为媒体视野下的公众所接受。尤其在当前对于媒体报道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无确定结论的情形下,即使先不质疑这种正当性,单是媒体报道出的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就与公众的思维存在出入。如震惊一时的云南李昌奎案件的再审改判,法官内心的法律信念理当无可责难,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攻势面前,其言行难免谨慎之中暗藏无奈,无奈之余屈从“民意”。此外,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案件的进展,其非理性或半理性的报道方式难免不反作用于司法,或将一些猜测性、评论性的意见夹在枯燥的叙述之中,或在报道中重者轻泛化、轻者重点化。总之,超前的媒体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曲解司法机关的办案方式与办案理念,不正当地引导公众的视线,进而影响到案件的后续侦查与审判工作。由此,司法机关与媒体之间又呈现出排斥关系。
(二)外在窗口的公信力与确定性
所谓公信,即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度。笔者此处所讨论的公信,包含权威之意。媒体与司法机关都拥有各自的权威体系,具体表现为两者在行业内的威望、信誉。当两者共同指向司法案件的某一特定对象时,就不再是谁与谁的权威比较问题,而是一种处理结果在外部的公信度和确定性问题。司法处理并不完全依照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进行,甚至在有些处理方式上与社会主流观念相悖,即便如此亦能名正言顺地彰显于法律文本之中。另一方面,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正义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思维方式下的正义思想。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方式提出质疑,是行使监督权使然。一种质疑大则推进制度改革或体制创新,小则纠正一种偏见或错误。然而,案件在司法程序之下必然有一个终局性结果,该结果经历法律处理后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即便媒体不予认同、公众尚存疑虑,亦不能轻易动摇这一结果。确定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既是对当事人实体权益的保护,也是防范司法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拖延办案的有效举措。但在确定案件结果前有必要对民意加以考虑,却又不能盲目屈从于民众的激情。
二、“媒体侦查”与司法侦查的二元交互作用
司法侦查机关与媒体不但在言论上存在竞争关系,在犯罪侦查领域也存在部分竞争关系。笔者认为,既然是竞争,就不存在隶属,仅存在一种职能上的交互影响关系。“媒体侦查”受司法机关的制约,表现为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需要“媒体侦查”的服从,其依据在于前者有国家立法的明确保障,而后者欠缺法律保障。当“媒体侦查”先于司法侦查,引发社会的合理性质疑时,公安司法机关才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部署和开展侦查工作。对于“媒体侦查”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法律应否对“媒体侦查”的范围、形式以及限度作出规制?笔者认为,当前较为理想的规制形式是,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已经正式侦查的案件,媒体再进行事实侦查则是禁止的。此时,媒体只有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向其提供破案线索的义务;对于已经发生但公安司法机关尚未介入的案件,“媒体侦查”应以不影响日后的正式侦查为前提。对于司法机关怠于行使侦查权的情形,媒体可以在事实侦查的限度内,以报道悬疑的形式督促公安司法机关履行其法律侦查职能。
在笔者看来,一种理性而明确的认识远比法律的硬性条框更具实践的空间,且这种界限能否在现行司法界与媒体行业形成共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实施侦查活动的主体,除专门侦查机关外,其他主体均处于一种配合调查的地位,竞争侦查的现象多发于两个同时具有侦查职能的机关之间,法律对此也有调和之规定,很少出现非侦查机关盘剥侦查机关侦查权之举。如此,只需将观察的重点置于“媒体侦查”对司法侦查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不利影响之上。就“媒体侦查”的实施主体而言,媒体工作者一般受过专门教育,其自律意识通常是具备的,在受媒体行业职业道德约束的同时,对国家法律法规有一定的了解。当新闻媒体的非专业性侦查无法深入到案件的实质要害时,一般应本着审慎的态度,暂停“媒体侦查”转而求助于侦查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抑或是配合侦查机关的活动,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下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像。毕竟,媒体机构也有防止侵害法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社会义务。
三、结语
为确保案件侦办过程的透明性,在现实的侦查工作中,我们时常发现媒体记者一同跟随司法侦查人员进行侦查取证,更有甚者不惜冒生命危险参与凶案对峙现场的过程拍摄。这表明,媒体与司法联合侦查模式已经运用于实践,媒体与司法的二元侦查终将向着服务于国家法治的方向靠拢。尽管媒体作为一个单纯的职业,其所实施的侦查是受限制的侦查,且事实侦查并非媒体的本能,但媒体最终需要借助它向社会打开一扇窗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目睹到这扇窗口所展现出的社会百态,这也是媒体行业的固有使命。当然,面对各种忧虑,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有必要构建共识性机制,在配合与监督之中共同推进媒体事业与法制事业的协调发展,使媒体与司法二元侦查模式发挥其积极效用。
[1]简海燕.媒体报道刑事侦查活动的法律限制[J].河北法学,2008 (1).
[2]施鹏鹏.论侦查程序中的媒体自由——一种政治社会的解读[J].东南学术,2013(1).
D631.2
A
1673―2391(2014)05―0039―02
2013-12-10 责任编校:边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