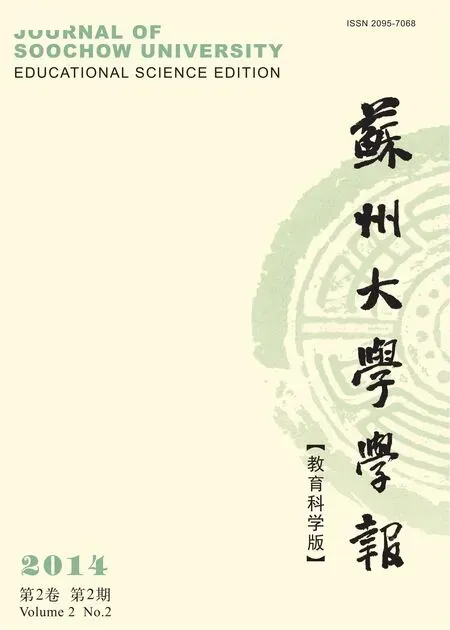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
——主体、过程与特点
2014-04-05孙进
孙 进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 域外比较
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
——主体、过程与特点
孙 进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在我国对德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对教育政策的介绍不少,但是对其教育政策制定机制的分析却十分鲜见。本文分析了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机制,指出其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联邦和州层面的官方机构、非官方的机构、联邦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机构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遵循的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上下互动与合作的模式。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特点在于:参与主体多元,注重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机构的参与,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特点。
德国教育;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形成;教育政策制定机制
教育政策是指由“执政党和政府制定与颁布的用以指导、规范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切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上教育政策不仅包括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规章,而且还包括了教育法律”[1]4。教育政策既是一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生成和改变着教育制度、影响着教育实践,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历来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点。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埃德蒙・金曾在《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一书中表示:比较教育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教育政策的研究。[2]7
在我国针对德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对具体教育政策的介绍和分析不少,但是对于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机制的分析却十分鲜见①吴遵民著《教育政策入门》一书在第六章介绍了“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机制”(吴遵民:《教育政策入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2-102页)。该章内容与赖秀龙刊于《现代教育管理》(2009年第11期)的文章《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启示》近乎一致。两者均没有采用德国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所引用的中文文献存在老化问题。此外,文中对一些关键机构和法律的概念翻译以及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也很值得商榷。。为了弥补我国在德国教育研究方面的这一缺陷,本文在下面重点分析一下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机制及其特点。
这里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16个联邦州组成。根据德国宪法《基本法》(Grundgesetz)的规定,各联邦州享有广泛的文化主权,可以自主决定本州的文教事务,联邦的权限被限定于一些特定的涉及到全国的教育事务(如科研资助和教育补助等)。与德国这种联邦制结构相适应,德国在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形成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教育决策体制。
一、德国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
研究者认为,西方国家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通常可分为官方与非官方两大类。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属于国家层次的,主要包括国家元首、国会、政府首脑、执政党、内阁;第二个方面是教育部长、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构;第三个方面是负责考试、课程设置与发展等活动的其他教育机构;第四个方面是咨询机构;第五个方面是中介组织。非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主要包括利益集团、在野党派和大众传媒组织。[1]9这一分类也适用于德国。因篇幅所限,本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德国官方的教育政策制定主体。
(一)德国联邦层面上的教育政策制定机构
联邦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定机构主要有联邦总理及联邦政府、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总统。他们在立法方面的关系是:联邦总理及联邦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向立法机构——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法律草案由其进行表决。据统计,德国大约75%获得通过的法律都是出自政府方面的提议。[3]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均有权提出法律草案。从这二者的关系来看,联邦议院是最主要的立法机关,有些法律需要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有些法律则不需要。德国联邦总统则负责最终签署法律使之生效。此外,当涉及到非法律类的教育政策时,联邦教育与科研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可以独立或者和各州政府合作以行政规定或者行政协定的形式出台教育政策。
1.联邦总理与联邦政府
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是联邦政府内唯一的民选职位。联邦总理有权独自选定部长作为最重要政治部门领导,也有权罢免他们。联邦总理还负责确定联邦各部的数量及其职责范围。他拥有制定纲领方针的职权(Richtlinienkompetenz),即有权规定政府工作的重点。联邦各部负责将联邦总理确定的纲领性方针政策加以具体化和落实。在联邦总理所确定的路线框架内,联邦政府的各位部长独立负责各部的事务(Ressortprinzip)。除了参与立法之外,联邦政府可以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行政规章(Verordnungen)。[4]
现届联邦政府包括15个部,其中负责管理教育事务的主要是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其前身是成立于1969年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该部于1994年与当时的联邦科研与技术部合并而成为现在的机构。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由一个中央部门(Zentralabteilung)和7个分部门组成:第1部门负责战略和基本问题;第2部门负责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欧洲与国际合作;第3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第4部门负责科研体系;第5部门负责核心科技——面向创新的科研;第6部门负责生命科学——面向健康的科研;第7部门负责未来保障——面向基础和可持续性的科研。[5]42德国许多教育政策都是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牵头发起的,比如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
2.联邦议院
联邦议院(Bundestag)就是德国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议会党团,并从其中选举产生议会议长。联邦议院的任务是选举联邦总理并通过认可其政策来支持其执政,议会也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来罢免总理。联邦议院的第二大任务是立法。1949年以来,议会共收到10 000多份法律提案,颁布了6 600余项法律,其中多数是关于法律条文的修改。联邦议院的第三大任务是监督政府工作。[6]
3.联邦参议院
联邦参议院(Bundesrat)是各州代表,是除了联邦议院之外的下院,它有义务咨议每一项联邦法律。作为各州在联邦的议事场所,联邦参议院与其他联邦制国家中通常称为参议院(Senat)的下院作用相同。联邦参议院内只有各州政府的代表。各州的表决权以适度的形式考虑到各州居民数:每个州至少拥有三票,人口众多的州最多可以有六票。[7]
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法律的形成过程,但与其他联邦制国家的下院有所不同。《基本法》赋予它两种参与方式。给联邦州带来额外行政开支或替代现行州法律的联邦法规必须获得联邦参议院的认可;联邦议院的法律议案必须得到联邦参议院批准,并使之生效。从这点来看,联邦参议院是享有与联邦议院相同权力的立法机构。目前,所有的法律决议中近半数须经联邦参议院批准。因为联邦法律基本上都由各联邦州的行政机构来实施,所以最重要或花费巨大的法律就会牵涉到各州的行政主权。[7]
4.联邦总统
联邦总统(Bundespräsident)作为国家元首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对外代表国家,任命政府成员、法官和政府高官。他签署法律文件,使之生效。他解散政府,并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提前解散议会。美国总统或其他国家的总统可以对议会颁布的法令行使否决权,而《基本法》并未赋予德国总统这种权力。虽然联邦总统确认议会决议和政府人选,但是他只是在按照《基本法》条文来检验其产生过程是否正确。联邦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联邦总统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联邦大会由联邦议院议员和由16个州议会选出的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8]
除了以上政府机构之外,在联邦层面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还有:联邦—州教育规划和科研促进委员会(Die Bund- Länder- 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orderung,BLK)/共同科学会议(Gemeinsame Wissenschaftskonferenz,GWK),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WR),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KMK)。它们也被称作是联邦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机构,负责在联邦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就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进行协调和合作。
在联邦制改革之前,联邦与州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是成立于1970年的“联邦—州教育规划和科研促进委员会”。在联邦制改革之后,这一机构被新成立的“共同科学会议”所取代。共同科学会议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工作。它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主管科研与资助的政府部长组成,负责商讨和协调同时涉及到联邦和各州的科研资助、科研政策和科学体系的问题。它同时也负责协调德国与欧洲以及国际层面上的科研政策,目标是增强德国作为科研基地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9]
成立于1957年的科学委员会也是联邦与各州之间的一个协调与合作机制,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代表,科学家和公共领域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向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就以下事务提出建议:高校、科学与研究的内容与结构发展,对重要的跨地区科研设施(含大型设备)的共同资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学委员会已经发展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教育政策咨询机构,所提出的许多建议被联邦和各州政府采纳,在德国教育体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科学委员会还负责对私立大学进行机构认证。[5]47
州与州之间最重要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成立于1948年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其任务是处理跨地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政策、高校和科研政策以及文化政策等方面的事务,旨在形成共同的意志和代表共同的关切。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一个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合作和形成共识为全德国的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流动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保证各地生活条件的可比性,代表并促进各州在文化领域的共同利益。根据决策内容的不同,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作出决议的前提条件是全体一致同意、绝对多数或简单多数。在其决议被纳入各州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之前,这些决议仅具有建议的性质。各州的部长有义务尽力将这些决议落实到本州的法律之中。通过在这一框架下的合作和协调,各州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具有了更大的可比性和一致性。[5]44作为各州利益的一个代表机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参与和联邦、欧盟、经合组织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10]
除了以上官方或半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以外,在联邦层面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还有学校及各类社会群体(雇主、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在全国层面的代表机构(工会、协会、联合会等),比如本文在第二部分提到的德国高校联合会(Der Deutsche Hochschulverband,DHV)和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HRK)。
(二)德国州层面上的教育政策制定机构
州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定机构主要包括州议会和州政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州议会可以通过制定学校法对涉及教育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作出规范。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涉及教育目标、教育体制的组织结构、教育管理机构、学校类型、学校的设立和撤销、教师的身份和地位、毕业证书等。州政府及其隶属的行政管理机构通过颁布法律规章和行政规定将学校法中的目标和任务加以具体化和落实。有研究者指出,德国政府更多地是通过行政规定(而非法律)来规范教育事务的。这也是为了提高教育政策的效率,因为教育立法的时间长,而且一旦公布之后修改起来也比较繁琐和耗时。与此相比,通过行政规定规范教育发展更能够灵活地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趋势。[11]176
1.州议会
州议会(Landesparlament)在各州的名称不同,有的州称作州议会(Landestag),有的州称作议院(Abgeordnetenhaus)。不过,他们的职权大体相似,即选举州长,监督政府,制定、通过和修改本州的法律以及审核州的预算等。各州的立法权主要限于文化事务,包括教育、警察以及社区三方面。通常来说,主要是由州政府向议会提供法律草案,不过,州议会也可从自己内部提出法律草案,如通过议会中的党团或者由七名以上的议员提出草案。[12]
2.州政府
州政府(Landesregierung)是一个州的最主要的行政机关,其名称在各州之间存在差异。有的州(如巴伐利亚,萨克森)使用的名称是国家政府(Staatsregierung),有的州(如巴符堡,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使用的名称是部长委员会(Ministerrat),还有些城邦州(如柏林,汉堡和不来梅)使用的名称是“Senat”。州政府由州长和不同的部组成,部的数量各州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在巴符州,有11个部,其中主管教育的有“文化、青少年和运动部”以及“科学、研究和艺术部”。[13]除了参与教育方面的立法之外,州政府及其各部(主要是主管教育的部)可以用行政规定(Verwaltungsvorschrift)的方式形成教育政策。
除了以上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以外,在州层面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还有各社会群体(雇主、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在州层面的代表机构(工会、协会、联合会、委员会等),比如本文将在第二部分提到的柏林地区的教育与科学工会(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GEW),柏林家长委员会(Landeselternausschuss),柏林学生委员会(Lande-chülerInnenausschuss Berlin,LSA),柏林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和工商业协会(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等。
二、德国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
通常来说,教育政策的制定大体经过以下的阶段:第一,分析教育政策问题并确定教育政策目标;第二,设计教育政策方案;第三,对教育政策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第四,选择教育政策方案;第五,教育政策的合法化和公布实施。[2]181教育政策的合法化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教育政策的法律化,也称教育立法,是指国家有关机构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立法活动。这一过程的结果让一部分教育政策上升为法律从而获得更强的法律约束力;二是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即通过国家有关机构对教育政策方案的审定而取得合法地位。[2]219也有研究者将教育政策的制定分为三个阶段: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教育政策合法化。[1]13不论是五阶段划分,还是三阶段划分,都只是研究者的一种理性化的分析模型。现实中的教育政策制定往往复杂得多,一是不一定遵循这里直线递进的步骤,而是充满了循环往复;二是不一定完整地走过每一步骤,也可能越过某一步骤,也可能中途夭折。
(一)德国联邦层面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
在德国,教育法律的制定过程包括:第一,提出教育法律议案,既可以由议会的党团或者议员群体提出,也可以由政府部门(主要是联邦教育与科研部)提出。第二,审议法律议案,联邦议会对法律议案进行审议,认为有问题的话可以要求做出修改。第三,表决与通过法律议案。如果法律议案被联邦议院表决通过,但是联邦参议院却不予以通过,那么,联邦参议院有权要求联邦议会修改。为了协调两个立法机构之间的分歧,也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进行斡旋直至达成妥协。第四,公布法律。通常由联邦总统签署和公布。德国的许多联邦法律都是这么制定的,涉及到教育的比如有《联邦培训促进法》(BaFög)和2008年已经失效的《高等学校总纲法》(HRG)。
非法律类教育政策(如行政法规和行政规定)的制定过程是:教育政策方案的提出,行政法规草案的审查,行政法规草案的批准,行政法规草案的颁布。在联邦层面,此类教育政策主要是由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制定或者牵头推动,不过,因为涉及到各州的负责领域,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和各州进行协调。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在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以“高等教育协定2020”(Hochschulpakt 2020)为例,看看联邦层面教育政策出台的过程。[14]
“高等教育协定2020”这一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国际方面来看,德国作为高科技立国的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要让德国在这一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依靠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不断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15]从国内方面来看,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以摆脱国内就业市场上周期性出现的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另外,受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人口结构的影响,德国高中毕业生中愿意参加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同时,德国各联邦州的文法中学(Gymnasium)的学制由以前的9年制改为现在的8年制,因此各州从2007年开始将相继出现一年有两届高中生同时毕业的情况。①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在两德统一时便实行了8年制文法中学。根据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预测,有的州可能会在双届毕业生出现的年份多出4万名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毕业生。[16]这无疑会给教学资源与学习位置现已紧张的高校带来额外的负担。如果没有相应的辅助措施,德国高校的教学质量势必将会恶化。
为了应对上述国内外的挑战,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经过协商出台了“高等教育协定2020”。正如下面对其出台历程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此项政策的出台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多次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
2005年10月14日,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发表了“有关2020年以前高校新生、在校生和毕业生的发展预测”。根据其预测,到2014年,德国高校的学生人数将由2005年时的198万增加至241万至267万,此后直至2020年将一直保持在这一规模之上。[17]这一预测引起了高校的关注和担忧。
2005年11月23日,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名为《是机会,而非负担:有关〈高等教育协定2020〉的建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必将所面临的高校学生入学高潮仅仅视为是负担,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机会。政府和高校应该把握住这一机会,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保证质量标准、增加教师数量、改善教学条件等)同时提升德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14]
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部长及各州文教部长都对这一决议表示了欢迎。双方于2006年1月25日举行了首次会谈,表示争取在2006年年内议定“高等教育协定2020”。2006年1月27日,科学委员会根据就业市场以及人口发展的需要提出扩大德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建议,并且强调指出各州之间以及各州与联邦之间有必要就此进行合作和协调。②因为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包括高等教育事业在内的文教事务均由各联邦州自主负责。特别是在2006年联邦制改革之后,联邦政府放弃了许多之前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任务(如高校设立、制订《高等学校总纲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科学委员会才特别强调联邦政府不要置身事外,要与各州政府共同应对挑战。6月19日,科学委员会发表了应对高校学生入学高潮所需资金的测算。[14]
在此期间,德国高校联合会以及联邦议会的各政党——绿党(Grünen)、社会民主党(SPD)、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以及自由民主党(FDP)相继针对“高等教育协定2020”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建议。2006年7月10日,民间的高等教育决策咨询机构——高校发展中心(CHE)也提出了如何应对学生入学高潮的行动建议。[14]
2006年5月4日,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温特曼特尔(Wintermantel)女士表示,面对高校学生的入学高潮,德国高校已经无路可退。7月11日,她再次敦促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尽快就“高等教育协定2020”达成一致。10月10日,高校校长联席会议通过了有关“高等教育协定2020要点”的决议。2006年11月20日,联邦教育与科研部部长及各州文教部长就高等教育协定的要点达成一致意见。[14]
2006年12月13日,联邦总理以及各州州长批准了高等教育协定的要点。在此基础之上,联邦及州教育规划和科研资助委员会(BLK)负责起草并于2007年4月24日通过了《联邦及各州有关高等教育协定2020的行政协定》(草案)。2007年8月20日,联邦总理与各州州长正式签署了《高等教育协定2020》。[14]
(二)德国联邦州层面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
在联邦州层面上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上面描述的基本一致,不过在州层面上的立法机构只有一个,即州议会,另外主管教育事务的相应地是各州文教部。下面以柏林的学校结构改革为例描述一下联邦州层面上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
因为受到PISA调查结果的冲击,有关学校结构改革的讨论已经在全国展开,许多州也已经将自己多轨制的中学体系转变为双轨制。柏林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其学校结构改革的,目标也是改变原有的多轨制中学体制,特别是主体中学(Hauptschule)面临着不可维系的困境,每年选择上这类学校的学生比例已经降至7%,而且没有任何改观。所以,改革的目标之一便是撤销这类中学。至于未来的学校应该是双轨制还是单轨制,不同的政党和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主张,人们就此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2009年2月10日,当时的柏林州的教育部长Jürgen Zöllner(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由其部门拟定的学校结构改革方案。[18]按照这一改革方案,从2010/2011学年开始,柏林便只有两类中学:一体化中学和文法中学。其中一体化中学合并了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总合中学。[19]从这一改革方案的提出,到最后得到议会的表决通过,各政党和利益团体的代表机构参与了对这一改革方案的讨论和修改。在小升初方面,父母还是获得选择权。不过,当学校的名额供不应求时,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选出60%的学生,30%的学生通过抽签决定,剩下10%的名额给予有特殊需要的人(比如需要和自己兄弟姐妹在同一所中学学习的人)。
当时柏林州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左派党(Die Linke)组成的联合政府,因为两个政党的颜色一个是红色,另一个是粉红色,所以,这两个政党组成的政府也被称作“红—红—政府”。他们是这一改革方案的支持者。社会民主党认为,学校结构改革将会带来一系列好处:更好的个性化的教育,清晰的学校结构,更长时间的共同学习,更好的办学条件,扩建全日制小学,促进机会公平。其他政党和机构对政府的这一改革方案褒贬不一。[19]
柏林的反对党基民盟对执政党的改革方案提出了批评,基民盟柏林州的党主席Frank Henkel及基民盟议会党团的教育政策发言人Sascha Steuer表示:政府的改革方案中缺少一种教育学方案,可以保证在学校合并后每一个学生都会得到个性化的发展,同时也缺少一个教师发展方案,以保证教师可以提供符合专业要求的课程,落实改革。同时,改革方案中通过抽签进行择校的程序也受到了批评。基民盟认为这种程序是不负责任的,主张按照学习成绩进行公平竞争。基民盟提出了一份29页的学校法修改申请。不过,红—红—政府拒绝了其法律修订案。[20]
另一个反对党自由民主党也对改革方案提出了批评,认为升学的筛选标准不利于学校方面形成和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应该有确定自己筛选标准的权利,否则最终只会形成一种“红—红”的学校特色(rot-rotes Schulprofil)——即“平庸”。[21]两个反对党的共同点反映了这两者的保守性倾向,二者都主张保持筛选性的学校体制。这两个政党在议会表决时投了反对票。[19]
绿党赞同部分改革内容,如两类学校的学生都可以获得Abitur(高级中学毕业文凭),一体化中学的学生可以用多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考试。同时,绿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例如:绿党主张建立全日制的学校,认为这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正确途径。另外,绿党认为,文法中学设置试学学年让文法中学获得了特权的地位,可以将不合格的学生送去一体化中学上8年级。这样一来,一体化中学和文法中学就不再是等值的学校,而是成了二等中学。因此,绿党主张取消试学学年和蹲班的制度,将学生是否适合上文法中学的决定置于中学5年级和6年级。但是,这些主张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和左派党的同意。因此,绿党在议会表决时选择了弃权。[22]
除了议会中的各政党之外,议会外的各利益团体的代表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发挥其影响。
柏林地区的教育与科学工会在2009年6月4日的决议中表示,他们坚信,只有一种全纳性的学校体制才能够同时实现机会公平和高质量,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性分化的学校体制,强烈建议引入“共同体学校”,实现所有的学生都上同一种学校(eine Schule für alle)的目标。教育与科学工会主张对学生的个性化的促进,反对对学生的筛选,认为这对于那些出身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十分不利,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动机、自我价值感和社交能力。[23]在收到政府学校结构改革的法律草案(2009年6月17日版本)之后,教育与科学工会在2009年6月24日针对这一草案提出了非常细致的意见,包括赞同的条款,存在疑问的条款和表示批评的条款,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24]
2009年4月1日,柏林家长委员会邀请感兴趣的家长参加与各党派(社会民主党、左派党、基民盟、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议员的讨论会。会上,这些党派的议员首先介绍了有关学校结构改革的支持和反对性意义,之后听取了家长们的见解。在这次会议上,受邀请的家长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觉得自己的孩子成了试验品。[25]
2009年11月17日,柏林学生委员会在媒体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柏林的学校结构改革,同时把这一改革视为实施通向共同体学校的第一步。学生委员会同时要求向教师提供培训,以便于让他们可以适应新的情况。学生委员会要求聘用更多的教师,每班一个负责老师已经不够。[26]
小学联合会(Grundschulverband)基本上也赞同学校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减轻了小学对学生进行分流的负担。因为未来两类中学都可参加Abitur考试,所以,小学毕业时不再需要过早地对学生作出是否适合参加Abitur的判断。另外,该组织也提出了对改革的批评和改进建议:(1)取消文法中学将自己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分流给一体化中学或特殊学校的特权,同时取消文法中学的试学学年。(2)有许多文法中学仍然保留着设立5、6年级的特殊权利。这种形式的早期筛选架空了柏林的6年制小学,妨碍到小学的教学工作,因此建议取消这些学校的特权。(3)这次的学校结构改革没有考虑《联合国残疾人公约》要求的全纳性教育,特殊学校继续存在。总而言之,小学联合会最终认同的也是全纳性共同体学校,即所有的学生都上同一类学校,中学不分流。该组织将现有的改革视为是通向这一目标的中间步骤。[27]
2010年1月12日,柏林手工业协会、工商业协会、自由职业联合会(Verband Freier Berufe)以及柏林和布兰登堡企业联合协会(Vereinigung der Unternehmensverbände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e.V.)与柏林教育、科学和研究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Bildung,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愿意作为一体化中学双元制学习(duales Lernen)的伙伴,帮助学校和教师将来自职业领域的实践性的知识融入学校的课程之中,帮助学校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向学生提供实习位置,与学校一起做项目和举办活动等。这份声明表明,柏林的学校结构改革得到了经济界的赞同和大力支持。[28]
经过长期的公共讨论,柏林州议会在2010年1月14日通过了改革柏林学校结构的学校法改革。社会民主党和左派党赞同,绿党/90联盟(Bündnis 90/Die Grünen)弃权,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反对。[27]柏林学校结构改革的政策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得到合法化。
三、德国教育政策制定的特点
研究者通常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模式有以下三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1]13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划分,现实中的教育政策制定可能比三种模式所说的更为复杂。例如,本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协定2020”这一政策是由下而上提出的,而柏林学校结构改革政策则是由上而下提出的。但在教育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上面的政府机构与下面各个利益团体的代表机构则是在互动之中不断协调和修改政策方案。鉴于德国政府机构是绝大多数教育政策的倡议者和提出者。所以,自上而下、上下互动与合作应该是德国主流的教育政策制定模式。这是德国教育政策制定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各州自主负责本州的教育事务。德国教育政策主体主要在于州和地方层面,联邦政府只是起到补充和平衡的作用。这一结构让各州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探索符合本州情况的教育政策,有助于产生创新性的教育政策方案,供各州相互参考和借鉴,也有助于提升教育政策的针对性和适切性,便于教育政策得到落实。
第三,德国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和范围的划分十分明确和细致,对各个社会群体利益代表机构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均通过法律条文加以制度化。教育政策的主体在形成和制定教育政策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得德国教育政策的形成具有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点。[29]101
第四,在德国教育政策制定和形成的过程中,决策者十分重视进行实证调查或者请专家与学者进行充分的论证,例如本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协定2020”的提出以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调查和科学预测为基础。另外,德国在引入国家教育标准前,先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完成了一份十分详尽的评估。这说明,德国教育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科学决策的导向。
第五,德国教育政策制定重视让不同的政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民主参与,具有民主化的特点。首先,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常都是联合执政政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力量单独执政,另外议会内外有多个反对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例如在柏林学校结构改革中,社会民主党和左派党更加看重社会公平,照顾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在择校方面采用精英化的筛选机制,而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则比较保守,偏重维护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利益,主张按照成绩原则择优录取,对学生进行分化。因此在教育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当利益难以通过谈判协调时,执政党往往会谋求通过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将其教育政策合法化,而不再顾及反对党的意见。
其次,除了政党之外,经济界、家长、学生、工会、教师、校长等相关利益群体的代表机构也被纳入教育决策或咨询的过程之中。此外,在有关政策的公开讨论中,教育研究机构和教育咨询机构、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媒体也都积极参与,表达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教育政策方案。
不同层次的政府机构、政党和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群体民主地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改革方案最终可以照顾到各个群体的利益,避免形成偏向一端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增强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但是,他们在教育政策方案方面的分歧也常常令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很长,导致许多教育政策方案最终偏离了提出时的目标和初衷,甚至中途夭折。因此,德国现有的教育政策制定机制既有优势,也有其问题所在。
因为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德国教育政策制定的模式对于我国可能仅具有有限的借鉴性,但是向地方政府“放权”令其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教育政策、基于科学论证的教育决策导向、重视多方利益群体民主参与教育决策等做法,我们却不妨学习和参考一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德国教育政策制定机制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德国也属少数。笔者在德国既没有找到教育政策学方面的专著和教科书,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章。德国研究者黑普(Hepp)最近出版的《德国教育政策导论》(Bild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一书也只是分析了具体的德国教育政策,而非教育政策的制定机制。[11]所以,对德国教育政策制定机制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1]褚宏启. 教育政策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袁振国. 教育政策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Hans-Joachim Lauth,Christian Wagner. Politikwissenschaft:Eine Einführung[M]. 7. überarbeitete Auflage. 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2012.
[4]Die Bundeskanzlerin. Die Aufgaben der Bundeskanzlerin[EB/OL].[2014-05-23].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 Webs/BKin/DE/Kanzleramt/Aufgaben/aufgaben_der_kanzlerin_node.html.
[5]KMK. Das Bildungswe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09[R]. Bonn:KMK,2009.
[6]德国概况.联邦议院[EB/OL].[2014-05-24]. http://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ch/political-system/ main-content-04/the-bundestag.html.
[7]德国概况.联邦参议院[EB/OL].[2014-05-24]. http://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ch/political-system/ main-content-04/the-bundesrat.html.
[8]德国概况.德国总统[EB/OL].[2014-05-24]. http://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ch/political-system/ main-content-04/the-federal-president.html.
[9]GWK. Allgemeines zur GWK[EB/OL].[2014-05-25]. http://www.gwk-bonn.de/index.php?id=252.
[10]KMK. Wir über uns[EB/OL].[2014-05-25]. http://www.kmk.org/wir-ueber-uns/aufgaben-der-kmk.html.
[11]Gerd F. Hepp. Bild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M].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1.
[12]Wikipedia. Landesparlament[EB/OL].[2014-05-25]. http://de.wikipedia.org/wiki/Landesparlament.
[13]Baden-Württemberg. Landesregierung[EB/OL].[2014-05-25]. http://www.baden-wuerttemberg.de/de/regierung/ landesregierung/ministerien/.
[14]孙进.《高等教育协定2020》评述——德国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0).
[15]Dagmar Klimpel. Der Hochschulpakt 2020. Ein Ergebnis gesamtstaatlicher Verantwortung[J]. Zeitschrift für Bildungsverwaltung,2007,(1).
[16]Ulrich Trautwein,Marko Neumann. Das Gymnasium[G]// Kai S Cortina,et al. Das Bildungswesen in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2008.
[17]HRK. Im Brennpunkt:Hochschulpakt 2020[EB/OL].[2014-05-25]. http://www.hrk.de/de/brennpunkte/3377.php.
[18]Zweiwochendienst. Zöllner stellt Schulstrukturreform vor[EB/OL].[2014-05-12]. http://www.mutlu.de/ presse/2370868.html.
[19]WIKIPEDIA. Schulstrukturreform in Berlin[EB/OL].[2014-05-12]. http://de.wikipedia.org/wiki/Schulstrukturrefo rm_in_Berlin.
[20]CDU Berlin. Rot-rote Schulstrukturreform verhindert Bildungschancen[EB/OL].[2014-05-12]. http://www. cdumitte.de/index.php?ka=1&ska=2&idn=14.
[21]FDP Berlin. Schulprofile fallen der schlecht gemachten Schulstrukturreform zum Opfer![EB/OL].[2014-05-12]. http://www.fdp-berlin.de/Schulprofile-fallen-der-schlecht-gemachten-Schulstrukturreform-zum-Opfer/ 437c528i1p20/index.html.
[22]Bündnis 90/Die Grünen. Schulstrukturreform aus grüner Sicht[EB/OL].[2013-07-01]. http://www.gruenefraktion-berlin.de/archiv/cms/bildung/dok/328/328694.schulstrukturreform_aus_gruener_sicht.html.
[23]GEW Berlin. Schulstrukturreform in Berlin. LDV-Beschluss vom(04.06.2009)[EB/OL].[2014-05-12]. http:// www.gew-berlin.de/18934.php.
[24] GEW Berlin. Vorläufige Stellungnahme der GEW Berlin zu den geplanten Änderungen des Schulgesetzes (24.09.2009)[EB/OL].[2014-05-12]. http://www.gew-berlin.de/documents_public/090624_Schulstrukturgesetz_GEW.pdf.
[25]Der TAGESSPIEGEL. Schulreform:Eltern warnen vor Abitur zweiter Klasse[EB/OL].[2014-05-13]. http://www. tagesspiegel.de/berlin/bildung-schulreform-eltern-warnen-vor-abitur-zweiter-klasse/1831722.html.
[26]LandesschülerInnenausschuss Berlin(LSA). Berlins Schülerausschuss unterstützt den bundesweiten Bildungsstreik[EB/OL].[2014-05-13]. http://bildungsklick.de/a/70874/berlins-schuelerausschuss-unterstuetzt-denbundesweiten-bildungsstreik/.
[27]Grundschulverband:Stellungnahme zur Berliner Schulstrukturreform(15.01.2010)[EB/OL].[2014-05-13].http://bildungsklick.de/pm/71629/stellungnahme-zur-berliner-schulstrukturreform/.
[28]IHK Berlin et cl. Erklärung der Partner des Dualen Lernens in Berlin[EB/OL].[2014-05-14]. http://bildungsklick. de/datei-archiv/50847/loi_duales-lernen.pdf.
[29]吴遵民.教育政策入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雨 夕]
孙进(1976— ),男,河北巨鹿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德国比较教育研究。
G40-011.8
A
2095-7068(2014)02-0110-09
2014-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