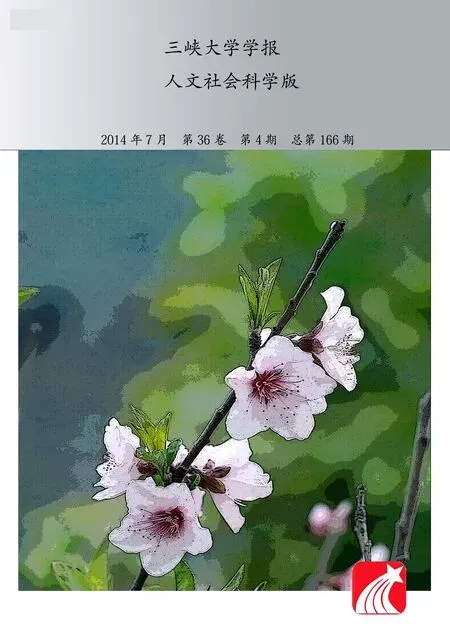中国古装历史电视剧的及物性叙事分析
——以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苏东坡》为例
2014-04-05王冬冬
王冬冬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上海 201804)
古装历史电视剧是指以我国古代历史为书写背景,所讲的故事是在历史确有之人和确有之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创造加工而来的,剧中的主要人物大多为真实历史人物,剧中的重大事件叙述以历史实在为由头,艺术真实与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距离在合理的范围内的电视剧。它通过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展示某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或品格,以及其所涉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达到给观众以启示和教益的目的[1]。广义的“古装历史电视剧”包括“正史型”、“野史型”以及“戏说型”等所有取材于历史中一个有代表性段落的电视剧,其中的“正史型”历史剧是指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展示历史人物的雄才大略与情感世界,通过艺术思维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情感等方面,来表现历史事件的艺术真实,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得到精神愉悦与美的享受的一种电视剧形式;“野史型”历史剧是以某些在社会生活中流传甚广的历史传说、小说或者话本为依据,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事件进行演绎的电视剧形式;“戏说型”历史剧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背景,从创作者的现代理念出发,以现代情怀对事实的结构为线索,运用艺术想象来叙述理想中的故事,这类剧已经抛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追求的仅仅是艺术真实,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甄嬛传》等[2]。中国当代文化正处在一个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元并存的多元结构之中。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广泛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必然受到文化消费供求的制约。在消费社会中,市场的作用对于电视剧创作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化”和历史戏说电视剧的“正剧化”,同样获得新的合法性,并赢得了成功。
然而,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集群化的形式盛装登场并大获成功之后,迅速进入到了一个以奇观进行媚俗倾向愈来愈严重,内容教化倾向迅速蔓延以及同质化越来越突出的泥潭之中。2005年4月,在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9项电视剧管理措施中,有两条影响到了古装历史剧在电视台的播出空间,分别是:“在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批中,进一步严格历史剧、古装剧的审批,适当放宽现实题材的审批,加大现实题材的立项比例”;“把播出现实剧的情况,作为对各级电视台年度考核的指标之一”[3]国家广电总局希望以此限制古装历史剧规模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胡编乱造、封建迷信、严重颠覆性篡改史实等倾向。2011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出禁令,要求从2012年1月1日起禁止宫斗戏、涉案剧和穿越剧在上星频道黄金档(19:00-21:00)播出[4],并在2012年8月进一步就电视剧创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包括古装历史剧不能捏造、戏说。应该说,电视剧需要在一个坚定的充满主体意识与社会性的真实空间的框架下进行叙事设计,才可能得到一个实质性的成果。古装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起起落落,在商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如何净化市场环境,与当代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相结合,引导社会思潮、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并进而提供更具特点与原创性的、有个性魅力的作品,使教化与娱乐相结合,市场与文化相契合,让历史与现实生活对接,是追赶时代步伐、走向未来的电视剧工作者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古装历史剧《苏东坡》在叙事设计上的特色,或许可以为古装历史剧的当下化、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提供借鉴。
一、及物性叙事是古装历史电视剧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必要手段
影视作品的作用在于传播信息、建构意义、表达情感和抚慰心灵。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它既要扮演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角色,又要履行其在市场中所必须承担的商业责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个产品必须同时表现出两个特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解决观众对电视剧需求的主要矛盾在于创作者通过影像和剧情诠释的意义。受众的主体意识是因为其对某种缺失的感知而存在的,主体意识确立之后,即会产生与大他者分离的危险感,意义就产生于受众为消除这种危险感的缝隙而与他者进行缝合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受众对意义的消费来自于心灵对慰藉的需求。因此,电视剧之于观众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对解决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心灵问题做出贡献,也就是需要通过电视剧叙事建构当代的文化价值观。而电视剧在叙事过程中输出当代价值观是通过及物性叙事实现的。
及物性是一个源自于语言学的概念,它指涉一个具有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过程”,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作用的语义系统[5]。韩礼德认为,系统功能语法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种纯理功能,其中,概念功能主要指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交际过程的参与者正在从事着什么样的活动。这种活动既可以指对外部世界的行为,也可能是在人们头脑中进行着的思想过程[6]。及物性和语态系统、归一性都是概念功能的体现形式。在影视叙事中,及物化强调叙述者在表意过程中所选用的对象和符号需具有明确的概念功能,以物质过程进行言说,来直接作用于受众,使得受众在物质性过程引导下进行感觉和认知,对视觉符码过程进行阐释;另一方面,需要被言说之物所产生的意蕴具有明确的当下性,能直接贡献人们的生活实践,以达到贡献受众心灵的目的。这也决定了及物化影像叙事需要从输出当代文化价值观出发,使影像表达过程中的物质过程在所体现的价值观上与当下契合,贴近社会生活,具有更强烈的可接受性、可感性和体验性。
一个影像文本意义的建构有四个层次:指示性意义、外在意义、内在意义和象征性意义。当我们在了解一部影片的外在与内在意义时,可以认为它承载着特定时期的社会价值,这个影片中蕴含的社会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性意义,而被凸显出来的象征性意义即被认为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电视剧中存在的象征性意义说明,无论指示性或是内在、外在的意义,都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现象,电视剧的意义都是关涉某种意识形态,并从文化上对世界的价值观所开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一部电视剧的深刻性正在于文本的叙事能否让材料通过形式系统生发出其切实的象征性意义,进一步说就是文本故事的表达是否具有当下性和及物性。我们常说的贴近生活并不是仅在作品文本能指层面的契合,而是意指功能上的一致性。它来自于文本叙述时空与受者观看时空的打通并互为喻体。例如,电视剧《苏东坡》的主人公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在经历五代战乱之后,北宋王朝经济发展迅速,商品交换发达,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社会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在北宋的社会繁荣局面之中,仍旧蕴含着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心灵建设问题,这一情况与我们国家当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之后所出现的社会矛盾复杂性和人心建设出现的问题有着明显的映射关系。
电视剧《苏东坡》从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出发进行叙事无疑在价值观的表达、人文精神引领上具有很鲜明的“及物性”特征,这正是当今中国人的精神建设中最需要解决的东西。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最深层的机制就是指向人的心灵和社会道德建设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绕不开的问题。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说到底是人类自身在物欲和神性之间的权变,苏东坡在剧中所体现出的高尚情怀正是人们在经历了价值观念混沌而重归高尚过程中所需的引领,该剧因此指向了最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
历史题材电视剧虽然在故事设定上已经固定在了古代这一非进行时的时间点上,但仍旧可以通过当代文化价值观这一因素寻找其当下性表达。也就是说,这一类型的电视剧在故事的内容选择以及叙述策略上应该以解决当代社会人们的心灵建设为出发点,从受众可接受的贴近性事件入手,通过及物性叙事输出当代文化价值观。
二、古装历史电视剧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及物性叙事策略
古装历史电视剧《苏东坡》通过对于苏东坡所生活的北宋岁月的史诗性叙述,把自己所诠释的象征性意义凸显出来。这部剧用苏轼身上体现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涤荡和照亮了当下人们在快节奏社会生活中被过度的物质迷恋所笼罩的心灵,用以民为本、正直达观的人文精神呼唤在世俗权利结构中沉溺的良知和理想,完美地呼应了当代文化价值。
一个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需求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之后,必然要遇到“高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城市化的加剧、资源和环境问题、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身处其中的个体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心灵的建设。当下,中国人普遍觉得生活压力大,有着集体不幸福的感觉,主要还是对于生活观念的把握,即价值观出了问题,这个时候社会需要集体的心灵抚慰,需要文艺作品有一个向上的引领,各媒体的选片人可以不相信观众的品位,但他(她)没法回避观众内心向上向善的欲望,观众对抚慰心灵的高尚精神的需求。
电视剧《苏东坡》全局所展示的苏轼高尚的人文情怀以及剧本台词时刻透射出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兼济天下的精英意识是当下社会建设中最需要的东西,是最对症、最富有营养的心灵鸡汤。该剧可能对东坡先生的塑造有过于完美之嫌,但创作者所表达的对崇高理想的建构,对以民为本、心怀苍生的情怀的向往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思想很好的诠释。我们可以从叙事学的故事和言说两个维度进行阐述:
在故事层面先看剧本中主要线索的选择。苏东坡既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卓著的大文学家,他在文学、思想和书法上都取得了超卓的成就,为世人所赞叹,同时又是一位襟怀奉于苍生、仕途坎坷却爱民不移的政治家,这就为剧本的主题表达提供了至少两条线索。一条是以他的文化成就、文人轶事为线索,做一次思想文学集大成者的传统文化之旅,毕竟以苏轼之才学和成就,影视文本完全可以凭借其厚重的指示性意义成为传承文化的精品;第二条线索就是这部电视剧所选择的以苏轼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为剧情推动的线索,将苏东坡宦海沉浮作为北宋自宋仁宗到宋徽宗那段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风貌展现出来的路径。事实上,这部剧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于此。这个表面看似故事叙述的背景实际上正是创作者着力描述的重心,在北宋那段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经济、文化和科技最为鼎盛的时期的政治风云际会中,苏东坡所体现出的高尚情怀找到了与当下现实打通的渠道,电视剧文本的意义由此敞开。
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在谈到创作经验时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影片创作者在创作每一部新作品时,首要的反应一定是寻找他理想中的这个影片的与众不同之处。电视剧《苏东坡》的创作团队在对这一题材处理上就体现出了良好的创作感觉——找到了最重要的与众不同:既不同于对苏东坡文学成就、文人趣事的复现,也不同于近十几年来我国电视剧舞台上的大多数作品的题材取向。
在以往热播的历史剧中主要是进行奇观化的叙事:比如帝王剧、宫廷戏中的政治奇观化叙事,它们主要是以历史史实为背景切入到宫廷的政治斗争叙述中,将叙事的重心放在权力斗争上,满足人们的政治窥视和父权想象;再比如《大明宫词》一类的文化奇观叙事,单纯宣示对中国文化盛景的膜拜并进行诗意化表达;又如穿越剧、悬疑探案剧等只是通过故事本身的奇观张力进行悬疑、青春或怀旧的缝合……我们必须承认在上述方面很多古装历史剧都是精品,但就其文本而言,对意义的表达更多地停留在故事的指示性意义和外在意义上。而《苏东坡》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将政治权力斗争推入背景,在大历史观的观念指导下,对事件中的人进行客观、系统化的分析,从权谋看人性,从诸多人性表现中凸显东坡先生的高尚情操。而这种将奇观化要素退为背景,用精神力量的建构引领叙事正是我们这个在文化上,尤其是通俗文化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去精英化之后最需要补缺的。
然而,精神需求的契合解决的是“看进去”的问题。在此之前,从文本的接受过程来思考还有一个受众“看不看”的问题。在文化进入产业之后,考虑市场的接受是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高尚的精神首先能被接受才能起到对受众的引领作用。在这方面,除了我上面谈到的在精神契合方面的“及物性”之外,还需在言说层面解决问题。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在文本言说层面的叙事结构、人物及情境设计和演员的选择等方面都颇具匠心,从而保证了该剧的可视性。
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上,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大量运用了“插入式叙事”的方法。虽然创作者将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作为叙事的基本线索,但并没有忽视他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书法家,作为才情与智慧并茂的典范,身上曾发生过的那些蜚声文坛内外的文人幽默资源。而这些故事轶闻之间并没有因果逻辑上的直接关联,单独依靠这些事件也无法为故事的推进提供足够强大的动机。然而,这些文人故事却具有奇观效应,能够满足受众对文化的“窥视”欲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瑰丽的东西,那些随着时间的风尘渐行渐远的东西是有诱惑力的,它们始终牵引着当下人的好奇心;其次,毕竟中国观众的血脉里澎湃的是中华文化的韵律,文化是具有最强烈的认同力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之一的宋代诗文在文化的沟通上是占有优势的,这些都可以回应人们对于在地文化的好奇。电视连续剧《苏东坡》虽然以社会政治为线索,但仍适时地插入反映苏轼的才情和文采的很大篇幅的段落。虽然这些情节和段落在时间叙事线上仍旧与主人公的政治经历保持前后的连续,但很显然它们与主要叙事线索上的事件向前推进的激励的关系不是很密切(除掉全剧第一部分三苏赴京赶考中有关文风改革的部分)。因此,该剧中反映苏东坡才、学、识、趣的部分都属于插入性叙事。根据麦茨的大组合段理论,这些插入段落指向奇观,在本剧中体现为满足受众的文化窥视心理[7]。
在电视剧《苏东坡》的第35集中出现的关于苏轼和刘贡父之间发生的“三白饭”和“三毛饭”的趣事,在该集所主要讲述的苏东坡与张璪、西夏使者、王岩叟和刘挚等人涉及政治的抗衡的情节在线索推进上无关,只关涉文化趣味,成为满足人们文化窥视的奇观化叙事。又如,该剧的第27集中,苏轼被贬黄州,路遇来接他的陈季常,在陈家苏轼的儿子苏迈与陈家丫鬟就“梅、兰、竹、菊”因何被称为四君子,以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故被佛家所推崇的对话;苏轼与陈季常就陈妻的泼辣赋诗的段落等,他们与苏轼政治生命历程没有因果逻辑联系,不是推进苏轼命运变化和反映北宋政治改革进程的激励性事件,依时间的线索出现在叙事主线之中,都属于典型的表现文化情趣的插入式叙事。这种平行的插入式叙事只是吸引观众看剧的“门”,而不是转移主题指向的“蜃景”,他们完成了通过文化旨趣和传统文化在受众心理的共通性积淀来吸引受众对文化“窥视”并满足其文化好奇心的目的。
这部44集的电视连续剧在人物及情境设计方面,能够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为人物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将所有的人物都放在其所处的具体宏观社会环境、微观自身处境、亲身遭遇、政治理念等层次上观照其行为,揭示其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于是司马光、王安石这些智慧过人、才情横溢的文学家、政治家为何在执政生涯中矫枉过正、提拔小人便也有了合理的解释。比如司马光年迈之后重获皇帝重用废除王安石变法期间施行的《免役法》和《青苗法》,由于《免役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执行过程中需要有政策的连续性,因此当司马光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废除该法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司马光本人过于自信,在推进自己的政令过程中也需要有人为其他地方官做个榜样,于是投其所好的小人蔡京被一代名相司马光看中就有了时势的必然性。同样地,还有剧中涉及的王安石主政变法期间的用人情况。对一个事件的判断要回到事件发生的环境中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莫言语)[8],艺术的真实性伴随着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跃然荧屏之上。艺术真实在其寄寓的历史真实之中凸现出来,艺术虚构为实现艺术真实的目的服务,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在影视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进而完成了向历史电视剧戏剧本体的回归。该剧情境设计的复杂性不仅从“及物性”上更好地设置了戏剧中激励人物行动的动机,而且通过与当下环境的打通,通过附加人物在情境中的行为为观众提供了一面镜子,反过来“照耀了我们那些不能说的东西,照耀着我们身上每个人跟内心相悖的东西”(康洪雷语)[9]。
在演员的选择上,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在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选择上,对以往历史剧重在追求演员与剧中人物形似的理念方面进行了突破。该剧确定陆毅扮演主人公苏轼,一方面基于剧本对主人公苏轼设计的率真、坦荡、倜傥的性格特点出发,追求演员在这个意义上与剧中人物神似;另一方面又借助陆毅作为青春偶像演艺明星所具有的奇观化效应和本身所具有的演绎大年龄跨度人物的出色表演能力,不仅使剧中的苏轼与现代观众在情感上获得了认同,而且满足了景观社会中作品本身所需要具有的奇观化特征。此外,林心如扮演苏轼的妻子王弗、申军谊扮演范缜、以及王诗槐、何伟等明星助阵,都是力图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媒介生态下,以奇观化的特征解决了吸引观众“看”的问题。
实际上,电视剧“及物性”的精神表达和奇观化的叙事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这里面存在一个主次的问题,重点在于作者希望将意义导向何处。古装历史电视连续剧需要在尊重基本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遵循艺术创造的假定性原则而创造出具有艺术真实性的“第二自然”,通过对素材主题方向的设计,形成与当代社会相观照的多层意义空间,使电视剧文本具有史诗性。电视连续剧《苏东坡》正是巧妙地将兼济天下的意识形态主题方向与文化旨趣的奇观化表达相结合,获得了可视性与深刻性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 秦俊香.电视剧的戏剧艺术冲突[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159.
[2] 李鹏飞.大众文化视野中历史电视剧的叙述策略——以《雍正王朝》为个案的叙事学解读[D].上海:复旦大学,2006(3):3-4.
[3] 国家广电总局将严控古装剧9项措施扶持现实剧[N].北京青年报,2005-04-04.
[4] 赵 斌.广电总局:去年十部剧五部是历史题材[N].成都日报,2012-02-18.
[5] 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5.
[6] 朱士昌.浅析英文小说的及物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2):5-11.
[7] 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58-67.
[8] 莫 言.讲故事的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EB/OL].凤凰网.http://qd.ifeng.com/xinwenzaobanche/detail_2012_12/08/470263_0.shtml.
[9] 朱慧憬.我们都丢掉了,但是许三多没有丢[J].新周刊,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