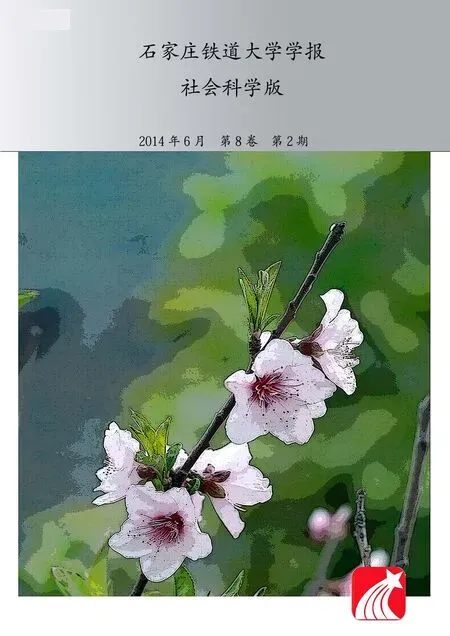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2014-04-04刘华领
刘华领, 彭 鹏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诗画的生命在于传承,园林的生命在于生长。诗画本身不会生长,但诗画里有了园林,园林里有花草树木,有雀鹤雁鹜,有虫鱼走兽,有许许多多可以生长的生命,诗词画卷也就因了这些生命的生长而生长。
诗词、绘画、园林的互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萌芽,而到了唐代,集诗人、书画家、造园家于一身的王维将三者有机地融合在辋川别业,则堪称典范。王维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他的诗里有景有情,有声有色,譬如“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譬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一首首诗就像一幅幅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生长,衍变成一座座立体的园林,诗、画、园林就在这一刻融为一体。苏轼评论王维的画:“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画里的景外之意,催生了文人写意画思想的萌芽。苏东坡在其画《蓝田烟雨图》中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首次提出了诗画互渗的审美思想,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1]前言5,50。
到北宋,文人画悄然兴起并自成一派,使得绘画与文学的结合更加直接、紧密。在北宋文化的滋养下大为兴盛的文人园林,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在文人山水诗画的影响下,在唐代创立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造园传统开始偏向于写意方向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向写意山水园的转化,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是其最大特色。
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正如一粒小小的芥子,能够容纳一座巨大的须弥山一样,画幅虽小,只有咫尺,诗词虽短,寥寥数语,却能容纳广阔的园林天地,任其蓬勃生长,生机无限。
一、诗画本一律
宋代的绘画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以宫廷画为代表的“写实”风格和以文人画为代表的“写意”形式并行发展,平分秋色;二是完成了绘画的“诗化”过程,确立了“以诗入画”的重要审美原则。
从五代到北宋,宫廷绘画艺术中较有成就的是花鸟画和山水画,其中尤以花鸟画因得到皇室青睐而发展更为成熟。北宋宫廷画院中的花鸟画,早期将近一个世纪,传承的都是以来自西蜀的黄筌父子为代表的“黄派”绘画格法,题材多为《杏花鹦鹉》、《海棠竹鹤》、《牡丹锦鸡》之类,深具富贵意味。从技法角度来说颇重视写生,不仅强调形似,更注意神态的刻画,讲求“气韵生动”。到北宋中期,崔白对“黄体”进行变格,将写生和传神更推进了一步,大大推进了宫廷绘画“写实”的艺术水平。其后赵佶主持的宣和画院,将宋初的黄氏富贵意蕴和写实精神更进一步完善化,使北宋的宫廷画派达到了巅峰状态,形成了宣和体,“专尚法度”已达极致[2]5-8。
正当写实风格臻于巅峰,难以再有发展之际,一股新生力量带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袭,一种名为“士人画”的崭新的绘画风格沛然兴起,他们又以“墨戏”自榜,即俗称的“写意”。倡导者苏轼、文同、米芾等,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但他们却以诗人、书法家的醇厚的文化素养,使这种创新带着猛烈的锐气,足以撼动当时写实形式的主流地位,遂与之形成了相互对峙、平分秋色的形势,并露出了取而代之的历史苗头。
苏轼界定“士人画”为“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士人画和画工画的区别在于:“士人画注重写意,画工画重在写实。”又提出了“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主张绘画既要有自然之意,又要有象外之意,倡导意似,贬议形似,同时要求绘画要表述一定的诗意,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1]79。
“律”,当指诗歌理论中的“比兴”之法,也就是借物表意,寓情于物,使欣赏者能够由此而联想到彼——象外之意。如苏轼所画的《古木怪石图》,用笔极其粗犷奔放,米芾评价其:“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黄庭坚《题子瞻枯木》云:“折冲儒墨陈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苏轼的画作正是其一生坎坷却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的写照,画品如人品,见画如见人,画竹石,非为传达竹石之神,而是表述作画者本人的主观精神,托物寓兴,借物表心。这就是文人画所谓的“意气”[3]前言2-3。
“诗画本一律”还表现在诗画互渗方面。苏轼的堂妹婿柳仲远有一天拿了杜子美的诗,求李公麟照诗意画一幅《憩寂图》,画由东坡和李公麟合作完成,画成之后子由在上面题诗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一幅画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1]47。诗僧惠崇擅写自然小景,且又擅画,他曾从自己的诗作中选出得心可喜者一百句,每句作一幅画,并刻在石头上,后人称为“《百句图》刻碑”。苏轼也曾为他的画题诗,如著名的《题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真正将诗词书画融为一体,《苏轼年谱》载,“七月六日,(苏轼)饮王齐愈家,醉后画墨竹,赋《定风波》。”苏轼集句为词体现了与其“墨戏”同样的艺术创作态度,亦较好地体现了“诗画一律”的创作主张[4]36。以诗入画、题画词等现象自北宋始,之后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绘画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其实更有效地实践着“诗画一律”原则的还是宫廷画院,最早题诗于画幅之上的人不是苏轼而是宋徽宗赵佶,并且他还将“诗题”用作画学招生考试的画题。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等,每一个题目画得最好的,都不是直白地描摹诗句中的景物,而是通过巧妙地构思,让人通过画面,能够领悟到画面之外的意境,所谓“逸情远致,超然于笔墨之外”。比如“乱山藏古寺”之题,占得头名的考生没有画一笔寺庙、塔尖等建筑,只有山水、羊肠小路、溪边挑水的老和尚,画面简单但把“藏”的意境表现的淋漓尽致。“踏花归去马蹄香”,由几只追逐着马蹄飞舞的小蜜蜂,泄露了“踏花”这一消息,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地跃然于纸上,给人联想空间,这就是所谓写意。
欧阳修有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无独有偶,西方也有“诗如画”的观点,古希腊诗人西蒙德斯曾说过: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与画有着共性的艺术特征,因此其二者的结合定是势在必行了。诗词与绘画到了北宋,相互渗透发展势头强劲,将山水诗词、山水画的发展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一个时期的园林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总是离不开当时文化环境的左右。诗画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园林的发展,更何况诗人画家还直接参与造园活动,这使得中国古典园林走到北宋,园林艺术开始有意识地融糅诗情画意,开始由写实走向写意,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这一发展特征与北宋的绘画发展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写实臻于巅峰,写意异军突起,二者平分秋色,诗画互渗,诗画一律。至于园林,则是写实写意并存,诗画园林互渗,诗画园林同源。
二、借得画论造园林
人们常常用“风景如画”来形容景观之美,用“如在画中游”来赞美园林之胜,甚至有人干脆将园林喻为铺在地上的画。画与园林水乳交融的关系,大概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同属于文化与艺术范畴,在艺术观、审美观和创作方法上具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所以许多营造园林的人,便常常借用绘画的方法和理论来叠山理水、布置建筑、栽植花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造园理论,其实都来自与画理画论,故现代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说:“不知中国画理画论,难以言中国园林”。事实上,很多园林便是由文人画家直接参与设计建造的,这就使得画与园林能够互通有无,关系更加直接,其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自然也就如出一辙,并无二致。第二,园林既是绘画的一个重要的描摹、表现对象,又是绘画创作的一个极其适宜的场所。所以,画家们在园林里雅聚、赋诗作画,园林景观自然也就常常出现在画作之中,园林的生命便以另一种同样生动的形式延续下来。第三,“以园入画”是绘画的一种创作手法,同样,“以画入园、因画成景”亦是造园的一种创作方式。山水画在北宋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为造园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更为造园提供了粉本素材。这种以画入园、以园入画的创作方法使画与园林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第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绘画与园林同时遇到了知音伯乐,且这个人又握有挥斥方遒、引领时尚之资本,则二者的发展自是大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之缠绵。这个人就是宋徽宗赵佶。
宫廷所画花鸟画,描摹的大都为禁苑中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等,再者皇帝为了写生之便利,势必会在宫苑中大量豢养珍禽瑞兽,设置奇花异石。《宣和画谱》形容赵佶收藏的2 786件花鸟画:“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艮岳中会有“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异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使得艮岳俨然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型植物园和动物园。延福宫内也豢养着大量的动物,《宋史·地理志》记载:“梁之上又为茅亭、鹤庄、鹿柴、孔翠诸栅,蹄尾动数千。嘉花名木,类聚区别,幽胜宛若生成。”玉津园则有为饲养珍奇禽兽而专门设置的动物园,园内蓄养着大象、麒麟、驺虞、神羊、灵犀、狻猊、孔雀、白鸽、吴牛等动物,皆为稀世珍品。琼林苑则是以南方花草取胜,园内都是南方进贡的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麝香等花,花间点缀梅亭、牡丹亭,还有石榴园、樱桃园等专类花卉植物园[5]278,286,288。“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皇家园林如此,那些贵戚官僚之园林想必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而山水画及山水画论的蓬勃发展,对园林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郭熙《山水训》开篇揭示了人们喜山乐水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从山水画中寻求寄托的情形:
“……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3]9
隐居山川林泽,过渔父樵夫的生活,与猿鹤烟霞为伴,有泉石林壑寄傲,远离人世间的烦扰,没有各种束缚羁绊,这是大家都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这种高蹈远引的生活岂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的!那么又如何来安抚一颗向往林泉的心?——悬挂山水画,这是郭熙给出的答案。可是,在“中隐于园”思想盛行的宋代,显然单凭张贴几张山水画是不能满足人们对林泉的渴望的。还有比挂画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家中营造园林,将自然山水搬到自己家中。不仅要满足于“可望”之神游,还要真正的可行、可游、可居,园林,才能够真正做到“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是世人之所以渴望林泉的原因,也是郭熙论山水画高下的标准[3]16,于是这个标准便被造园家们拿来用做兴造园林的目标和评判标准。在这种标准要求之下,中国古典园林首先应该是美的,其次要有供居住、停驻、观赏的建筑物以及供游览行走的道路,具备了这些基本要素的园林则无异于是符合审美特征的立体图画了。至于园林中的道路、山水、建筑如何摆放,从山水画论中也可以一一找到设计依据。如“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大松大石必画于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于浅滩平渚之边”,“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要奔趋。回抱处僧舍可安,水陆边人家可置”,等等,不一而足[3]49,76,124。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是绘画的方法,同样也是营造园林的方法。如何“外师造化”?郭熙给出的建议是,惟有“饱游沃看”,方能“取其精粹”而“夺其造化”,方法只有一个,多到真山真水间去游览,观察山水之形状、四时晨昏之变化,将自然物态烂熟于胸。无论是郭熙的《林泉高致》,还是李成的《山水诀》,荆浩的《山水赋》,都提到了在四时朝暮不同的气象条件下,山水呈现出浑然不同的景观特征。扬州个园的设计就直接展现了郭熙画论中的“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如睡”,以及“春山宜游,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画理[3]26。
然而,仅仅“外师造化”,即使模仿的再像,那也不过只是对自然山水的简单再现,尚没有体现太多的艺术成分。自唐中叶出现了写意画的萌芽开始,园林的创作也开始从写实走向写意,园林堆山理水不再是简单地模仿与再现自然,而是多了对自然的概括和提炼,开始更多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诗情画意的创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北宋文人园林的兴盛上。顾恺之提倡的“以形写神”,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郭熙的将绘画艺术的美学本性概括为“写貌物情,摅发人思”,都是对“外师造化”的更进一步的要求,即“中得心源”。只有加入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提炼与艺术的加工,才可以做到“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这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古典园林最基本的美学思想,符合中国人基于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思想基础之上的审美习惯。
三、园林即文章
佑文抑武政策下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北宋文风非常兴盛,兴盛到连和尚道士都喜欢作诗填词,附庸风雅。进士许洞非常看不惯僧道们的这些“不务正业”之举,就琢磨找个机会给他们点教训,便组织了一次文化高僧们的赋诗雅聚,但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们,说诗词中不得出现纸上的字,高僧们都不以为然,但一看到纸上的字却都傻眼了,纷纷搁笔而去,竟没一人能作。只见纸上写着: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6]198。
这些恰巧都是组成山水园林的元素。由此可见,宋代文人们所作诗词,内容几乎难以离开山水园林之风花雪月,园林诗和园林词已成为宋代诗词中的一大类别,这也是由宋朝文化的特征影响所致。自中唐以后,盛唐所形成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弘气度日渐式微,主流文化已开始由外向的拓展转向纵深的内在发掘,盛唐文学中洋溢的那种气吞山河的豪迈,到了宋代,一部分被传承下来,亦有一部分则被风花雪月的精微细腻、缠绵悱恻、空灵婉约所替代,内容也由修齐治平转变为对山居、田园闲适生活的吟咏,茶酒书画、文房四宝、花草树木、庭园泉石开始大量的走入诗词文章之中,即使如陆游这样的爱国诗人也未能超凡脱俗。这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园林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园林兴游促进了山水文学的大发展。但园林与文学的关系远不止于此,首先,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园林的发展,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北宋文人园林的大行其道,就是文人参与造园的直接产物。其次,园林的结构与创作手法与诗文的结构与创作手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从诗文中又可领悟造园之法。第三,以文入园,因园成文,文中见园林,园中有诗文,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在表明一个关系:“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文心雕龙》有“为情而造文”之说,王国维亦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情能生文,亦能生景,其源一也。所以说:园林即文章。
宋代园林的最大成就与最突出特色是文人园林的兴盛与发展,文人园林的最大特色是写意,如何在园林中表现诗画的情趣,意境的涵蕴,以及思想情感的寄寓?除了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之外,又一种表达方式在宋朝园林里头出现并得到普遍发展,那就是点题。文学化的、写意的额匾题名在宋代文人园林中大量出现,在命名上大做文章,构成了宋代园林有别于前朝园林的又一特色。如司马光将其园命名为“独乐园”,苏舜钦的“沧浪”,朱长文的“乐圃”,晁无咎的“归去来园”,都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有些园名和景名则直接来自于古人诗文,甚至园林空间就是按照诗词的意境来布设。《洛阳名园记》所记李氏仁丰园的“四并亭”,取意于西晋谢灵运“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洪适《盘洲记》“鹅池”、“墨沼”、“曲水流觞”皆为兰亭古迹,“木瓜以为径,桃李以为屏”的“琼报亭”,显然出自于《诗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茧翁亭”说的是北宋隐士王樵“茧室自囚” 的故事,“芥纳寮”当是芥子纳须弥之意,而供孙息读书处的“聚萤斋”,则借晋代车胤少时家贫,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的故事来劝学,还有“云起”,”显然就是对王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之诗句的物化[7]48,66-68。
园林与诗词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往往园林建成之后,会有为之所做的传记、诗词、绘画。今人之所以能够对古代的园林有所了解,主要是仰仗了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比如通过《艮岳记》和《艮岳组诗》,艮岳的山水格局以及景点布置情况便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而对独乐园和乐圃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其园主人所写的园记。此外诸如《沧浪亭记》、《梦溪自记》、《洛阳名园记》、《盘洲记》、《南园记》、《研山园记》、《吴兴园林记》等,为研究宋代园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凭山水以传”,说的大概就是这层意思吧。
诗词文章之于园林的作用,不仅是运用景名、匾额、楹联等文学手段对园景作直接的点题,升华园林意境,或者是把古人诗文中的某些境界、场景再现于园林之中,还在于园林空间的规划布置可以借鉴文学艺术的章法结构,使得园林空间序列的展开,亦如文章一般,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等,变化有序,节奏清晰,层次丰富,使空间的连贯犹如文章的一气呵成,严谨、流畅、和谐,正如钱詠所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座优秀的园林即是一篇佳文。
四、西园雅集
最后,用一次文人的雅聚来结束对园林、诗词、绘画关系的探讨。
在中国文化史上,记载有非常多的文人雅集活动,尤其自魏晋王羲之以来,兰亭修禊活动就成为了文人们追逐风雅的范本。西晋石崇的“金谷二十四友”诗社,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北宋文彦博的洛阳耆英会,都是文人的雅聚活动。北宋王诜的西园雅集,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堪与兰亭修禊相媲美。
王诜,妻英宗之女魏国长公主,官驸马都尉,虽出身显贵,但因他琴棋书画诗词文章,集文人风流于一身,故而能与京城的馆职词臣、风流雅士情趣相投而往来颇多。他有一个园子,在很多诗词文献中都有提及,《宋史》魏国大长公主传记中描述:“主第池苑服玩极其华缛”,李之仪有《晚过王晋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烂开》诗,从诗中的“华屋高明占城北”可见宅第之华丽,“万盖摇香俯澄碧”可见池沼之清澈,“阴森老树藤千尺”可见花木之秀茂,“刻桷雕楹初未识”可见建筑之精美,“乱点金钿翠被张”可见陈设之富丽。如此华贵幽雅的环境,正是文化名流交游的理想场所。所以,当时的大文豪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等人,都曾集会于此,或挥毫用墨,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极尽宴游之乐,史称“西园雅集”。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把自己和友人苏轼、苏辙、秦观、米芾等一十六人在园中集会的情景画在一起,取名《西园雅集图》。米芾还为图作了《西园雅集图记》,描述了画中十六人的不同活动情景,并发议论曰:“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8]136-164
“西园”或许并非王诜府邸宅园的名字,或许就像南浦、西楼、东皋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含有典雅韵味的通称,或者有宴集宾客的“西席“、”“西宾”之意,还有古人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之雅兴,大概不过是为了渲染浪漫与书卷意境而被当时的文人们随手拈来为名吧。就是这样一个园子,成功的将园林、诗、画汇聚到一起,创造了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进入南宋之后,由于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等都是千百年难遇的翰苑奇才,西园雅集活动更被加以有声有色地渲染,涌现出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摹本,著名画家如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使得“雅集”成了中国人物画的一个重要母题。
园林里的文会,享受山水之乐的同时,饮酒品茗、弹琴弈棋、赋诗唱和、写字绘画,更享受人文之乐。如此既高雅又有意趣的活动,如今能得几回见闻?在羡慕古人的同时,也不禁感慨万千,如此真才学,真性情,真境界者,当今还能有几人?
参考文献:
[1][宋]苏轼.东坡画论[M].王其和,校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2]徐书城.宋代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3]郭熙.林泉高致[M].周远斌,点校,纂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4]于广杰,罗海燕,郝远.两宋题画词与苏轼文人集团综合文艺观念[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3):34-38.
[5]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3版.北京:清华出版社,2008.
[6]赵家三郎.微历史@宋朝人[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7]陈植,张公弛.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8]徐建融.宋代绘画研究十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