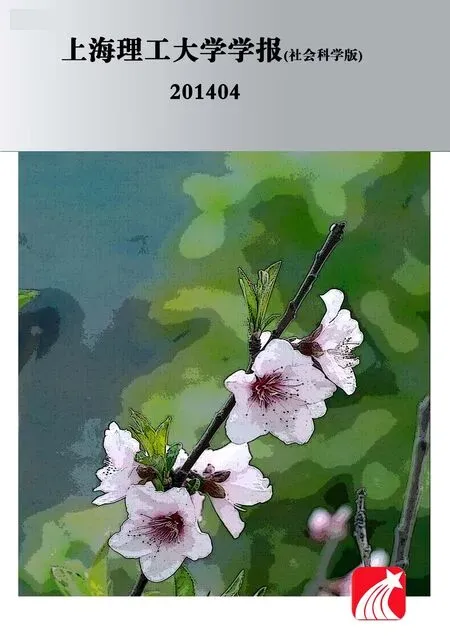文化记忆及想象视角下的《祖先游戏》
2014-04-03吴慧
吴 慧
(上海海关学院 外语系,上海 201204)
文化记忆及想象视角下的《祖先游戏》
吴 慧
(上海海关学院 外语系,上海 201204)
到2009年为止,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已发表了六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写作技巧的日臻成熟和完美使得他的每部作品都可圈可点,令关注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人们很是满意。在众多的作品中,无论从创作技巧,还是从作品传递的思想性方面来看,《祖先游戏》堪称最好的一部。重读米勒这部获多项文学大奖的作品《祖先游戏》,会强烈地为作品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及想象所折服和震撼,而这一切均出自一位澳大利亚作家之笔。针对文本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及想象所具有的意义,从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来关照文化记忆以及想象视角下的《祖先游戏》,以期进一步体会作品的深刻内涵以及它在重构澳大利亚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化记忆;文化想象;文化身份;中澳关系
截止2009年已发表六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的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在写作技巧方面日臻成熟和完美,每部小说都可圈可点,好评如潮,令关注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人们很是满意。从20世纪90年代始已发表的小说《祖先游戏》、《被画者》、《忠诚的条件》到参加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角逐的《爱之歌》(LoveSong),让读者目睹了一位作家的成长轨迹。然而,在众多的作品中,无论从创作技巧,还是从作品传递的思想性方面来看,笔者始终觉得《祖先游戏》都是最好的一部。其实,这也印证了作者本人的看法。2002年冬季,亚历克斯·米勒在上海访问期间,曾接受我国著名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黄源深教授的采访,当黄源深教授问:“假如要在你过去已发表的六部小说中选出一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只选一部作品,而不是两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祖先游戏》,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呢?” 米勒回答说: “我想你是对的。”[1]当人们今天再次重读米勒的这部获多项文学大奖的作品时,会强烈地为作品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及想象所折服和震撼,而这一切均出自一位澳大利亚作家之笔。那么在今天看来,文本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及想象又究竟有何意义呢?笔者拟从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来关照文化记忆以及想象视角下的《祖先游戏》,以期进一步挖掘该作品在重构澳大利亚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记忆” 在《祖先游戏》中的显现
在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所要回答的是 “我们是谁” 和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的文化认同性问题。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2]。“文化记忆有其固定点,它的范围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过去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其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意识、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维持的,人们称之为‘记忆形象’”[3],具体到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记忆与想象应该指的是 “艺术家以属于历史的事实、现象、故事、人物作为创作的素材,但是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将这些素材转换为具有文化怀想特征与文化记忆色泽的内容,在作品中注入了一种丰富的有指向的文化意味”[4]。想必《祖先游戏》真正撼动人心的原因应该是一位未曾在中国生活过的澳大利亚人,与一些中国人共事,通过访谈、阅读,获得大量素材后,大胆将其转换成了具有 “文化怀想特征与文化记忆色泽的内容”,在形、色、味等方面均达到了符合现实的境地。读者阅读体验后得到满足当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德国作家格拉斯曾经说过: “一切都没有过去,什么都会重新来过的。” 在他看来,小说家的任务原本就是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虚构的全景图[5]。倘若我们将米勒的文学回忆放在这一框架中,就会发现米勒演示的虽是个体的记忆,但指向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祖先游戏》所截取的时代背景分别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 “淘金热” 时期,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时期,描写了中国福建移民凤氏家族四代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这与人们对中国文化乃至对澳大利亚文化记忆完全吻合。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由于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的第一和第三阶段往往被忽视了……就澳大利亚而言,土著文化、亚太文化、除英国以外的欧洲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都在其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痕迹。澳大利亚文化是诸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6]3-4。也就是说。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家们有义务和责任如实反映这一层面的文化内容,对这一事实的文化记忆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米勒这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一使命,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如实地记录和呈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给读者最深刻印象的是该小说的宏大如史诗般的气势。以现在叙述为切入点,米勒巧妙地将故事的情节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通过时空交错,形成了澳大利亚发展的寓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大量事实细节的历史书。在空间上,该小说超越了澳大利亚小说多局限于欧洲或澳洲的限制,将神秘的东方文化要素植入小说中,使澳大利亚读者有机会体验和了解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也使中国读者重温自己的文化记忆,加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而在重温文化记忆的过程中,米勒以他超凡的能力将一些无形的印象和感觉转化成了具体的描述。女主角之一的莲在结婚后重游黄玉华位于杭州的住所时的描述就是极佳的一个佐证: “在她面前是又脏又窄的空地,四周是黑乎乎的污渍斑斑的砖墙,院子很像上海的廉价中式小吃店后的小巷,腐烂的白菜帮、草和鸭粪散落在院中。她快走四步来到了仓房的入口处,仓房里弥漫着家禽的粪便散发出的酸臭味。”[7]“记忆形象” 的运用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有曾经生活在浙江的读者对这一段的描述感到惊讶不已。这位在1937年并不曾生活在杭州的澳大利亚作家何以对当时的杭州有如此精准的描述呢?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的记忆作者是如何捕捉的呢?在《中国印象》一文[8]中,米勒本人如是说: “并非历史,而是印象保持了历史的原貌。”这恐怕也是创作素材转换为文化记忆色泽和文化想象在发挥作用的最好证明吧。读者禁不住要为作者捕捉生活、再现生活的能力赞叹不已。
二、“文化记忆” 赋予《祖先游戏》的时代意义
另一方面,从移民个人的外部经历向内在情感描述迈进的这一过程也表明了澳大利亚小说朝国际化写作技巧迈进的进步。毋庸置疑,米勒在小说文化记忆情节的构成上是胜人一筹的,他已经以超出英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以对中国文化记忆和想象的形式赋予了这部小说以现代的意义,即转向亚洲而非欧洲和美国来探寻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这一手法也印证了在该部小说开始时Soren Kierkegaard所说的话: “我们这个时代已丧失了有关家庭与种族的基本分类,使得每一个人都完全属于自己,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个人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和想象不仅体现了作者有意要强调澳大利亚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也道出了作为亚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小视的作用,同时也刻意拉近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间不可隔断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祖先游戏》绝不仅仅是一本小说而已。正如一位澳大利亚作家Sophie Masson在她的评论中所写的那样: “这不是一本拿起来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读完的书;它也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它的内容丰富,富于启发力。有关中国和中国社会的一级片段使得这本小说很独特和特别。小说充分运用了幻象和奇特的感觉,读者必须要进行二次思考,要看两遍,读两遍。”[9]
透过这部小说,读者还可以目睹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文化变化,这一变化丝毫不亚于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里战胜经济萧条,设计并最后在1901年建立了联邦国家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显示出澳大利亚已充分认识到了其远离母国,距离亚洲国家较近的事实和重要意义。这本小说可以说掀起了有关亚洲叙述小说的第二次浪潮,先于米勒进行创作的澳大利亚作家们,如:Koch,Grant,Drewe,Moffit等通常都是间接地通过人物寻找亚洲导师,来为读者提供一种渐渐消退的因在越南战争中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而带来的负罪感。米勒却将视角聚焦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长久存在的中国人身上,所以,很少有作品像米勒的这部小说一样在思考澳大利亚一个半世纪以来如何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勒是在为存在于文化表层下面的亚文化在欢呼,这绝非易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读者说这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小说,它搅动了深植于许多澳大利亚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作为生活在当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在思考有关自己国家的文化记忆时,肯定会提出这一类问题,诸如:作为一个国家,它已走过了哪些路,或者它会有可能走向何方?有关凤氏家族第一代的回忆始于19世纪中叶,这让读者自然就想起了当时发生在澳大利亚的 “淘金热” 以及在此过程中华人所遭遇的一切。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国政府在南半球建立的罪犯安置地,所以,英国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烙印被永久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然而,1851年随着 “淘金热” 浪潮而涌入的其他欧洲、亚洲、美洲的淘金者们打破了澳大利亚白人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从此,亚文化与带有英国文化烙印的白人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必然。小说中第一代凤在厦门嗅到了有可能 “变成一个富人” 的希望的气息后,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踏上澳洲大陆。可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富人,而只是成了一个牧羊人,白人文化的排他性使他根本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是金矿的发现为他带来了转机,在他和好友帕特里克掩埋另一位被白人杀害的好友时无意间发现了金矿。虽然不久后他门发现的金矿被官方占有,但无意间发现的金子彻底改变了他的境况,他因此而建立起了 “维多利亚凤凰合作社”。这段有关凤的个人经历演示无疑很好地重现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 “淘金热” 以及白澳政策盛行时期的华人的苦难经历。也正是通过对个人经历进行演示的交际记忆的方式,米勒达到了构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记忆的目的。这与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黄源深教授在《从孤立中走向世界》一书中对 “淘金热” 在澳大利亚文化方面产生的作用做过如下描述: “当时的土著文化已根本不可能构成与欧洲(英国)文化传统相抗争的局面。然而,随淘金热潮而到来的亚洲(中国)文化却变得日益强大起来……在一些淘金人集中的城镇,中国文化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与英澳文化并存。”[6]34或许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地位,决定了米勒在选择小说中人物的文化背景和身份时将视角的重点聚焦在了中国移民及其后代的身上。其实,这也是还民族文化记忆以本来面目的一种做法。
但是,身为移民作家的米勒深知移民在澳大利亚经历的 “无根” 与 “异化” 的痛楚,作家将对这一心路历程的叙述用小说文本的形式定格在凤二维多利亚的身上,她形容自己在母亲和姐姐中间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凭借她本人的作家身份,她预见死亡是她唯一的归宿。而有关大多数移民在澳大利亚经历的身份迷失则在凤家第三代人身上凸显出来。这是通过作者截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来反应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不仅在外部沦为众多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在思想意识上也受到重创,一部分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放弃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转而开始憎恨中国文化,更有甚者开始鄙视那些想保存它们的人,并将一切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东西拒之门外,以此来显示他们对纯正的国际主义的承诺。据此,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一种 “错位的文化”。以凤氏家族三代人对自身中国文化记忆的背叛来折射澳大利亚历史上众多移民的经历,也显示出了米勒在充分利用史实,高度概括地进行艺术加工方面的非凡能力,她在积聚能量为小说的高潮部分做铺垫。
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化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开始改变着澳大利亚人的思维,使得澳大利亚逐步走出先前的 “唯英独尊” 和 “唯我独尊” 的误区,迅速地成长、坚强、走向成熟[6]43-44。这个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化处于相对较宽容的 “多元文化主义” 阶段,随着非英裔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澳大利亚对亚洲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50年代,白澳政策已开始松动,到了70年代,澳政府正式提出了多元文化的概念:国内各民族应当在平等的原则上保存自身的传统,并达到共荣共存,共同为澳大利亚的发展而努力[6]48。然而,外部政策的改变并不能迅速地改变各国移民的生存状态,米勒的小说文本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则是通过凤氏第四代人——浪子来完成的。这个生存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的人物感到无所适从,他从小接受的是父亲为他指定的西方教育,而母亲又试图将他拉回到中国文化一侧,结果致使错位感和异化感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他先是烧毁了象征祖宗的家谱,后又把世代相传的宝镜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扔进了钱塘江,可这样的举动都无法消除他的错位和异化感,于是,“放逐” 成了他 “不可逃避的任务” 和生存状态。可逃离祖先文化疆域的短暂的解脱并没有让他真正释然,随之而来的 “无根” 的折磨更令他痛苦不堪,关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不时地在他的身上显现,表面上无论他怎么排斥祖先的文化,可心灵上的归属感还会使她很难完全融入到新的国度,内心深处的家园早已使他具有了拒绝被新的国度的信仰感染的免疫力,那些早已失去的祖先们无时无刻不在对活着的人 “施加着影响力”[10]127。米勒这里显然是想借浪子对凤氏家族祖先的文化记忆来昭示亚文化也应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流文化享有同等的作用,所有进入澳大利亚的文化都不应被视作 “异类”,文化一经移植,就该成为当地的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多元性的本质就是: “不管是苏格兰人,还是中国人,有某种东西是相同的。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把它抹去,而别人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模仿。”[10]20-21因为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吹雨打后所保留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的基点”[11]。
三、“文化记忆 ” 对小说主题的升华
米勒设想凭借文化记忆素材的积累,以小说文本中的文化记忆和想象来影射澳大利亚未来的效果至此达到了,而且是以酣畅淋漓的方式让读者体会到的。文本层面上主人公的个体记忆明显有指向文本以外文化记忆的作用,作者在此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讲述个体的经历来启发读者思考与反思。人们不得不赞叹米勒在运用文化记忆方面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借助某种方法把作为文学现象的历史变成了叙事,即历史事件被作为叙述者的亲身经历或体验过的故事讲述了出来。结果就是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读者都会积极地介入作品中,在接受文本叙事的同时还完成了反观自我的任务,而作品也自然地实现了由个体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文化以及想象在米勒的小说文本中不仅是他作品的主题,同时也是他展开叙事的缘由,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文化记忆和想象的方式,米勒让澳大利亚文化的特征得以具体化和形象化,也使文学在文化记忆和想象中的特殊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为米勒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再现是有所选择的,而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翻版。米勒的小说文本清楚地告诉读者,在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文化身份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无论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多么洒脱,就算他可以洒脱到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进入当代通俗文化的零度态,他也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他的相貌、肤色等特征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在这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选择做文化上的 “无根” 的世界公民或选择与本民族文化记忆认同,只做它的代言人都是不足取的。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 “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心态和全球文化视野的世界公民”[12]。该部小说在这个层面上的深刻意蕴是任何其它澳大利亚作品都无法媲美的。
米勒《祖先游戏》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它帮助读者厘清了澳大利亚历史上中国与澳大利亚彼此间的关系,而且让读者透过文学叙事承载的文化记忆及想象变成了驰骋在澳大利亚文化疆域中的骑手,一路走来既领略了澳大利亚的自然风貌,也在米勒的引领下穿梭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们的母国文化的疆域中,仔细品味各种不同文化的滋味,从而体味到了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国家和民族在一步步形成自己文化特色的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笔者之所以认为该部作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充满希望的作品就是因为读者在解读这部作品时会渐渐悟出:米勒竭力塑造一个亚洲家庭几代人与澳大利亚有联系的良苦用心在于他想告诉人们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寻求与亚洲源远流长的联系,将凤氏四代人这样一个亚洲家庭生活在澳大利亚作为作品的叙述主线旨在颂扬主流文化中的亚文化,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和叙事方式冷静地考察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历史和人类史上长期而复杂的交往,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清楚地告诉读者澳大利亚正在日益变得成熟,她已勇于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的过失。虽然澳大利亚人未必真的能改变对亚文化的态度,但这部作品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 “它将永远改变我们对澳大利亚的看法”[13]。
[1]亚历克斯·米勒,黄源深. 追寻记忆和想象的创作[J].译文,2003(2):57-61.
[2]王霄冰. 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41-48.
[3]简·奥斯曼.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J]. 陶东风,译. 新德国批评,1995(6):125-133.
[4]王霄冰. 文化记忆与文化传承[J]. 励耘学刊,2008(1):227-236.
[5]冯亚琳. 记忆的构建与选择——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格拉斯小说[J]. 外国文学,2008(1):84-90.
[6]黄源深,陈弘. 从孤立中走向世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7]吴慧. “无”与“静”——以《被画者》为中心透视亚历克斯·米勒的小说艺术[J]. 名作欣赏,2009(8):72-75.
[8]Miller A. Chinese Impression[N].24 Hours Supplement,1995-06-25(第6版).
[9]Masson S. Comment on The Ancestor Game[J].Australian Book Review,1993(4):42-44.
[10]Miller A. The Ancestor Game[M].Sydney: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92.
[11]冯海燕. 文化战火中的凤凰涅槃——解读澳大利亚作家米勒的小说《祖先游戏》[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24(2):91-96.
[12]张明德. 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1(3):11-15.
[13]Rimer A. Exiles from the past[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992-08-15(第4版).
(编辑: 朱渭波)
TheAncestorGame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MemoryandImagination
Wu Hui
(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CustomsCollege,Shanghai201204,China)
Today we will again b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ovelTheAncestorGameof Alex Miller for which he has won several awards. All are so vividly described and expressed by an Australian writer who has never been living so long in China. We cannot help asking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in the text concerning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will try to decode the prize-winning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nd imagination based on the German scholar Jan Assmann’s cultural memory theory so as to find out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embedded in it and the role played by it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Australian culture.
culturalmemory;culturalimagination;culturalidentity;sino-australianrelationship
2013-12-27
吴 慧(1964-),女,教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英美文学。E-mail: lisa_happy_hi@163.com
I 106.4
A
1009-895X(2014)04-0353-05
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