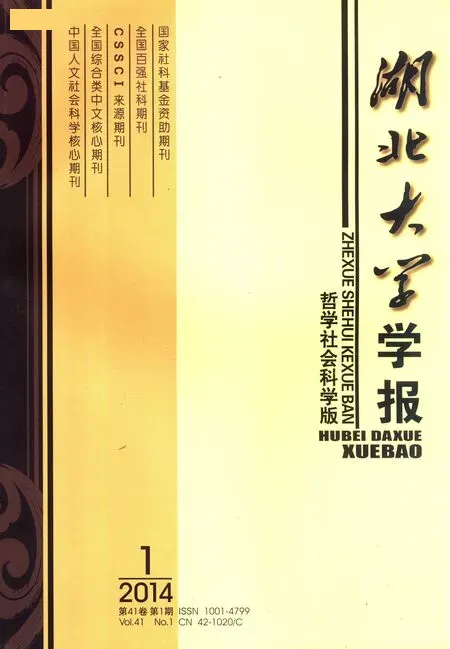论湖北现存碑刻的历史文化价值
2014-04-01李灵玢
郭 莹,李灵玢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碑刻,被誉为“石刻档案”。其价值历来为学术界所注重。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碑刻对于研究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的意义被更充分地发掘,成为“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地域广大,文物资源丰富,碑刻遗存众多。但是,由于大多碑刻长期在旷野中栉风沐雨,不断损毁,数量日益减少。近二十年来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迅速,又加速了碑刻的消失过程。对现存碑刻进行抢救性整理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为了拯救这些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民间的历史档案,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从2009年开始从事湖北现存碑刻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足迹踏遍了湖北省的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38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38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共计116个行政单位。清理出可辨识碑刻近2000块,整理出碑刻文字60余万。这些碑刻,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湖北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学校教育、名贤人物、家族家庭、宗族祭祀、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灾害赈济、水利科技以及乡村社会治安等,由此展现出湖北历史文化的新线索、新内容,成为今日研究湖北区域历史的重要补充。以下试依照其内容分述所发现碑刻对湖北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
一、开拓宗教研究的新视野
湖北宗教源远流长,教派众多,但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和系统的认识,目前对湖北宗教传播与变迁中的许多问题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在目前所收集到的湖北碑刻中,宗教碑刻的数量较多,对这些碑文内容的解读,有助于重构湖北地方宗教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
现存于襄阳米公祠石苑内的一通唐代《襄州重兴报善寺再移葬释迦佛真身舍利年代记》碑,记载了在襄阳报善寺发现梁武帝所赐释迦佛舍利一事。这块碑的镌刻时间至少在唐咸通十三年(873),距今已有1130多年。据碑刻记载,晋代始建的安国善集寺于唐代咸通二年进行重新修缮时,在一石函中发现南朝梁天监七年梁武帝从江南丹阳县移至襄阳的佛舍利三粒并佛小指节骨。此事一时震惊朝野,唐懿宗重赐寺名“报善寺”并建灵塔以供奉佛骨舍利。碑刻所述揭示了东晋至南朝期间襄阳在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地位。让研究者得以以全新的目光,审视地处华中腹地的襄阳在文化南北交汇地理格局中曾经有过的枢纽地位,揭示其在佛教传播于长安、建康、巴蜀之间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时佛教大师道安曾率弟子四百南下襄阳传播佛教,一居十五年,在“深居创新学”的同时大力弘扬佛法[1]。碑刻反映了在道安师徒南下之后,襄阳地区佛教发展所进入的一个崭新阶段。正是由于襄阳曾一度成为香火兴盛的佛教中心,东晋时在中国佛教传播中享有崇高地位,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才会下诏将佛舍利移至襄阳安国善集寺即后来的报善寺内。虽然现今报善寺已难觅踪迹,但这块石碑的记载无疑拓宽了宗教研究的视野,对重新认识湖北佛教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古襄阳类似,随州大洪山在中国禅宗史中的地位历来亦未曾引起过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国早期佛教传扬以律宗为主,故庙以律寺为多;唐代以后,禅风大开,故文献一般反映湖北佛教自唐以降,以禅宗为主流,其中又以临济、曹洞二宗为盛。而随州大洪山自北宋至明初数十通圣旨碑,却极为难得地记载了随州大洪山保寿禅院由宋第一、二、三、四、六、十一代禅师至明第一代禅师奉诏入寺住持的详细经历。首块《宋故随州大洪山十方崇宁保寿禅院第一代住持恩禅师塔铭》碑就记载有:“丞相韩公尹河南,延师住持篙山少林寺。席未暖,绍圣元年诏改随州大洪山律寺为禅院。……部使者奏请师住持,已而垂相范公守随,复左右之。”记载直至“绍圣元年(1094)”,即元佑二年(1087)在哲宗下诏全国“革律为禅”并所有佛寺都冠以“禅”名七年之后,随州大洪山律寺才“改为禅院”,纠正了历来研究佛教的史家认为国家诏令与民间改禅如同“响之应声”的一贯之见。此外,研究禅宗的学者一直以来还认为禅宗诸派之中,曹洞宗为最不与朝廷及权贵势力相往来的一宗,然而碑文在以上所引之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记载:
崇宁二年,有诏命师往东京法云禅寺,从附马都尉张公请也。师志尚闲远,安于清旷,曾不阅岁,退还林泽。朝廷重违其请,听以意行,径诣篙山,旋趋大阳。属大洪虚席,守臣念师之有德于兹山也,五年再奏还师于旧,因辞弗获,复坐道场。凡前日之未追暇者,咸弥纶而成就焉。师勤于诲励,晨夕不倦。缁徒辐凑几三百人。既遐振宗风,而自持戒律严甚,终身坏衣,略不加饰。张公虽尝奏赐紫方袍,卒盘辟不敢当。故权贵示欲以师号言者,皆无复措意矣。
由这些碑文可知,即使如曹洞宗的禅宗大师,与当时的皇权、官府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仅主持由中央调派,受丞相邀约主持嵩山少林,建寺也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不仅遵驸马都尉张公礼请,大洪山报恩禅师曾于宋崇宁二年(1103)奉敕前往东京法云禅寺担任住持,还于崇宁五年(1106)经地方官员奏请,再次回到大洪山重任住持,驸马都尉张公还曾奏请赐报恩禅师紫袈裟以示尊崇。与朝廷权贵往来不可谓不密。其间志尚闲远,退归山林,对权贵以己号向皇帝进言不以为意,辞谢紫袍馈赠等等,皆似有刻意为之的痕迹。碑文的记载显示了湖北曹洞一系与政权之间若即若离、半推半就、貌离神合的关系,为研究者更加深入地认识曹洞宗风提供了新的视点。
从唐末至北宋初的近百年间,曹洞宗稍显颓势,由于有芙蓉道楷、洪山报恩等一批优秀传法人物的出现,曹洞宗走向中兴,靖康二年《随州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十方第二代楷师塔铭》碑记载:“今庆预在大洪,禅子至二千;清了在长芦,正觉在普照,亦至千众。盖天下三大禅刹,曹洞之宗至是大振矣。”由于大洪山成为曹洞宗传法中心,以至于现代日本佛教学者两度到洪山寺寻根访祖,可见大洪曹洞宗的影响之深远,而碑刻所记,为湖北曹洞一系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除佛教以外,碑刻对湖北的道教地位记述亦甚有价值。例如武当山永乐十六年《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命修武当圣旨碑》、嘉靖三十二年《御制重修大岳太和山玄殿纪成之碑》等,都表明了皇帝对武当道场的重视,均可作为第一手史料与现存明代诸种《太和山志》等文献互证。
二、提供人口迁徙的新线索
明清时期,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的空间流动,造成湖北大部分地区“生齿日繁、流徙日聚”、“五方杂处,家自为俗”的特殊景象。鄂西山区及相邻的川东北、陕南、豫南山区是当时流民、移民落居的中心地带之一。湖北襄阳习家沟万历乙巳年的《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就记载:“五代中,其子姓稍稍流寓,不获安其故土,而客豫章者最繁衍。我明成化间,国士四世祖升鹗,复自豫章归襄,而卜居于城南三十里曰虎尾州者止焉。”其中的“豫章”即今江西南昌一带。建始县嘉庆年间的《由氏墓碑》也记载其祖上由江西迁往湖北的经历:由氏祖先本为江西瑞州府人,清初以骠骑将军之职到此镇苗清疆,其后便在此落户繁衍,“士族蕃盛,相传有半街之说”。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这是在四川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麻城孝感乡”也是很多四川人家谱中祖籍的所在地。“麻城孝感乡”从地理名称、历史记忆,也渐渐上升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文化符号之一。但是多年来,“麻城孝感乡”是否真实存在,学术界一直争议较多,而明末清初麻城名士邹知新所作《都碑记》解释了这一疑惑,其主要记载如下:
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云是古之孝感乡都。昔麻邑存四乡,独孝感乡有遗碑。耆老谓之世宝也。今刘氏后裔珍护之,可谓知所重也。新龆时,闻故老言:“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都府、面坊多逢回禄,惟都碑、米研犹存,甚异!”……惜新幼时未知,不知究辨。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害。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今民散久矣,百遗二三,莫一能奉。日不见□龠渔歌,夜无柝击双六,烛火孤点。新叹曰:“名乡耳!岂可独忘此乡乎?”都门之阳有碑碣,额镌:“邑东南七里磨子场,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背阴有字,铭文漫辨。……彼其近周,破垣环故井,荒草冠遗坛。往牍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绕碑偕刘氏多居焉。访问之,曰:孝都离邑七里,究之,乃知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嗟乎!新幼所闻之,今访其墟,观其金石亦相合,然益信乎!恐其古胜久淹,予谨述其事,存其传者耳,以示不朽矣!
从文中可知,“孝感”之号始自汉代,因赵氏至孝受封宗正而得名,与汉代“举孝廉:”之制合。旧时麻城有“四乡”,独孝感乡存有遗碑。而自宋、元以来,因人口过多,“常为乡之患害”,明初经由朝廷倡导,乡人不畏川道艰险,多往居之,后又因向四川移民过多、人口锐减,孝感乡撤并;而也正因为有记录古碑的邹氏《都碑记》的存在,证实了这个曾经作为多少迁蜀者心目中永远的故乡,并非虚无飘渺的所在。
“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这两次大的人口流动,并不限于鄂川赣三个地区,而是以这三个地区为主线,带动了江浙闽广豫皖陕滇黔等地的人口迁移。嘉庆十三年南漳县板桥《陶家沟族碑》记载:陶氏原籍河南汝宁府鹊山县,明成化元年始迁湖北襄阳南漳。咸丰八年利川县《胡王让墓碑》介绍墓主胡王让原籍为广东嘉应,因前来利川经商而落户湖北。光绪元年南漳板桥《新建陕西桥碑》解释“桥以陕西名,因山得名也。山何以有陕西?因人得名也。明中叶,我始祖自陕西凤翔迁此,不忘其乡,遂以其省名名之。”碑刻具体入微地记述了桩桩件件移民细流经由不同来源汇往湖北的活动,为今天研究明清移民史提供了真实、确切、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三、发掘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史料
“湖广足,天下熟。”民谚反映出明代以后“湖广”成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和输出地,而这与当时江汉平原一带低地垸田开发、水利治理密切相关[2]895。
湖北境内江汉平原向来为水患多发区,为防范水患对低地垸田的威胁,兴修堤防一直是地方治理的头等大事,而在多丘陵的山区地带,则又存在引水灌溉的问题[3]311~315。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就曾对湖北水利及政府在水利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而多有论述[4]。而现存数十通湖北水利碑刻既反映了官府作为水利工程中的主导力量,规划、修建并维护整个水利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叙述来自民间的士绅、百姓通过集资修建并配合承担各自区域内的水利工作,如何用水、分水,形成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乾隆四十八年《上谕毕沅疏通水道碑》,记载了皇帝传谕毕沅责令地方官留心查察水道,以免居民在其上搭盖房屋形成阻碍而引发水灾,反映了中央对水利问题的重视。光绪二十二年江陵县《荆州万城堤上新垲工程记》碑也记述荆州府知府余肇康在听闻“新垲堤段矬裂深至二丈许,长至四十余丈,一时居民相传说甚恐”后,积极组织人员重修新垲堤段。嘉庆十三年《江陵县郝穴范家堤建闸记》碑,记载“荆州知府松亭郡伯率知县李若嶂周历各垸,详核淹渍情形,勘得郝穴汛有熊家河可引桑湖汇归之水,直接出范家堤”,遂在郝穴建闸。作为历史上水患频发的“重灾区”,湖北襄樊地区出土的二十七通碑刻乃是研究该地水利问题不可多得的民间史料。其中同治年间《重浚襄渠记》碑记载地方官府为了重修襄渠,晓谕地方乡绅儒士担任渠道总理及各渠段监工,令其“通力合作,计亩派工”,渠修成之后“分四段,由绅耆公选勤慎晓事者十二人,每年以四人充当四段值年渠长,经理渠事”,展现了官民合作的水利模式。而道光十年《三瑞亭记》碑附有修建三瑞亭时的本镇官员、增生、绅商个人及会馆、票号等商业团体、宗教团体的捐款记录,为了解湖北“水利共同体”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地方政府除了在水利建设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在解决水利纠纷的案件中也扮演了必不可少的仲裁角色。光绪三年,荆门知州李辀为解决水利纠纷颁布告示,所立碑除介绍颁布告示的原因外,还在碑阴处订立规约十条,对主沟灌溉的田地、摊派银两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以防水利纠纷再起。道光十五年钟祥《夏家垱放水牌》、同治六年荆门《具息碑》、同治十三年荆门安团《勒石刊碑以杜后患》碑等,都是官府为解决水利纠纷建章立制所立碑石。不同于传统的文献,这些石碑刊载的内容生动地再现了湖北地区围绕水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重构湖北地方水利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随着农林业的发展,过度开垦之弊逐渐显现,地方生态环境渐趋恶化。湖北钟祥咸丰十一年《为示禁事》碑就记述了该地因长期的乱砍滥伐、挖山开堰,使得山林“渐为淤池,而高岸为谷”。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破坏的更为战乱。据碑刻记述,湖北境内自明末以来战争不断。南明永历九年兴山县《圣地行宫之碑》,记录闯王李自成之孙李来亨在兴山坚持抗清达十三年之久。清咸丰十年武当山《绩冠云台碑》,记录了时任均州知州的唐训方扑灭红巾军起义,在武当山擒斩红巾军头目高二现的过程。而嘉庆三年兴山县榛子乡《永古不朽》碑,更记述白莲教“至山东山西河南陕川湖广以来,掳劫挠杀,无不警惧。今者本境,连骚两次”的惨况。嘉庆二年利川《如膏书院碑》,记述“川匪窜境,焚扰馆舍,为灾数载”。咸丰八年京山《置惠山书院膏火碑记》,记述咸丰间太平天国军过境,“焚掠一空,商典不存”。而同治九年湖北鄂州灵泉寺《永垂示禁》碑则记载了这些战事的灾难性结果:“兵燹之后,树木耗尽”,对地方造成了极度破坏。
为了保护山林,各地方政府在灾难过后纷纷刊刻护林碑、订立规约。嘉庆十七年鹤峰县《古银杏树碑》就记载该地的银杏树畅茂条达,历经多年而不朽,规定地方人士“勿剪勿折”。光绪十三年宣恩县《芋荷坪护林碑》为劝导时人封山育林,特镌刻护林韵文:“伐人树木,情理两亏,罚落演戏酒常随,宜各受其业,莫占莫凿,后有行者,仍照前规。”宣统元年恩施黄泥塘《护林碑》警示:“自示之后,倘再有违反禁令,偷伐树木者,准告该团,约地邻事主协力扭送来县。”神农架咸丰九年《严禁山林碑》规定:“倘若日后再擅伐者,罚戏一台,罚钱十千充公,酒席十张。”同治元年《严禁山林碑》要求对林木进行严格保护:“再入偷砍,有犯者,罚钱八串文充公,酒席三台。”光绪四年巴东县《龚家山碑刻》:“砍伐者罚百斤猪羊祭扫。”这些规定和劝导反映了古人护林育林的先进理念。古人亦曾有意识地植树造林,如鄂州灵泉寺《永垂示禁》碑就记载当地寺庙僧侣在兵燹之后,“遍山栽植小树,费尽心勤,不辞劳□。惟冀树木森上,复还旧日之禅林,以为一邑之胜迹”。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肯定中国文化渊源中“自然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古代自然环境概念成熟较早,而灵泉寺碑刻在显示中国古代先进的生态保护观念较早出现的同时,亦反映出这种意识仍局限于一定精英群体,并未在民间得到普及。碑文对附近村民“以其耕牛牧放山中”,以至树毁秧践,提出婉劝。这些关于地方生态保护的文献不常见于正史,而碑刻却向我们展现了民间生态观念的文化遗存,从中反映出的科学思想内核,对于今天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启示与借鉴价值。
由于明清时期湖北水利的兴修,农林的发展,促进了湖北经济快速增长,商业也逐渐发展,到清中叶已极趋繁荣。如襄阳樊镇,地当孔道,历来商贾荟萃。乾隆三十九年《创建三官殿碑记》就载有为筹建三官殿进行捐资的共56家商号名称与捐资数额,展现当时樊镇营业格局与各商号资金状况。《重修山门门面乐楼碑序》介绍当地重修山门门面的捐款情况,开列了涌泉号、广信典、楚兴号、泰昌号、元丰号、乾复号、致祥号、大兴号、晋和行、隆泰行等共计60余家商号,亦反映出商贾辐辏、市面兴旺的景况。随着商业贸易日趋繁盛,建章立制成为保证市场正常运作的需要。清朝南漳县《钱色章程》碑,针对当时甘溪巡检地方与武镇通商过程中,有商人私钱搀和制钱作九折、作八折,影响当地钱币正常使用,所谓“行商坐买,朝三暮四,持筹握算”的现象,官府规定:“自光绪十年以前,无论当价会借庄钱,皆以九八钱票归款。自十年至二十年,票项皆以八折归款,若是大钱过项,仍照大钱归款。自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票项皆以六折归款。自二十七年以后,买卖来往通用九八五典钱,出进一体,永不准再出六折之票。倘有再出者,□出受罚,所有陈票一并收清□定。”光绪二十九年南漳巡检甘溪《谨遵县示碑》,记载甘溪与武镇通商,“武镇钱票先有九折八四之分,甘溪亦因变更,嗣后武镇改为九八”,因“有典钱市钱之分”,“市钱买卖其价较典钱甚昂,乡人贪利始而携钱回家,勉强挡抵,继而一倡百和成为风俗。有以市钱市票,作八折者,作六折者,其害不可胜言”。针对此一积弊,政府勒石规定:“嗣后除完粮找税缴捐外,无论何项使用,务各遵用九八五制钱,不准再有八折六扣等项。各邑其以前当价借项庄钱会款,仍照各年折扣算清,以八五钱归款,以昭大公而免两亏。倘敢违禁苛勒,一经告发或被防闻,定即究不贷。”这些有关银钱制法和流通的制度条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代金融运作。同治八年宜城流水莺河《按亩纳税碑》规定:“每征银一两,加火耗一钱一分、征比一分、公公随封一分,余银贰钱四分存房,作解办理工食,合共三十八分外,竟无别派。嗣后完纳,无论耆绅贫富,一体遵照年银价低昂扣算完纳,书役不得分外苛索矣。”
光绪二年鄂州《遵示勒石》碑,记载汉川县正堂查处县市煤炭牙行勾串奸商的不法行径,并立碑示警:“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拏案,从严究办,决不宽贷。”钟祥道光十四年《永行严禁》碑载官府规定:“一、永禁大钱折换私钱。擅敢违示,严加治罪。一、永禁米粮湿水。一、永禁猪肉灌水。一、永禁柴炭发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商贩陋习,以及官府对这些奸邪不轨之举的惩治。为维护商业秩序,地方商号和绅耆也自发组织行会,订立规约。清朝兴山县《公平交易碑》记载丁大经在县境桑林坪通往郧襄的古大道处开办商市,后因商户渐多,奸邪丛生,于是共立规章,勒于石碑。碑上还刻有一把标准尺子,除示“公平交易”之外,对了解清代标准度量尺寸也提供了宝贵的直观资料。道光十七年钟祥市张集镇《盖闻宰割有常职》碑,经由地方众姓公议,对屠宰、木竹等市场经营行风和价格作出规定,如“称以每斤十六两为鼎,虽肉至贵,不许短少分毫”,“他如过称者亦不可私计用诡”。道光六年京山县《典当行规》碑,由绅耆保甲同列,为“清源流除积弊”、“正风俗儆刁健”,特立十条典当规则,规范典当行为。道光二十九年来凤县《卯洞油行章程碑》,针对当地桐油商贩进行掺兑出售的行为,订立章程以维护客商利益:“尤恐乡愚有油上街出卖,防有枯脚、水渣等弊为害客商,有亏成本,所以凭行经理稽查,消除弊端。定以桐油每篓七十五斤收领,用钱二十四文,不敢有二。会特刊板重碑,永定章程。”而蒲圻县光绪十三年《合帮公议》碑记载,由于咸宁地区茶业兴盛,崛起不少茶叶商家、茶庄以及运茶车帮,羊楼洞地区以茶为生者渐多,特聚本帮共议,建章立制,议定力资行佣标准,要求“额例恪遵,切勿恃强,越规蹈矩”。这些碑刻上规章,为研究晚清商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四、呈现地方治理的新视角
现存碑刻中有诸多官府所立规约,意在威慑防范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发生。乾隆三十年襄阳府宜城县正堂立《奉宪永禁》碑,为“驱恶除匪,保善安良”,规定“如有外来匪类,三五成群,在境强乞滋扰。及本地不法之徒,仍蹈前辙,未至仲冬,即放之六畜”,“许该地士民人等,协同保甲,拴锁赴县,以凭按律从重治罪,决不姑宽。”嘉庆二年谷城县正堂颁布的《永尊县示》碑规定更为详审:“一、禁酗酒打降及窝留匪人,犯者罚戏三本;一、禁厂内竹木□顶恐有鼠窃,犯者罚银十两;一、厂有远近,所起牌竹不许□窃,犯者罚五两;一、街内房屋招佃非人,即连地主公同并罚。以上数条各自守分遵禁,有恃强不服者,即送县呈禀惩治。”道光八年谷城县《奉示严禁》碑叙述“不法土棍流丐三五成群,结党恶讨恶要”,“种种不法,殊堪痛恨”,规定嗣后如再有恶行,许该保甲人等“击解赴县,以凭按法究治”。嘉庆十一年监利县《弥盗条规》碑、道光四年襄阳武镇《奉示永禁》碑、道光十八年京山县《遵示禁碑》、光绪十四年南漳县《正堂胡示》等碑刻都公示详细规约,以保证社会治安。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维系和支撑国家的,除县以上的官治行政力量外,县以下治理中更多依靠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组织。碑刻反映了这些基层社会组织也通过制定乡规民约来规范民众行为。光绪十年襄阳《稼穑维艰》碑中对田间农事和地方民俗都作了细致规定:“一议,不准包娼窝赌,宰杀耕牛,花鼓淫戏,倘有不准者,定即禀官究其惩。一议,不准撒放六畜,若有违者,立即打死勿论。一议,不准铲青草、打秧蒿,倘有不遵者,罚小戏三本。一议,不准春季摘豆角、小麦,地内拔大麦并拔豆秧,若有违者,罚小戏三本;一议,不准偷搬包谷,己种者亦不准私搬,若有违者,罚钱二佰纳甲。红白事,不准乞丐滋事。一议,不准粟谷地内割莠子,凡有豆秧,概不准割,若有违者,罚小戏三本。一议,不准捡野棉花,并五谷概不准捡,若有违者,罚小戏三本。一议,来历不明,不准窝藏,并抢捡庄家人等,若有强抢者,定将本主重罚。”清代咸宁《塘岭古井碑》针对当地村民不注重用水卫生,影响健康,规定“上井得清洁饮”、“中井洗菜浣衣”,如有干犯,“处钱三千六百文”。湖北为“千湖之省”,堰塘星罗,港汊纵横,渔业发达,而有人行放水竭泽捕鱼之事。咸丰十一年南漳县东巩苍坪村《古渠碑》痛斥这种行为是“一夫作俑,致万姓受殃,贪己口腹而忘人身家性命”,特勒碑示戒,再有挖沟放水捕鱼者,将送官纠治。
明代伴随着里甲制度在地方的推行,宗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民间成为乡村自治的核心。在湖北,宗族组织的形式主要是以宗族祠堂为中心发挥作用。嘉靖年间蕲州《顾氏祠堂记》碑记载:“楚俗号称朴啬,其民淫于外鬼而略于祀先,蕲顾公业诸生时则已中非之……此何以教民且合族哉!于是谋置祠……楚自是愧祭寝矣……楚之大夫家有庙也,顾公风之矣”。明中叶以后,建宗祠者渐多。乾隆三十二年南漳县巡检《唐氏宗祠碑》中讲述了建宗祠的原因:“我始祖唐清冠始迁居斯,今人经乡代历百余年,未建宗祠。则各拜扫于荒郊之,无以序之列矣。以陈奠献之礼且而远移近居,恐失宗派。”于是“七代孙等公议各捐资财,修立祠堂以奉宗祀”。乾隆五十二年竹溪县中峰镇《甘氏祠堂碑》、同治四年襄阳法龙赵山村《王氏祠堂碑》、同治十一年枣阳吴店镇《傅家祠堂记》、光绪七年郧县马安镇《汪氏宗祠碑》、光绪十四年郧县南化镇《周氏祖祠碑》等,都记述了修建祠堂的原因和过程,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湖北地区敬宗建祠的原委和动因。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将儒家礼治贯穿社会,按照血缘亲疏关系,礼法由近及远地在宗族中述及。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家庭与宗族为核心,但并不限于家庭和宗族,而是像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许多同心圆,就“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由此形成一种“差序格局”[5]26。宗族由血缘为纽带,以尊长正面的德行榜样为民众的行为进行引导,费孝通由此认为在这样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社会中,“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5]68。这种教化对民众行为的规范往往能够做到和风细雨,具体而又细致,如光绪元年随县长岗镇洪山坪村《老屋湾界碑》警示:“船户不凭良心,恐怕风□。窃娼聚赌逞雄,难守祖业。挖墙削洞行凶,牢狱终身。僧道出言惑众,恐受非刑。宰杀耕牛,子孙必绝。捉乌龟钓虾蟆,无屋可住。所有淫乱作恶者,恐有报应。在衙门中修德者,子孙必发。凡田中有坟茔者,宽留一点。若打三春鸟兽者,望母归来。争田夺界闘殴者,忍让为高。”言语委婉,核心是劝善积德。
宗族在宗法基础之上,利用血缘将个人、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对族人劝仁义、敦和睦,而对违背宗规乃至国法的行为,则予以强力制裁。光绪二十八年南漳薛坪栗林坪《以亲九族二碑》:“凡我族人各怀忠义之志,念先人一脉相传之德,合起一团,共胆同心,……倘敢违不遵,该族长、族正传至祠堂,重则究罚。……族门有年精力壮者不务正业,或好讼多争,或游荡好赌涓败家产,以致流离失所,辄在祠堂霸住,毁坏屋宇,即时逐出。”对于吸毒、赌博等恶习,宗族也加以惩戒。光绪二十一年蒲圻《永遵无违》碑规定,牌赌及吸食鸦片:“凡刻石后有犯,送信者赏钱二串文,一经捉获,罚酒四席,钱八串文。公同着议,还要送回惩治,无论亲疏,决不徇情。”光绪二十九年南漳县《永远禁赌》碑则力斥“赌博之害,小则废时失业,大则荡产倾家。甚至一朝赌输,或流为盗贼,或愁急自尽,若不严禁,流毒无穷。”要求“及素喜赌博之人,务即痛改前非,各安本业。……倘有敢怙恶不悛□,仍蹈前辙,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从重惩办,并将开赌房屋暨所赌财物,照例查追入官,其有赌输财产到官自首者,查审得实,即将所输财产,断还自首之人。”道光二十年宜城《请遵示各条》碑规定:“禁开场聚赌,犯者送官究治”,光绪二十年通山县《三禁碑》:“合保严禁烟馆、赌博、宰剥、窝屯匪类、抹牌掷骰一切等事。如违重罚,倘不遵者,送官究办。”在示禁的同时,对于族中子弟走正途读书求取功名,宗族也给相应的资助以资鼓励,如《李氏族碑》规定:凡族中有诵读者进学帮钱两串,乡试帮钱三串,京试帮钱四串,如□中者俱帮钱五十串。这些对于宗族成员或乡民恩威并施的教化条例往往不见于任何书籍文档,而碑刻资料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选择。
湖北历来重视人文教育,乾隆六年鹤峰县《义学碑记》碑:“从来先养后教,……无如蚩蚩之氓,止图耕种,罔识诗书,粗鄙之风,顿难转移”,“颛蒙之聋聩何自而开?固陋之人材何由而振?偏隅之文教何籍而兴?”于是提倡重学兴文,“先为关内举设义学,延请通儒,教习文章”,“一时济济师师、横经而受业者,皆沐浴圣人之化”。明清时期湖北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二十年荆门《祖老夫子创建龙泉书院碑记》记载,龙泉书院仿古嵩阳、岳麓诸书院而建成,“凡楼堂、门庑、斋舍、庖库之类,靡不毕具”。黄冈有问津书院,清刘泽溥《捐置问津书院祀田碑记》记载:“去黄冈北九十里为问津书院,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湖至此,有‘子路问津处’五大字石刻。其水为孔子河,其桥为孔叹桥,其中高阜为孔子庙,相沿既久,累朝递有废兴。”广提学使蒋永修作新洲《重新问津书院碑记》,记载他有鉴于当时书院“不过力孝弟,明仁义而止”的局限,进而要求问津书院之设,要学习当年孔子“处极困之境,而汲汲不敢或停其辙,……宁迷津而不悔”的入世精神,并进而论云:“津有往来之义焉,格至诚正,礤近者家国天下,其远者是贵修身,为之津以往也。”要求书院起到当代“孔子使子路问津”的作用,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津要研修之所,成为读书人走向社会发挥作用之前人格、精神、学养培育成长的圣地。碑中还记载了问津书院自康熙二十九年(1697)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百余年间,培养新洲万氏一族共有贡生35名,举人39名,进士11名(其中翰林4名),秀才约205名。蒋永修于是感慨:“惟楚有才,雄长天下,独黄为之冠”,这些记述,为研究传统教育理念及湖北黄州地区的教育、人才乃至名胜古迹的状况提供了资料。
这些有关教育教化的碑刻还时时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如嘉庆六年利川《如膏书院碑》记载其“周历劝捐,乃得酬金置产,以作学田,核计每岁收入,除取馆谷之外,余尚足为一切经费之需”,从经济角度对研究古代教育经费的筹办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咸丰八年京山县《置惠山书院膏火碑记》则记载该“书院向以发典生息三百余两为生童膏火之资”,而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军过境,“焚掠一空”,旧有膏火费用来源枯竭。而有意思的是碑文记录太平军失败之后,该地“爰稽案牍,控诉胁从者如鳞,而当时或富逼无奈,愚出无知,尽取而诛,非所以体皇仁、召天和也。乃酌甚可原,予以自新,薄从金赎,惠我士林,凡此罚锾,统交邑绅尚培源、肖士彬经理生息,计自是年秋至戊午夏,共积存钱八百余贯,置买瓦房二栋,水田二十九亩六分,蔬圃二十一块,每年收租钱七十八贯三百文,以为生童膏火费。”生动地记录了太平军失败后乡绅对众多如鳞的“胁从者”的反攻倒算,所收罚金竟,年入租数十贯文。对太平天国事件的研究亦甚有助益。
然而更多的时候,为教育提供支撑的还是宗族的公产。宗族的公产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公产除用来修缮祠堂、祭祀外,赡养、接济族人是其又一重要功能。很多宗族碑刻对族人之间的互助及赡养接济都进行了规定。光绪三年襄阳《王氏宗祠记》碑:“凡族之老者、弱者、孤者、寡者、贫不能葬娶者,周恤之。”光绪年间襄阳习家沟《李氏族碑》规定则更为具体:“凡族人有孤寡无靠者,临终时帮钱三串以作安葬之资,若有半亩地者则不帮。凡族间有娶婚无出者,成婚后帮钱四串,为立禋祀之计,若有一亩地者则不帮。”光绪三年咸丰县《严家祠堂碑刻》为一组碑刻,共24块石碑。其中有宗规十六条,每条一碑。标题分别为:乡约当尊、祠墓当展、族类当辨、名非当立、宗族当睦、谱牒当重、闺门当重、蒙养当豫、姻里当厚、职业当勤、赋役当供、争讼当止、节俭当从、守望当严、邪巫当禁、四礼当行。此外,还对宗祠规序、首士戒规、祀典规则都进行了规定。最后两块碑分别规定了宗族的奖惩规则,如“祠中公事,办事者不可从中图利,违者议罚。”“祠中无事之时,不得因别事而用祠中酒食,违者追赔。”等等。
地方治理当然不限于汉族基层,对于边远地方,碑刻有涉及。鄂西容美土司田氏,为明清之际当地最高统治者。现存记其事者仅《容美纪游》等极少文献有涉,其生平大多阙如。而鹤峰县城后坝的容美土司田舜年、田甘霖、田九龙墓碑,以及《容美副总兵官桂崇皋墓碑》,对他们的事迹和官职都有所记载,反映了容美土司从明到清身份地位的变化,对研究容美土司史也有重要价值。
湖北历代碑刻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由于贴近地方和基层社会,这些碑刻为方方面面提供了有别于一般文献的历史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湖北地方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证据。
湖北碑刻整理历史悠久,前人已有《湖北金石通志》、《江夏金石志》、《武昌金石志》、《咸宁金石志》、《黄州金石志》等著录和整理成果问世,今人也有《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荆门碑刻》、《兴山古今碑文选》、《黄州赤壁碑刻集》等地方碑刻整理成果,但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碑刻还未涉及。且由于碑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有关部门尚未全面的地进行保护,多数碑刻散落野外,历经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许多珍贵的碑刻已经难以辨认甚至风化破碎,不少有价值的石碑成了桥板或路石。它们的损毁,是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亟待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保护,认识碑刻作为历史记忆的研究意义,发挥碑刻文献在湖北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与价值。
[1]释慧皎.高僧传: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周积明.湖北文化史:下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3]章开沅.湖北通史:明清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魏丕信.中国的水利周期:以16至19世纪的湖北省为例[J]//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981,68.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