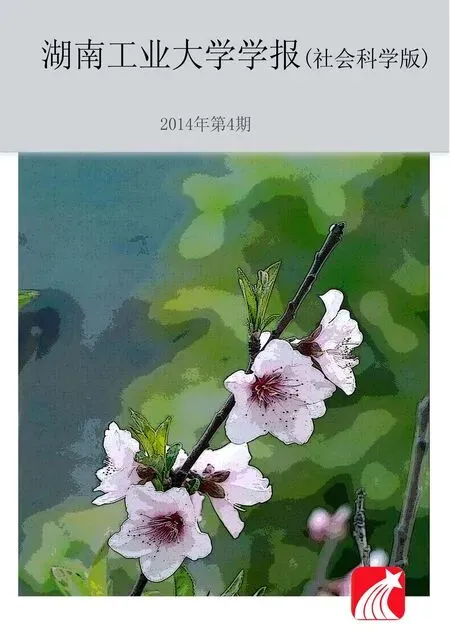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2014-03-31王志谋廖元旦
王志谋,廖元旦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2.双峰县第三中学,湖南 双峰 417700)
1990 年代以来,文学与启蒙纠缠不清的关系受到诸多质疑,“启蒙”作为一个大词,被越来越多的人谨慎规避。有学者甚至公开宣称与启蒙划清界线,以此来标明自己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启蒙的神圣地位被颠覆,变得面目可疑。但正如童明所归纳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丰富多彩,并非铁板一块……启蒙是多样的。”[1]统一的启蒙运动分崩离析,理性变成了独裁与专制的新神话,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启蒙思想,相反,在身体、欲望等不加节制的宣泄导致精神日益平面,深度模式被解构与弃置,思想日渐远离结实的质地而变得悬浮无根的语境下,重新清理启蒙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生发的原初语境,关注主流启蒙途径外的另类启蒙方式提供的可能意义,对缓解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不无启发。
一“启蒙”中的感性维度
“启蒙”一词,在启蒙思想最初产生与形成的国度,意义各别。enlightenment(英语),eclaircissement、luniere(法语),Aufklaarung(德语),或指光亮穿透阴霾,或指思维由暗而转明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不局限于理性,尤其不局限于工具理性。启蒙(enlightenment,光明)最初只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关于人类理想状态的认定。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启蒙的设计中,就有主张非理性的一翼(如蒙田)。理性将这一价值观加以系统化,这一被系统化的启蒙蓝图反过来进一步依赖于理性,以致理性片面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大一统的启蒙体系观,这只是启蒙的误入歧途,而不是启蒙本身的问题。
回顾西方思想史上,康德与福柯在不同时期得到广泛认同的启蒙定义,对这一问题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将理性置于极高的地位,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的途径在于:“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并接着指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非常重视理性。但是,应该注意到,康德是针对中世纪宗教伦理的束缚而提出理性概念,以理性的思考来摆脱神对人的禁锢,进而建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人的理念。在他看来,人是多维度的,而多维度与总体性的人所根植的原理在于自由,自由与理性休戚相关。康德是在“自由”这一意义上突出理性。换言之,理性固然是其启蒙思想的重要一环,但却绝非惟一的一环,“多维度”才是其所追求的目标。如果考虑到康德深受其影响的休谟对理性与情感的定位,也许能对此作更好的理解:“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3]也就是说,理性不过是实现启蒙的手段,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实现、人的感性力量的舒展;而理性的片面发展,不过是对启蒙本末倒置的挟持。卢梭这样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学者同样被归于启蒙阵营,就说明了启蒙的包容性。不可否认的是,紧跟蒙昧时代之后的启蒙时代,缺乏的不是情感而是理性,这一背景导致了康德的启蒙定义向偏于理性的一极发展。
康德之后,面对理性的偏至,福柯站在后现代立场对其启蒙概念进行了批判和重建。他认为,启蒙与现代性的真正关联不在于康德注入其中的理性本质,而在于启蒙具有一种重要功能,即“对现实性进行自我追问”。这一定义解构了启蒙大一统的体系观。他认为应合理地对待并适度地运用理性,而不将其视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真理与惟一尺度。并且,他将启蒙视为一种“气质”,它是“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气质的东西。”[4]这样,启蒙进一步与人的主体品格相关联。
所以,启蒙并不等于理性,应该受批判的并不是启蒙本身,而是被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绑架而误入歧途的启蒙途径。从本质上讲,作为动词的启蒙,应是一种被包括康德和福柯在内的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所认可和践行的行为方式:摆脱权威,敢于认知。作为名词的启蒙,其焦点则应在于“人”,在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解放,在于从休谟、卢梭到尼采的众多启蒙者,在怀疑理性的角度下对完善人性的呼唤。归根结底,“人”才是人自身的目的。因此,从最终目的来看,关乎感性的启蒙才是完整的启蒙。
启蒙拒绝盲从,启蒙关乎感性,这正是本文谈论王国维启蒙思想的出发点。
二 清末的启蒙思潮与王国维的启蒙思想
(一)清末的启蒙思潮与小说的功用观
“以启蒙思潮为主导的理性主义在最初正是以感性的觉醒为标志的,因为启蒙的根本使命正在于对外在理性权威的解构,在新理性权威尚未长成的前提下,担此重任者非感性生命之觉醒莫属。”[5]从晚清启蒙主义的传统源头来看,晚明李贽的童心说、陆王哲学“心即理”的主体性原则等,都张扬了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主体主义立场,形成了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在清末启蒙思潮的开启者之一龚自珍那里,“心力”这一概念中同样包含了情与理这两个层面,其后的洋务运动执著于器物层面的变革,客观上促进了科技理性的发展,情感的维度遭遇冷淡。
启蒙思潮在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亡国焦虑中开始加速发展,对自由情感关注的额度进一步被随落后焦虑而膨胀的理性侵占。这时新民思潮开始出现,在强国梦的支配下,国民性问题作为理性批判的对象与唤醒理性的场域,在器物、制度之后被集中关注。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情,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6]即因国之腐败而注目于民之奴性,因奴性而施自由之药,以“除此情”而使“中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这一思路成了清末启蒙者普遍的思维逻辑。从其启蒙的动力学来讲,救国,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被置于中心位置,换言之,国民是在救国的名义下被关注。因此,作为自由根基的理性,特别是政治(工具)理性成为其启蒙关注的重点,而个性与情感则被延宕,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康有为鼓吹西学,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都是这一思维方式的表现。其时,惰性、奴性、旁观者等概念广为流传,对国民性加以批判的政论文堪称一时之盛,启蒙在其最初的生发期就被理性以救国的名义劫持,张光芒所谓的“新理性权威”开始形成。
但若说清末的启蒙不关注情感的维度也不符合历史的原貌。上述启蒙思潮就是以一种奇特的充满激情的方式被传播。问题在于,感性不是出于其自身的目的被强调,而是处在了被支配的地位,以其为工具指向理性的自觉。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政治小说这一奇特的文学形式在当时受到的空前重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7]这一意在借审美来教育国民的小说教化论影响广播,严复、夏曾佑等纷纷附和,梁启超并总结出小说传播启蒙思想的“熏”“浸”“刺”“提”功能,进而率先译印政治小说以实践其文学救国的思想,小说创作与翻译因而极度繁荣。但这一把审美当作启蒙工具,进而将情感作为启蒙渠道的思路决定了其对情感、趣味及艺术性的强调并不在于看重情感、趣味与艺术性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启蒙”。这样,工具理性的膨胀扭曲了人的发现的主题,理性的人、工具的人排挤了本应是理性与感性和谐的完整的人。表现在创作中,则是小说的艺术特色被极大忽视,情感的维度让路于理性的表达。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而论,小说叙述自1902 年以来60 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主干部分记述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辩论,驳诘往复达44 段,几乎囊括了20 世纪初关于“中国往何处去”论争之基本要旨。这样的“感性”究竟对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能有多少帮助?启蒙的面目在这时难免变得暧昧不明了。
(二)“非功利”与王国维启蒙思想的出发点
针对晚清士人高扬小说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小说的艺术价值,王国维提出了非功利的学术观与文艺观:“又观近年之文学,又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术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8]38观点的不同,往往涉及立场的各异,如果说梁启超们是站在救国的立场“以经术文饰其政论”,那么王国维显然是站在文学与学术自身的立场求其独立。王国维认为,人类眼光可分为“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政治家局限于一人一事,而诗人则能以长远眼光看待人事,故“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9]他不愿意让文学(审美、感性)局限为“一时”的“物质”利益(理性)的工具,他要把文学与学术从从属的、作为手段的地位转变为独立的、自律的个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自律又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让人生问题在学术(哲学和艺术等)中凸显出来(“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他是从“精神上之利益”,即完善人性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试图将被倒置的感性与理性还原。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区别于纯粹的“书呆子”,而进入了生存关怀的启蒙层面。生存层面的人类,而非文学或学术本身,才是他提出“非功利”的出发点。
王国维对“精神”与“物质”这一对词组的运用,突出表现了他与晚清启蒙派的分歧。就康梁诸人而言,他们提倡政治小说正是欲以之新民,改变国人的思想(精神)。但在王国维看来,以政治小说的教育而达的国人思想的改变,根本不能算是精神层面的。因为其背后隐藏的救国目的,已经将其变成了一种物质手段。换言之,这种被新之民也还仅仅是救亡的工具而已,谈不上涉及个体生命层面的精神自由。从这一点来看,坚定的人本主义立场,是王国维启蒙思想的核心。他反对任何定型的外在的理性权威对启蒙本身的戕害。
如前所述,从生命本身出发,追求人类的精神自由,这是王国维启蒙思想的基点。由此出发,王国维进入了对欲望的分析。他认为,人类之精神之所以常常处于种种禁锢之中,不得舒展,根本的原因在于生命中充斥着各种欲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10]2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旧的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又会产生,所以,他认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也……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10]2所以,为保持个体生命的完满与舒展,就应超越生活,摆脱欲望。问题在于,欲望本身就是感性生命的表现形式,古人以理性来压制欲望,在晚明被认为压抑了人性,其时对人的发现即是从肯定欲望开始。压制欲望势必形成一种对人性的漠视,而一任欲望不加限制地蔓延,也必然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找到了其启蒙思想的支点。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作为个体的人认识到(通过理性)欲望(感性的片面发展)对人生的劫持,从而对欲望形成一种免疫力。[10]6-9即单纯的理性或感性都不足以令生命完满,而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能以启蒙派的功利性为前提,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必须在自然的状态下达到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样,王国维最终走向了游戏说。
三 王国维“游戏说”中的启蒙思想
艺术是游戏之说始于康德。康德把各种艺术看作人的感觉、想象力及知性的自由活动,并称之为游戏,它“超越感性而又不离开感性,趋向概念而又无确定的概念”。[11]席勒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因素,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它们对人性都带有强制性,不过一个是物质的、感性的强制,一个是道德的、理性的强制。只有消除他们的对立,调解它们的矛盾,把它们结合起来,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就需要第三种力量——“游戏冲动”来作为中介和桥梁。席勒举例说:“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被鄙视的人,我们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当我们敌视一个我们不得不尊敬的人,我们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强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既赢得我们的爱慕,又博得我们的尊敬,感觉的强制就消失了,我们就开始爱他,就是说,同时既同我们的爱慕也同我们的尊敬一起游戏。”[12]74换言之,当某一对象既符合感性冲动,又符合理性冲动时,人性的分裂就会得以弥合。席勒认为,游戏冲动的这一对象实际上是最广义的美,他称之为“活的形象”。这一“活的形象”融合了物质与形式、感性与理性,所以在美的观照中,人才能处于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能达到人性的完满和心灵的优美。所以,席勒这样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的人。”[12]80
在这一对游戏说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学说对王国维的可能诱惑。在王国维对生命的探索中,“欲望”作为与生俱来的感性冲动成为了其启蒙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纽结,压抑欲望与启蒙的初衷相背,不加节制则会令其凌驾于人类的尊严之上。所以,一方面,有尊严的生命中必然要引进理性这一维度;另一方面,理性的运用如果违背了感性的取向则又失去了自我的完满。席勒所谓的游戏冲动为这一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在游戏冲动中,感性与理性目标一致,既不会出现理性压抑欲望的情况,欲望也不会超出理性所划定的范围,二者协调一致,人由此成为了“完全的人”。审美,作为游戏冲动的对象因而得到了王国维的极度重视。
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这样提出游戏说: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10]25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文学是无功利的游戏;文学是“所储蓄之势力”的“发泄”。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提到了审美对生命完满的作用:“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10]9这一说法看似与上述游戏说的非功利主义相矛盾,实际上与前者共同表明了王国维以审美来解决人生问题的一贯思路:游戏本身是非功利的,但非功利的游戏又能使纠缠人生的欲望得到转移和消解,获取内心的“平和”。这样,王国维就由审美的无功利转向了文学的无用之用:“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8]158
所以,王国维提倡游戏说,实际上有着个体与民族的双重启蒙目的。就个体而言,审美的游戏能使个体的精神趋向完满,避免成为工具性的人,推而广之,众多个体精神的完满则有助于“吾侪冯生之徒”构成的民族、社会的改良。由此出发,王国维的启蒙又由个体而扩展到了群体,由无功利而达成了功利目的。
回到王国维在倡导游戏说时所突出的两点上来分析,首先,王国维强调审美是无功利的游戏,目的在于还审美以本来面目——被工具理性匆匆忙忙征用的“审美”不能称为审美。当这种伪装的审美占据文坛,真正的审美就会被取消。因此,王国维倡导游戏化的写作,要求文学家们不为“职业的文学家”,而为“专门之文学家”,[10]29不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而让其与永恒的人性对话,召回被放逐的审美,还文艺以本来面目,从而矫正文艺被理性压制的不正常状态。更进一步讲,是还文学的游戏功能,即感性与理性的谐和。他在《文学小言》《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多次指出,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在于中国人注重现实利害关系,注重“生活之欲”的满足,把哲学美术视为无用的东西,从而使得中国“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8]7。这实际上也是指出中国哲学文学缺乏那种超出利害关系限制的“游戏精神”,换句话说,缺乏圆融的人性,具有的都是沉重的理性压抑。其强调文学是游戏,呼唤纯正学术,最终目的都在于解放被理性所压制的感性,并让二者在游戏中结合,从而找回本真的人性。这是王国维以游戏启蒙的第一个层面。
其次,在对游戏说的表述中,王国维突出了另一个关键词:“势力之发表”,其启蒙由此超出个体而进入群体的层面。
王国维继承了席勒的过剩精力说,认为用于生存而有余的过剩精力必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宣泄出来,否则就会感到一种“消极的痛苦”“空虚的痛苦”:“活动之不能以须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动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8]27解决的办法则是将其移于某一嗜好,而最高尚的嗜好即文学与美术。
基于这一观点,对作为群体的“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8]64的现状,王国维认为其致病之由在于国人精神空虚,其剩余势力无处发表,缺乏情感上的慰藉,因而去寻找各种刺激以资填补。“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8]23而“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8]25因此,王国维提倡“美育”:“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3]王国维认为,以审美为途径可从根本上影响国人的精神建构——一时的审美可获一时之平和,持续的审美则可改变人的整体精神状态。从这一点来看,王国维其实是认同梁启超的“熏、浸、刺、提”说的,而不是纯粹的审美无功利论者。王国维启蒙的另一层面也由此而与晚清启蒙派诸子达成了目的上的一致。
总之,王国维以追求个体生命完满开始的启蒙,经由理性与感性和谐结合的游戏,最后终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可见,并不存在脱离时代的文学观,远离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如此之美术,惟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10]16
如果说梁启超们的启蒙意在立资产阶级之人以救国,王国维的启蒙则在源头上追求感性与理性的谐和,追求人类自由的实现,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眼光。事实证明,当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片面发展,导致人性的萎缩时,感性的大旗就又在文坛被高高擎起。王国维之后,五四的启蒙就带有了强烈的感性色彩,创造社,新感觉派,京派,乃至80 年代的新潮小说,90 年代以来的个人写作,无不突出个体的感觉。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味突出人的理性,固然会使人成为理性之神的奴隶,但无节制地宣泄个体的感觉,也会使人陷入价值真空。人类幸福的实现,在于不断地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永远也不会是过去时。
[1]童 明.启蒙[M]//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87.
[2]康 德.历史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3]休 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53.
[4]福柯集[M].杜小真,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534.
[5]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16.
[6]梁启超全集:10 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920.
[7]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 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
[8]王国维文集:3 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9]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51.
[10]王国维文集:1 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11]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上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96.
[12]席 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3]刘刚强.王国维美学论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