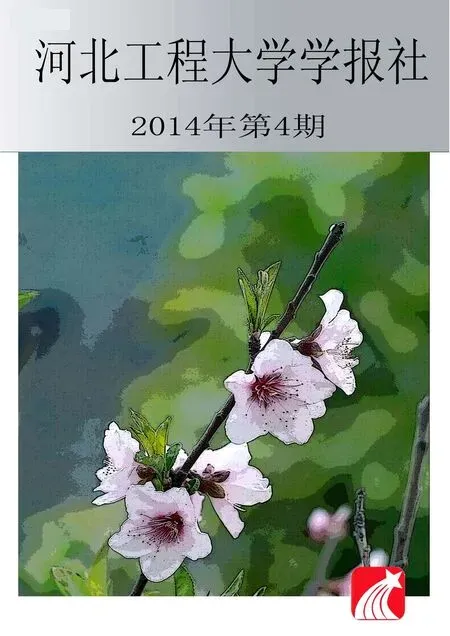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文本经典性的生成机制重释评骘
2014-03-31汪莹
汪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一、引言
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布鲁姆斯伯里”文化集团的核心人物、英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以及现代小说文论的倡导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重要创作观念“文本经典性的生成机制”(generating mechanism of fictional classics)一直是国内外文评界常说常新的议题。然而,不少人在引述伍尔夫的诗学思想和小说创作观时,却常常有所误解,常把这一概念表述的内涵与“有意味的存在的时刻”(moments of significance)相混相淆。后来,在英国学者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撰写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的中译本中,我们才又看到了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用以释读作家伍尔夫的生命意识与文本创作观,那就是:“应从那些形成我们生命的出乎意料的存在的瞬间的语境源头出发,来还原小说情节的结构原则和情感路标,从而寻找到小说艺术的生命写作节点。”[1](P94)
具体而言,“文本经典性的生成机制”是伍尔夫创作实践自然延伸的必然结果。它应该包含作家本人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技巧两个层面的重要而特殊的内涵。推己及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文本层面在一个力主“生命写作”(life-writing)的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涉及“存在”的关键性的为数不多的时间节点。因此,在对生命与自然本质的探求中,捕捉纷繁的精神纪实、定格有意味的生命瞬间无疑就成为小说文本经典性生成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文学惯例。
二、伍尔夫小说文本经典性的存在图式
从文体学发展史的源头上说,“小说文本经典性的生成机制”并非是作家伍尔夫本人为自己的片段式往事素描所确定的技法标题,而是一位女性作家以当下的“存在瞬间”作为审视的平台,对过去的小说创作进行个体意识超越的一种调剂。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伍尔夫对“存在”与“非存在”两个罕见时刻的所指和内涵的清晰表达。在伍尔夫看来,小说文本经典性的存在图式应是这两种时间层次的一种对比形式。正是由于这些大量普通的、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常规瞬间的存在,才促就了伍尔夫有关写作概念的生成和她那独特的生命哲学的主旋律。
在《往事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中,伍尔夫栩栩如生地回忆了3件她一生中记忆最清晰、最深刻的事情来具体说明创作中那种比现在的时刻还要真实的文本经典性:“假如生命有一个建立于其上的根基,假如它是一只某人不断往里倾倒的碗——那么毫无疑问,我的碗就建立在这一记忆基础上。它就是半睡半醒地躺在圣艾维斯育儿室的床上。它就是听见海浪撞击,一二,一二,在沙滩上溅起浪花;然后又是撞击,一二,一二,从一面黄色的窗帘后传来……。”[5](P78)对伍尔夫而言,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乃至个体生命与宏观世界的整个关系等等,似乎都具备小说文本经典性生成机制的某种“发现”意义。这里,伍尔夫反复提及的“窥见了宇宙奥秘与生命永恒的文本高峰点”[4](P142)似乎时刻都被普通生活中伴随而来的普通事件掩藏着、占据着。这些直达生命本质的特殊时刻,恰如“存在”一词本就具有的浓厚哲理一般,以艺术家对事物真谛的敏锐顿悟去捕捉它们的冲动,就决定了伍尔夫文本创作观的生命底色和艺术特色:“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尽管我在遭遇这类突然的震惊时依然会有奇异之感,但它们现在一直是受到欢迎的;在起初的惊讶过后,我总是立即感觉到它们尤其具有价值。因此,我接着猜想正是那种接受震动的能力使我成为一名作家。”[2](P185)
据此,不难悟出,伍尔夫的创作动机并非单纯来自于展现某种现实秩序的冲动,而是要通过文字之法让藏身于表象背后的真实事物成为自己生命整体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要通过写作使这些暗藏着“某种秩序”的灵光乍现的生命片段通过艺术而迈向“永恒”。这种与生命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写作观反过来又自然地对伍尔夫的小说文本艺术产生了净化乃至升华的功效。在这个方面,众所周知的例证理应首推伍尔夫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构思与灵感——一个在“存在的瞬间”完成“自我救赎”的思想事实:“一天正在塔维斯托克广场周围散步,就像有时构思我的小说那样,我构思出了《到灯塔去》在一种强烈的、显然不由自主的冲动之中。一件事猛然引发另一件事。我脑海中迅速涌出各种各样的场景,感觉就像从一根吸管中往外吹气泡,以致我在行走时双唇似乎都在自动地吐出语句。”[3](P161)
伍尔夫一生的创作都体现出一位女性作家对生命无常的质询与执着。她对时间流逝的强烈意识和对生命脆弱的危机感在文本经典意义生成的背后确实隐藏着某种珍贵的“存在瞬间”的真实图式,一种与整个世界彼此相连的艺术表达的真实图式,只不过我们都是这件包含有“真实图式”的艺术品中的定格部分和匆匆过客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伍尔夫的创作轨迹和她的个体生命均是彼此印证的。从《远航》(The Voyage Out)到《幕间》(Between the Acts)的创作征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表现了作家思想灵魂深处的每一经历、每一秘密、每一特征,也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作家呈现艺术生命把握时间之流的疑惑与努力。
三、伍尔夫小说文本经典性的精神实验
如前所述,就伍尔夫的文本生成机制而言,小说的使命就是要敏锐地捕捉住每个人的生命中那些耐人寻味的重要精神时刻。“要抓住翩然飞过的野鹅、网住珊瑚丛中的那条大鱼,还要成为溪流中的一条鱼,”[2](P83)才能以小说文本的经典描绘方式从大量的“存在瞬间”中提炼与嵌入许许多多“非存在”的时刻。事实也证明,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就是要能成功地在“非存在”的物质表象下呈现“内在真实”的存在意义和精神主义,即伍尔夫心目中真正的以生命意识为文本起点的现代主义美学实验。她在收入随笔集《普通读者》(Ordinary Readers)的《现代小说》(Modern Novels)论文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那些忠实摹写现实的‘物质主义’做法净写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它们不仅抹煞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还浪费了无穷的精力和技巧使貌似持久的真实的东西与‘生活’相去甚远。”[3](P112)>之后,1927年,伍尔夫伍尔夫也在《狭窄的艺术之桥》(The Narrow Bridge of Art)中再次提出:“小说,应观察一下一个普通的内心世界在一个普通日子里的印象经验,并接受与过去有所不同、来自各个方面的无数奇妙易逝的刻骨铭心的瞬间感觉才是。每一个作家都要站在从生活退后一步的地方来记录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也就是生活本身。”[4](P137)因此,优秀小说文本的生成机制和存在意义就是一大批尚未预料的“存在瞬间”的荟萃中心和聚集地。在这一点上,这些生命重要时刻的心理变化和意识反应与伍尔夫的精神主义写作追求就在探触生命哲理的瞬间感悟中产生了某种交集,且息息相通——以人物的片刻思想去表现精神自省的永恒。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伍尔夫对“文本意义”与“文本机制”要两者兼顾的强调和倡扬并非是对一味停留于表面的“非存在”描写的一概否定。最好的例证就是她在《海浪》(The Waves)的构思日记中所写的唯美与纪实的内容:“我觉得,外部事物也是好的;它们的部分结合应该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我打算把一切都囊括进去,但要饱满。这就是我想在《飞蛾》(The Moth)中做的事。它必须包含无聊的言辞、事实和肮脏的东西,但要被创造得透明才行。”[5](P139)
英国学者琼·贝内特(Joan Bennett)在分析、论及《海浪》的创作形式时,也指出:“映现于那6个人物中的1个或1个以上的意识描写取消了传记艺术对人物、客体或事件的纪实老套。读者只有穿透文字沉默行为的神秘根源,才能读懂作家本人那真实的一生。”[4](P125)
对此评价,伍尔夫颇为认同,但她同时也肯定了外部事件与内部心理在此情形下的对位性和融合性,认为:“一位自传作家,要有所创新地在生存的文学层面讲述一生的全部故事,一定得保证在转瞬即逝的事件和行为中将文本的意义和生成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记录下来,好用以激发生命意识的强烈感情和庄严时刻。”[3](P137)所以,对“经典意义”与“文本机制”关系的准确把握,也有助于我们澄清伍尔夫的小说创作观对精神主义和内部真实性标准的本质区别问题。
虽然其小说文本捕捉瞬间的现实环境和心灵际遇是琐碎的、局部的,但正是这些背负着人物存在无限可能性的微粒个体心灵构成了文本经典意义的一个个“生活尺度”,既澄明,又唯美。
四、结语
综上,或许,对作家伍尔夫来说,小说文本的经典意义本身就是生命意识存在的延续。她笔下的记忆片断与意识印象既为作家本人所亲历,又属于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个体。那些如出一辙的意识瞬间分明是创作实践对她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最真实的记录和写照,更何况这些琐碎的意识瞬间的背后还孕育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值得记录。毕竟,“以我观物、物我两忘”的意识呈现方式还原了挣扎的现代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多样存在方式,拓宽了小说家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边界。更难能可贵的是,伍尔夫的文本生成观体现了小说艺术的持久力和生命意识的情感化,这种开放的唯美主义思维模式引领了当今西方文论建设的的新方向,同时也给物欲横流的迷茫的现代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生命启示和生活希冀。如她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所说:“很不幸,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些东西。你不可能手里拿着所有的表达工具,去穿越那座狭窄的艺术之桥。有些东西你必须留下,否则你会在中途把它们扔到水中,或者更糟,你会失去平衡,连你自己也会遭到灭顶之灾。”[4](P580)
其实,伍尔夫追求艺术平衡与和谐节律的一生,就是在凝聚了她的全部个体生命意识的不断实验中回归生活、回归自我的一种“诗意的栖居”[6](P80)。那么,生命的归宿与诗意的境界只有通过日常现实中的写诗才能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典意义”与“文本机制”合二为一的创作观给现代小说的创作实践开辟了一片纯然自由的诗意氛围和情感天地,它的核心观念注重把本真的存在看作是小说艺术的审美需求,亦如一个指示着未来前途的方向标一般,引领着读者在伍尔夫那诗意葱笼的艺术世界里继续追问人生的意义、冥思物我交融的空灵与极致。
[1]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瞿世镜.伍尔夫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吴尔夫文集(十卷本)[M].黄宜思,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M].苏克,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5]Alt, C.Virginia Woolf and the Study of Natur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Bradbury, M. & McFarlane, J. (eds.).Modernism: 1890-1930[M]. London: Penguin,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