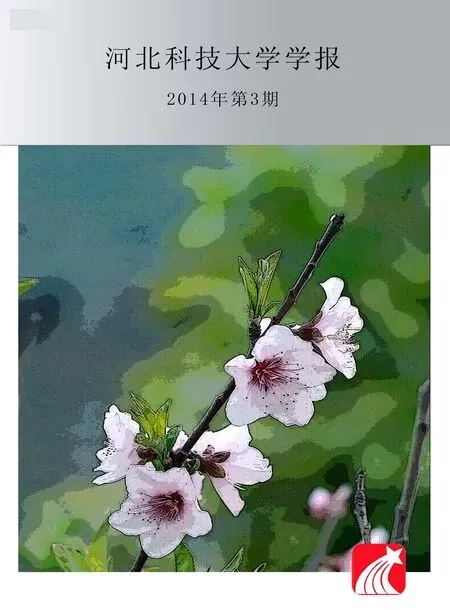基于荣格人格理论探析塔希自我完整之旅
2014-03-30阮明月
杨 波, 阮明月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拥有快乐的秘密》是美国杰出黑人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沃克一贯的大胆探讨黑人文化和传统上的禁忌话题创作风格,而且更加直接地剖析了人物内心,给读者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在沃克细腻的描述下读者能深刻感受到“女性割礼”给黑人女性带来的身心上的折磨。小说由几位叙述者内心独白构成,围绕奥林卡部落传统习俗中的女性割礼术对女主人公塔希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她命运的影响展开。古斯塔夫·卡尔·荣格(1875~1961)的人格分析理论认为完整的人格是由意识、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构成。其中,集体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本能和原型。原型能在意识中直接表现,但会在梦、幻想、幻觉和神经症中以原始意象或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原型有: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和自性。荣格认为,人格是在个性化的基础上,通过超越功能趋于整合的,即依赖于人格各方面的充分发展,把各种矛盾、冲突的部分统一起来。本文将主要从荣格心理分析的角度探究塔希追求自我人格完整的历程,进而分析塔希自我意识的产生及发展,以揭示小说的原型意义和作者艾丽斯·沃克对黑人女性在男权统治下如何实现自我完整与生存的关怀。
一、 塔希分裂的自我
小说伊始,塔希通过三只黑豹的故事描述她的处境。其中,她把自己想象成劳拉,她的丈夫亚当是巴巴,而他丈夫的情人丽赛特则是拉拉。可以看出,此时的塔希对自我形象的定位是错位的他者。她用“它”称呼自己,对劳拉则用“她”进行描述:“劳拉,它说,一个明亮的早晨,当她意识到自己被吻和被爱时……”[1](P4)因此,她内心感受到的是分裂异化的自我,甚至感受为他者(other)。而如贝尔·胡克斯所说,“他者不再是无能为力的观看对象,而是观看主体,这个主体不仅看,而且想用我的看法改变现实。”[2](P199)故事的开始便预示着塔希将由他者的感受,慢慢观看到主体并且会有主体的意识。另外,荣格提到“实际的人性化过程……以人格受损和伴随的痛苦开始。”塔希非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昭示了她的人格分裂以及将遭受的双重苦难和压迫的命运。然而,小说赋予塔希的人格分裂并非是她命运的终点,而是走上追求自我完整道路的新起点。
分裂不是无根之果,塔希的分裂是多个原因造成的。荣格说:“人并不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个人。”[3](P37)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在部落中缺失存在感和认同感,自卑的情结从意识中转移大量能量给个体,因此它掌控着塔希,驱使她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古老的割礼术。塔希的分裂之旅也就由此展开。与男性割礼不同,女性割礼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只是割伤,切开或切除阴蒂上的包皮,但依旧保留腺体,阴蒂功能基本没有损坏;第二类是部分割除女性阴蒂;第三类是将女性阴蒂全部切除,有时小阴唇也同时切除;第四类是将女性阴蒂两侧全部切除,然后将露着肉的两边缝合,只留下一个小口让尿液和经血流出。虽然对女性肉体造成了巨大伤害,然而部落的长者宣称这是女人们应有的美德,蒙昧的女人们都认为割礼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不容置疑。在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下,塔希则是在行割礼者(Tsunga)穆丽莎的操刀下,成了最后一类割礼的牺牲品。遵从传统而选择顺从的妇女却不能得到与男性的平等。割礼给塔希身心带来了巨大伤痛,也成为一系列悲剧的导火索,显然与她期待的割礼后的身份认同背道而驰。塔希迷失了自我,人格陷入分裂。由于缺失先前所信仰的非洲文化,她开始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奥林卡的一员塔希,还是美国公民伊芙琳。这正体现出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她无论纯粹地要展现出哪一种,都还是异化的,不完整的自我。
在外来殖民主义文化入侵后,黑人群体生存整体受到了威胁,而对于还在夫权下生活的黑人女性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沃克小说中族长式人物宣扬的禁忌,也不过是对黑人女性的进一步统治和戕害。男性社会给女性赋予利他主义的色彩,它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局限为为男性无私奉献的妻子与完美的母亲等,它往往利用某种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意识形态起作用,认为女性有其与男性不同的本性,女子的本性只有通过性被动,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才能实现。就如同奥利维亚说的,“你都不知道你迷失了自己。”[1](P23)而如果黑人女性一味沉默,她们只会“被那些宣称你情愿享受这种痛苦的人杀死。”[1](P23)小说中塔希的顺应使其自我意识被长期残酷地压制在社会所要求她扮演的他者的角色面具下。然而,美国社会上的白人价值观及其对黑人男性的消极影响,使黑人妇女蒙受双重压迫,这种顺应不良往往化作最隐秘的个人不幸或是最好的冒险,它们是降临到个体头上的原型。[4](P49)作为开启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型“人格面具”(persona)起到了关键作用。该词源于演员所戴的面具,用来表示区分他/她扮演的角色;而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员本人,或者说,我们的人格面具,并非是真实的自我。根据荣格的说法,人格面具的两个来源:“符合社会条件要求的社会性角色,一方面受到社会期待与要求的引导,另一方面受到个人的社会目的与抱负的影响。”[5](P69)虽然说人格面具在人的成长中能维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给个体带来社会认同,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认同的命题本身就带有虚假性,并且要求强行压制个体真实自我,或是令个体过分沉溺于其中的话,结果往往是负面的。个体会在真实自我与所扮演角色间举棋不定,进一步地便会发展成为人格分裂。塔希人格分裂的缘由可见一斑。然而,幸运的是,塔希还能记起幼年时期自己曾“坐在红皮箱上感到非常快乐……胡乱地写着大大的字母。”[1](P107)胡乱的书写象征她回到了人类的童年(集体无意识),这种原型的自主性即自主情结在暗中制约和影响意识,潜意识里的自我意识如一座活火山,等待迸发出新的生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塔希的姐姐杜拉,对之后塔希自我意识萌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塔希自我的萌芽
在面对社会习俗观念对女性的要求时,女性会进行心理认可,逐渐使自我意识受到压抑,并将这一部分自我变为无意识心理的一部分。主人公塔希意识呈现片段式存在时,一位朋友拍摄的照片勾起了她被压抑的记忆。她回忆起了幼年时听见杜拉在割礼台上的尖叫,“那天我爬到那偏远的茅屋旁,从里面传来痛苦和恐惧的叫喊……我知道是杜拉……杜拉凄惨的叫喊划破天空使我的心变得冰冷。”[1](P73)想起行割礼者穆丽莎残忍而无情地“用脚趾把一块血淋淋的东西踢给早就等在那里的母鸡。”[1](P73)这些经历早就在塔希的心里播下了恐惧的种子,痛苦的回忆在她也遭受割礼后再次浮现,塔希的自我苏醒了。
自我在长期的压抑下还未现行,但是会外化为冲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2012)中提到,只要个体将这个强烈的冲动付诸实践,而就算决定使自己停止这个念头,同样都说明个体具有“自我”意识。只是实践和停止二者在脑中相互斗争较量。当阻止的意识占上风时,就形成了压抑。长期以来,塔希压抑自己的记忆。也对自己为什么害怕见到血茫然不知,她的自我得不到发展,甚至呈现出退化的现象。然而,当塔希压抑着的活跃的“‘力比多’(libido)得不到满足时,她便要寻求新的替代物了。”[6](P139)长期的无法释放的压抑也可能成为“阴影”(shadow)。荣格用阴影来描述内心深处或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他认为“阴影指人格‘消极’方面和所有那些我们喜欢加以掩饰的不愉快品质,以及没有充分发挥的功能和个人无意识内容。”[5](P68~69)就塔希来说,她精神冲动的表现便是施虐,她的第一个施暴对象是她的儿子本尼。塔西接受割礼本想拥有美好的“人格面具”,却导致了本尼的智力障碍。心里意象的失落无疑扭曲了塔希的面具,她将压抑的情绪以暴力的形式转移到本尼身上。她常为一点小事揪扯本尼的耳朵,“直到他被折磨得痛苦尖叫,萎缩在隐蔽处。”[1](P142)究其原因,不得不提到“情结”问题,弗洛伊德与荣格等人认为情结的形成多来自于创伤性经验、情感困扰或道德冲突等,如“恋父情结”、“性欲情结”、“自卑情结”等。荣格指出它有一个源于原型的核心,并带着某种情绪基调。而塔希特殊的部落情结和自卑情结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它基于部落给女性的人格面具。在她个人无意识时期,集体无意识便会替代她的自主性,成为她所有情绪的原型;然而,当她个人意识逐渐可以察觉时,原先的平衡便被打破。如果要解决对“力比多”的压抑和它与外力的矛盾,她需要使用“移情”给她提供一个发泄的出口。“阴影”作为意识原型之一,首先为塔希的自我提供了一扇门,让她看见门后涌动的令人惊异的东西,同时它与人格面具形成对立冲突的关系,为塔希进一步寻求自我创造了可能。
除此以外,塔希对丈夫亚当和他的情人丽赛特所生的儿子也充满了愤恨。亚当不理解她的处境和所承受的痛苦,还由于无法再与塔希行男女之事得到男性的快感,他远走美国,还发生了婚外情。丈夫角色的缺失,以及他对塔希经历的无动于衷,都令塔希作为一名在夫权统治下的黑人女性身心所受的压抑更加严重。“我的‘快感’(女性在男性胯下痛苦挣扎)令我憎恨我的丈夫”[1](P240),塔希显然产生了叛逆的情绪。于是她的阴影驱使她转向亚当和丽赛特的儿子皮埃尔。塔希见到皮埃尔时,感觉到体内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暴力倾向。她疯狂地把石头砸向他和他乘坐的出租车。而发泄完后,塔希·伊芙琳发出快意的狂笑。塔希开始接受她的阴影,并且对阴影的“恣意妄为”表示出满意和快感。
当塔希从被动顺从的面具下,勇敢地拿起粗糙的石头宣泄自己时,她开始成长为奥林卡部落传统和外来文化入侵的反叛者。她发展出自己的阴影,即压抑与遗漏良久的阳刚气质的另一部分自我。荣格所说的阿尼姆斯(animus),就在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出来。“在与阿尼玛/阿尼姆斯的遭逢中,所接触的心灵层级具有引导自我朝向最深最高处(以各种标准而言都是极致的)发展的潜能。”[7](P183)正如荣格自己所讲:“ 因为邪恶而使我得到许多善良,我也以这种方式接受自己本性中的正面与负面。于是每件事物变得更加有生气。”[7](P159)积极的阿尼姆斯也是女性内在智慧与精神中的潜在力量,它可以化身为勇气、精神、真诚并创造自我。塔希追求自我完整的脚步再次向前跨了一大步。
三、 塔希追求自我完整
在周围人看来,塔希似乎成了疯女人。然而,在黑人女性作家笔下,这样的疯狂并不是都会带来纳卡索斯(Narcissus)式的自我毁灭。在许多作家看来,比起压抑、沉默和接受,女性的疯狂是一种极为神圣的形式,它帮助女性寻找到真正完整的自我形象。艾米丽·迪金森(1862)就表示,疯狂是最神圣的感受。奥古涅米(Qgunyemi)也强调黑人女性作家笔下的疯狂的黑人女性在潜意识里清楚地知道她得为了其他手无寸铁的人勇敢生存下去;所以她得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疯狂的行为是精神成长,是心灵治愈和实现自我完整过程中暂时的失常。[8](P74)塔希的疯狂是萌动的自我意识在集体无意识和生存环境与现实中的限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不仅如此,诸如托拉比(Torabe)的妻子,阿伊莎(Ayisha)和艾米(Amy)等无数女性同胞悲惨的遭遇让塔希意识到,愚忠和沉默换来的只会是自我的丢失和真正的黑人传统的失落。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的纵容,只会让今后更多女性难逃一劫,造成无法改变的恶性循环。塔希渴望受害的女性能团结起来,在遭受迫害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勇敢抵抗。不同于塔希对阴影的正确认识,小说中行割礼者穆丽莎,在成为“国家纪念碑”式的人物前,她也是割礼的受害者。虽然她的母亲试图在给穆丽莎的割礼中“放水”以减轻她将面临的痛苦,但没能逃过男巫医师的法眼,她因此受到了更残酷的对待。由于割礼,她的身体出现残疾,左腿的韧带也被割除了,导致她走起路来总是拖着腿,并且声称自割礼以后她“再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样。”[1](P215)然而,本该受到同情的她,却走向一条邪恶的不归路。穆丽莎拿起伤害自己的割礼“屠石”伸向其他黑人女性同胞,成了部落男权的屠刀和代理人。她的自我已经完全为阴影所吞噬。荣格(2003)认为,要走向一个完整自我,人们必须能正确认识包括阴影、人格面具等原型。[4](P49)因此,穆丽莎以自我失落的悲剧收场,而塔希在意识到自己的阴影后,并未被吓倒,而是变得清醒和坚强,她终会在不断对自我重新认识和构建中获得完整自我。
塔希对自己的不断认识,就如荣格提到的,还借助梦、幻想以及某种神秘体验来实现。在小说中,塔希的梦和幻想是揭示一切的主要来源。荣格把“无意识自发地通过一长长的梦系列象征表述自己的过程叫做个体化过程。”[9](P240)个性化过程是要为自性(无意识中的真正自我)剥去人格面具的虚伪外表。塔希在幻想或者说是她的梦中,把自己看成是黑豹劳拉,劳拉对着水中的倒影顾影自怜。显然,女性观看世界,再到反观自身。塔希在用他者的身份审视自己,说明她渴望认识自我。关于黑塔(Dark Tower)的噩梦,显然是塔希自我意识中对男性话语权压抑的恐惧。塔希还幻想自己听见了白蚁的对话,白蚁们遵循着上帝的指示,他们对上帝这个形象的认识还不完整,却不加怀疑地相信。所谓来自“上帝”的美妙辞藻和现实对塔希造成的伤害,让塔希产生对人格面具的怀疑和抵制情绪。“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了。”[1](P240)塔希曾对穆丽莎如是说。她能够表达“自己”而不是她/它了,自我的意识由幻想走向真实,她也将以行动证明自我的真实存在。
塔希的意识觉醒了,她从内心里发出反抗的声音——她对奥利维亚坚称她要身穿红色,小说中曾提到“红色代表人们反抗专制政权所撒出的鲜血”[1](P108),塔希就从那样的觉醒中意识到她的自我“正开始完全地回到了自己早已丢失了的身体。”[1](P109)不仅如此,她的反抗还通过疯狂的行径——意图谋杀穆丽莎来呈现。在西方文化中,就像让厄舍塔倒塌一样,只有“推倒”具有标志性的“国家纪念碑”[1](P147),才能激起女性内心真实声音的集体爆发。但是假设她为了自己复仇而杀死穆丽莎,那么她的结局势必是被群体唾弃,妇女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所改变,甚至将遭到更加残酷的压迫。另一方面,如荣格指出的,人类往往有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上文也提到,情结是集体的无意识的表现,伤害性的记忆往往唤起这些情结。塔希意图杀死穆丽莎,这个称受割礼女性为女儿的“母亲”一样的角色,展现出塔希可能存在的弑母情结。这种弑母情结在神话中也有原型,那就是俄勒克特拉协助其弟俄瑞斯忒斯间接杀害了其母克吕泰墨斯忒拉。“女儿杀死自己的母亲,更深的一层意义,她也许是为了拿失去母亲来报复某个兄长或丈夫。”[10](P175)显然,她所指向的并不是这个行割礼者本身,她的阿尼姆斯带领她勇敢向男权发起反抗。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的阐释中认为,他者的地位和特性就是女性的地位特性,即相对于男性的附属性、非自主性、次要性和被决定(定义)性,等等。然而这样的关系显然被塔希的自我打破。在反抗中的塔希已具有阳刚的一面,有了强硬的自我态度,她获得了荣格所说的灵魂意象——阿尼姆斯,因此,最后,塔希作为叙述者,名字变成了塔希—伊芙琳—约翰逊—灵魂。她不但放弃了社会赋予她的面具“夫人”,摆脱了丈夫的所有物属性,还看到一个对自己有了全新认识、整合了无意识中部分自我的灵魂深处的塔希。
要达到完整自我的建立,光靠与世界为敌是不能实现的,她必须接受自性的约束。所谓自性,是荣格在1928年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型,“指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的结合,是包括集体无意识在内的整个人格精神的主体。”[11](P174)自性也被视为对立面在其中统一起来的总和与整体[12](P509),它能具有一种超越与整合的功能,使对立面达到整合统一与平衡。这种超越的功能也可以“使我们对引起内心冲突的事件或观念保持完全开放的心态,从而能够发现某种全新的意义,最后我们可以在一种新的综合中包容对立的两面(或多面)。”[13](P141)最终她接纳了本尼和皮埃尔,也在信中表示了对她与亚当关系的重新审视,并且对丽赛特宽容地敞开心扉。不仅如此,她由一开始决意杀死穆丽莎,到后来放弃了杀死穆丽莎的念头,都是自性对她完整自我的规范和整合。小说最后,塔希坦承自己的罪行,选择以自我牺牲换来妇女们的觉醒。尽管肉体死去了,但她的灵魂得到了重生,她也真正达到自我完整的最高境界。有所感悟的奥林卡妇女们在塔希被执行死刑时,纷纷前来送行,给她带来“具有象征意义的野花、草药、种子、珠子、谷穗”[1](P181),她们用女性特有的盛典庆祝妇女的丰收,即塔希给自己还有其他妇女们带来了身心的成熟和觉醒,她在最后给丽赛特的信中宣称自己“是所有妇女的母亲,并且获得了自由”与“重生”[1](P276~277),所有人包括亚当、奥利维亚、皮埃尔、本尼,都牢牢托起上书“反抗是快乐的秘密”(RESISTANCE IS THE SECTET OF JOY)的标语。因此,她离开人世时不畏惧死亡,而是“心满意足的”。[1](P278~279)
四、 结语
在艾丽斯·沃克这部《拥有快乐的秘密》作品中,通过主人公塔希入狱前对自己在奥林卡和美国悲惨生活以及其他几位重要角色的一系列叙述,揭露出割礼这种所谓非洲(奥林卡)传统对女性的摧残,表达了沃克对非洲文化深刻的忧患意识以及唤醒黑人女性自我的觉醒和寻求自我完整的生存意图。所谓自我完整,就是要完成自性的寻找,即在心理上的整合。荣格心理学理论的心理范式是通过正/反/合这一逻辑范式所达到的调和的类似物[14](P24)一样,荣格认为,人们内心的成长也正是通过对一系列具有对立面倾向的心理意识的整合,即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女性因素与男性因素、理性与非理性的超越统一,也就是对每个人存在于无意识心底深处的真正完整自我,即自性的寻找所完成的。塔希正是在经历了恐惧中的自我分裂,认识阴影的自我意识的萌芽阶段,以及经历了荣格所说的女性的男性气质阶段,即阿尼姆斯(animus)的阶段,最终达到自性对自我的完善,从而获得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的自我完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自我完整,更是沃克理想中对黑人女性的期待。黑人女性要勇于发现自我,寻求自我的意义,并且追求自我完整存在,最终从对抗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Walker,Alice.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M].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New Press,1992.
[2]Hooks,Bell.Reel to Real:Race,Sex,and Class at the Mov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3][美]霍尔,诺德贝.冯 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M].上海:三联书店,1987.
[4][瑞]荣格.李德荣,编译.荣格性格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5]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第2版)[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瑞]弗洛伊德.张堂会,编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7][美]莫瑞·史坦.朱侃如,译.荣格心灵地图[M].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9.
[8]Ogunyemi,Chikwenye Okonjo.African Wo/Man Palava.The Nigerian Novel by Women[M].Chicago and 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6.
[9][瑞]荣格.论梦的本性[A].L·弗雷罗恩.陈恢钦,译.从弗洛伊德到荣格[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10][美]菲利斯·切斯勒.汪洪友,译.女性的负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瑞]荣格.冯 川,苏 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12][瑞]荣格.冯 川,苏 克,译.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13][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Roberta Rubenstein.The Novelistic Vision of Doris Lessing:Breaking the Form of Consciousness[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