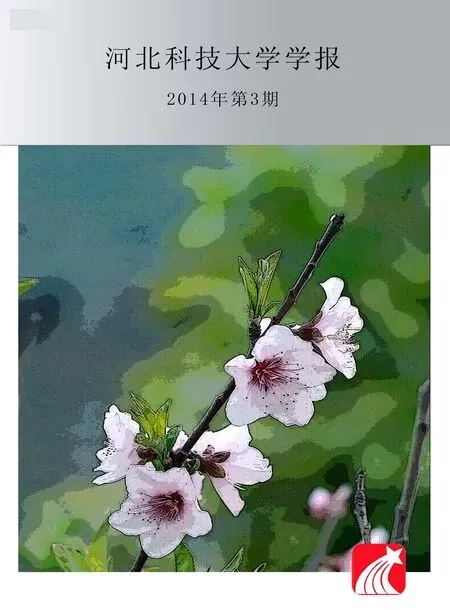深远、高远、平远:从杜甫、李白、王维诗歌看盛唐诗歌之美的三个维度
2014-03-30王晓明
王 晓 明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延绵数千年的诗性文化土壤孕育了多姿多彩的诗歌作品。唐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达到了巅峰,而盛唐诗歌则是峰顶上的明珠。宋代画论家郭熙曾论山水画之画山有“深远、高远、平远”三远之分。[1](P51)笔者认为,盛唐诗人杜甫、李白、王维最具特色的作品,恰是分别从深远、高远、平远这三个维度表征了盛唐诗歌之美,从而使得盛唐诗歌气象更具立体感与丰富感。
一、深远之美——诗圣杜甫
闻一多先生曾说杜甫是华夏民族“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P121)。之所以“庄严、瑰丽、永久”,是因为杜诗中蕴含着一片浓浓的忧国忧民之情,他的人生与民族、时代极其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感时之切使花溅泪,恨别之深使鸟惊心;之所以为“最”, 是因为他的生命与创作实践为后世竖起一块最具分量的丰碑。
在杜甫诗作中的家国之情,延绵不息,愈远,愈浓,愈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3](P9)是他用世之心的最真切体现。于上,他所关切的不仅是君,更是“致君”;于下,他所渴盼的是民风之淳、尧舜时代的复归。史册中的杜甫形象特征是忧国忧民,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飑”[4](P14)。《子美画像》,《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可以说,张载所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5](P320)(《张子语录·语录中》)之主张在杜甫思想中已经有了萌芽。杜甫一生都没有机会像诸葛亮那样能遭逢明主,运筹帷幄,掌控天下之局,这或许也是他常慨叹诸葛公的缘由,譬如“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3](P182)(《蜀相》)他也一生都没有机会像王安石那样以高层行政主体的身份来践行其“致君”之夙愿。然而杜甫之可贵正在于他在平平凡凡的生命历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忘却“致君”,尽己所能,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6](P235)当他有机会参政时,他宁愿冒风险直言进谏。当他浪迹江湖时,时时关切民生之疾苦,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3](P21)(《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堪为划过时代夜空的闪电。《丽人行》中他对杨妃姐妹的讥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对玄宗的披露,《忆昔》二首中对肃宗、张后的嘲讽,都是他“疾恶怀刚肠”(《壮游》)的表露。安史之乱中众多达官贵人在已经陷落的长安苟活,而刚得到“从八品下”这一微职的杜甫却宁愿冒着“死去凭谁报”[3](P158)(《喜达行在所》之三)成为他忠君爱国之心的写照,他心心念念的是“致君”,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儒。又因为他自觉实践着人生的理想,坚守着人格的高度,于是他完成了从诗儒向诗圣的跨越。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在杜甫身上实现了。
在杜甫的诗歌中,“亲亲、仁民、爱物”[7](P322)的悲悯情怀有着充分的体现。对家人的亲爱之情是杜甫人文情怀的逻辑起点。长安沦陷后,他独自望月怀念妻子儿女的心情甚是感人。他在同谷深山挖掘黄独时,也是心系妻儿、兄弟姐妹。开边战争是盛唐巍巍国势的重要军事体现,而战争的本质终归是生灵涂炭。于是杜甫在《兵车行》中揭露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前出塞》之六”中他写到:“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3](P49)于是他的悲悯之情在“吾国之民”外兼具了“民,吾同胞”的普世情怀。在亲人、生民之外,杜甫对世间其它生命也有一份怜爱之心。他有诗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3](P133)(《过津口》);“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3](P197)(《题桃栅》);“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3](P77)(《寄题江外草堂》),这些都是他“爱物”、“物,吾与也”之心的诗性表达。
杜甫一生共写有1 500多首诗歌,以古体诗、律诗见长,其内容涵盖面广,思想深刻。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律诗多用于叙写山水、宴游、羁旅、应酬和咏怀,杜甫则把律诗的写作范围延伸到时事中,在题材上实现了突破,在字数格律的严格限制中创作出了许多针砭时弊、感人肺腑的作品。其古体诗也在回旋往复中铺叙咏叹、夹叙夹议,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既写一己心绪,又反映社会现实。杜诗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唐代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获得了充分的表述,被称赞为“诗史”,具有纯艺术作品之外的史料价值,已经被广泛用于以诗证史的研究中。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即是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延续。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代,天水一朝军事实力羸弱、社会矛盾重重,经济社会背景也自然会影响到文艺创作。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给予很高的评价。江西诗派的创作即以杜甫为宗,注重用典,有关注民生疾苦之作。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等遗民诗人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慷慨激昂。为数众多的杜诗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即是杜甫诗学与文化影响的见证。
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感洪流凝结成作品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其诗歌的思想基础是塑造了华夏民族文化品格的儒家仁学,其人生与诗学实践的意义在于为世人树立了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4](P11)南宋诗人陆游则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8](P281)王安石、陆游对杜甫的评价已经超越其诗歌文本而进入人格的视角。在中国诗学传统中,文品与人品有着密切的联系,杜甫即是二者相互印证的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有着“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学品格,有着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才使得杜诗中所蕴含的深远之情,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所体现的深远之美,足可以开出盛唐诗歌纵深之沉潜美的一个维度。
二、高远之美——诗仙李白
论及盛唐诗歌,唱响青春激昂之音的李白总是文学史上讲不完的话题,他震撼人心的诗歌艺术达到了后世文人似乎总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值得探寻的是,李白这位盛唐诗坛上的首席诗人,不归属于任何可以定位的群体,因为他总是那么高拔超越、卓尔不群。评论家常常把李白及其作品称为诗仙、仙人之语,认为非人力所能及,这也说明他与同期诗人存在着差异,他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是游离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之外的。
史家对李白的身世历来持有争论,汉化的胡人抑或胡化的汉人这种复杂的背景确乎可为李白的人生与诗歌实践提供一个解释的维度。然而要想深入理解李白那不羁的性格、浪漫的气质,需要把他的诗歌与他所处的时代相结合去探寻其中蕴藏着的价值取向。在《古风五十九首》中,李白对自己的定位是:“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9](P10)从“删述”、“获麟”之典故看,李白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孔子那样,成为时代的文化领袖,这是他人生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与人生实践的追寻终点。李白对出世用世有着极其强烈的追求,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理想莫过于“如逢渭川猎,尤可帝王师”[9](P104)(《赠钱征君少阳》);“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9](P104)(《送张秀才从军》)。“帝王师、解世纷”是李白所渴望实现的“志”,这其中充满了他对儒学古风的追慕。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到:“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查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士人耳?此则未可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难矣。”[9](P251)李白对中国古代士之地位与作用的认同实际上也是他自己价值取向的判断与认定,从而他的人生价值系统就不能不以古风的士精神——志于道为主导。士作为道这一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能够对政治产生师教与抗衡作用,古风时代的理想君主是要能够“礼贤”。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昭王往见郭隗先生曰:“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10](P313)(《燕昭王收破燕后章》)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这种君主与贤士间的师友关系赋予了士以人格的独立性,士与君主之间并非附属关系。“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6](P539~540)既是古风时代“士”、“道”、“政”关系的诠释,也是李白所钦慕与持守的价值原则。然而唐代毕竟已去李白理想中的古风时代甚远,时势的变化使得世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转变,或是崇武尚实、主张开创军功,或是汲汲于仕途、讨得君主欢心而荣耀自身。士与君主间的师友关系不复,唐代科举制度招募的人才臣服于皇权,皇权成为师,士则成为学生、门生。李白心目中的士精神趋于消退和缺失,传统中士对道的执着已转变为对政权的依附,传统中君主对士的礼遇已转变为士答谢君主的知遇之恩。于是他不得不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中,在诗中慨叹:“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9](P24)(《行路难》),“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9](P64)(《永王东巡歌》之二),“燕昭延郭魏,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9](P13)(《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李白终身未能真正进入仕途正在于其价值理想与社会现实、通行的社会价值观念间的冲突。他“羞与时人同”[9](P155)(《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一生傲岸苦不谐”[9](P160)(《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9](P79)(《赠郭季鹰》)。当他的用世理想终究处于绝望中时,他悲吟到“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9](P144)(《送蔡山人》)。于是他卓拔超迈的个性在不受格律拘束的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诸如“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9](P160)(《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9](P110)(《忆旧游寄憔郡元参军》),“壮志恐磋蛇,功名若云浮”[9](P82)(《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9](P191)(《商山四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9](P22)(《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9](P121)(《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9](P152)(《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意图继陈子昂之后再溯诗骚传统,将夸张想象、拟人比喻等手法综合运用到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体和绝句中,情感的抒发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就如他奔放不羁的个性一样,李白在歌行体中打破了传统的创作模式,在跳跃宕荡、大开大合的整体篇章中展示出变化多端的笔法,形成瑰丽多彩、摇曳多姿的艺术境界。其歌行体多是三段式呈现,开篇先声夺人如闪电划过,中间往复回环、令人荡气回肠,结尾如交响乐到达高潮随即戛然而止,让读者惊愕于其境而不易自拔。对于绝句,五言七言在李白手中都能妙笔生花,独领风骚,他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传达情感,风格清新飘逸、潇洒自然,如民歌般天真淳朴。其诗歌描写山川风物、人生体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充满浪漫气息。随后的李贺、辛弃疾、龚自珍等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李白继屈原之后给后世竖起了又一个极其浪漫的精神高度,他对中国文学、文化、文人的影响是丰富深刻的。李白的艺术与人生总体上呈现出高拔的气质,这应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他对士当为帝王师的极具复古意味的恪守和追求,这与他所处时代的用事观念相冲突;二是当在现实中理想破灭、道终不能行时,他所表现出的极具道骨仙风意味的超脱,又与他所处时代的众人皆醉之现实相冲突。于是,李白诗歌中所呈现的就必然是一个放达不羁的形象,一个总在超越的角色,一个充满激情的生命。传统士的性格特征在李白的气骨中得到了积淀与呈现。正是由于有着“删述、获麟”的对儒学古风的追求,有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11](P295)的道家精神,才使得李白诗中充溢着天马流星式的高远之美,从而为盛唐诗歌开出了纵向之超拔美的一个维度。
三、平远之美——诗佛王维
如果说诗圣杜甫诗歌中深情传达的是一种沉郁顿挫、回肠荡气的深远之美,诗仙李白诗歌中的激情迸发出的是一种高拔超越、放达不羁的高远之美,那么盛唐时期的又一位诗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所流露出的则是一种宁静空灵而蕴含生机的平远之美,即盛唐诗歌气象之美的第三个维度。
王维早年亦有修齐治平之志,而宦海沉浮着实令人无奈,亦官亦隐的人生价值取向正说明了释道思想对他的影响。他曾写到:“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送纂毋秘(一作校)书弃官还江东》)”[12](P52),对本真之心的追求清晰可见。王维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诗主要创作于他亦官亦隐的生活时期。此期间他的知遇之人张九龄罢相贬为荆州长史,他失去了政治靠山和文艺知音,陷于孤独痛苦之中。于是他寄情于山水之间来获取心灵慰籍,四十岁后归隐终南山四年,购置辋川别业并营建二十年之久。《田园乐七首》、《田家》、《新晴野望》、《终南山》、《辋川集二十首》、《青溪》、《辋川别业》等即是在此生活背景中产生。
王维优游山水时寻求的是一种恬静适意、与自然相融的状态,他的诗歌中常常蕴含着平远之中的宁静美。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12](P39)(《终南别业》),“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12](P274)(《竹里馆》),“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12](P127)(《酬张少府》),“草堂蛰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归”[12](P292)(《早秋山中作》),“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12](P38)(《青溪》),等等。不难想象,诗人在对自然美的静观与体验中常处于物我两忘的状态,这其中蕴含着他喜静的意向。王维曾写到:“吾生好清净,蔬食去情尘”[12](P28)(《戏赠张五弟三首》),“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12](P127)(《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12](P203)(《积雨辋川庄作》),“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12](P133)(《淇上即事田园》)。这种趋静的思想倾向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源头。《老子》曰:“涤除玄览,能无疵乎”[13](P40),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3](P64~65),庄子则认为,“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淮,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11](P113)(《天道》),又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11](P205)(《庚桑楚》)。老庄主张排除杂念,以虚极、静笃、澄明的心境照万物、参造化。王维不仅有深厚的儒道学养,他的佛学修养也非常深厚。他笔下那些平和、宁静的诗句也只有在静的心境中才能产生,并且延绵悠远而有韵味。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尽管没有激荡、澎湃的情感,但不是无情的死寂,而是在平远宁静中蕴藏着生意生机。如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2](P268),又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12](P274),还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12](P129)(《山居秋暝》),“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12](P201)(《辋川别业》),“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春园即事》)[12](P132),等等。这一系列自然意象形成的基础是在平和、宁静的心境中对生命的观察和感悟,于是王维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花一叶就具有了空灵的气质。
王维诗歌中的平远之美不仅表现在以上诸多诗性意象的选取与组合中,也表现在他可以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取景,用轻快的笔触描写自由清新的田家生活和生机勃发的山川景物。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12](P42),如《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林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12](P70),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与杜甫的深沉、李白的超拔相比,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更富于平远之美的意味。
相较于杜甫的颠沛流离、李白的怀才不遇,王维早年的仕宦生活相对悠闲稳定。晚年时期安史之乱爆发,他在战乱中被叛军捕获并被迫出任安禄山的伪官,这在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是折节之举,为士人所不耻。战乱平息后,王维被交付有司受审,论罪当斩。后因他曾于伪官任上怀着复杂的心绪写下思慕大唐天子的诗歌,加之其弟愿以官职换兄性命的恳请,才侥幸获免,但官职被贬。此后王维又升至尚书右丞,宦海沉浮的体验也是其艺术风格的成因。王维是诗人,同时擅长绘画和音乐。经历过生死考验之后,他的心态趋于平和,主动构建着内心宁静澄明的艺术境界。对自然的亲切感、山林生活经验、深厚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诗性素材有着极其敏锐细腻的感受,他笔下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从容的呈现出自然界光色和音响的变化,充满了诗情画意,动静结合、意境悠远。他的诗歌句式、节奏富于变化,音韵和谐,清新明快,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上王维有“诗佛”之称。他在亦宦亦隐中与佛结缘,研习佛典,交游佛僧,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他所生活的盛唐正是禅宗特别是倡顿悟之说的南禅形成的时期,这都对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产生影响。而王维又是一位深具中国传统儒道学养的文人士大夫,骨子里既有用世理想,又有对平和宁静、自由适意之生活的向往。当佛道思想与他所禀赋的诗性气质浑融时,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就为盛唐诗歌开出了又一审美维度——平远之美。
盛唐诗歌是华夏民族文学史上的明珠,它的永恒与其生态时空息息相关。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分别为其开出了“深远、高远、平远”的时空维度,从而使得这朵奇葩美的深沉、美的超拔、美的平和、美的延绵悠远,使得它从容大气、优雅自信闪耀在华夏民族的诗性土壤中,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宋)郭 熙.林泉高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闻一多.唐诗杂论[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
[3]张式铭,标点.杜工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
[4]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J].杜甫研究学刊. 2000,(4).
[5](宋)张 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6]程树德.论语集释(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徐 放.陆游诗今译[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
[9]张式铭.李太白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0](清)程夔初.战国策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1]王先谦.庄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杨文生,注.王维诗集笺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3]朱谦之.老子校释(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