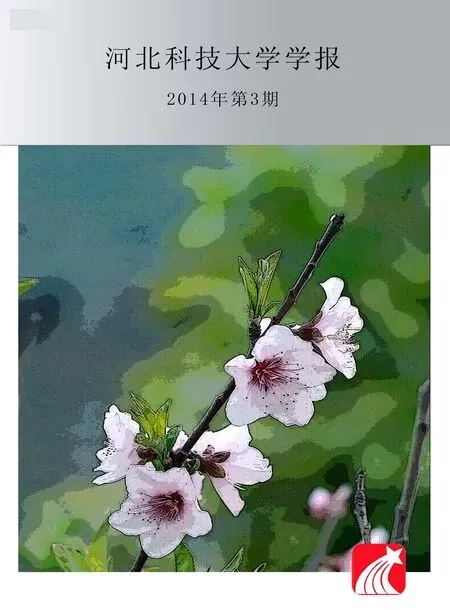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2014-03-30宋雯
宋 雯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文学理论中的“张力”这一概念源于美国新批评理论家艾伦·退特,1937年,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为描述这种成就,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P117)“张力”作为诗学概念,是新批评派对康德“二律背反”命题在文学批评中的一次创造性运用,“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它主要得益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亦即福勒所谓‘一般而论,凡是存在着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张力诗学’或张力论不断地被引申,并越出了诗歌理论的边界,在文学批评的众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2](P41~45)卡西尔曾说过:“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3](P207)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元素分布在其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诸多方面,毕飞宇在谈自己的小说理想时曾说:“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4](P120)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实现了他“轻盈而凝重”的小说理想。
一、叙述语言构成的张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毕飞宇的小说之所以在新生代小说中能脱颖而出是与他的小说语言分不开的,反讽、戏仿、比喻等叙事技法的运用使得小说语言充满了张力,带来了陌生化的效果。
毕飞宇小说语言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对于意识形态公众话语的移用,在《玉米》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5](P4~5)“持久战”、“排除万难”这些词汇本来是那个年代严肃的政治用语,而王连方却将它们“形象”地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使得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化了的语言重新复活,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调侃。这样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移用还体现在毕飞宇的许多现代都市小说中,比如在《男人还剩下什么》中:“主任的意思我懂,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搞’,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伸出双手,握了握,保证说,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6](P129)施战军用家庭关系、性爱关系与社会交往中政治词汇的移用现象来概括毕飞宇的这种语言,他认为:“这样的话看似俏皮、轻浮,实则带有本然的‘中国含量’。这种露出端倪的语风都是解颐的或解恨的。同时不仅使作品增添了表面的光辉,也让小说的内里透气有氧。”[7](P379~38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诗词的移用,如“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岁了还红杏枝头春意闹。”[8](P105)“父亲听着党的乡村方言,一个人站在房屋中央,胸中霞光万丈,玉宇澄清万里埃。”[9](P43)这些移用使得人们熟知的经典诗句得以重新焕发新的光彩和活力。
戏仿也是毕飞宇喜欢使用的一个叙事策略,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常会看到这样的语句:“盐碱地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蒲苇的。”[10](P241)“是高端五使我们变成一只高尚的猪,一只纯粹的猪。”[11](P231)“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12](P273)这些语句都是对人们熟知的政治口号、名人名言和经典诗词的戏仿,这种戏仿把我们习以为常的语句以一个陌生的方式重现,使小说充满了幽默感。那些沉重的故事也因此取得了轻逸的效果,这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在《平原》里,顾先生处境悲惨,可在对顾先生的描写中,叙述者用了这样的语言:“顾先生失眠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念党。顾先生擦干了眼角的泪,肩膀上的担子更沉重了。”[13](P108~109)这种戏谑的语言和语调消解了故事本身的沉重和严肃。“王家庄故事由此获得了一种舒缓的张力:它既让读者在一定程度上窥见政治、道德、人性等层面的悲剧内涵,却又不使读者跌入紧张与沉重;它既使读者在游戏的轻快的语言中体会到颠覆革命的快感,又不因对革命过于分明的价值判断而被有识者断定为偏执甚至无知”。[14](P50~60)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是毕飞宇小说的一个突出现象,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优秀的日子们到了五月八日依旧桃红柳绿,眉清目秀。”[15](P56)“为此我曾伤心万分,内心风雨交加,千古悲伤风起云涌。”[9](P20)这些超常规的词汇搭配破坏了正常的语法规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借助异于常规的语法结构造成了语言的张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毕飞宇甚至会把意义截然相反的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如“充满爱意的冷若冰霜”[16](P189),“没有物质地纷乱如麻”[9](P13),“最痛苦最残酷的幸福和愉悦”[17](P120)等。相反的力量被纳入到同一个语境,产生了冲突,建立起了一个不可能逻辑解决的悖论漩涡。截然相反的词义所构成的巨大张力使我们体会到文本意义的多种指向和哲理意义。
感性和智性的双重叙述话语的运用也是构成毕飞宇小说语言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毕飞宇总是赋予他的文本一种非常感性、直观的‘外壳’——生动的故事、新奇的想象、生活化的经验、丰满的细节、变幻的景物、戏剧性的场面……在他的小说中可谓层出不穷”[18](P49~57),但是我们在文本中也常看到很多哲理性的语句,如:“故事没有平面,故事的惟一可能就是它的纵深难度,这是故事的属性。”[19](P96)“什么也别想逃过人们的想象力。历史是沿着想象力顺流而下的局面。”[20](P11)“形而下”的感性话语和“形而上”的智性话语使小说文本在充满故事性和可读性的同时,还具备了思想深度。这也把他和以“欲望化叙事”和“平面化叙事”为特征的其他新生代作家区别开来。
除此之外,简省凝练的语言同样可以形成一种张力。“凝练,简练,前提都在于以‘多’炼‘少’,自此才会‘一’中又‘多’,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意义的外指与文字的内指形成相反相成的力。”[21](P61~67)毕飞宇在小说中大量运用短句、散句,结构简单,短小精悍,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由于篇幅的限制,就更加注重语言自身价值的扩展,简短而内涵丰富的语言极大地延展了短篇文体的容量,如“女孩的美与丑与政治很像,处在悬崖之上,要么在峰巅,要么在深谷。没有中间地带。”[16](P180)“但小云到底出事了,她给‘抓住了’。这三个字常跟随在美人身后,世俗生活因此险象环生又饶有情致。”[22](P93)可以看出,在这些简洁凝练的语言中,有着很大的信息密度,小说的叙事容量和艺术蕴含得到了丰富和扩大。
二、叙述方式构成的张力
(一)叙述结构构成的张力
毕飞宇的小说多采取两组或多组叙事序列交织的结构,其中有种对比式的复调结构,通过不同叙事序列的不同之处来表达意义,相互对立又交叉呼应,“这种复调式的叙事结构恰好实现了多声部的言说,并且能在比较之中使作者的意图得到更深刻鲜明的呈现,使小说文本更具有张力与表现力,从而构成了一种深度批判模式。”[23](P22)
《九层电梯》中“我”的乡村童年生活和女儿的都市童年生活两组叙事的对比,揭示了现代都市文明对儿童乐趣的剥夺;《驾纸飞机飞行》中“我”和妻子的婚姻同表姐与排长的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作者对于爱情世俗化这个命题的思考。在这些小说中,对比叙事序列构成的张力使文本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此外,毕飞宇的小说还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所构成的张力,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成长叙事中。巴赫金认为在成熟的“成长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24](P232)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和《那个夏天,那个秋天》中,主人公们都经历了他们生命中残酷的青春成长,但是到最后,无论是性格坚强的玉米和吴蔓玲,还是软弱的玉秧、耿东亮,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成长,时代的荒谬、政治的压抑、现实的残酷、权威的压制,使得他们不是随着时间一起成长,“而是个体和时间在晦暗的历史深处一起陷落。”[25](P131~135)在这里,作为小说表层结构的成长叙事和作为深层结构的反成长叙事构成一种张力,展现了青春成长的苦闷、无奈和残酷。也使得毕飞宇小说中的青春成长经验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恒久的人性诗学。
毕飞宇笔下的故事多以悲剧为主,毕飞宇曾说:“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伤害。我的所有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26](P26~33)毕飞宇在部分文本中运用了“悲/喜”互峙的张力形式,即用表层的、外部的喜剧方式来表达深层的、内在的悲剧内涵。比如在《平原》中,沈翠珍一行因为秘密从事佛事活动而被游街,游街本身是一件严肃的富有政治色彩意味的事情,在小说里却被交给了十来个七八岁的孩子闹剧似的完成,三丫的死也是个悲剧,可看看事发后作者的描述:“所有的人都冲出了家门,他们在跑。许多人都在咀嚼,许多人的手上还握着碗筷。他们冲到了孔素贞的天井,当然,扑空了。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凭借着对事态的发展无与伦比的判断,直接向合作医疗冲锋而去。在孔素贞的家与合作医疗之间,一路鸡飞,一路狗跳。”[13](P200)这无疑是一场民间的狂欢,这种“悲/喜”互峙的张力形式深刻揭示了故事深层次的悲剧内涵,却又不使读者跌入紧张和沉重,使叙事节奏变得张弛有度,在“驰”里有“张”的深思和批判。
(二)叙述视角构成的张力
儿童视角也是毕飞宇经常采用的一个策略,但是身为成人的作者在面对以儿童视角建构的文本时,不可能完全不做任何的干预和介入,尤其是当这些作者建构的故事往往与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时,作者采纳的儿童视角更不可能是纯粹的。成年人对现实的评论性声音与姿态总是掩饰不住地显现在少儿的叙述中。在毕飞宇的儿童视角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富有哲理意味的议论:“然而,水,米,火,这三个字构成了我对汉字及生活的基本认识。它们至关重要,是我们生活的偏旁部首。”“专制不领巴结的情,只有服从,这是专制的凌厉处,也是专制的无用处。”[27](P214)这些极富哲理性的语言明显超过了身为儿童的叙述人的认知,是叙述人背后那个隐含的成年作者的声音,这实际上形成了儿童和成人两套话语系统,使文本具备了叙事的张力,在丰富文本内涵的同时将主题引向了更深的层面。
此外,毕飞宇还擅于运用乡村人的视角来写城市,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在城市的时候很少单纯地写城市,同样,写乡村的时候也很少单纯地写乡村,而是用城市的眼光写乡村和用乡村的视角写城市。”[4](P144)这就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对比的张力。在《生活在天上》中,蚕婆婆在村里人羡慕的目光下进城同儿子享受城市生活,却无比失望的发现城市就是“上得了天、入不了地的鬼地方”;《哥俩好》中的图北,出身乡村,却背负着家族使命在城里读书,他一直努力去融入城市,却最终以出卖肉体维生的悲剧收场。图北本来是为了逃避乡村来到城市,当遍体鳞伤之后,渴望故土的抚慰时,却发现自己曾经的故乡和自己的初恋对象一样,在追逐城市化的过程中面目全非。作家在批判乡村人盲目热衷城市的心理的同时,对都市造成的人和生活的异化进行了揭示。这种城乡间的互文表达构成了一种张力,“表现出一种双向批判的立场和态度——人无论来自哪里,身处哪里,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困境。”[28](P51~56)
(三)叙述节奏、时空构成的张力
毕飞宇的小说“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这种举重若轻的张力的形成与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也是分不开的,“无论冲突何等剧烈,主题何等尖锐,一旦话语进入人物的内心,便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节奏。”[29](P57)《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的“我”,因为无意中抢了兄弟的女人而紧张不已,冲突一触即发,但一切矛盾都被作者化解到了人物的内心中,情节始终保持着轻松自如的状态,《写字》中的“我”对父亲的权威保持了一种内心特有的对抗方式,不剧烈爆发,但是也决不屈服。“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毕飞宇的小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步履,舒缓,柔软,纤细,仿佛行云流水,所有的波澜都潜藏在内部。”[29](P57)
“在叙事中,还可以通过模糊掉物理时空,使叙述指向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每一日并贯穿其一生而获得张力效果。”[30](P20~25)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虽然写的是文革时期,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文革的正面叙事,“在王家庄,历史/反历史编码都失效了,发生‘文革’也好,不发生也好,对于玉米、端方、和三丫,都留不下大的痕迹。一代代人的经验几乎不变地从他们身上流过,他们在麦收、歇夏、拉练、恋爱等过程中经历着自己的丰富、疼痛与惊心动魄的微妙。”[14](P50~56)故事因为时代背景的虚化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这样就和那些同样以文革为背景的启蒙叙事区别开来。
(四)意象构成的张力
毕飞宇喜欢在小说中设置意象,擅长用意象来蕴含深层的意义。在“王家庄”系列小说中,“高音喇叭”就是个很重要的意象。毕飞宇曾说:“熟悉我作品的朋友们一定知道,高音喇叭是我时常描绘的对象。可以这样说,高音喇叭充斥了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每一天。喇叭只是播音,或者说,只是有人说话。但是,如果声音的音量到了一定的限度,那就不只是播音,不只是有人说话。你必须听。……高音喇叭里从来没有新闻,只有宣传,它是一种暴力。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31](P59)在这里,高音喇叭是专制和权威的象征,是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手段。《生活在天上》中那些“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的蚕;《九层电梯》中“关在高楼里的猫”、“装在瓶子里的蚂蚁”;《遥控》中没有内脏却依旧可以游泳的鱼等意象都暗示出都市中的生命个体的“作茧自缚”以及现代人压抑空虚寂寞的生存困境。《雨天的棉花糖》中的“二胡”贯穿始终,既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力量,又象征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哀婉凄迷的二胡声给全文笼罩了一层忧伤的调子。
三、角色的张力
“角色张力的有两种方式:一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张力;二是角色自身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张力。”[21](P61~67)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式都普遍存在。
先来看角色与角色间的张力,无论是《青衣》中筱燕秋和李雪芬、春来的冲突,还是《玉秀》中玉米和郭巧巧、玉秀的对抗,都构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角色张力。而且在有的小说中,角色之间的张力趋于多层化,如在《玉秀》中,郭巧巧因为敌视后母而和玉米产生矛盾,玉秀因为争取权力而讨好郭巧巧,和郭巧巧站到了一方,从而使得玉米和玉秀又发生了冲突。在《那个夏天,那个秋天》中,主人公耿东亮与母亲之间,与老师炳璋之间,与经理李建国之间,与富婆之间,都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关联。这种关联带来了角色之间的对立矛盾冲突却又相互统一,彼此连结。耿东亮与母亲的妥协与抗争,对炳璋的感激和逃避,对经理李建国的依赖和反感都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就构成了角色之间的张力。
“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形与圆形两类,圆形人物的魅力便在于角色内部的张力。”[21](P61~67)毕飞宇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圆形人物,《玉秧》中的玉秧是个平庸本分且勤奋用功的乡下姑娘,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城里师范学校。玉秧老实得近乎懦弱,身体不适也不敢拒绝老师要求的长跑,因怕被误认作小偷宁愿倒贴钱也不敢据理力争。可是,玉秧的内心又有着强烈的对权力的渴望和出人头地的欲望,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甘愿接受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的猥亵,利用手上的权力伤害了很多周围的人,多重对立的性格侧面统一到了一个人身上,矛盾冲突同时在性格内部展开,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集中表现出人性的弱点。《那个夏天,那个秋天》中的耿东亮,从小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内心却强烈渴望着自由,在寻找自由和失去自由的对立与联系中,耿东亮这一角色内部的张力得到恰到好处的展现,使得这一人物蕴含了蓄势待发的气势,这就是角色内部张力带来的效果。
“另外,荒诞、魔幻、变形,这也是形成角色张力的一种方式。司空见惯的角色在客观描述下与生活原态一样平淡无奇,因而再现生活逻辑的叙述也就未必具有意义。反之,若将习以为常的人物置于神魔境界,则会有异于寻常的效果。”[21](P61~67)毕飞宇在部分小说中也运用了荒诞、变形的手法,在《蛐蛐蛐蛐》中,蛐蛐都是亡魂变的,而一无是处的孤儿二呆却在蛐蛐面前有惊人的智慧,总是能抓住最厉害的蛐蛐。而秘诀竟是:“盯着每一个活着的人。”怨气越深的人死后变的蛐蛐越厉害,反映出那个荒诞的时代对人们造成的伤害。《遥控》则用漫画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一切生活都靠遥控的“包租公”。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包租公”因闲得无聊去买菜做饭,却没能吃上这顿饭,因为“当我把这样的一条鱼放进水桶的时候,它竟然没有死,它在游,又安详又平静,腆着一只白花花的大肚皮。它空了,没有一张鳞片,没有一丝内脏,没有一片腮。就是这样一条鱼居然那样安详、那样目空一切,悠闲地摆动它的尾部。”[32](P116)这个情景显然是不真实的,但这却隐喻了一种极度空虚无聊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变形的事件和客观的描述形成了张力,引发出新的观察角度,更加发人深省。
“意象、意境、叙事与角色,这几个方面的张力往往水乳交融。有时角色即是意象,角色张力与意象张力都是在叙事张力中得以展开,也正是叙事张力的一步步推进使得角色张力、意象张力得以完成。往往是这几个方面的合力促成了非常情境的营建。”[21](P61~67)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实质就是制造非常情境的过程。张力叙事不仅使毕飞宇实现了自己“轻盈而凝重”的小说理想,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富有歧义的,多价的,也是抵制终极阐释的小说文本。”[33](P5)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王思焱.当代小说的张力叙事[J].文学评论,2002,(2).
[3][德]恩斯特·卡西尔.甘 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张 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毕飞宇.玉米[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6]毕飞宇.男人还剩下什么[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7]施战军.克制着的激情叙事——毕飞宇论[A].胡健玲.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中)[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8]毕飞宇.马家父子[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9]毕飞宇.叙事[A].毕飞宇作品集(第5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0]毕飞宇.怀念妹妹小青[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1]毕飞宇.手指与枪[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2]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3]毕飞宇.平原[M].上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14]张 钧.“现代”之后 我们往哪里去?[J].小说评论,2006,(3).
[15]毕飞宇.五月九日和十日[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6]毕飞宇.枸杞子[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7]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A].毕飞宇作品集(第5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18]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J].当代作家评论,2000,(6).
[19]毕飞宇.家里乱了[A].操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0]毕飞宇.充满瓷器的时代[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1]孙书文.文学张力:非常情境的营建[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3).
[22]毕飞宇.是谁在深夜说话[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3]宋 平.毕飞宇小说叙事论[D].苏州:苏州大学,2008.
[24]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5]吴雪丽.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及其文学史意义[J].南方文坛,2012,(3).
[26]毕飞宇,汪 政.语言的宿命[J].南方文坛,2002,(4).
[27]毕飞宇.写字[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8]王 越,宋喜坤.主体,立场与姿态[J].文艺评论,2003,(1).
[29]洪治纲.谈毕飞宇的小说[J].南方文坛,2004,(4).
[30]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6).
[31]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32]毕飞宇.遥控[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33][美]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