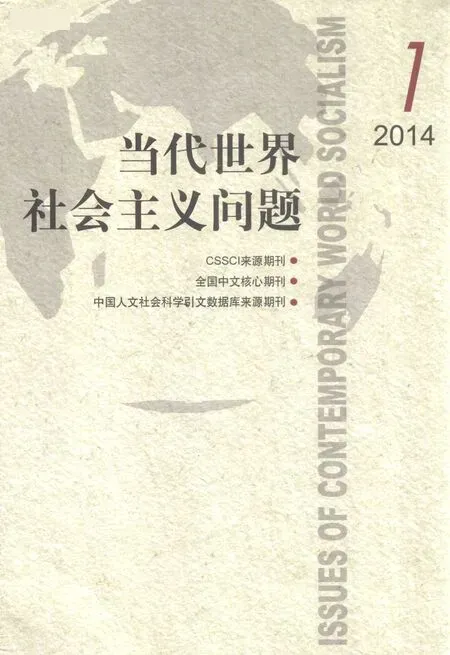公民社会与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型
2014-03-29何海根
何海根
在斯洛文尼亚学术界,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学者将1980年代公民社会的复苏、发展和壮大看作斯洛文尼亚实现民主转型的动力。在80年代的政治变革进程中,公民社会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公民社会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环,斯洛文尼亚共盟作为整个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斯洛文尼亚学界关于公民社会概念的探讨
1981年,匈牙利籍美国学者安德鲁·阿拉托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著作《公民社会对抗国家:1980—1981年的波兰》,公民社会这一术语被用来解释和构想波兰团结工会的作用和特征①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Poland 1980-1981”,in Telos,No.47,1981.。波兰的经验提供了关于东欧民主反对派活动的新解释,即建立一种居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强大的和独立的社团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在东欧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中,最著名的有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一系列反对派团体。许多研究反对派的理论家将公民社会看作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主义的“第三条道路”②[英]吉迪恩·贝克:《公民社会和民主:理论和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在分析促使斯洛文尼亚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转型的因素时,众学者都会谈及公民社会在其中的作用③例如Frane Adam and Matej Makarovicˇ,“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nd social sciences:the case of Slovenia”,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36,No.3,2002. 以及 Anton Bebler,“Slovenia's smooth transi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等在谈及斯洛文尼亚的民主转型时都专门论述了公民社会的作用。。
在斯洛文尼亚学界,公民社会一词在80年代才被“再创造”出来。而在此之前,公民社会只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才被使用,基本上没有关于公民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斯洛文尼亚80年代出现的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源于三点:第一,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政府和团结工会之间的斗争表明了政府和自我管理形式之间的区别,团结工会的经验及其管理形式和意识形态立场受到广泛研究。1981年波兰颁布戒严令并取缔团结工会两个月之后,斯洛文尼亚便发表了一份一千多页的报告,分析和评论了波兰形势以及共产主义体制的将来。第二,80年代初斯洛文尼亚自身的状况。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和新兴文化团体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出现,并很快与“国家”发生冲突。几乎所有参与讨论公民社会的人士,同时也参与了至少一项新社会运动。这些人通过参与讨论来反映自身行为。因此,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特征,通过将各类自治组织的形式概念化,进而与国家机构分庭抗礼。第三,国际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一封题为“公民社会对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为何重要”的信件,激发了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学会的内部讨论。但这些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相关的理论圈之内,而是扩展到报刊杂志领域,如《青年》、《电报》等。到80年代中期,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已在政治和理论层面普遍使用④Pavel Grantar,Discussions on civil society in Slovenia,In Adolf Bibicˇ,GigiGraziano(eds.),Civil society,political society,democracy.Ljubljana:Sloven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4,p.356.。
在这场讨论中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功能以及实现它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异见政治活动家弗拉内·阿达姆归纳了当时主要的三种践行公民社会的路径:(1)作为社会反对派,包括新社会运动;(2)作为“自治”的社会;(3)作为一个关系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①Frane Adam:O trehpristopih k pojmu"civilnadružba"(Threeapproaches to the notion of civilsociety),in Družboslovne Razprave(Social Discussions),Vol.4,Issue 5,1987.。
第一种路径强调公民社会的“反对派”特征。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团体、组织和运动,以一种“反政治”的形式,将自身与受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支配的政治空间划清界限。这种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要求摆脱体制管制,实现个人生活的自主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拓展社会生活的自主空间时如何免遭国家、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建立公民社会被看作要建立一个“平行的社会”(相对于国家而言),为人权和公民权而进行斗争。第二种路径尝试协调社会主义的自治理念和公民社会。这是将社会主义自治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后者已不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相适应。这种路径强调,将共产党的行为作为公民社会中一项共同的智力资源,从而实现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将“自由工人的联合”概念化,并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部分。这种路径的倡导者一开始便拒绝了政治多元化的理念。第三种路径更具有社会学的倾向,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和观点来定义公民社会。现代化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的自主范围发生分化和构建,这些社会行动区别于国家行为。公民社会是现代化的结果,被用来界定社会生活的自主范围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弗拉内·阿达姆关于践行公民社会的三种路径实际上分属于民主运动的两个不同时期,在斯洛文尼亚民主转型时期,公民社会的特征是作为反对派运动,而在民主巩固时期,则要从斯洛文尼亚的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待和分析斯洛文尼亚的公民社会。
二、民主转型时期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的三个阶段
在斯洛文尼亚民主转型时期,公民社会的复苏和兴起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象征意义和对政治转型的作用都不同。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公民社会开始复苏;(2)80年代中后期,公民社会“政治化”,形成特定意义上的“政治社会”;(3)90年代初作为“反对派”的公民社会实现“政党化”,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
第一个阶段是“新兴运动时期”,是公民社会的复苏时期。由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全部公民社会组织,而是或多或少地将各种社会组织纳入以共盟为主导的体制之中或对其加以限制,例如宗教组织、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都存在于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因此,80年代公民社会的发展指的是新组织的产生和旧组织附属地位的改变。其中,开启公民社会复苏进程的是众多新兴活动和组织的产生,它属于西欧新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早期新社会运动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被参与者称为“新兴场景”(Alternative Scene,或者简称为Alternative)。公民社会便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并成为东欧各国公民社会“再创造”风潮的一部分。新兴运动以“自主的社会团体”的形式,70年代后半期开始活跃于斯洛文尼亚民间社会。1983年,一个主题为“什么是新兴的?”的研讨会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组织者是卢布尔雅那的“新兴场景”。“新兴场景”的意义在于它培育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奠定公民社会组织化的基础,特别是,它是出现独立的公共领域的催化剂。在第一个阶段,公民社会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有别于共盟意识形态的“另类”生活理想,而不是作为斯洛文尼亚共盟当局的反对派,因此,这一时期公民社会运动主要是各种青年亚文化活动的流行,常被学者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社会”。斯洛文尼亚兴起的第一种新社会运动是朋克。朋克这种非主流的摇滚音乐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出现在1977年,是重构具有独立性的斯洛文尼亚社会的首次尝试①TomažMastnak,“Civil society in Slovenia:from opposition to power”,in Jim Seroka and Vukasin Pavlovic edited,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rmonk,N.Y.:M.E.Sharpe,1992,p.51.。朋克首次突破了60年代南斯拉夫镇压自由化运动之后的体制,它的主要参与者成长为斯洛文尼亚未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教影响的第一代青年。当局对朋克的最初反应是使用警察力量进行压制和约束,但最终未能如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朋克的参与者将对当局的控诉通过大众媒体诉诸公众领域,警察与朋克之间的冲突被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内;第二,朋克促进了具有更广泛基础的社会动员的出现 (如“民主阵线”),斯洛文尼亚当局被谴责奉行“反青年的沙文主义”,并且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第三,具有官方背景的斯洛文尼亚青年联盟屈从于来自“底层”的压力,将朋克青年吸纳进该组织,并“倾听”这些更具有批判性和活跃的新一代青年的声音。警察机关的“失败”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朋克运动开启了领域更广泛、自主性更强的社会活动公共空间。紧随朋克运动的是以和平主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等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到80年代中期,新社会运动和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斯洛文尼亚社会逐渐建立起关系网络。
第二个阶段是“政治化时期”,始于80年代中后期,公民社会的作用不再是脱离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二社会”,而是逐渐走向体制内或者与体制发生冲突。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府、执政党、反对党和公民社会本是不同角色、不同功能、相互区别的民主行动者,但斯洛文尼亚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公民社会却是以自身政治化的方式发挥其功能。就这些社会组织的性质而言,斯洛文尼亚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公民社会更接近一个“政治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本质上是社会政治组织。1985年,以新兴运动发端的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开始“政治化”,这几乎是公民社会继续发挥其功能的唯一方式。1985年以前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并不成熟,组织性差、制度化水平低、聚众性强,许多社会运动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甚至不能称其为运动,准确讲它们属于聚众“活动”。在非民主体制下,特别是全能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十分有限,要获得更宽的发展空间和实现诉求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参与政治领域中的活动,降低自身社会性,增加政治性的成分。这个“政治化”过程也并非只是斯洛文尼亚政治社会形势的内部产物,而是和整个东欧的民主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其转型方式的一部分。
“政治化”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当局主动将部分公民社会组织和运动纳入体制内,二是公民社会自身衍生出“反对派”。前者始于1985年斯洛文尼亚共盟的话语体系开始使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后者始于1988年人权保护委员会的成立。
斯洛文尼亚共盟改变态度开始接受公民社会,起初是因为共盟认为,新社会运动只是对西方类似活动的“赶时髦模仿”,未来这些运动自会消散。此外,共盟利用葛兰西的新马克思主义将公民社会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语言的解释范围,以此证明公民社会问题本质上与自治社会主义相联系,自治模式实际上是真正能够实现的公民社会,因此公民社会就成为党的纲领的目标之一。共盟内部也开始将新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正面的社会现象。关于公民社会的党内讨论持续了数年,直到斯洛文尼亚共盟意识到,公民社会问题绝不是单纯的观念和理论问题,而是一场“争取青年”的较量。将一些新社会运动纳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进行管控,虽然这是十分精明的决定,但这项政策却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共盟实际上未能争取到青年人。1986年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大会一反常规,宣布青年联盟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组织,这等于公开声明青年联盟不再发挥作为党的“青年传送带”的作用。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不再作为新社会运动组织的“保护伞”,而是全盘接收新社会运动的目标诉求,通过自身的转变来实现与新社会运动更加紧密的合作。如此一来,“新兴场景”自然而然地成为斯洛文尼亚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青年支持者的流失和来自公民社会相对较强的压力迫使斯洛文尼亚当局不得不推进自身的改革,共盟改革派摆脱老人政治家的束缚,开始谨慎地向社会民主党转型。除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反叛”之外,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也整合了一些独立的社会团体,使其运作和活动合法化。通过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两大政治社会组织合作,公民社会实现了部分“政治化”。
公民社会“政治化”的第二种方式是社会性组织转变为政治性组织,社会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从而转变为共盟的反对派。这种转变途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民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要与共产党当局对抗,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对于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来说,斯洛文尼亚共盟当局属于“温和派”,真正的强硬对手来自联邦,以南斯拉夫人民军为核心。有证据显示,早在1985年,军队就启动了名为M ladost(意思为“青年”,塞尔维亚语)的反对民主化的行动,实际上斯洛文尼亚的“新兴场景”一直受到军警的监控,新社会运动和其他自主性行动被视为“反社会主义”。1988年春“四人受审”事件可以看作是军队直接干涉斯洛文尼亚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步。出乎意料的是,这次逮捕和审判,立即导致斯洛文尼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强有力的社会抵抗。因为80年代兴起的各类新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经验、参与体验和行动习惯的基础,故而少数知识分子成立人权保护委员会之后便迅速得到公众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各类新社会运动组织纷纷加入这个委员会,新社会运动最活跃的参与者在人权保护委员会中发挥核心作用。一个专门为四位“嫌犯”维权的普通组织,能在短期之内发展为拥有超过一千名集体会员,近十万名个体支持者的政治性组织,而且能够有效地做好内部协调、组织活动、表达诉求等,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功不可没,特别是从国家的管控之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以人权保护委员会的行动为契机,独立的社会行动演变为独立的政治行动,此前那些非政治的、反政治的自主行动相继加入了政治成分。因为非政治性的特征和纯法律的目标,人权保护委员会才吸引了公民社会组织和人员的加入,但委员会的运作又不得不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的“政治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使斯洛文尼亚在1988年和1989年两年间出现特殊的多元主义结构。一方面,斯洛文尼亚政治空间的多元化得益于人权保护委员会的成立和壮大;另一方面,由于人权保护委员会对公民社会的“吸收”,独立的社会组织几乎消失,对政治冷漠的反政治群体转变为热衷政治的政治反对派,进而形成一个两极化的政治空间:人权保护委员会和日渐衰落的斯洛文尼亚当局。然而,即便是这个两极化的“多元结构”也有相当高的同质性,因为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贝尔格莱德被视为民主化的最大威胁,从这个角度上看,到80年代末,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斯洛文尼亚已经“暂时消失”,政治领域内的多元性由于“一致对外”的需要也已经同质化。与其说人权保护委员会是斯洛文尼亚共盟当局的反对派,不如说只是持相似政治立场的双方在进行权力竞争。
第三个阶段是“政党化时期”,公民社会中的许多组织转变为正式的政党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继续“政治化”的延续。到1989年2月,估计斯洛文尼亚已有一百多个独立的基层组织和十个独立的政治社团①Paul Shoup,“Crisis and Reform in Yugoslavia”,in Telos,No.79(Spring 1989),p.141.。在法律允许之前,具有政党形式和功能的政治组织以联盟的形式存在。新政党的先驱是1988年5月20日成立的斯洛文尼亚农民联盟 (Peasant Alliance),不过农民联盟仍是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员,起初它的自我定位是专业性组织。类似性质的其他联盟相继新建并进入政治领域,然而这些联盟的纲领迥异,有些主要关注民主化问题,有些优先考虑民族问题,还有些联盟的纲领纯粹以反共产主义为基础。到1990年初,附属于斯洛文尼亚共盟的一些政治组织和联盟也基本完成了“政党化”。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改名为自由民主党,社会主义联盟改名为社会党,老战士协会和社会主义工会依旧是非政党的组织,斯洛文尼亚共盟1990年2月在原名的基础上改名为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复兴党。为了参加多党制选举,农民联盟、社会民主联盟、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于1989年11月成立“民主反对党联盟”,即“德莫斯” (Demos)。次年选举前,规模较小的绿党,代表小商人的自由党、代表退休者的灰豹党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党也加入了“德莫斯”,从公民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德莫斯”在大选中获胜,取代了共盟的执政地位。
三、公民社会与共盟共同推进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型
斯洛文尼亚学者托马日·马斯特纳克认为,开启斯洛文尼亚民主化进程的行为者是“新社会运动”,而不是异见知识分子、共盟改革派或者老的新左派精英。而且,正是“新社会运动”在公民社会的形成阶段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①TomažMastnak,“Civil society in Slovenia:from opposition to power”,in Jim Seroka and Vukasin Pavlovic edited,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rmonk,N.Y.:M.E.Sharpe,1992,p.49.。这种观点在斯洛文尼亚学术界很有代表性,大多数学者都把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发展归功于公民社会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反对派运动,认为公民社会是导致东欧民主转型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忽视了原社会主义政党的自我革新。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的复苏和发展与其民主化进程始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将民主的成功转型完全归功于公民社会,或者把各种非主流运动都等同于民主行动也是不客观的。因此,要正确评价公民社会对斯洛文尼亚民主发展的作用。
第一,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首先,公民社会的作用在于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防止政治国家的膨胀,这是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复苏最重要的意义,如果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这种制约关系,民主政治也无从谈起;其次,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最初以“第二社会”、非政治的活动形式出现,以一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共盟进行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改革,没有“多元主义”,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再次,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的复苏促进了政治参与,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组织性和民意支持的社会组织,锻炼了社团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这些组织发展为新政党的雏形,而且多党制选举后首届政府和议会的精英大多是新社会运动和反政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公民社会孕育了民主的政治文化,它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丰富、思想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提供了土壤和接纳空间,这也是认为早期新社会运动开启斯洛文尼亚民主进程的原因所在。
第二,公民社会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斯洛文尼亚的公民社会必须区分早期和晚期的不同特征,早期公民社会运动大多表现为各种非主流文化的传播、新兴团体组织的出现,这些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分散性、聚众性和低度的组织性,不属于成熟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它所涉及的内容和主题与民主政治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朋克和一些非传统的新兴运动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专门的活动场地逐渐关闭,后来连酒吧也明确拒绝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甚至随处可见的涂鸦也被清除,海报和通知被撕掉。发起、参与抵制新兴活动的人以“有道德的大多数”的名义积极行动,或者视自身为“民意”(voxpopuli),要求“相关责任者和单位”采取行动。抵制行动在邻居间、地方社区、公共场所都构成一定程度的组织网络,成为另一种公民社会的力量。新兴运动激活了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转而反对其自身的民主潜力,这种现象被托马日·马斯特纳克称为“来自底层的全能主义”①TomažMastnak,“Civil society in Slovenia:from opposition to power”,in Jim Seroka and Vukasin Pavlovic edited,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rmonk,N.Y.:M.E.Sharpe,1992,p.55.。斯洛文尼亚学者将反对“新兴场景”的声音,特别是非国家力量对新兴运动的抵制,看作是暴力的“社会化”以及“公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的表现。这种看法缺乏对斯洛文尼亚早期公民社会的正确认识。严格地讲,“新兴场景”只是新社会运动的开端,而且只是新社会运动诸多主题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斯洛文尼亚1985年以前的公民社会是不成熟的。斯洛文尼亚早期公民社会的作用在于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而真正对民主转型发挥作用的是1985年以后的公民社会。此后这一时期的公民社会运动逐渐转向和平主义、女权主义、环保和争取同性恋权利等方面,直到1987年各项新社会运动才被斯洛文尼亚社会普遍接受,这些运动描绘的政治和社会图景才获得公众较为广泛的认同。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5%的人认可这些运动,多于40%的人表示有意愿加入其中②Božo Repe,Slovene history——20th century:selected articles.Ljubljana:Department of history,Faculty of arts,2005,p.97.,这在1985年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要客观评价斯洛文尼亚共盟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学者常常聚焦于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给予公民社会的支持。强调公民社会的影响的同时,也要正确地评价斯洛文尼亚共盟80年代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对诸多民主形式的认同。
首先,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欧洲现象”,在包括东欧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里都存在,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斯洛文尼亚特有现象,但斯洛文尼亚社会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官方背景的许多组织也参与其中。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属于“个人层面”,来自政治异见人士、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工会主义者、学生、生态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第二部分属于“组织层面”,大量的非宗教性团体和组织性相对较弱的非正式团体,大多是共盟体制的“附属组织”,如作为党的“传送带”的两大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它们使用共盟的设施、人力和资金招待那些新的学术小组、俱乐部、协会和新政党的前身组织。
其次,斯洛文尼亚共盟接受公民社会的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公民社会的新主体。在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模式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所赋予民众的“参与”是最多的,“参与”虽不自由,却是客观存在的形式,并且有法律规定的保障。用独裁、专制、极权主义等术语来形容80年代的斯洛文尼亚共盟是不准确的。改革派掌权以后,共盟在这一时期坚定地反对塞尔维亚的集中主义政策,对各种反对派运动持包容和妥协的态度,而且顶住来自联邦政府的压力,在斯洛文尼亚率先进行多党制选举。对于日渐兴盛的新社会运动,包括一些非主流的团体活动,斯洛文尼亚当局在尝试干涉失败后便认识到国家政权的能力有限,于是放弃了继续行使暴力压制的权力,将其转交给“公民社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还将部分新社会运动团体纳入了体制之内,使之合法化且不丧失自主性。在所有的媒体中,青年联盟的官方出版物《青年》周刊的声音最为激进,而且不再盲目服从斯洛文尼亚共盟的领导和管理。每一次《青年》的封面或文章遭当局封禁之后,销量就会大增。80年代初的发行量大约在一万份,而在政治气息浓厚的1987—1989年里,发行量猛增到八万,其他斯洛文尼亚周刊都不能与之匹敌①Leopoldina Plut-Pregelj,AlesˇGabricˇand Božo Repe,The repluralization of Slovenia in the1980s:new revelations from archival records.Seattle:The Henry M.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Washington,2000,p.33.。但斯洛文尼亚当局并没有取缔这一周刊,而是尽可能地容忍它的存在。除此之外,斯洛文尼亚共盟还包容具有官方背景的“作家协会”积极“介入政治”的传统。1984年,在协会的框架内成立了思想和创作自由保护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回应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行为。1988年4月,作家协会出版了一份“斯洛文尼亚宪法材料” (俗称“作家宪法”),以“外部专家”的形式积极参与斯洛文尼亚共盟主导的修宪进程,阿道夫·比比奇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平行的议会”②Adolf Bibicˇ,The emergence of pluralism in Slovenia,in Communist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26,No.4,p.372.。1989年5月8日在议会广场宣读要求斯洛文尼亚实现民主和独立的“五月宣言”的托内·帕夫切克曾在1979年至1983年担任作家协会主席。
最后,斯洛文尼亚共盟和政府与反对运动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特殊,其处理反对派运动的立场是“批评与支持”的“混合”,一方面对反对派持批评态度,一方面又赞同反对派的一些观点和理念。1986年,斯洛文尼亚各类“新兴运动”深受民众的欢迎与支持,发展势头如日中天。斯洛文尼亚领导层一方面谨慎地分析“新兴运动”的走向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对批评和异见又持有一种“软态度”。面对反对的声音和行动,当局避免专制的南斯拉夫司法系统的介入,绝大多数个案都交由警察和检察官处理。当局的处理方式表明,一方面迫于公众压力,掌权者的个人责任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或政治中枢的分支机构具有相对高的独立性的结果。尽管中央委员会主席仍然拥有最大的权力,但这些分支机构不再严格地听从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①Leopoldina Plut-Pregelj,Aleˇs Gabriˇc and Boˇzo Repe,The repluralization of Slovenia in the1980s:new revelations from archival records.Seattle:The Henry M.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Washington,2000,p.40.。“软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个人的容忍水平,以及这些人支持和保护斯洛文尼亚业已开启的民主化进程,并抵制来自南斯拉夫联邦的压力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