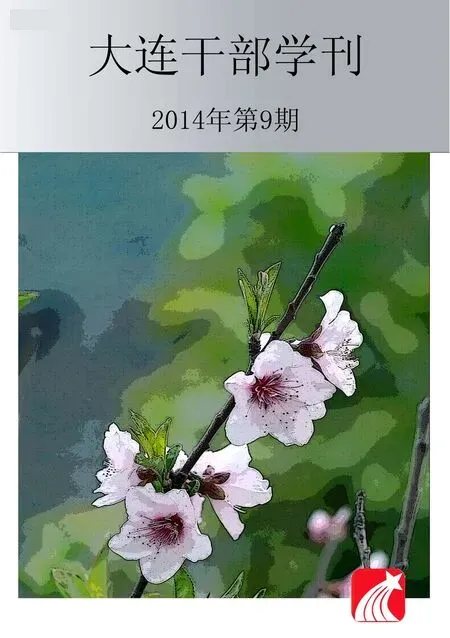甲午战争之平壤会战、黄海海战述略
2014-03-29孙高杰
孙高杰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辽宁 大连 116013)
甲午战争之平壤会战、黄海海战述略
孙高杰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辽宁 大连 116013)
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战争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会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平壤会战是近代以来清日两国陆军正规部队首次大规模交战,以清军的败退而告终,使战火烧至中国境内。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的转折点。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避战保船政策,致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军手中。
甲午战争;平壤会战;黄海海战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 “济远” “广乙”,悍然击沉清军租借运兵的英国商轮 “高升”号,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略计划是:首先在陆路击败驻朝清军,在海路以联合舰队击败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主力军队在山海关登陆,会同自辽东南下的日军与清军进行平原大决战。清政府的战略总方针是 “海守陆攻”。在海路由北洋舰队集结于旅顺口或威海卫, “做猛虎在山之势”,使日舰 “不敢轻与争锋”,确保京畿门户安全。在陆路,迅速增兵朝鲜,将陆路战斗限制于朝鲜境内[1]。在甲午战争第一阶段中,战争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会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一、平壤会战:近代中日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
丰岛海战发生时,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考虑到牙山易攻难守,为 “军事绝地”,且可能成为日军进攻对象,在聂士成的提议下,清军决定退出牙山。聂士成率部移师成欢布阵,主帅叶志超则率千余军移向天安,坐镇聂军后方。同期,日本陆军4000余人由大岛旅团长指挥,从汉城南下准备进攻牙山之清军。探明清军主力已经移师成欢后,日军迅速跟进,并于28日拂晓突然发起进攻。驻守天安的叶志超闻知前方战斗,心中胆怯,按兵不动没有增援聂军。激战数小时后,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天安方向遁逃。途中聂军和叶军相遇,二人决定放弃成欢向平壤方向撤退。
成欢战役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接仗,虽然规模相对较小,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役,清军伤亡500余名[2],遗弃大炮8门,帐篷90顶、步枪30支及大量的枪炮弹药[3]36。其官兵军事素质落后,无法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等问题也在这场战役中暴露无遗,此后失败主义情绪一直在军中弥漫。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在战后不但讳言清军在成欢之战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粉饰败绩,铺张战功,谎报此战杀敌数千, “倭先逃遁”,而朝廷竟不明察,传旨嘉奖。这样,其结果只能使清军沿着这条失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4]。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完全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为后来发动平壤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大量军粮有效补充了粮食短缺的前线部队。 “开战后第一冲突之胜败,关于尔后两军志气者极大”[5],因此可以说,成欢之战的结果,预示了清军平壤战役的失败。
遵照光绪帝的出兵谕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下令向朝鲜增派援兵。自7月21日开始,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和丰升阿四部人马先后赶赴平壤。四路大军日夜兼程、头顶酷暑徒步数百里,分别于8月4日至9日间抵达平壤。清廷的早期作战目标是用赴平壤的援兵和牙山之叶聂军汇合,对京城的日军形成夹击攻势。但派往平壤的兵力尚未到达,日军就击溃了叶聂军,迫使清廷放弃夹击计划,只能固守平壤与日军决战。不久,叶志超、聂士成带领的成欢残兵陆续到达平壤。届时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400人,拥有山炮28门、机关炮6门,贮存了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3]37。8月23日,李鸿章接朝廷上谕,命令在朝清军向日军发动进攻,同时任命谎报战功的叶志超担任在朝清军总指挥,统帅各路人马,引起诸将不满,为日后平壤大败的结局埋下了隐患。9月8日,平壤守军完成御敌部署,在平壤城周边构筑了大量堡垒和各种防御工事。平壤城内到处是备战的清军,叶、聂、卫、马、左、丰的军旗林立,街道周围设有八所清军幕营。而实际上,清军的现状不容乐观,军内风纪涣散,士气沮丧不断在军中蔓延。
进攻平壤的各队日军于9月12日至14日陆续到达平壤附近,很快完成了对平壤的战略包围,切断了清军的退路。9月14日中午,炮兵部队发起佯攻,炮击大同门外清军堡垒,配合步兵进入预定战斗位置。15日凌晨,在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的指挥下,14000名日军分四路,采取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向平壤发起总攻,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
1.大同江南岸战场
15日凌晨3时,由大岛义昌少将指挥的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随即遭到了马玉崑指挥的守垒清军的猛烈还击。同时,驻扎在大同江北岸的清军也通过大炮隔江炮击来袭日军。据日方记载: “敌人似亦早有准备,激烈应战不遗余力,硝烟蔽天,炮声震地”[6]。由于毫无掩蔽,进攻的日军完全暴露在垒前开阔地面,因而伤亡惨重。日军督队官下令宁死勿退,挥刀驱赶士兵拼死冲击。在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下,日军虽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不久,清军增援部队到达,守垒部队及时补充了弹药,士气为之大振,火力愈加猛烈。而日军自凌晨零时未进早餐就从宿营地出发,在经历逾半日之战斗后,士兵早已是饥疲不堪,而且弹药也将用尽。看到部队已无力再战,指挥官大岛义昌不得不下令撤退。至午后2时,进攻大同江南岸之日军全部退离战场。
2.城北牡丹台、玄武门战场
城北一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参加进攻的日军也最多,包括朔宁、元山两个支队,总兵力达到7800余人,是清军防守部队的2.7倍。15日拂晓,两个支队分东西两路向牡丹台外侧清军堡垒实施夹击。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一旦失守将使全城遭受威胁。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守垒清军凭借坚固堡垒进行了顽强抵抗,奉军总统左宝贵亲自登上玄武门城楼指挥。日军虽然伤亡巨大,但仍然持续猛攻。破晓,日军设于坎北山南麓炮兵阵地12门山炮,集中火力轰击清军堡垒和城北奉军防守阵地。日军发射了对步兵杀伤力极强的榴霰弹,造成堡垒内清兵死伤惨重,平壤城北四座堡垒陷落,日军直趋牡丹台下。日军从三面向牡丹台发起猛攻,皆被清军火力压制。朔宁支队的炮兵中队和元山支队的炮兵大队,立即把向玄武门射击的炮口转向牡丹台,轰击牡丹台堡垒阵地。炮弹炸坏牡丹台胸壁,清兵伤亡惨重,抵挡不住敌军炮火攻击。8时30分,清兵放弃牡丹台阵地溃退。
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道大势已去,决心以死与敌相拼。他换上御赐朝服,亲自操作火炮发弹,不幸被日军榴霰弹片击中身亡。其所部营官也相继阵亡,勇战中的兵勇虽然士气开始动摇,但仍然坚守阵地。日军将大炮移至牡丹台堡垒上,向玄武门轰击。不久,玄武门城楼被炸毁,清军火力顿减。日军乘机派出一队士兵潜奔至城下,通过绳梯攀援而上玄武门,守军受惊逃散,玄武门失守。左宝贵战死,对平壤会战影响极大。左宝贵是清军中 “最彪悍者,并能服众”,他战死后, “清军士气从此沮丧,众皆欲逃”,自是平壤不守[7]。
3.城西南战场
清晨7时,野津道贯亲自率领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发起进攻。该部试图用炮火掩护步兵向清军堡垒冲锋,但由于这一线清军堡垒多而坚固,日军的山炮无力摧毁,因此未能如愿。清军派出马队进行反击,但被日军击退。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此时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崑率部击退了敌军进攻,并获胜利;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城北战场各垒被攻陷,牡丹台、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清军凭借堡垒防御占有较大优势,战事犹有可为。但总指挥叶志超早已丧失续战信心,召集众将商议撤兵之策。各路将军中除马玉崑主张抗敌外,其余将官皆同意弃城。下午4时,城内清军停止了枪炮射击,并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等处清军防地同时挂出了白色降旗,日军见状也停止了炮击。是夜平壤大雨滂沱,8时许清军开始撤退,大队清兵急于突围毫无秩序。日军在沿途设伏,重创清军,被击毙者1500余人[3]41。平壤会战以清军大败而告终。在此后的6天时间里,清军一路狂奔500公里,于21日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而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
平壤会战是近代以来清日两国陆军正规部队首次大规模交战。经此一役,清军不仅伤亡损失惨重,而且人心沮丧,士气低落。 “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战斗的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8]相反,日军在作战之初,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战争投入的范围仅圈定在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因此攻占平壤,被日本认为是 “近代史上罕有之大胜”,军心士气大振。作战结果暴露了清军的脆弱,更加刺激了日军扩张野心,进而坚定了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决心。缴获清军足够一个月食用的粮食及大量武器弹药则为其扩大战事提供了保障。9月17日,日军先遣队由平壤出发北上,开始发动新一轮进攻,把侵略战火烧向鸭绿江边。
二、黄海海战:决定甲午战争战局的关键一役
平壤战役发生第二天,即9月16日,北洋舰队护送提督刘盛休铭字军4000人和辎重武器赶赴平壤增援。下午2时,清军在大东沟开始换船登陆,北洋舰队战舰驶离大东沟约12海里的海面上投锚警戒。17日清晨,停泊在大东沟口外的北洋舰队例行作息鸣钟起床,上午各舰如往常一样进行战术操练。正在寻找清舰,意欲与北洋水师决战,以夺取制海权的日本联合舰队驶入大东沟附近海域,提前一个半小时发现了北洋舰队的煤烟,舰队即刻投入判读和备战态势。直到中午12时,北洋舰队瞭望哨才发出警报,提督丁汝昌命各舰准备迎战。
12时50分,两舰队迎面接近,北洋舰队采用“鳞次横阵”队形,以主力铁甲巨舰 “定远” “镇远”居中迎敌,其他舰只分列于侧后翼,均以舰首迎敌,力图发挥 “定远” “镇远”装甲防护性强和舰首重炮火力猛的长处。日本联合舰队则以机动性很强的 “吉野” “浪速” “高千穗” “秋津洲”4舰为第一游击队, “松岛” “千代田”等本舰队紧随其后,摆出 “单纵阵”队形,以便有效发挥日舰侧面速射炮火优势。当两舰队相距5700米时,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30厘米巨炮率先向日舰第一游击队发炮,北洋舰队诸舰随后也相继向敌舰开火。当两舰队间距离缩小至3000米左右时①,日舰向清舰发起猛烈炮击,黄海海战开始[3]50-51。
日舰队利用其舰只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的侧后翼。北洋舰队战斗力较差的 “扬威”和 “超勇”相继中弹起火。 “超勇”很快沉没, “扬威”退出战斗后搁浅沉毁。“靖远” “来远” “平远”舰先后中弹发生火灾,被迫退出战斗。提督丁汝昌因 “定远”号飞桥被震塌摔伤,但他仍裹伤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右翼总兵、 “定远”管带刘步蟾代其指挥督战。不久,日第一游击队与日舰本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之势。当日舰严重威胁主力舰 “定远”时, “致远”管带邓世昌下令 “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用猛烈火力诱敌攻击,以保护旗舰不会中弹沉没。“致远”鏖战多时,弹药将尽,船舰受创,恰与日舰 “吉野”相遇。邓世昌认为: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下令鼓轮怒驶,猛撞 “吉野”,欲与之同归于尽,不幸中鱼雷沉没,240余名官兵阵亡。 “经远”号受到4艘日舰围攻,全舰官兵毫无惧色,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 “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在军舰被鱼雷击中即将沉没之时,官兵仍继续开炮战斗。
开战3个多小时后,北洋舰队只剩下 “定远”“镇远”两艘巨舰,仍然顽强与 “松岛” “千代田”“严岛” “桥立” “扶桑”5艘围攻而来的日舰对战。两舰频繁发生火灾,舰体被弹千疮百孔,多数舰炮被炸坏或发生机械故障,炮弹已呈匮乏局面。两舰且战且退向西南方向移动,企图把日舰尽量引向远离大东沟的方向,掩护登陆中的陆军部队。
激战中,日旗舰 “松岛”号中 “镇远”舰所发巨弹,死伤日军100余人,船轴倾斜。 “严岛”舰后部水线附近的轮机舱中弹爆炸, “桥立”舰主炮塔被摧毁。 “定远”舰一枚榴霰弹射入 “比叡”舰舱内爆炸,当即炸死日兵19名。 “扶桑” “赤城”两舰在清舰攻击下负伤退出战场。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 “西京丸”巡洋舰,被定远舰炮命中舰体受伤。
下午5时许,北洋舰队 “靖远” “来远”经抢修后重新投入战斗,泊于大东沟港内的 “镇中”“镇南”等炮艇亦来助战,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担心夜幕降临,容易遭受北洋舰队鱼雷艇袭击,于5时45分下令各舰撤出战斗东南方向遁去。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亦收队向大东沟方向驶去,历时近5个小时的黄海海战宣告结束。
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凭借吨位、速度、炮数上所占优势,击败清朝北洋水师取得胜利。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经远” “致远” “超勇”3舰被击沉, “扬威” “广甲”自爆沉没, “定远”“镇远” “来远” “靖远”等皆不同程度受损,死伤合计837人;而日本联合舰队无一舰沉没,虽然“松岛” “比叡” “赤城” “西京丸”被重创,但经过短暂修理后便恢复了战斗力。作战中,日军死伤合计298人[3]54。
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的转折点。此后,清政府被迫放弃 “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实行 “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全面防御方针。一方面,令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致使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另一方面,调集宋庆、聂士成等部清兵20000余人,布防鸭绿江沿线,防止战火烧至中国本土。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取得胜利,打开了通向中国的海上通道。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首先攻占辽东半岛,进而占领全东北,然后以东北作为根据地,南下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注释:
①日本舰队装备的速射炮存在射程短的弱点,只有在3000米距离时才能发挥最佳射击效果。
[1]郑师渠.中国近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4.
[2]关捷,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2卷(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52.
[3]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4]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86.
[5][日]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附录)[G]//孙克复,等.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4.
[6]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6.
[7]戚其章.中日战争: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58.
[8]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27.
[责任编辑:于洋]
K256.3
A
1671-6183(2014)09-0039-04
2014-09-11
孙高杰 (1982-),女,辽宁大连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