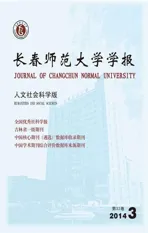关于《古今书最》的几个问题
2014-03-29熊熠辉张固也
熊熠辉,张固也
(1.华中师范大学 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关于《古今书最》的几个问题
熊熠辉1,张固也2
(1.华中师范大学 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阮孝绪《七录序》中附以《古今书最》,主要目的是注释说明序文,同时反映了历代藏书变化的大致情况,但并未包括当时所有存世官簿。其中前面四种目录的图书存亡统计,实际抄自王俭《七志》。关于“帙”的记载反映出当时藏书已有合帙现象。
《七录序》;《古今书最》;阮孝绪;王俭
梁阮孝绪《七录序》中的《古今书最》记载了汉晋至梁代几种主要目录所收图书卷帙及其存亡情况,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图书发展史的最珍贵史料,经常被人引用,而其本身的一些问题向来罕见讨论。薛红、唐明元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4期发表《〈七录序〉所附〈古今书最〉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下设七个小标题,首次对它作全面研究,颇具启发。惜其考虑似欠周到和深入,许多说法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本文按其所列问题,谈些不同看法,当否敬请两先生并学界同仁指正。
一、《古今书最》的内容
阮孝绪在《七录》序文之下明标“古今书最”四字,前辈学者往往把下面的文字都看作它的内容。如刘纪泽先生说:“《七录》于《经典录》之先,综前代目录为《古今书最》,胪举《七略》以下凡十种,而以新旧集本录(当作‘新集《七录》’)殿焉。”[1]王重民先生说:“在《古今书最》内,他列举了十种古代目录。”又说:“《七录》虽亡,《古今书最》把它的分类表完整的保存下来。”“《古今书最》附载了阮孝绪的个人著述七种。”[2]
《探微》认为《古今书最》“全文”只包括十种目录的记载,“关于《七录》各类著录图书数量的文字应是道宣辑之于《七录》正文各类之末尾”,而阮孝绪个人著述名目“应是以附录形式出现于《七录》一书之末尾”,都不属于《古今书最》。这确实指出了前人的疏误,但所作解释并不准确。
《七录序》今保存在《广弘明集》卷三,该书是唐释道宣汇编的佛教资料集。这篇序文及其附录的大多数内容与佛教无关,道宣为何不厌其烦地将其一概收入?因为他的编选体例是全篇或全卷抄录的,一般不作删削,而这整篇序我们推测正是《七录》的末卷。据阮孝绪自述: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录一卷。
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
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录一帙七卷。
序录二帙一十一卷。
杂文一帙十卷。 声纬一帙十卷。
右七种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绪撰,不足编诸前录,而载于此。[3]
王重民先生曾推测“《七录》著录的简单说明,或许就是从《序录》中节取来的”[2]。似嫌过于谨慎,《序录》当即《七录》的正文十一卷,隋唐史志著录《七录》为十二卷,则合此序一卷计之。上引小计“一百八十一卷”,较七种卷数之和亦多一卷,也是合计此序的缘故。若如《探微》所说,“新集《七录》”以下文字都是道宣抄入的,则其前序文加上《古今书最》,不足以凑成一卷篇幅;道宣又何必多此一举,不厌其烦地从各类的末尾抄出这么多与佛教无关的内容呢?在序文之后列出全书篇目,本来就是刘向、刘歆父子写作序录的体例,阮孝绪改为列载大类、小类,应是目录本身之序录的变体。且阮孝绪所撰《文字集略》等三书正文后都有《序录》或《序例》一卷,足证《七录》末卷亦当为“序录”,但他既然将正文称为“序录”,而这份自著书目又附在《七录序》之内,就没有列出“序录一卷”而已。
至此再来读《七录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由五部分组成:序文、古今书最、《七录》目录、阮氏自著书目、阮氏传记。其中阮氏传记言及其卒,又称梁元帝为“世祖”,当是梁末人所写并附入序末的。前面四部分则为阮序的本来面目,其中“古今书最”、“《七录》目录”两个小标题为阮氏自题,介于其间的“新集《七录》内外篇图书……内篇五录……外篇二录……”三条二百余字,当然应该属于《古今书最》。否则,“古今”之“今”就涵盖不全了。《探微》将这些文字与《七录》目录混同看待,说成“关于《七录》各类著录图书数量的文字”,并未理解阮氏的真意。
二、阮孝绪设置《古今书最》的目的
《探微》说“书最”一词的含义,“历来学者皆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并援引《汉书·严助传》“计最”、《南史·张邵传》“簿最”二证,认为“所谓‘古今书最’即指从古至今不同时代图书收藏的总记录”。傅荣贤先生早已指出:“‘最’意为‘会聚’”,“‘古今书最’不是书目之名,而是指古今图书的总会,即图书总财产账”[4]。其实周秦古书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管子·禁藏》《地数》、《史记·殷本纪》《周本纪》,以及出土《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孙膑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明君》等“最”可训为“会聚”的例证很多,而“簿最”一词仅《新唐书》中就用过十多次,所以“书最”之义并不难解,也并非探讨阮孝绪设置《古今书最》目的之关键。
《探微》对阮氏之目的提出两点分析:“(1)《七录》正文簿录类只有所收目录著作本身之卷数,而未能反映该目录著录图书的数量,《古今书最》恰能弥补这一著录上的缺憾;(2)将不同时代目录及所收录图书的数量汇集一起,一目了然,便于阅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古今图书收藏以及古代图书流传存佚情况。”阮孝绪自言对每部图书“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3],即写有简明的“序录”,焉知簿录类没有记载“该目录著录图书的数量”,而须另设《古今书最》来“弥补”?故前一点不可信。后一点略有道理,但并非问题之关键。
我们认为阮孝绪设置《古今书最》另有更直接的目的:(1)吸取王俭《七志》的成功经验,粗略反映图书发展历史和存亡状况,详见下文。(2)注释说明序文。其前序文除首尾论述图书的意义、编撰经过等外,中间主体内容可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叙历代藏书编目,后言目录分类。序文所述比较笼统,不便详尽记载大量数字,而《古今书最》、《七录》目录分别自成体例,条列记载,一目了然。其中《古今书最》所列十种目录,都在序文中或明或暗提到过,最后“新集《七录》”三条,无疑是序文前部之末“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于当今者也”两句的绝好注脚,这正好补证上文对其属于《古今书最》的论述;而这两句序文正好说明《古今书最》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直观反映出当朝藏书和文化之盛。
三、《古今书最》收录目录著作的范围
《七录》目录说“簿录部三十六种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而《古今书最》所列官修目录只有《七略》等八种,以及《汉书·艺文志》、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两种史志目录。《探微》据此分析其收录目录著作的范围仅限于“综合性官目及史志目录”,大体不误。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私家目录、专科目录收录图书的数量都少于同时的官目,或者抄撮而成并非藏书目录,而《古今书最》只要收录代表某一时期图书收藏或发展水平的目录即可,不必滥列这些次要目录。
但《探微》以为这十种目录就是阮孝绪见过的“所有”官目和史志,进而提出“已经亡佚的综合性官目不著录”的说法,并以《古今书最》没有提到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为理由,推断阮氏撰成《七录》时,刘遵的目录“尚未成书”,这些推论似皆过当。其论证思路,以为《古今书最》既已列举《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亦当同时列举郑默《中经》,“《中经》不见录的真正原因就在于阮孝绪撰《七录》时《中经》已亡佚”。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更与事实明显相左。阮孝绪在《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下注云:“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3]这不已明确告诉人们,《古今书最》只列同时目录中著录图书较多者,并未列出所有存世官目吗?姚振宗说:“刘遵初为昭明太子舍人,后为简文帝东宫中庶子,所著目录本传不载其事,不知何时,或当在中大通(529-534)以后。”[5]今人考证说:“是目当遵为昭明太子舍人时所撰。据《梁书·刘遵传》,其为太子舍人当在天监十三年(514)之前。今暂系此事于是年(天监十二年)。《昭明太子传》有‘于是东宫有书几三万卷’云,遵当据以撰为目录。”[6]则早在阮氏普通四年(523)开始编撰《七录》前,刘遵的目录已经编成。其实据我们考证,阮氏目录至大同二年(536)去世前夕才编成,而刘遵已于前一年去世[7],无论刘遵所编是哪位太子的东宫藏书目录,都早于《七录》。其虽亦属广义官目,毕竟比秘阁目录低一个层次,《古今书最》不见录极为正常,并非没有成书。
四、《古今书最》对图书存佚情况的反映
《古今书最》前四条列举《七略》、《汉书·艺文志》、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晋中经簿》四种目录著录图书的家(部)数、卷数,还注明若干家(部)亡、若干家(部)存。《探微》称赞这“详细反映了各官目及史志目录所收录图书至梁时的存佚情况”,是一大“创举”。并指出来新夏先生的一个错误说法,最后分析说:“透过《古今书最》可以看到,自《七略》至《晋中经簿》,各目所著录图书皆大量亡佚,而自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起,各目录收录图书至阮孝绪时皆存。这说明,两汉末年、西晋末年三次大的战乱对图书事业造成了无以弥补的惨重损失。然而自东晋至梁,虽历经动荡、战乱,但由于历朝政权的重视,图书事业却未受大的影响。”最末数语显然与阮氏序文“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之说不符。究其致誤之由,是因为没有深思《古今书最》仅前四种目录有存亡统计,而后六种目录没有存亡统计的真正根源。
来新夏先生在谈到《晋中经簿》时认为,“《晋中经簿》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开后来目录书著存亡的先例”,其所著录“包括西晋时存、亡书在内的总数”,即误以这里的存亡为晋荀勖的统计。而在谈《七录》时又说:“《七录》将其所引用的古代目录列于序后称《古今书最》,使后人借以了解古代目录著录图书数量及存亡残缺”[8]。后一说法中的“存亡残缺”当指梁时情况,与学界通说无别,说明前一自相矛盾之说属于不应有的疏忽。问题是这里反映的果真是“梁时的存佚情况”吗?
阮孝绪《七录序》说王俭《七志》在正文之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且自述《七录》编撰依据:“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3]而据刘知几说:“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9]综合这三条史料,可知王俭将《七略》等四种目录著录而南朝初已佚的书名一一抄出,作为《七志》的三个附录之一。而阮孝绪是以《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为主要依据,又补充了《晋元帝书目》以下官目和宋齐以来私人目录多出之书(仅内篇就多近一万五千卷)。这样做的缘由,是他以处士之身、个人之力,无法尽见天下图书,难以断定这些近世尚见著录之书果真存世与否。这正如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对于近书不知存佚者标为“未见”而不轻易断言为“佚”一样,都反映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因此,阮孝绪实际并未亲自做过图书存亡的统计,则前四条统计应该都是照抄王俭《七志》而来。
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习焉不察。如郑樵说:“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10]俨然王俭、阮孝绪分别做过统计,但阮氏所记明明是“《晋中经簿》”,他却说成《魏中经》、《晋四部》;王俭明明是在七志之外附记亡书,阮氏更只在《古今书最》略记存亡数字,他却说成单独为“一志”、“一录”。这都完全不符实际,表明王、阮二人各条阙亡之书的说法本身也不可信。我们多年前就已提出阮氏存亡统计抄自王俭的说法[11],可惜似未引起学界重视。近年仍有人说《七录》是“最早著录图书存亡的书目”,“阮氏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也在实践上努力践行‘通记天下有无图书’,无疑是郑樵‘通记’思想的先响”[4]。这恐怕是不妥当的,因为附录亡书的是王俭,阮孝绪根本没有这一做法。其实王俭正文记南朝存书,附录记亡书,比郑樵《通志·艺文略》混编古今、不辨存亡的做法高明得多,想来不屑于为郑氏之“先响”。
五、《古今书最》并记“帙”、“卷”的意义
《古今书最》记载《七略》、两《汉志》收录图书若干“家”、若干“卷”,《晋中经簿》下则称“部”、“卷”,东晋南朝目录则并记“帙”、“卷”。《探微》认为“家”与“部”相同,均为“种”义。这一粗略类比,未尝不可。但不甚准确,汉代目录的一家,有时不止一种书,如同一家经学有经、有传、有记等。
《探微》又认为,“自《晋元帝四部书目》起至梁时的官修书目,只记录帙、卷,则不能如实反映官府收藏的图书种数,因而不能准确反映一个时代图书的全貌,这应是这些目录编制上的一大阙失。”未记种(家、部)数,固然是一大阙失,阮孝绪《七录》并记“种”、“帙”、“卷”,正是有意识地弥补了这一阙失。但东晋南朝目录增记“帙”数,反映出当时藏书制度的合帙现象,别具重要意义。卷轴时代帙、卷之间的数量关系究竟如何,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近代以来,叶德辉、马衡、余嘉锡等大家各有研究,大致认为以五卷或十卷为一帙,惜不能言之具体。辛德勇先生通过研究《金楼子·著书篇》中的梁元帝著述书目,得出两点规律:“(1)每一帙内不能混装两种以上不同的书籍。(2)一种书每十卷装入一帙,余出的零头和不足十卷的书籍,均单盛一帙,不与其它书籍相混。”[12]这一规律验之于《七录》目录,亦若合符契,但与《古今书最》似不甚相符。其并记帙、卷的五种目录,一帙多含八、九卷,最多的“《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接近十卷一帙。若按上述规律,则其所收绝大多数图书的卷数都得是十的倍数,这显然有违常理。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实际的藏书目录应与现存唐代佛经目录一样,卷数太少的图书可以混装在一帙之内。梁元帝著述书目和《七录》都不是实际的藏书目录,才会有“每一帙内不能混装两种以上不同的书籍”的做法。
六、佛经的归类与收录问题
《古今书最》列举的十种目录中,《晋中经簿》下注云:“其中十六卷佛经。”《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下注云:“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其他目录是否收录佛经,则未作说明。《探微》对这种“奇怪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在两种收录佛经的目录中,“佛经被归入附录,而不在甲乙丙丁四部之内”,而东晋以后四部目录除元嘉目外“皆未著录佛经”“的原因颇为复杂”:《晋元帝目录》是因东晋渡江后,“《晋中经簿》所著录的区区十六卷佛经,很可能也已经亡佚,导致官中无藏不能著录”;“刘宋官藏中有佛经”,“《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却未再收录佛经,应是源于王俭本人的抑佛思想”;“梁时华林园虽藏有大量佛经,但刘孝标《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殷钧《秘阁四部》乃分别依据文德殿、秘阁藏书而撰,而此两处并不收藏佛经,因而二目录不录,正所谓‘释氏不豫焉’”。
所谓“附录”之说,应该是受《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以佛、道书作为附录或外篇的启发,但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后三种目录收录的佛、道书都多达数百甚至数千种,与四部中的一部相当,无法纳入四部分类体系,于是设为附录或外篇,而且都是佛、道并列为二附录,没有单以佛经作为附录的。《晋中经簿》仅收录区区十六卷佛经,显然不足以成为单独的附录。该目有一卷名为“近世子家”,收录与古诸子不类的子书,余嘉锡先生认为佛经应归入此,是较为合理的推论,不宜轻易否定。《古今书最》因其最早收录佛经,特予注明,“其中”二字,似亦表明不是附录而归入四部之内。东晋以后,佛经传译迅猛发展,但进入秘阁的未必很多,仍不足以增设附录。宋元嘉八年秘阁佛经才增至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确有可能归入附录。而这又属目录史上之创举,故《古今书最》又予注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不载佛经,则因当时佛经主要收藏在华林园,僧绍、宝唱各自别撰经录。介于二者之间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阮孝绪未言其收录佛经,很可能元徽元年以前已将佛经移藏华林园,而不可能因“王俭本人的抑佛思想”而导致元徽目不收录佛经。因为反映王俭个人思想的私撰《七志》是将佛、道书归入附录的,他怎么可能无视秘阁藏书实际而在主持编目时故意不收佛经?齐永明目又受谁的“抑佛思想”影响呢?当然,也有可能元徽、永明中佛经仍藏秘阁,目录亦归入附录,阮孝绪因其已无创始之特殊意义,没有注明。
综上所述,《探微》提出的六个问题,确实对人们认识《古今书最》具有启迪意义,但作者给出的解释大都不够准确,甚至多有错误。倒是文末“二个疑问”部分,怀疑《后汉艺文志》、《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二条在传抄过程中有所残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为增录图书与重新整理缮写之旧录图书的总卷数,比较合理可信,本文就不再多言。
[1]刘纪泽.目录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1:81.
[2]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75,62,68.
[3]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0-115.
[4]傅荣贤.浅论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5).
[5]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389.
[6]俞绍初.昭明太子萧统年谱[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7]张固也,殷炳艳.阮孝绪《七录》成书年代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8]来新夏.古典目录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1:111,116,140.
[9]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04.
[10]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讎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06.
[11]张固也.《七录序》探微二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1).
[12]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兼论卷轴时代卷与帙的关系[C]∥文史(49).北京:中华书局,1999.
2013-12-26
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1030)。
熊熠辉(1964- ),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从事图书管理学研究; 张固也(1964- ),男,浙江淳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G256.3
A
2095-7602(2014)03-0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