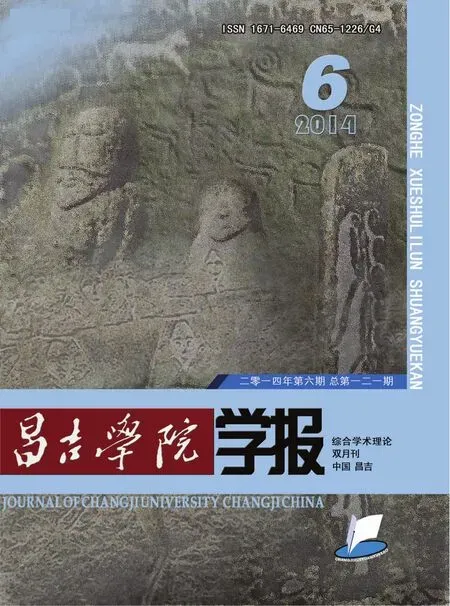略论叶尔克西文学创作的文体跨界相通现象及艺术效应
2014-03-29胡冬汶
胡冬汶
(昌吉学院中文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很明显的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融合与跨界,这些小说或散文作品,既具有小说的肌理,又有散文的气质,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使得这样的作品既不同于常规化的小说,也不同于一般性的散文,而独具面貌。比如在苏曼殊、郁达夫、鲁迅、萧红、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中,散文与小说的跨界相通是比较鲜明的。这些作家在文体创造上作出这样的艺术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动因与理念,或出于干预社会的目标、或缘于个人性情的契合、或源于他人创作的影响等等。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这位活跃在当今文坛的新疆哈萨克族女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主动而自然地选择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跨界融合。这一特点是我们在探究她的创作时所不能忽视的。
一、叶尔克西创作中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跨界相通现象呈示
虽然近年来叶尔克西的创作足迹也涉及影视领域,但就其文学创作的文体选择而言,基本是小说和散文两种样式。在她的小说与散文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因素、气质相融合贯通的特点,二者的边界是模糊的,难以截然区分开来。截止到目前,叶尔克西已出版有七部作品集,分别是《永生羊》(2003年)、《草原火母》(2006年)、《黑马归去》(2006年)、《蓝光中的狼》(2011年)、《永生羊》新版(2012年)、《天亮天又黑》(2012年)、《远离严寒》(2013年)。这七部作品集中,《黑马归去》、《天亮天又黑》两部是小说集,其余皆为散文集。对照七部作品集的篇目,《蓝光中的狼》、《远离严寒》两部集子中的作品基本都是来自《永生羊》(旧版和新版)和《草原火母》,显示叶尔克西的新作不多。通过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和事实,就是有些作品既出现在散文集中,也出现在小说集中,如《额尔齐斯河小调》、《子弹》、《帷幔两边》、《老坟地》、《远离严寒》、《少年》、《阳坡》、《夏至》、《金河》、《多年前飘过的一片云》这十篇作品就既被散文集《永生羊》(旧版和新版,《永生羊》新版仅未收录《金河》)收录,又被小说集《黑马归去》收录,只是《多年前飘过的一片云》(收录于《永生羊》集中的题名)在被收录入《黑马归去》集时改名为“多少年前的一片云”。《萨满铃鼓》、《留在草地上的牛迹》现身于散文集《草原火母》,又被收入《黑马归去》集中,只是收入小说集时分别更名为“铃鼓谣”和“牛迹”。《金河》、《老坟地》、《夏至》、《子弹》四篇作品还被收入小说集《天亮天又黑》中,《新娘》、《大风》被收在新版《永生羊》集中,又被辑入《天亮天又黑》中。这些作品被收入到分别以小说或散文界定的不同作品集中,并不显突兀或不协调,无论是作为散文看待还是作为小说来看待都很相宜。
伴随同一作品既收入小说集又收入散文集的情况,在研究界,也存在对于叶尔克西作品文体归属问题认识的模糊现象,也出现同一作品被不同研究者认定为不同文体的情况,因而有些作品或被作为小说评述,或被作为散文分析,没有划定清晰明确的文体归属。比如在翟新菊、吴孝成的《舒展自己深沉的生命体验——哈萨克女作家叶尔克西创作述评》一文中,作品《额尔齐斯河小调》、《阳坡》、《夏至》、《金河》是被当做小说来分析的,《子弹》、《帷幔两边》则被视为散文来论述的,而这些作品又同时被收入到小说集中。任一鸣、何英则是按出版性质将《永生羊》集中的全部作品视为散文来加以论述。而王志萍将《额尔齐斯河小调》、《阳坡》、《夏至》、《金河》与《骑兵八十八》、《无痛》两篇并列,展开对于叶尔克西小说创作的论析。这一情况在目前对于叶尔克西创作的相关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也有论者并不考究具体篇目的文体属性,而是综合看待加以分析。或者可以说,无论作者本人还是文学编辑,还有研究者都不执着于这些作品的明确文体归属。而之所以如此,是源于在叶尔克西的创作中,确实存在着小说、散文两种文体的模糊与相通、互渗与跨界。学界针对散文与小说边界的勘界本就观点丰富,没有权威性的见解能一统江山,而且也并不倾向于划定清晰的边界,而是立足于边界模糊情况一定程度存在的现实,更多探讨散文、小说的各自特征以及二种文体的互渗与交叉。诚如何平所论:“虽然明明有个散文和小说的文类边界在,这样的文类边界总是不断被两边的越境者突破和篡改,以至于所谓的边界常常弄得犬牙交错暧昧不清。”[1]所以我们不必刻意厘定叶尔克西每篇作品的文体属性,显然,综合整体地去把握是很适宜的一条路径。
二、叶尔克西在创作中选择文体跨界相通的缘由
文体跨界相通既源于作家的性情依归与创作观念的使然,亦是民族生活、文化浸染的结果。叶尔克西除翻译诗歌等作品外,主要写小说、散文,其中以散文作品数量居多,小说作品数量不及散文作品。就叶尔克西的创作气质而言,是更近于诗和偏于散文的,而在写作实践中她选择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的跨界互渗,这一文体方式的选择既源于作家个人的性情依归与创作观念的使然,亦是哈萨克民族生活、文化浸染的结果。
首先,敏感纤细、多思而主体凸显的个人性情使得叶尔克西在文体上倾向于小说与散文的跨界相通
叶尔克西早年在北塔山生活过十三年,在北塔山这个地方,人是极容易与天地自然亲近的,但同时也更易感知人的生命存在的孤独。叶尔克西自小是个体物细致,情感细腻,敏感、忧郁而又多思的孩子,这一性情特点使得她很善于体察事物,感受生命之种种滋味,包括鲜明深刻的孤独体验,而且这一个性特质因着北塔山这一特殊地域的滋养而愈发勃郁鲜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虽有所变化,但未有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体察天地万物之时,叶尔克西的主体自我是敞开的,强烈地投身进去的,她以直接性、情感化和不隔的方式感知天地自然和人间生活。于是,这样敏感细腻、沉静多思的气质,有我有情的性情状态,与平缓悠长的哈萨克牧区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铸就的是近于散文的心灵。而这样的叶尔克西进入文学创作的天地,立足于自身早年在北塔山地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经验,进行具体写作时,要么直书个体生命经验,写成散文,要么依托原型生活,创作小说,即便是小说创作,也很自然地偏于散文气质,并流溢出诗意。
叶尔克西接受过完整的文学教育,又从事过文学编辑工作,这使得她对于各种文体的认识是充分的,也可以自如驾驭不同文体,但其近于散文的个性气质使得她选择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并在两种文体之间自由出入,让两种文体交谈对话,形成其文体跨界相通的创作面貌。
其次,从创作观念讲,叶尔克西本就无意于写文体规范、边界清晰的散文和小说,她本心是要“把小说和散文混着写”的
在写作中表现出小说散文两种文体融合情况的,有些是作者自然写来就是那样了,有些则是作者有意识这样写,就想这样写,并且有明确的自我认知。比如汪曾祺就表达过:“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大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我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做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2]显然,汪曾祺是很明确尝试突破文体边界,按自己的意图写作融小说、散文,甚至是诗歌于一炉的作品。在笔者对于叶尔克西的采访中,这位女作家也曾谈到,她确实是把小说和散文混着写的,而且是从《额尔齐斯河小调》就已经开始这样混着写了,也就是说从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她就不以文体的边界清晰为目标,而是向着散文小说跨界互渗的路径前行。叶尔克西认为早年的北塔山生活提供给她的是很实在又很诗意的东西,本身就是既非散文又非小说的东西,因而只有以那样一种散文与小说混合的方式去表现北塔山的全部生活才是得心应手的,若要以一种纯粹的小说语言或散文笔调去叙述一个故事,就会使得书写僵硬死板,失去生动与鲜活。可以说,散文与小说跨界相通的文体创作直觉成为她明确的写作观念。叶尔克西也曾在另外的访谈中谈及她创作中“文体界线的模糊可能源于写作方法的现实与老实:我笔下的东西大多是真实的,比方老坟地中讲到的那个箭头,我到现在还保留着。”[3]小说、散文勘界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真实性问题,一般观点认为散文比较讲求、追求真实性。叶尔克西的创作取向是扎根于自身生命经验,而不是更偏向艺术想象,这既是她所说的“现实与老实”的写作方法,也是她的关于写作的直觉性理念。毫无疑问,这是散文的气质和观念倾向,由此出发,叶尔克西写作了优秀的散文作品,并将散文的气质与精神带入小说写作,使得二者融合相通。可以说,叶尔克西依循自己的创作直觉,由明确的观念自觉导引,选择了最契合她自己的文体方式。
再次,散文小说跨界融合的文体选择也是哈萨克民族生活、民族文化浸润的结果
就生活现实而言,哈萨克族草原游牧生活的内容是较为单纯的,节奏是缓慢的,随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舒徐展开,人与自然物的生老病死都不是急匆匆的、瞬息万变的。这一生活样态平凡而稳定,时间在这里是慢的,人与自然贴近契合,富于散文的韵律与精神。那么,当以文学的方式去呈现、叙写这一民族生活,那么散文以及富于散文气质的小说便是合宜的文体方式之一,叶尔克西在创作中是这样选择的,无独有偶,新疆的另一位汉族女作家李娟书写哈萨克族生活的时候也选择了散文。
就民族精神与文化而言,哈萨克民族是富于诗的气质和感觉的民族,其民族俗语说,“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在普通哈萨克人的生活里,歌和音乐是他们主要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歌声伴你躺进摇篮,歌声送你离开人间”。而哈萨克的文学传统是诗歌的传统,在哈萨克文学的口传文学作品中随处可以见到把小说性的叙事、诗歌的形象性、散文的笔法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很具普遍性。叶尔克西是哈萨克民族的女儿,她早年曾经历非常自然、原生态的哈萨克牧区日常生活的琢磨,有着丰厚的哈萨克民族生活经验,并在精神上领受哈萨克民族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及至成年后,叶尔克西也曾有意识地主动深入到哈萨克民族文化、文学中去,去补充和吸收民族文化的营养。因而,她的创作是直接受到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影响的。作为哈萨克民族生活、文化育养的写作者,叶尔克西以鲜活、血肉丰满的民族生活为根基,加之母语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自然地使得她在创作中更倾向于把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打通,自由出入两者间,并把诗的气息灌注其中,进行从容自在的表达。
叶尔克西的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个体生命经验,尤其是北塔山地区的哈萨克生活,她的作品深深地带有自身生命印记,她以有我有情的方式叙说北塔山的自然和生灵,是近于真实的,这很自然促成她的选择散文,也很自然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特征。可以说,叶尔克西的生命和创作中累积、沉淀的诸多因素与内容成就她在文体方面的灵感与特有表达方式,所以,只有以小说与散文互融的方式去写哈萨克的生活与情感,她自己才觉得舒服顺畅,既与个人心灵和气质契合无间,又与母族文化精神实现了共振和同一。
三、文体跨界相通所成就的艺术效应
叶尔克西在文体上尝试将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打破,进行“混搭”写作,这在她的第一篇作品《额尔齐斯河小调》中就已显现出来。这篇作品讲述哈萨克老奶奶与小盲孙的故事,既有小说的基本人物、情节元素,又有悠长舒缓、饱含感情的细描深绘,还有散文的从容笔法。可以从这么一段文本中来考察:
奶奶爱孙子,她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吵吵嚷嚷的男子汉身上了。
太阳从高高的阿尔泰山上升起来了,奶奶背起小盲孙挤奶去了。“噗、噗、噗,”小盲孙在这柔和的节奏中睡着了。奶奶的头巾,却在他脸上印出可爱的“皱纹”。
草原上的野花开了,黄的、红的、紫的,还有的说不上来是什么颜色,然而是那样的好看。奶奶领着小孙子,到草原上捡回许多牛粪,扔进地灶中。火光映红了小孙子的脸,他也会哼哼那首小调了。
树叶黄了,山草瑟缩着身子。小孙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娇滴滴地咳嗽几声,奶奶抱着他,急匆匆地来到山村医院。医生把用手焐热的听诊器伸进小盲孙的衬衣里,他调皮地咯咯笑了起来,她的一滴眼泪,却掉在小盲孙的脸颊上。
屋外,没有一丝风,只是鹅毛大雪漫天飞扬,小木屋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奶奶把小盲孙裹进皮大衣里,端来一碗热牛奶。她给他讲传说,神话……[4]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有简单的人物、情节,但不属于戏剧性情节,而是细碎片段化的日常生活情景,而且不具备情节的完整展开及叙述的连贯性;它是以散文的概括的、跳跃的、舒缓的、抒情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样将散文与小说笔法融合运用的策略很是独到,造成的艺术效果是和谐、贴切自然和生活的,使得短短的一篇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不嫌单薄而又有情味。在叶尔克西自己看来,《额尔齐斯河小调》至少有诗化的感觉,而且把她自己对于作品原型人物的印象和内心的感觉传达出来了。
将散文与小说跨界融合的文体策略,给叶尔克西的创作带来了独特的面貌和魅力。我们在叶尔克西的散文、小说作品中都可见到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主体色彩强烈,抒情性浓郁,有诗意,如《永生羊》、《帷幔两边》、《大人不在家的日子》等;长于氛围的营造,善于营造鲜明、强烈的情境氛围,如《不死猫》、《黑马归去》等;描写传神出彩,感觉性突出,画面细致鲜明,如《子弹》、《夏牧场》等;多采用回忆的叙述方式,有的兼用成人与儿童两种眼光与视角,如《永生羊》、《少年》、《黑马归去》、《老坟地》等;还有文学语言的灵动鲜活,这些特征无论在散文还是小说作品中都是比较一致和突出的。
叶尔克西的文学创作根脉是北塔山地区哈萨克族群生活、生命的经验与记忆,于作家而言,“北塔山是有故事的阿拉丁神灯”[5]这里有平凡的草原游牧时光,也有传奇的人与事。地域、时光、自然与人事着落在叶尔克西的写作中时,她不是以戏剧性方式去追求传奇化效应,也不写完整跌宕的人生故事,而是经由具体的一草一木、一朵云、一条虫、一只鸡述说传奇与平凡普通纽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状貌和生命真相。这一写作策略反射到文体方面,就是在散文作品中有小说化的情节片段,使得散文的舒缓叙述,着落到自然生灵生活、生命的实处,增强了质感,使得别致的描写和流溢的抒情免于空虚和飘忽,而有了扎实的根底。比如《永生羊》在写“我”与萨尔巴斯的结缘显出万物有生的生命联系和生死的神秘中,就有萨尔巴斯与“我”历险而安然无恙的情节,这一情节是小说化的,但却使整个散文的叙述有了坚实的底子。而在小说中淡化情节,也不以人物为唯一的核心,而着意于氛围的营造,以舒缓从容的散文调子叙写、抒情,使得小说也富于诗意和情调。如《黑马归去》这篇小说,在婚礼、黄毛的人生、黑马的生命终结等故事里,“我”这一中年女性的种种情绪、回忆、感受始终流动其中,时时阻断叙事进程,不急着讲完故事,而是以“我”内在的心曲起伏来调动安排小说的旋律和节奏,使得这篇小说宛如忧伤的歌曲,在夏夜的牧场反复吟唱。
四、结语
可以说,小说与散文的融合相通既是叶尔克西文学创作独特的文体表达方式,也是她独特生命气质的体现,就是生命体验性的一面与人生经验性的一面无间地融和在一起,形诸于创作,就是体验诉说与经验传递的结合,使得其作品既是小说的,又是散文的,同时又充满诗意,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讲述北塔山的故事,写那里的天地生灵,唯有这个方式与路径是最妥贴契合的。
[1]何平.互相篡改的散文和小说[J].美文(上半月).2011,(8):92.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93.
[3]http://www.xj.cninfo.net/culture/writer/yerkx/talk.htm丝路作家坛
[4]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永生羊[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79-180.
[5]丁艳艳.叶尔克西“童话”北塔山乃奇遇(作家大讲堂)[N].晨报.乌鲁木齐.新疆经济报社,2012-5-29,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