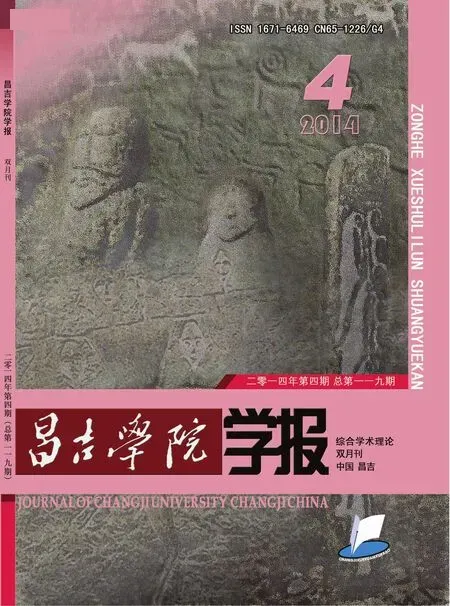《熊从山那边来》的叙事艺术
2014-03-28景淑君
景淑君
(新疆大学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1969年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首创了法语“narratologie”英语“narratology”,并直接翻译为“叙事科学”,作为一门与生物学、人类学等术语具有同样科学性质的学科。每一个叙事型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叙事者,正如罗兰·巴特所认为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叙事作为小说的基础必然存在着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声音。
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所达到的效果必然不同,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以家乡安大略省温格姆镇作为创作背景,创造了一个独具风格的文学世界。她擅长于描写生活的琐碎平凡之事,在琐碎之中将生活的表象抽丝剥茧式的揭示出来,而这种独具风格的小说,在叙事上也具有其不同的魅力。以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叙事者、叙述声音、叙述时间作为研究重点,探讨其叙事的魅力所在。
一、叙述者——异故事型的叙述者
作为叙事型的作品,必然存在叙述者,而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他只是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通过一定的话语操作和铺展构成叙事。而正如杰拉尔德·普林斯对叙述者的定义:“叙述者就是讲述故事的人,他被印记在文本之内。每个叙事故事里至少有这样一个叙述者,和他或她对之陈述的受述者位于同一叙述层次中。”[2]米克·巴尔以《艾玛》为例进行说明:“艾玛的叙述人并非简·奥斯丁。历史人物简·奥斯丁对于文学史当然不无重要性,但她生活的环境对于特定的叙述学学科并无影响。”[3]这就是说,作者的生活经历,所处的环境与我们故事中的叙述人,叙述学科是没有关系的。叙述者,存在于文本中,并不能与现实世界相提并论。因此,借用热奈特先生的定义:“真实的作者是创作叙事作品的人,而叙述者是文本内讲故事的人。叙述者有时可以等同于作者,并以其忠实的代言人身份出现,但这通常只适用于编年史和自传体这样的叙事作品中。在虚构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忽而带有作者的影子,忽而又极力撇清和作者的关系”。[4]他将叙述者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外部——异叙述型,即叙述者处于第一层次不参与故事;外部——同叙述型,即叙述者第一层次参与故事;内部——异叙述型,即叙述者处于第二层次不参与故事;内部——同叙述性,即叙述者处于第二层次参与故事。在门罗的小说《熊从山那边来》中则主要采用的是外部——异叙述型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开始,引入故事,但不参与故事的发展,同时,还加入一些评论。
这种叙述者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无所不知的角度进行叙事,在作品中可以处于支配地位,以便其随时转换其叙述焦点,自由度更高。
小说开始就是一整段的对于菲奥娜家庭的介绍。“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上留下了印子。她目前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政治观念,他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的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5]这段介绍既包含了对于菲奥娜家庭的具体客观的介绍,而且还带有了不同的视角转换,例如在格兰特看来,菲奥娜的家庭等,同时还插入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评判,门罗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将自己隐藏于故事的外部,而又无处不在,并能够穿梭于不同人物的心里,并对事件给予评价。
如罗兰·巴特所言:“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一个人物认同”[6]虽然这种叙事方式历史久远,在荷马史诗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带有一种上帝式的权威,看似是全知叙述,但是事实上也是有选择有重点的,而这种选择和重点则会影响读者对于某个人物的了解程度,进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小说中,作者对于着重叙述的除了故事本身,就是选择性的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而对这一人物的选择即是格兰特,借格兰特的意识展现出他眼中的妻子、女人们。
格兰特眼中的妻子菲奥娜“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蓬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7];格兰特眼中的情人“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件事情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他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8];格兰特眼中的玛丽安“玛丽安很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善于求生,能够搜寻事物,可以在街上把死人脚上的鞋子脱掉。”[9]因此,作者虽然采用了外部——异叙述型的叙述者,但是这种叙述者穿过格兰特的意识不断旁观他人,并且评头论足,这种有侧重的全知叙事,虽然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但是由于其选择性的人物心理描写,却让我们对格兰特本人的认识更加拉近,而不自觉对于其他人的看法也是借格兰特而看到的,从而看似客观的叙事,实际上已经带有了格兰特的眼光,因此并非客观。
在作品的叙事中,并不存在其他人的对于格兰特的观察,也就是整个的故事都是由外部——异叙述型的叙述者,来描写,同时对于其他人物的构建,又是通过格兰特和对话来实现的,无论是对灵魂性的人物菲奥娜,还是对于追求物质的玛丽安,还是那些挑拨撩逗他的女人们,都是借由格兰特的观察和无意识来实现的。而叙述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带有了主观性,却由于是外部——异叙述型的讲述而赋予了更为客观、冷静的叙述,使得原本感性的情感,化为了抽象、冷静的观察。
因此,看似客观全面的叙事,事实上也是有选择的,但不可否认,整部作品中这种叙述者能够统筹故事,出入故事之外故事之内,并作出其评论,这也是其独特之处,对其作品的冷峻的风格和客观的叙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叙事所构建的叙事权威,也会因叙事者的侧重而构成不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的整部小说集的九个故事中,其他的八个故事均是描写女性的心理来关照自身的,而在《熊从山那边来》则换了一种不同的叙事策略,以男性格兰特来关照女性。长久以来,文学史中为女性声音的书写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也就是作者采用的这种作者型的叙述者所发出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到后来的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所用手法不同,达到的效果却使得女性的声音得以言说。
作者型的叙述声音,作为最原始的一种女性书写的表达,这种叙述形式不要求作者的自然性别,只要叙述中的“我”不等同于自然性别的女性,那么就可以参与“男性”权威。在门罗的小说集的前八个故事中多以个人型叙述声音为主,表现女性面对生活的态度,心理。而在最后的《熊从山那边来》却转向了作者型的叙述声音,他无处不在,却有所选择的借格兰特的心理动向,表达自己。例如对于女性的看法“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么。”[10]再如“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行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11]
因此,女性人物的塑造不仅仅是通过对话实现的,更多的是依赖于格兰特来实现,并且还加入了格兰特自身的价值判断,例如对于女性的观点,对于玛丽安物质化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对于自身婚姻的看法,而这种都是在男性对女性的关照中实现的,而小说中女性的描写却极为稀少,除了外部描写基本上都是借格兰特实现的。但是作为关心女性,以描写女性生活,写平凡琐碎生活的门罗来说,这种叙事中是否有女性的言说?首先,就要对格兰特的言行做出分析,在作品中各种各样的评价寄居于格兰特的意识中,借这一男人之口,完成了对于女性的“客观观点”。例如,认为自己才是在调情中的受害者,是不是?这种文本的解读就具备了双重性,一方面是男性的自身的冤屈,另一方面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声音的缺失,作品中基本上没有对于某一位女性意识的描写,这就构成了一种张力。女性形象的缺失和构建,及其声音的自述。
看似客观的外部——异叙述型的叙述却具备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格兰特作为男人的表述,一方面女性声音通过男性而言说。而叙述者又无处不在的作为插入性的表达着对于命运的看法。作品中表层也正如传统的性别文化所构建的那样,男性看女性,定位女性的位置。作品深层次上看则是,女性未被言说却更加具有生命的力量,无论是闪耀着生命力量的菲奥娜,还是充满力量的女性主义者,还是为求生存不顾一切的玛丽安,都拥着不同而强韧的生命力,而格兰特则纠缠于其中,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和女性气质的特征。因此,尽管表层看是传统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玩物,深层看由于女性在这一男性的反照中更显活力,则更加证明了女性的力量,和女性声音权威的建构。
二、叙述时间
叙述时间是故事的基本构成要素,正如热奈特先生所言,“由于存在某种不对称(其深刻原因我们尚不甚了了,但它表现在语言的结构中,或者至少表现在西方文化的主要“文明语言”的结构中),我完全可以将一个故事而不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该地点与我所讲述故事的地点之间的距离,但我几乎不可能不确定这个故事和我的叙述行为相对而言的发生时间,因为我必须用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一个时间来讲述它。叙述主体的时间的限定明显的比空间限定重要,原因也许正在于此。”[12]因此作为时间艺术的叙事作品,时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热奈特根据叙述主体与故事的相对时间,对叙事时间做出了四种划分分别是:事前叙述、事后叙述、插入叙述和同时叙述。
在小说中,时序的问题,整体上看叙事时间与叙事主体是一种事后叙述的关系,叙述人无所不知,大致根据与叙述主体的关系可以确定菲奥娜与格兰特的婚姻为故事起点,而菲奥娜的回忆出现二者相认是故事终点(开放式的结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插入叙述。例如,开篇是描写二者婚姻,之后便是准备送菲奥娜去医院,然后就开始了“一年多以前”之后均是现在时与过去时的交错,也就是插入叙事。这种插入叙事也是由格兰特来完成的,并且多涉及到格兰特与菲奥娜的回忆,例如“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目前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的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13]前半部分从“他想”到“那是他一生中最长的日子,那时他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这一部分属于他的回忆,而这种性质的插入,使得故事与叙述时间上的差距最短,也就最能够拉近读者的感受,而后面的“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则再次拉开距离,形成对比。这种形式在作品中不断出现,而且能够将格兰特的心理动向更为确切地展现给读者,拉近与读者的关系,从而在人物塑造上使得格兰特更加立体丰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格兰特的回忆,梦境得到了更多的叙述,并且回忆梦境的确定性与现实的模糊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回忆、梦境中的时间。例如对于回忆的确定性,他们多年前一同看望过住在医院的法卡先生,对于医院法兰特的记忆极为清晰,甚至记得当时看的书目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得当时建筑的建筑年代,和空气中的味道。再如他的梦境中与一些女人的关系以及一些感受“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遍布,收拢,绕住他的器官,笼罩在房间顶上”[14]而对于现在的叙述则呈现为多种的怀疑和模糊性的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例如,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就会支付她,让她顺服到可以听从他的程度,把奥布里带回到菲奥娜身边?”[15]“你永远无法预测这类事情的结果会怎样。你几乎知道但永远也不能确定”[16]在故事中的相对时间是与叙事者的相对位置来确定的,但是通过对比我们能够看到以人物的活动时间为进程的过程中,在菲奥娜患病之前和之后的事情出现了一种记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对比,而更加清晰的反映出了对于过去时间的确定性,和对于未来的模糊性处理,从而可以看出以这样的方式,用一种生活平常的琐碎,表达出了对于生活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阐释。
三、结语
以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叙事者和叙事时间对《熊从山那边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叙述者,叙事声音所达到的目的是不同的,作者选用了外部——异叙述型的叙述者形成的一种作者型的叙述权威,借用传统的性别文化建构的表层结构,看与被看的关系依然存在于文本之中,但是却可以有着另类的解答,借格兰特看不同的女人,读者借叙述者看人物,更为凸显的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少言寡语,虽然并没有更多的发言,但是此时的缺席,却更显出了格兰特的犹豫不决的精神气质,虽然有格兰特为自己婚外情的辩白,但是却显的更加无力。这样的双重解读,为作品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女性在作品中更是无声胜有声的存在。
从叙事时间上看,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可以看到时间在故事叙事中的重要作用,热奈特先生做了更为全面的划分,小说整体上依据叙述者与叙述时间的距离划分了四种,但《熊从山那边来》主要采用的还是过去时,但是却包含了大量的插入性叙事,不断的在回忆与现实的对比中突显。而回忆的不确定性和现实的模糊性也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从而能够看到对于不能确定和充满可能性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或许正如作品中所言“你从来都无法预测这类事情结果会怎样。你几乎知道,但是你永远也不能确定”[17]因此,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淡然处之,才是生活本身的意义。
[1]张德寅.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
[2]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P65.
[3]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38.
[4][12]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48,149.
[5][7][8][9][10][11][13][14][15][16][17]爱丽丝·门罗.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97,298,308,341,308,309,304,307,343,344,344.
[6]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