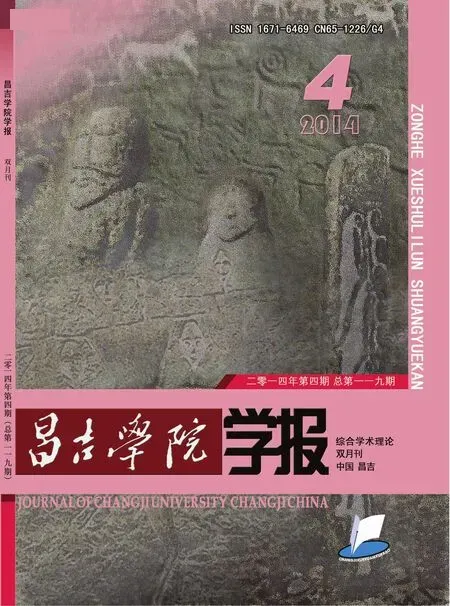论李娟散文中的女性形象
2014-03-28艾成伟胡昌平
艾成伟胡昌平
(1,2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论李娟散文中的女性形象
艾成伟1胡昌平2
(1,2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李娟散文中的女性形象整体上都表现出在不同文化之间游离,不断遭遇精神困境的生存状态。从深层次上说,这种表现是李娟通过散文构建纯粹女性世界的一部分,更是她对当代边缘化人物的严肃思考。
家庭本位;女性世界;边缘化环境;精神困境
李娟是新疆女性散文创作的后起之秀,擅长以清新的笔法书写自己经历的岁月。这种书写不仅是空间与时间的转换,更是精神困境与现实遭遇的交织。李娟在她的作品中,以家庭为本位,塑造了“我”、“母亲”、“外婆”三个核心女性形象,通过在典型环境下的书写,深切反映了当代女性在面对精神困境所展开的自我救赎与集体觉醒。李娟在作品中刻意回避了对男性形象的塑造,通过众多的女性形象的书写而构建了完整的女性世界。
一、“我”与“母亲”
李娟散文中的“我”是一位新生代青年女性,身处在已经形成的边缘化环境中,是在边缘化中反抗的主体,“我”面对破碎的家庭环境和艰苦的外部生存环境,以及自身近乎空白的精神环境,毅然选择了出走,去为自己所缺失的找寻补偿。家庭的破碎是导致“我”迷失的重要因素。“家庭对于个人来说是个人生活的栖息地,是个人进入社会的窗口,同时还是个人步入社会的初级阶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构成稳定的家庭三角。家庭的存在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各种需求。”[1]缺失父亲的保护与教育,使“我”丧失了对传统经验的继承,使“我”与过去的历史断开了链接,增添了“我”对未知的恐惧,迫使“我”不得不自己探索社会经验,取得认知,来促进自我的成长。李娟在《青春五号》中所提到的父亲,并不是家庭中的角色,而是一种“土地”文化概念。父爱的缺失,使“我”不得不过早的直面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的缓冲,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每一次外部冲击都直接打在“我”的身心之上。“那条落叶的街道,就这样从我的童年经过,却不知通向生活的某一处角落,哪一个日子。”(《落叶的街道》)父亲的缺失让一切充满迷失与未知,“我”不知自己有什么可以依靠,将归何处。“那么房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破的呢?”“可为什么没有一所房子,能够贯穿我们漫长的一生,像一个真正的家那样。甚至没有那样一把伞,阻隔风雨与生活之外。”“房子怎么会在人睡着的时候塌掉呢?”(《房子破了》)最后的
最坚固的依靠都倒下了,没有可以依靠的事物了,连心灵隐蔽之处也已崩塌,“我”对世界充满了恐惧,危机感始终围绕着“我”。“那一天,当我们顶着寒流和巨大的疲惫,走很长的一截黑路回家,哆哆嗦嗦的推开门之前,房子已经塌了。”(《这样的生活》)“尤其是想到自己要去的是那样遥远,尤其是想到那个地方将更为寒冷。”(《什么叫零下42度》),过去的岁月使“我”感到寒冷和永恒的缺失。“我”是如此的缺乏保护,如此的渴望着完整。李娟以“我”的心境反映了所有边缘化人物的真实心境。
在边缘化环境中,“我”始终是一个孤独者,找寻不到同类,没有模范可循,只有通过不断异化自身的角色,才能支撑自身走过困境。“我”本来是家庭的孩子,社会的弱者,需要关心、教育和保护。而事实却是,在山中,“我”需要扮演母亲和外婆的孩子来支撑她们的生活,又需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来支撑家庭(未感受父爱和父亲的责任,无法扮演)。而在城市中又需要扮演强大的男性,来支撑自身,独自面对种种陌生的人情世故。“我”充分认知到自己的弱小,并为之感到不安,不断促使自身发生改变,不断异化自身的角色。“我想我才是真的什么也不能做的一个,我才是两手空空,我只能等待而已。”(《星空》)。如此,“我”选择直面痛苦,选择用劳动来证明自己。将洗衣、挑水、看店、养鸡鸭、搭帐篷、赶场等等大体力劳动都扛在肩上。在《空手心》和《像针尖》中,“我”十几岁就选择离家去陌生的城市闯荡。通过自我奋斗,较早的独立,在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愈发渴望在生存压力与精神压抑之前突破现实的自我,在精神突围中寻找更加强大的自己。也正是如此,现实中的“我”——李娟拿起了笔走向了创作之路。可见边缘化人物对自身定位是极困难的,只有在不断地游离中,完成对自身的定位,才能直面边缘化环境。
父辈的文化系统,对于“我”来说,始终是缺失的,又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触及到的,这种缺失使“我”时时产生疑惑,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对自己和家庭缺乏根本的认同,也就对生存缺乏根本的认知。所以,当“我”选择出走时,所遭遇的仍是边缘化环境。“我”对于这早已习惯的边缘化环境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一方面渴望亲近,获得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渴望远离,去寻找自己的根。《童年》、《姑娘》、《星空》、《南戈壁》、《风雪一程》、《孩子的手》、《荒野花园》、《草野之羊》等书写的就是“我”作为边缘化女性的精神成长史,由幼稚到成熟,由疯狂到沉静,由错位到回归。成长的丧失感,让在“我”游离中不断找寻丧失的补偿,用外表的坚强掩饰自身的脆弱,选择以成长的方式告别过去,选择用爱的方式去拒绝孤独与黑暗。也正是如此李娟的散文创作并不是为“他者”写书立传,而是希望通过理清过去,来为自身所代表的这一群困境中的人寻找出路。
母亲是边缘化环境的塑造者之一,同时这一形象也代表着在边缘化环境中挣扎与反抗之后,却最终“随遇而安”的一代。母亲是三个核心女性形象中唯一一个面对边缘化环境能够自主选择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逃避自身的精神困境,她不得不选择了困守于边缘化环境之中。然而母亲对“我”和外婆的爱是不言而喻的,母亲需要家庭来支撑自身,在护卫“我”与外婆,抚慰“我们”的痛苦的同时也时刻面对自己的痛苦。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逼“我”成长,是作为已被边缘化的一代的无奈,母亲在边缘化环境中已认识到自己将无法保护“我”。
当母亲从另一个熟悉的边缘化环境退守到更为陌生和恶劣的边缘化环境中时,她所遭受的打击依然是巨大的,她虽然有众多的选择,但最终不得不选择逃避之前的生活,甚至出现角色的迷失。当过去与现在的精神困境一同袭来时,她只能退化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为自己和家庭
寻求解脱。她的痛苦是孤独的,是无法分享的。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是“我”的姐妹,照出“我”的早熟,照出“我”的未来,将“我”的痛苦陪伴,却同“我”一样无助。但其角色的迷失并不是彻底的缺失,母亲有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想要找回自己本来的角色。母亲看似是李娟散文中最自我、最自由的一个,其实是束缚最深的一个。她自身的一部分正在与现实脱节,她离开的愿景正在消失,更多的则是留下,留在这有自己创造成分的边缘化环境中。《在河边》中母亲让“我”独自在河边洗衣服,又为“我”的落水而着急,最终又以自己落水的方式安慰“我”。此时母亲虽在河边笑着,但她的眼泪一直在河中流淌,她内心其实有着强烈的矛盾与痛苦。在《妈妈知道的麻雀窝》中,母亲独自面对世间的边缘化环境,不愿外部事物纷扰家人。而母亲面对“我”的呼唤,在《落叶的街道》、《房子破了》中却显现了与“我”同样的无助,因而加深了自身的痛苦。她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我”的呼唤,渴望塑造与自身不一样的“我”。
母亲作为过去的一代,有着清醒认知的一代,在责任意识觉醒的同时伴随着角色的回归,在最想逃避的现实面前再次坚强面对。母亲和“我”所在同态边缘化环境中呈现的都是“现在进行时”,但母亲所代表的一群人身上还附有她们最想抹去的“过去式”,角色的回归使她不愿将过去痛苦传递给下一代,却给“我”所代表的新一代留下了新一层的迷失。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表明,母亲代表的这一群人正走在消亡的边缘。在《草野之羊》中,李娟以的梦呓般的书写形式构造了母亲真实而完整的形象。“我的乳汁充盈,我忍泪听着我的孩子嗷嗷待哺的哭声,把奶水洒向周围的大地。”在李娟的意识里母亲不是冷酷自私的,母亲作为过去的一代承受了莫大的痛苦。母亲的种种放任自流的方式,都是为了让“我”适应边缘化环境,并于其中成长。而李娟对母亲形象“利他”的写作也是一种刻意遮掩,即“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来看他们。”[2]李娟出于对母亲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母亲的形象。
二、外婆及其他女性
从李娟散文整体创造来说,“我”虽是女性世界的抒情主体,却不是创作的根基,而外婆这一女性形象的存在,正是这一切得以存在的基础,得以维系的动力。作为边缘化环境中逝去一代的代表,外婆形象始终“依托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3]这一准则,出现在典型化环境之中。外婆对于突然遭遇的边缘化环境是完全漠然的,她身上承载着一种过去,是过去文化与经验的集合。外婆形象存在的一部分是对“我”和母亲形象的补充,与“我”和母亲形成对照。外婆是边缘化环境中孤独的坚守者,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缺乏精神的传承与呼应。外婆与“我”和母亲“融入”、“习惯”、“迷失”的状态不同,她必须坚守过去的文化,才能支撑自己,乃至家庭的存在。外婆承载的厚重在于她是整个家庭伦理与情感观念的构造者,是传递文化的纽带,她将一种遥远而又模糊的人群和乡情带进这枯燥空白的世界,让“我们”告别孤寂与无助。只要外婆存在,“我”妈就是完整的母亲,是一个有所依托的孩子,而“我”就是一个有“根”的人。若外婆也在这边缘化环境中迷失,则“我”和母亲存在的世界将完全破碎。外婆所代表的久远文化是“我”和母亲的灵魂,也是她们得以成为完整的人的印证,然而这种文化是不为边缘化环境所见容的。外婆承载着遥远的过去和与她格格不入的现在,将一种温暖而又厚重的亲缘留给“我”和母亲,用这份最大的羁绊将她们牢牢地拴在这充满苦难的人间,让她们彼此照应、彼此安慰。可见亲缘是联系边缘化人物的纽带,也是缓解边缘化人物精神痛苦的重要途径。外婆的形象被物化为异乡的草帽,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之中,始终坚持自
我认同,并渴望文化的皈依,拒绝迷失与摇摆。“从染坊垭口走下去,有一个村庄桃花似海。然后又是蓝色的额尔齐斯河。阿尔泰群山间升起明月,恰娜曼骑着马,从山的尽头缓缓过来”(《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李娟以“我”混杂的美丽梦境,来表现外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外婆在文本中既是“我们”的母亲,又是“我”的父亲,这种现实又促使外婆不得不进行妥协,去应对当前的状况。这种妥协是痛苦的,也是必须的,唯有在坚守与妥协的悖论中外婆才能坚持走下去,这也是外婆所代表的过去一代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外婆在文本中“现在的状态”是“我”和母亲所向往的,是两代人对自身命运的预见,外婆的存在是作者本身“我”的一种希望,也是对自身精神困境的一种思考。外婆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我”和母亲的未来。“我”虽在外婆身边,却离外婆的文化心境十分遥远,无法理解外婆在文化困境中的坚持。“替你感受陌生,替你防备地看着世界,替你不停地怀想故乡。”出于外婆的依赖而诉说隐藏得最悲凉的话:“外婆,这个世界多么,陌生冰凉。”这是外婆所面对的世界。“你的草帽在街头巷尾固执的强调着你是一个异乡人。”李娟将外婆的定位为“异乡人”,反映外婆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我”对于过去文化感到陌生的态度,“外婆的草帽”凸显“我”想融入当前的状态,却无法走出时刻面临的的文化困境。外婆代表“我们”的过去,她作为过去的文化人终将远去。祖孙俩艰难地抢修帐篷,“(一块篷布)却怎么也拉不动,心中一片无望与悲伤。这时回过头来,看到外婆的草帽被风吹走了。”(《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外婆矮小的身影在狂风暴雨中“一直追啊追啊,似乎这样一直追下去,永远都不回来了”。这表明两代人的文化疏离,“草帽”象征着一种久远的文化,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反应了一代人在精神困境中的坚持。“我们祖孙三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帐篷里,却因为一只鸟儿,彼此分离得那么远。”(《花脸雀》)外婆代表的文化离我和母亲如此遥远,“我们”必须花费更大的精力面对现在,逃避外婆所代表过去就成为必然。但无法割裂亲情之爱始终是外婆联系“我们”的纽带,这促使外婆留下来,即对这种精神的游离妥协。
仅依靠较少的家庭核心女性形象无法构成典型的女性世界,所以李娟在作品中被动地构造了其他女性形象。李娟散文中的其他女性根据所处地域不同可以分为城市女性和牧区女性,但对她们的塑造都围绕劳动女性这一形象出发,依照外部世界女性生存状态的现实存在,与家庭之内的女性形象一起构成完整的女性世界。这种书写表现了“我”在不同境遇中的表现,不同状态中的作为。其中女老板形象是“我”的未来形象构想与现实重合的所在。“我”的现在就是她们的过去,她们理解“我”会走向什么样的境遇,但肯定我的现在就是否定她们的过去。她们同情“我”出走,对“我”的出走既有不舍也有欣慰。哈萨克族女性形象,在“我”的世界里不是缺失的创造者,而是外部世界与“我”联系的桥梁,是代表另一种文化来接纳“我”,她们所代表的环境意志,时刻想要改变“我”。而水边的女孩则是“我”一生理想的烛照,即为所爱所要保护的,去追求,去反抗,甚至去毁灭,“艺术可以表现神圣的理想”,而理想“比起任何未经心灵渗透的自然产品更高一层。”[4]她是合乎李娟心灵愿望的升华物。
李娟散文作中的女性形象都呈现一种边缘化人物的状态,而边缘化的女性,出于自我保护,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在不同的精神困境中会分化为一个更为敏感的群体。对这一点的表达,李娟抛弃了一味对人的形象的构造,而是通过动物形象的人化书写,来表达边缘化人物的情感。在《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中,对雪兔形象的构造,就是边缘化人物心声的真实袒露。在边缘化环境中,“雪兔”虽然极尽伪装,但仍旧难逃束
缚,而“我们”一家人对雪兔的同情,就是对自身遭遇的同情。雪兔在笼中困惑无助,以拒绝的方式保护自身,沉浸在自己构想的世界中,渴望逃离。“那时它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雪兔渴望春天的来临,一如边缘化的人渴望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根,而雪兔最终以垂死的形象又回到了笼中,又更加反映了边缘化人物的真实遭遇,在逃离之后,无路可走,又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的痛苦心境。“雪兔”已不单是“我”家饲养的小动物,而是“我们”命运的真实写照,“雪兔”是唯美的,是孤独的,是敏感的,是脆弱的,李娟完全把雪兔当做一个“女性”来塑造,当做自身的一面“镜子”来塑造。
三、女性的困境
边缘化环境是李娟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面对的现实环境,其中包含自然地理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边缘化环境是非主流的,包含着不安因素。李娟通过对三个核心女性形象的书写真实地反映了边缘化人物面对边缘化环境时,展现的较为普遍的三种状态。与此同时必须了解边缘化环境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更是女性形象所承载的一种代代相传且不断累积的精神困境。
三个核心女性形象都呈现出“无根”和“寻根”的状态,缺乏精神的依托,但她们寻求的方式都不相同。其中“我”是“缺失——找寻——迷失”;母亲是“缺失——找寻——回归”;外婆是“缺失——找寻——妥协”。虽然每个女性应对精神困境的方式不同,但同样渴望从困境中走出。这种自寻出路的方式虽是孤独的,却是全然自主的,三代女性形象共存共生构成一个整体,真实地表现了边缘化环境中生存的女性的完整形象。她们不是沉沦的,她们不断遭遇精神困境,却又不断寻找出路,相信希望,坚强求生。她们是我们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群人,是急需关注的一群人。她们选择了自己的路,但同样需要主流社会的帮助。对于她们来说,已觉醒的不可抹杀,救赎之路不可践踏。
李娟在《森林》、《富蕴县的树》中都写到森林,但森林不仅是自然物,更是一种文化集合的象征,对于出生和生长在其中的“树木”来说,它是温暖安逸的,是母亲与父亲的怀抱,是祖辈的荣誉与传承。而对于住居在其边缘的人来说,“森林”只是边缘化的环境,是生存之地,是想融入却无法融入的地方,与之前所信任、依托而又遗失的地方有着很大的差异,缺乏相互的认同。
这也道出了三个主要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人群面临的真实的困境,她们只是在这种困境中挣扎的代表,她们是所有身处边缘化环境中的人群中的一部分。她们好似三棵无根的树,没有土壤供她们栖息。她们始终行走在不同精神文化森林的边缘,这世界没有固定的森林是流浪的她们所拥有的了,过去的森林早已焚毁丢失。李娟在《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中写到:“我们早已成为随波逐流的人了,生活把我们带向任何一个未知的远方。”她们保留着原初民族(身份等自我认同)文化的心,却以一种游牧民族的方式(所遭遇的普遍方式)生存。她们这三棵联系紧密的树,呈现着不同的自然和现代性成长状态,且两者互为反比。她们在不同的精神文化森林之间徘徊,迷失,找寻。找寻自身行走的意义,找寻自身的最终归宿。她们回不到过去,也无法融入现在,想要进入森林之中隐藏痛苦,却最终成为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旁观者。
李娟在《九篇雪》中写道:“我们这样在群山中四处游荡,却永远不能走遍它的所有角落,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我们想去,那儿汽车无法到达,双脚不能抵至,甚至梦想也未可及之,我们到处搬家,一步一步走向一些地方,又像是在一步一步地永远离开。”这一群人脱离了生长的原初土壤,他们只能在茂盛的森林(不同环境的盛况)边
缘行走伸展。李娟在《马桩子》中写到:“我们这个家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想着离开。”李娟的《故事》中集体人物的的命运则回应着这种游离。三棵树所代表的不仅是女性的命运,更是在不同角落里经历着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境遇的人群的命运。
李娟的创作是基于回忆来进行的,“艺术物品或其它物品的功能是作为一个记号以指明某些事实——某人感受如何、他信仰何物、他生活于何时何地、他的梦幻为何事所折磨困惑。”[5]但李娟散文中女性形象的书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距离文本素材较近。“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6]正是这种近距离的“旁观者”的视角,对李娟的女性形象创作影响较深。其中“我”的形象的塑造大部分依靠其他形象的对比与映衬来完成,而母亲则是塑造得最为丰满的形象,外婆形象出现的篇幅虽然极少,却是最为厚重,最不可或缺的。
李娟在散文中塑造的三个核心女性形象,都是精神依托的丧失者。即便李娟力图通过积极的笔法,塑造美的形象,以其“诗意的裁判”[7]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但实际她所描绘的美,都是核心女性形象遭遇的真实悲欢。李娟通过在典型环境下的书写,深切地反映了当代女性所面对的精神困境。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女性形象的个人遭遇看做个例,她们所代表的应是一群人,迷失在边缘化环境中而又不断游离的一群人。这种自然而非自觉地流露,正是对部分评论家所认为的:“李娟的创作只合大众趣味,而缺乏文化内涵”的最好驳斥。
[1]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苏)普列汉诺夫著.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M].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6.
[3](法)左拉著.论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卷[M].柳九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22.
[4](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37.
[5]苏珊·朗格.情感的象征符号·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1—41.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3.
[7]朱光潜.谈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I206.7
A
1671-6469(2014)04-0001-06
2014-07-12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21075570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XZW038)
艾成伟(1993-),男,湖北浠水县人,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