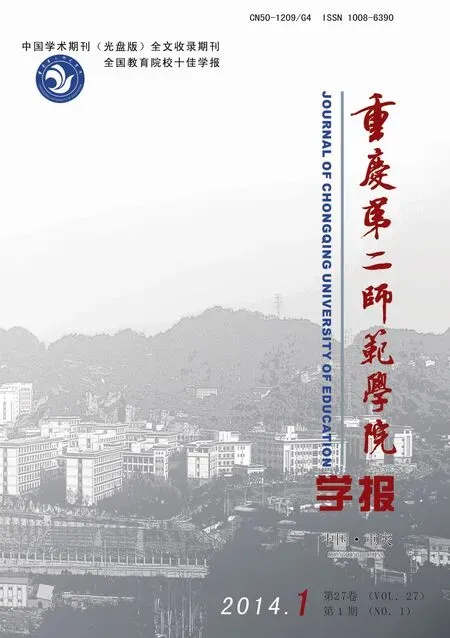白居易与“永贞革新”主要成员的关系研究
2014-03-28刘秀梅
刘秀梅
(内江师范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北碚,400715)
“永贞革新”在中唐时期确实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衰与未来走向,更关联到许多有才能的、正直的、有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的读书人的命运与政治成败。那时的白居易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亲身参与“永贞革新”,但他在公开场合和其它场合对“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和措施是非常赞成的。这主要表现在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的态度上,同时也表现在他与“永贞革新”主要骨干成员交往的诗文中。
一、白居易与韦执谊
韦执谊,革新派的主要支柱,顺宗时官拜宰相。《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韦执谊,京兆旧族也。……顺宗立,以疾不亲政,叔文用事,乃擢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顺宗实录》记载:“二十六日,顺宗即位,至二月初三日,始朝百官、听政。十一日,以吏部郎中执谊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白居易集》卷四四标明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所写的《为人上宰相书》,就是给同年二月十一日辛亥,以吏部侍郎擢授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韦执谊的,他是“八司马”中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书中说:“二十九日,某官某乙谨拜手奉书献于相公执事:书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难也。某以为未甚难也。以尊干卑,以贱和贵,斯为难矣。何者?夫尊贵人之心,坚也,强也,不转也甚于石也。卑贱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于水焉。则其合之难也,岂不甚于水投石哉?此盖以心遇心,以道济道故也。……”“某伏观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盖先皇所以辍己知人之明,用贤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赐今上也。故今上在谅阴(居丧)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是以庶政阙于内,则庶事致于外,致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马日滋。游手于道途市井者不知归,托足于军籍释流者不知反。计数之吏日进,聚敛之法日兴。田畴不辟,而麦禾之赋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日贱。吏部则上人多而官员少,奸滥日生;诸使则课利少而羡馀多,侵削日甚,举一知十,可胜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边陲未甚静,水旱之灾不戒,兵戎之动无期。然则为宰相者,得不图将来之安,补既往之败乎?……。某游长安,仅十年矣,足不践相公之门,目不识相公之面,名不闻相公之耳,……实不自揆,欲以区区之闻见,裨相公聪明万分之一分也,又欲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也。相公以为如何?”[3]这封洋洋洒洒三千余言的长信,不仅表示作者对时局的热切关注,而且提出了不少建议。花房英树在《白居易》中说:“当时政治改革的势力已在逐渐高涨。在与贵族式的高级官僚阶层相对抗的王叔文、王伾的指导下,年轻的官僚们掀起了变革运动。柳宗元与刘禹锡也参加了这次运动,这就是‘永贞革新’。”[4]白居易大概也被这种动向所激动从而无所顾及地奋起批判现实,悄悄研拟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范围广泛的改革方略。这与白居易一向主张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主张,都是相符合的,也是其同情“永贞革新”的思想基础。革新夭折后,白居易在诗歌里表示了对韦执谊等的同情和惋惜。《新乐府·太行路》题下小序云:“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说:“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又说:“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诗乃追刺德宗朝颇负盛名的宰相杨炎、窦参、刘晏等的旋用旋废,并惨遭屠戮,而且也有慨于永贞朝宰相韦执谊的贬死崖州。他说:“韦执谊流贬于宪宗即位之年,距乐天作诗甚近。……虽未赐死,但进退荣辱,易致乐天之感触,自甚明也。乐天此篇之作,或竟为近慨崖州之沉沦,追刺德宗之猜刻,遂取以讽刺元和天子耶?”[5]如《寓意》第二首:“赫赫京内史,炎炎中书郎。昨传徵拜日,恩赐颇殊常。……。”[6]据旧纪:永贞元年二月,以韦执谊为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诗中以京内史和中书郎并举,且朝拜夕贬,意指执谊等,确然无疑,但诗人以一种朝荣夕悴,盛衰无定的委婉表现手法表示对韦的同情。另《寄隐者》云:“道有驰驲者,色有非常惧;亲戚走相送,欲别不敢住。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7]这首诗作者作于永贞元年韦执谊贬官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称为右丞相,且明言崖州,是指韦执谊无疑,与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年谱》考证亦同。[8]这首诗,描写被贬及亲友送别的凄惨场面,明白表示出作者对韦的同情。这类诗,作于事变之后不久,囿于政治因素,只能隐隐约约地透露点滴意见和感想。作者对韦执谊的同情,亦即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二、白居易与刘禹锡
在“永贞革新”中,除二王和韦执谊外,革新派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刘禹锡了,后来白居易与其结下了特殊的友情。《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刘禹锡,字梦得,……淮南杜佑表管书记。入为监察御使。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9]刘禹锡和王叔文等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又帮助王叔文掌握全国财政大权。从现存刘、白两人的集子和别的记载来看,他们互通诗篇,约在元和二年至六年,[10]即白居易作翰林学士、刘禹锡贬朗州司马的时期。《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刘禹锡赠白居易的诗。诗云:“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11]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时白居易罢苏州刺史,与刘禹锡相遇于扬子津,结伴游扬州。[12]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13]刘禹锡答白居易《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14]第一首诗中,白居易对刘禹锡贬谪二十多年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不仅指他的诗是“国手”,实际是称赞并惋惜刘禹锡的才华,才能虽高,却无用武之处。白居易也有过相同的被诬陷贬谪的经历,对于刘禹锡的处境和心情,自然是十分理解和同情了。在第二首刘禹锡赠答白居易的诗中,感情深沉,于叹惋中感怀自己凄凉的经历,虽然身遭险境,但终于还是重返政治舞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充分表现了刘禹锡一种乐观的心态和一股顽强的劲儿。白居易对刘禹锡十分了解,深敬其人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屈服于时势。刘禹锡未卒前,自为《子刘子自传》,自为铭云:“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刘禹锡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而这份傲骨与凛然既是白居易追求的又是其自身所做不到的,因此,白居易对刘禹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因为这份感情的维系,使得白居易和刘禹锡后来的关系从政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诗歌王国中,并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情。
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在扬州会面以后,一直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死,将近二十年里,两人同游共饮,酬唱殆无虚日。故陈寅恪先生指出:“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15],此言实允当。刘禹锡《汝洛集引》中云:“太和八年,予自姑苏转临汝,乐天罢三川守,复以宾客分司东都。……明年,予罢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16]《白居易集》五十九卷《与刘苏州书》云:“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然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17]同集第六十一卷《醉吟先生传略》云:“退居洛下,(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18]二人在诗歌唱和中,刘禹锡对白居易的诗赞不绝口,白居易则把刘禹锡看作诗友、劲敌,二人互相钦佩比慕,共同探索于艺术的最高峰,为诗坛倍添佳话。会昌二年,刘禹锡卒,白居易作《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委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19]诗中白居易不只肯定他是英雄,更引之为特殊的知己;而“文章委婉”之语,既指出了刘禹锡诗之所长,亦是白居易一直想要达到的境界,也概括了刘禹锡一生的遭际与刘、白二人思想之契合,其旨深远。
三、白居易与“永贞革新”其他重要成员
(一)白居易与李谅
李谅,《唐书》无传,《全唐诗》云:“李谅,字复言,三宰剧县,再为郡牧,终京兆尹。诗一首。[20]”李谅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人物。王叔文用李谅为度支巡官,又荐其为左拾遗。《柳集》卷三十八《为王户部荐李谅表》,云:“窃见新授某官李谅,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礼,敏而甚文。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谅为巡官,为及荐闻。……谅实国器,合在朝行;伏望天恩,授以荐官,使备献纳。……”[21]李谅荐官一职当是王叔文推荐的结果,后王叔文败,元和二年,李由左拾遗被贬为澄城县令。元和元年春,白居易校书郎任期将满,闲居华阳观,准备参加制科考试时,有《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诗:“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事知。争忍开时不同醉,明朝后日即空枝。”[22]元和十年秋,白居易贬江州司马赴任途中,有《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诗:“忽忆两家同里巷,何曾一处不追随?同游预算分朝日,静话多同待漏时。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做彻明棋。可知风雨孤舟夜,芦苇丛中作此诗?”[23]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谓李六郎中即李谅。不久白居易由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寄诗给钱徽和李谅,有《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谩道风烟接,何曾笑语同?吏稀秋税毕,客散晚庭空。霁后当楼月,潮来满座风。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唐郡,忙闲恰得中。”[24]钱、白是翰林院的老同事,钱当时由江州刺史移湖州,李谅已由寿州移苏州。钱、李知道白居易喜欢饮酒,各以当地名酒送他,他又写下《钱湖州以箸下,李苏州以五骰酒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以所怀》,结句说:“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25]白、钱曾作中书舍人,白、李曾同官尚书省外郎、正郎,“曾陪西省与南宫”,表明了老同事老朋友对往事的回忆。
(二)白居易与李景俭
李景俭,字宽中,陇西人,汉中王瑀之孙。《唐书》载:“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自负霸王之略,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贞元末,韦执谊、王叔文东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窃政,属景俭母丧,故不及从坐。”[26]其后为韦夏卿东都从事,迁监察御史,贬江陵户曹,转忠州刺史。为谏议大夫,授楚州刺史。在“永贞革新”集团中,“叔文最所贤重者李景俭”。[27]李景俭不以诗文著名,但白居易和他的关系非比一般。灭吴元济时,李为行军司马,立下战功,白居易由江州贬所寄去贺诗《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泥埋剑戟终难久,水借蛟龙可再多。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28]元和十四年春(公元819年)白居易接任李景俭为忠州刺史,有《初到忠州,赠李六诗》:“好在天涯李使君,江头相见日黄昏。……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29]李景俭因与同僚独孤朗等在史馆饮酒,乘醉诣中书,当面谩骂宰相。对于这一件事,白居易奏有《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为之辩护,认为李与独孤朗等“皆是僚友,旦夕往还,一饭一饮,盖是常事”,“然皆贬官,即恐太过”。他又说:“臣又见贞元之末,时政初言。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30]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含有肯定“永贞革新”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意味。李死后,白居易曾作诗纪念他,表达对好友的怀念。
(三)白居易与柳宗元
柳宗元是与白居易同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新唐书》载:“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裹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31]柳宗元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调官京兆府,此后至永贞元年(公元805)九月被贬官为止,有三年左右与白居易同在长安。但就二人文集考察,白居易与柳宗元在这一时期没有直接交往。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诗文往来,但如果说白居易与柳宗元没有间接的接触,恐怕是说不过去,他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其成员的同情也就成为了空谈。首先,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白居易以“肆”字论诗,或许就受到柳宗元的影响。[32]其次,白居易在《策林》中一再强调“政化速成”在于“不变礼,不易俗”(十二),“达聪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创新规”(三十六),“国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若一王,理经十圣,变革之议,非臣敢知”(五十一)。这些说法是重复一种普遍的政治信条,肯定现实制度的合理性;但白居易不赞同郡县为封建的“变革之议”,又与柳宗元“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亦”的观点是一致的。再次,在反对藩镇,反对进奉等弊政及元和连年用兵上,白居易与柳宗元及其他政治家一样注重务实,主张统一集权的唐王朝的国家常制,革除弊政。二人虽没有直接的书信交往,但这种间接的思想交流还是不少的,这也是二人达到某种默契的重要思想基础。
永贞内禅后,从白居易与被视为“永贞逆党”的“八司马”党人的文字交往,可以窥知他对“永贞革新”持同情赞许的态度。在“罪谤交积,群疑当道”,“未尝有故旧大夫肯以书信见及”[33]的形势下,白居易却不避风险,同他们唱酬应和,倾心相与。这说明他们在思想及政治倾向方面,彼此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参考文献:
[1][9][26]刘晌,等.旧唐书:卷一六八.一七一.一六八.一七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23.4455.5129.
[2][27]韩愈.顺宗实录:卷一.五[M].韩愈.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366.381.
[3][6][7][13][17][18][19][22][23][24][25][29][30][31]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二.二十七.五十五.五十九.六十一.六十九.十三.十五.二十.二十.十八.四十三.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97.19.28.417.853.943.974.1124.193.248.335.337.263.293.647.
[4]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82.
[5][1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北京三联书社,2001.181.251.
[8][12]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4.170.
[10]朱金城.白居易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82.
[11][14]刘禹锡.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28.1047.
[16]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5.
[20]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268.
[21][33]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779.986.
[2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95.
[32]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