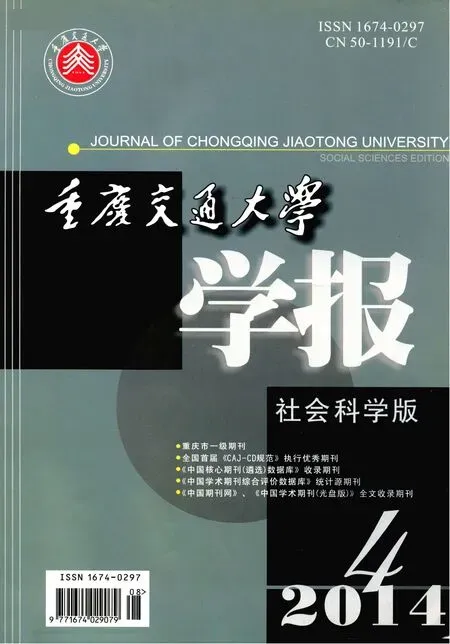李渔诗风宗中晚唐及其原因探析
2014-03-25王逸群
王逸群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和美学家。学者对李渔的研究也集中在戏曲和小说领域。其实,李渔是难得的全才,其诗歌创作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遗憾的是,对李渔诗歌的研究历来不受学者的重视。李渔诗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其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和对特殊历史时代的因应,研究李渔的诗歌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其“全人”的形象。李渔的诗歌流畅浅近、清丽绮艳,颇有意趣和特色。他在《一家言释义》中说:“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成一家,云所欲云而止。”[1]81自诩为不师法古人。然而,李渔诗歌虽然自出胸臆、“云所欲云”,但其浅近清新、天然隽永、深婉绮艳的风格,与中晚唐诗风十分接近;其诗歌中表现的感伤和闲适自足的基调,颇肖中晚唐诗歌的感情基调,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在对《一家言诗文集》的评注中,不少人指出李渔之诗颇有唐诗风韵。本文拟从感情基调、审美风格分析其诗与中晚唐诗风相近的具体表现,并探究其宗中晚唐的主要因由。
一、李渔诗风宗中晚唐的具体表现
(一)感情基调
1.无奈感伤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趋衰落。盛唐气象到了中唐无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思索和消极惆怅的感情基调。昂扬壮大、气魄刚健被对现实的无奈感伤取代。热切的入世愿望变成了冷眼旁观,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变成了谨小慎微的生活态度。正如白居易所言:“外容内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2]203诗歌中频频出现感伤的字眼,或伤感于社会上的悲惨之事,或伤感于作者本身经历的种种不顺心。
李渔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清易代之际,战争频仍,烽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安身。李渔诗作中有不少对战争的描写,充满了厌恶、消极的情绪。如《甲申纪乱》:“……纷纷弃家逃,只期少所累。伯道庆无儿,向平憾有嗣。国色委菜佣,黄金归溷厕。入山恐不深,愈深愈多祟。内有绿林豪,外有黄巾辈。表里俱受攻,伤腹更伤背。又虑官兵入,壶浆多所费。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乱世遇崔苻,其道利用讳。可怜山中人,刻刻友魑魅。饥寒死素封,忧愁老童稚。人生贵逢时,世瑞人即瑞。既为乱世民,蜉蝣即同类。难民徒纷纷,天道胡可避。”[3]8-9对战乱的厌恶、对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情与无奈共同构成了一种凄凉感伤的情感。
2.闲适自足
身处乱世之际,士子的豪雄之气渐渐被冰冷的现实扑灭,苦闷无处寄托,往往会寄情于山水游乐、生活享受之中。李渔的作品中经常体现出一种对生活闲适的享受和追求。在经历战乱躲避山中的那几年,他感到痛苦和厌恶,逐渐寄情于山水之美以及生活中的享乐,甚至称避乱山中的三年“以无事为荣”,得享“列仙之福”。如其《山家二首》其二:山犬无人亦吠,林鸡不晓常鸣。少此闲中聒噪,终年幽梦谁醒[3]298。此诗与杜牧《即事》[4]72诗所表现的意境与情怀很接近:
小院无人雨长苔,满庭修竹间疏槐。春愁兀兀成幽梦,又被流莺唤醒来。
幽静闲适的环境正契合诗人追求的心境。李渔自战乱后生活拮据,为维持生计终年奔波在外,但是始终保持对美的追求和享受。他曾经“质簪珥”购水仙,在家人劝阻的时候说道:“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1]50。当李渔客居广州的时候,不以瘴气为害,而是“饱餐鲜荔子,醉读古蝇头”[3]110;他在京城看到达官贵人匆忙进宫之状后表示“求富贵须忙,为贪慵,脱不下、雨蓑烟笠”[1]50。没有年少时对立功立身的强烈渴望,变成了对幽趣生活的眷恋与自足。“富贵可羡劳亦足,输予一枕南山巅。”[3]60李渔的诗歌中常常表现出这样的闲适自足之情。
(二)审美风格
1.浅近流畅
近人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指出李渔诗风颇类白居易:“其诗规抚香山,真率而近俚。”[5]333李渔诗歌浅近平易,很少用艰深之典。读其诗,有娓娓道来之感,浅近易懂。周伯衡评笠翁诗:“一气如话。”其诗句“我爱江村晚,牛归饭熟时。家家儿女笑,为绝远人思”,“春游芳草地,落得几朝闲。归去骄妻妾,云从世外还”[3]295等,浅近直如面语,但觉诗意盎然。诸如此类的诗句在李渔的诗集中俯拾皆是,如《瓶梅》:“散脚道人无定性,闭关十日为梅花”[3]302,与白居易咏桃花“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2]187诗风相近,诗意清新,用语灵动浅近,皆平易而流畅。
李渔对白居易评价很高,他和白居易的《咏慵诗》虽是趣言白居易不如嵇康善“慵”,却又云“白慵稍逊嵇,只为才兴戎”,赞《长庆集》“矫健如游龙”。正如黄无傲所评:“名曰坦嵇,实为赞白。”[3]26李渔对白居易十分赞赏,认为白居易的诗歌“清空复灵逸,欲辨无痕瘢。诗中觅昆季,千古成二难”[3]21。在李渔的诗歌中,最明显的风格特征就是浅近流畅,如《别熊元献归白门》[3]202:
此番作客似归家,赖有人居汉水涯。近日谈诗来有意,经年投辖去无车。
鲜交为我朋心热,不饮逢君酒兴赊。莫怪临沂催折柳,得知何日寄梅花?
姚天逋评此诗云:“元白体久不讲矣,读笠翁诗如读《长庆》倡和中得意句,快甚!”[3]202明确指出李渔诗歌与白居易诗歌相似的审美风格。
2.清丽绮艳
李渔有不少清丽深婉诗作,与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格调极相似。郭麐在《灵芬馆诗话》中说:“李笠翁以填词擅名,无他著作,人多俳优蓄之。然清词丽句,亦有不可没者。《晓行》云云,又绝句云云。”[5]320如李渔《送金长真太守之任维扬》[3]215:
雄才自合理繁疆,醉拥旌旄出帝乡。小别亦令诗思减,盛游难续酒杯长。
风摇隋柳迎车入,雪作琼花引路香。却怪故人燕市里,不随竹马去南方。
韵致深婉,意象幽秀,词句绮丽雕琢,与温庭筠《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相比,虽所咏内容不同,但格调颇为相近。
清人胡介评李渔“艳才拔俗,藻思难羁”[5]30,洵为确论。李渔的才思俊藻表现在诗歌中,形成了深婉清丽的风格。即使是路过战乱后的荒居,李渔题壁诗亦有“竹许从容看,花怜着意栽”[3]99之句,患痛之语,轻倩流出。在描绘景物时,李渔构思巧妙,出语绮艳。如咏自己设计的伊山别业:“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3]166字句清丽,读来芬芳。如咏西湖:“载酒看迟云,居高景不凡。如来空艳相,西子缟春衫。色淡黄金柳,花装白玉岩。江湖同一抹,无处觅征帆。”[3]99语境绮丽清婉,王茂衍评其:“庭筠、商隐之间”[3]99。
3.奇趣隽永
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诗人,诗风中已没有了初唐的悲壮慷慨和盛唐的恢宏昂扬。人们经历过离乱奔波之后,“气骨顿衰”,诗人流于性情,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这种情感的压抑使诗人们开始转移注意力,注重生活的细节,流连享乐,在诗歌创作上不再表现出宏大的志向而是偏重于趣味与新奇的现象。
李渔的诗歌中多奇思隽语,构思巧妙,颇具趣味性。如清人黄携埙评论李渔诗歌云:“笠翁以词曲知名于时,而诗句亦往往有可采者。七绝云:‘云雾山中虎豹眠,千年松子大于拳。自从烂柯无人伐,万丈奇杉欲上天。’疏宕之中,颇露奇气。”[5]320清人余鸿客评李渔云:“矢口而谈,皆成妙谛”[3]276。如《伊园十二宜》之《宜晓》[3]314:
开窗放出隔宵云,近水楼台易得昕。不向池中观日色,但从壁上看波纹。
思致奇绝,寻常的景致在李渔的笔下变得趣味盎然。如王左车所评:“极寻常话,入手便成隽语。”再如顾赤方评其《野性》:“启梅尧、放翁于今日。”陆游是中晚唐诗风的学习者①,所以这实际指出了李渔与中晚唐诗歌的关系。
二、李渔诗风宗中晚唐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文化环境
李渔出生于1611年②,父辈行医或者经商,家境素饶。但后来家道中落,李渔不得不四处奔波,卖赋求生。黄鹤山农说:“(李渔)家素饶,其园亭罗琦甲邑内。久之中落,始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1]32在四处奔波的过程中,李渔得以接触当时的许多文人,比较接近当时的文坛。清人顾景星在康熙十八年所作的《簏稿诗序》称:“今海内称诗家,数年以前,争趋温、李、致光,近又争称宋诗。”[6]200这表明在清初的诗坛上有过对晚唐诗歌的推崇。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提到:“在明末清初的诗坛有过一股晚唐诗歌热……在明天启、崇祯年间,就有王次回以学香奁体而著名。……杜紫纶、杜诒谷选编《中晚唐诗叩弹集》十二卷,其《中、晚唐诗叩弹集序》称:‘唐人如白香山以迄罗、韦诸家,不拘蹊径,直抒胸臆,或因时感愤,或缘情绮靡,使神无不畅,景无不宣,而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之旨,未尝不存乎其间,求其所谓尽与俚者不可得。’”[6]199-203可以看出,明末清初的诗坛对中晚唐诗歌的审美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李渔在编《资治新书》的时候,曾数次远游,与诸多诗人唱和,这种诗风与李渔内心厌战、追求美的享受的情感相呼应,对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李渔的思想
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首先动摇了朱熹学派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随后王艮的泰州学派、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推进了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李渔,其思想中鲜明地表现出这一思想启蒙运动造成的影响。李渔宣称:“我所师者心。”[7]2在文学创作中指出“文章者,心之花也”,力主性灵,写出自己的精神和个性。正如黄强在《李渔的哲学观点和文学思想》中所说:“崇尚性灵,形成了李渔独特的文风。……诗词不见得高明,但特点是坦率,性灵流泻,真情自见。”[7]5
在李渔的思想中亦有老庄哲学的痕迹。道教主张重视个体生命,老子提出四大,即道、天、地、人,庄子强调个人生命、自由的价值,主张“不以一国易一己之身”[8]。道教把心灵的自由看得重于一切,庄子宁居于贫贱而拒绝宰相之位。嵇康称:“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不足耳。”[9]李渔也时常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如他赴试过程中闻警而返,所表现的不是惋惜、悲痛,而是“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并且从此绝意仕进,享受“列仙之福”。他在赠友人的诗歌中也有“富贵可羡劳亦足,输予一枕南山巅”,他热衷于戏曲创作,并不因时人轻贱转投举业,他所追求的是灵魂的自由和心灵的满足。这使他的诗歌中时常流露出对趣味的追求和享受,并表达向往平和生活的一种闲适自足的情感。
(三)戏曲理论的影响
李渔首先是个剧作家,他的一生也确实为戏曲的发展不懈努力,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戏曲理论。李渔论戏曲主张浅显、尖新、自然、雅俗共赏,要求词曲既要易于场上领会,也要耐得住案头观赏。他的戏曲“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5]328,有人指责他的科白充满市井气息,却“不知作者命意,正惟雅俗共赏,使人易于观听”(丘炜萲评)[5]327。对汤显祖的《牡丹亭》,李渔曾论道:“予最赏心者,不专在惊梦、寻梦二折,谓其心花笔蕊,散见于前后各折之中……以其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也”[10]34-35。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时人作曲在字词典丽上苦费经营提出批评:“近词颇似西湖月,纵好谁人耐冷看。”[11]278并对自己作曲浅近感到自豪,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调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12]。这种创作理论表现在李渔的诗歌中,形成了其平易浅近的风格。
需要注意的是,李渔贵浅显而反对粗俗,他所提倡的乃是一种浅近、雅炼的风格。他虽认为好的戏曲应当使观众易于领会,但对当时一种以排场的热闹与否评价戏曲优劣的风气很不以为然。他在诗中表达过:“白雪阳春世所嗔,满场洗耳听巴人。调高犹喜非春雪,冷热同观但未匀。”[11]279赵山林分析此诗谈及李渔的戏曲理论:“他认为戏曲应当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应当创造出‘冷中有热’、‘雅中有俗’的艺术境界,以便‘冷热同观’,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审美需要。”[11]279李渔曾经指出:“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7]57他所提倡的文人之笔并不仅是浅显流畅,还包括用词清丽,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绮艳清丽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除了主张风格浅近、雅俗共赏以外,李渔还提倡“意取尖新”,指出“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10]70。他在戏曲创作中不仅出语新奇,而且构思巧妙。李渔认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10]36在李渔的诗歌创作中,他很好地展现了构思的奇巧,使得他的诗歌充满意趣,情境隽永。吴战垒在《一家言》序中论及李渔的词曾言:“其词虽不乏佳作,然结体稍弱……风格逼近于曲,这或许是他曲家本色的自然流露吧。”[3]1李渔的“曲家本色”不仅对其词作有影响,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即其诗歌接近中晚唐诗风的审美风格——浅近的诗风、清丽的词句以及鲜活的意趣。
注释:
①见钱钟书《谈艺录》中《陆游与中晚唐诗人》一节。
②据黄强《李渔生平三考》一、生年新证:“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11年9月。”
[1]单锦珩.李渔年谱[M]//李渔全集:第19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2]谢思炜.白居易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李渔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全唐诗: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5]单锦珩.李渔研究资料选辑[M]//李渔全集:第19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社,1990.
[6]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黄强.李渔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8]崔大华,等.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9]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江巨荣,卢寿荣.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赵山林.历代咏剧诗歌选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2]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M]//李渔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