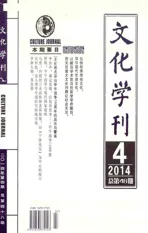从《挂枝儿》《山歌》看晚明社会风习
2014-03-20陶慕宁
陶慕宁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云:
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而七字件尤多。至欺诳人处,必曰“风云”,而里中恶少燕闲,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竟不知此风从何而起也。[1]
范濂,松江华亭人,生于嘉靖十九年。《云间据目抄》五卷,万历二十一年已问世,上段引文所述当是万历十五年以后事。【打枣竿】又名【挂枝儿】,是万历以迄清初风行南北的时尚曲调。
冯梦龙辑录的《挂枝儿》《山歌》是明代收录民歌时调最全的专集,《挂枝儿》存曲词379首,《山歌》存歌词380首,足以揭示万历以来民间时调歌曲的流变兴替轨迹,亦可反映文坛士林趋俗求真尚趣的审美诉求。辑者的眉批夹评,或涉方言市语,或及掌故流俗,颇可资吾人采择,藉以窥知晚明社会风气之迁转。
《挂枝儿》《山歌》远绍《诗三百》缘情咏言的现实主义传统,内容上则直承六朝“吴声西曲”的多诉男女之事,而因地域物产之差异,又可见南北市井风气之不同。在艺术上,《挂枝儿》《山歌》吸收了元曲的长短句式,衬字,多用双关隐喻 (当然这亦是六朝民歌的特点),结句力求波俏精警的技法,在晚明诗坛独树一帜。卓珂月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2]但《挂枝儿》《山歌》的作者不必认为皆出民间市井,其中应有相当数量的文人拟作。如《挂枝儿》卷五“隙部”有“是非”六支曲,第五支后评曰:“此黄季子方胤作。”按:方胤,金陵人。所作《陌花轩杂剧》十折,颇涉市井敝俗。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列其为“具品”,然则其非市井中人可知。又《挂枝儿》卷三“想部”有“喷嚏”一曲,词曰: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
冯梦龙评曰:“此篇乃董遐周所作。遐周旷世才人,亦千古情人,诗赋文辞,靡所不工。其才吾不能测之,而其情则津津笔舌下矣。‘愿言则嚏’,一发于诗人,再发于遐周,遂使无情之人,喷嚏亦不许打一个。可以人而无情乎哉!”按:董遐周,名斯张,浙之乌程人,监生。有《静啸斋词》 《明史·艺文志》著录其《广博物志》五十卷,《吴兴艺文补》七十卷,别部四卷。又《挂枝儿》卷四“别部”录“送别”数曲,多文人所翻作,冯梦龙引董斯张语云:“遐周曰:愈转愈妙,乃知文人之心濬于不竭。”观以上数则文字,可知董遐周乃兼学者与文人为一身而饶有趣味之人。《挂枝儿》《山歌》尚提及祝枝山、张伯起、江盈科、戴章甫等一时胜流,或模拟仿作,或评骘推毂,足见这种新型的民歌样式已引起当时士林普遍的关注,且与万历以来泰州学派、公安派求真尚趣的文学主张符契若合。
《挂枝儿》《山歌》的写法大量借鉴了《诗三百》以降民歌比兴双关咏言的传统,试举三例,以见一斑:
小阿姐儿无丈夫,二十后生无家婆。好似学堂门相对子箍桶匠,一边读字一边箍。(《山歌》卷三“私情”四句)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樁要开船。挟绢做裙郎无幅,屋檐头种菜姐无园。(《山歌》卷三“私情四句)
郎种荷花姐要莲,姐要花蚕郎要绵。井泉吊水奴要桶,姐做汗衫郎要穿。(《山歌》卷四“私情四句)
以上二例中“箍”“幅”“园”分别谐音“孤”“福”“圆”,“读字”谐音“独自”。第三例“莲、绵、桶、穿”四字则兼有谐音双关之修辞功能,而明代民歌实亦多方汲取古诗词曲之法乳,按以新腔,遂极一时之盛。下引数例以见晚明时调源流:
一、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词·三·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二、杨朝英《阳春白雪》卷四贯酸斋【中吕·红绣鞋】(《乐府群珠》题作《欢情》):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
三、冯梦龙《挂枝儿》卷七《感部·鸡》:
五更鸡,叫得我心慌撩乱,枕儿边说几句离别言。一声声只怨着钦天监。你做闰年并闰月,何不闰下了一更天。日儿里能长也,夜儿里这么样短。
四、冯梦龙《山歌》卷二《私情四句·五更头》:
姐听情哥郎正在床上哱喽喽,忽然鸡叫咦是五更头。世上官员只有钦天监第一无见识。你做闰年闰月 了正弗闰子介个五更头。
此数例皆写男女幽期,怅恨于时光飞逝。手法则如出一辙,皆着眼于时间之想象。不约而同,提出“闰”字,欲延佳期,以见痴情,用时间之短暂反衬私情之浓烈。这种手法在诗、词中皆难以运用,却是曲的拿手之处。
《山歌》与《挂枝儿》中众多媟狎冶荡之作,实不必视为生活中真有之事,正如周作人所谓:“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庄端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其实一切情诗的起源都是如此,现在不过只是应用在民歌上罢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