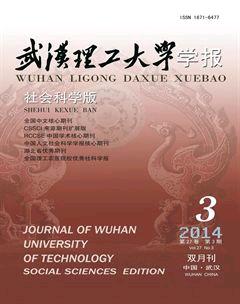情倾中国 执着汉学*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访谈录
2014-03-20周奕珺,包向飞
情倾中国 执着汉学*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访谈录
受访人:沃尔夫冈·顾彬(1945-),男,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系主任
采访整理:周奕珺、包向飞
采访地点: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顾彬教授办公室
采访时间:2014年1月9日下午
周奕珺:顾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一直以来都盼望有个机会,能单独听您谈谈您做学问的历程以及您对于一些文学问题的看法,今天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感到特别荣幸。您在汉学和中国文学这一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40余年,但是听说您最初进入大学选择的专业是神学,为什么后来很快就转向研究文学了呢?
顾彬:不是很快,而是过了两年以后,在转到文学之前我学了一段时间哲学,我的学术出身既包括神学,也包括哲学,直到现在所有的文学问题,我都是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的。刚进大学时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于神学和哲学没有深刻的体验,难以领会其中蕴涵的精髓,所以转而学习文学,最初学的是日耳曼文学,直到有一天读到李白的诗,觉得译文特别棒,所以想学一点古代汉语,看看李白的诗的原文是否也跟译文一样棒,从此开始与中国文学和汉学结缘。
周奕珺:您当时看到李白的诗,觉得译文特别好,是谁翻译的呢?
顾彬:潘德。潘德可以称得上是整个西方第一个真正了解唐诗美学的人,他能深刻体会唐诗的意境,恐怕到现在英语国家也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方面与他相媲美。在我看过的所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英文翻译中,在语言上潘德毫无疑问是最出色的。
周奕珺: 您最初看到的是英文版的唐诗,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把中国的文学翻译成德语吗?
顾彬:不能这么说。德国从18世纪开始,有人翻译中国文学,但是中文水平有限,也没有形成系统,我们最晚在19世纪有翻译的德文《诗经》。
周奕珺:在您研究中国文学之前,据说您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日本学?
顾彬:不敢说日本学,因为当时没有办法来华,只能去别的地方寻找中国的踪迹,对当时的我来说,中国就是唐朝,日本有他们的唐朝时代,所以为了去日本看唐朝的建筑和画,我不得不学日语,当时的日本很少有人能说外语,我1969年夏天在日本呆了三个月都是说日语。确切地说我只是学了日语,并没有研究日本学。
周奕珺: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中国文学结缘开始,至今已经为此辛勤地工作了四十余年,您能否对自己这四十几年的工作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呢?
顾彬:从1969年一直到1974年,我研究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哲学,1974年到1975年在北京学习现代汉语,从此慢慢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回国以后我有机会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比如鲁迅、巴金、茅盾等。80年代或者80年代中旬开始,我开始更多地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期间我自己出版了不少著作,也翻译了不少作品。从95年开始,波恩大学允许我回到中国古典文学,他们说你已经教了二三十年的现代汉语、现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你想上古代汉语课可以开设这门课程,所以从95年到现在,我写的大部分书都跟古代有关系。我还会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史有关的书,但是相对而言少一些,这段时间除了当时所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外,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及哲学这一块。
周奕珺:有人说,您是一个怀古的人,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您更青睐中国古代文学,您是怎么看的。
顾彬:对,虽然当代的文学我也继续翻译介绍,但是我的心在古代,不在当代,不仅是文学,还包括哲学。我从未停止研究中国古代的工作,我翻译介绍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哲学书,现在在德国我正在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一共十本,已经出版了《孟子》《孔子》《庄子》《老子》,目前我正在翻译《大学》《中庸》《孝经》。
周奕珺:您经常批判中国的当代文学,而且有时还会用到非常犀利的言词,对此能否具体谈谈您的观点。
顾彬:首先我也经常批判德国的当代文学,一个学者应该时时持有批判的态度。其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但是人们不想听或者不想思考,我说过中国有世界文学,当代也会有,但是基本上都是诗人写的,因为问我的人他们都不看诗,所以诗歌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他们跟德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一样,觉得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文学就是长篇小说。所以他们应该具体问我,我为什么觉得中国长篇小说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无疑在于话剧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更严重,因为长篇小说是最复杂最难写的,另外如果要写长篇小说,恐怕没有办法跟过去的小说家比,因为他们的水平太高了,谁能够跟托马斯·曼(Thomas Mann)比呢,谁可以跟乔伊斯(James Joyce)比呢?这个我说了很多次了,但是现在没有人会考虑这个。
周奕珺:莫言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您似乎不太欣赏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除了您常说起的语言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顾彬:莫言的问题不在于语言,他有他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我承认。他的问题在于形式,但是评论他小说的形式我很容易说,因为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新的形式。长篇小说我们基本上无法创造出新的形式,莫言的问题在于世界观,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思想,他给我们描述了很多中国的图像和画面,但是读者无法了解到这些画面后面隐藏的根源,以及画面中所隐含的问题如何才能得以改变。通过莫言的小说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很痛苦,但却无从得知他们的痛苦从哪里来以及人们面对这些痛苦时该怎么办。他自己可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回答,但是从他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答案。
周奕珺:您能否再具体谈谈莫言小说的形式问题?
顾彬:莫言以前是先锋作家,但是很快他决定回到过去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完全已经过时了。他偶尔也会加入一些先锋写作的方式,但是给我的感觉却有些做作。
周奕珺:您觉得为什么莫言能够在西方取得成功呢?
顾彬:我不一定觉得莫言在德国非常成功,虽然他的书卖得很好,但是我没有碰到哪个读者对我说,他特别喜欢看莫言的小说。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德国读者,他们为了好奇而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看了。
周奕珺:您经常提到忧郁,认为忧郁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态度,只有一个忧郁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文人、诗人,莫言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您能在莫言的作品中读出忧郁吗?
顾彬:没有,莫言跟忧郁没有什么关系,莫言所探讨的是社会问题,他描写的人感觉完全没有爱,而是心中充满了恨。他描写的人除了主人公以外,都不是忧郁的。
周奕珺:您经常对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进行评判,也时常写各种书的书评,您评价书或者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顾彬:有三个标准:第一是语言水平;第二是形式,因为每一个艺术品每一本书都需要固定的形式,否则我们无法观赏它,好的文学作品形式必须很特别;第三则是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必须跟别人不同,他不应该盲目地重复别人说的话,他应该有自己的立场。
周奕珺:您在选择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西方的时候,是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呢?
顾彬:对,我也会参照这个标准。如果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一本特别喜欢的中文作品,而这本书没有德文译文,又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话,我就会考虑把它翻译介绍给德国人。
周奕珺:您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咋一听上去,感觉您是一个特别狂傲的人。
顾彬:我确实说过这句话,而别人经常误会这句话。首先我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学,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人们都以为在德语国家会有很多人专门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八十年代确实是这样,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再研究和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只是最近才恢复,这可能跟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有关系。实际上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八十年代的状况,八十年代谁学汉学谁就会翻译,或者谁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也会翻译,现在德语国家有不少一流的译者,他们拼命翻译,但是不一定会研究。之前德语国家有三个教授教席,分别位于科隆、波鸿、苏黎世,负责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波恩的任务实际上是介绍中国历史、哲学、古代汉语等,我的任务不在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这只是我的业余工作。科隆原来的那个教授,什么都没有翻译,也没有介绍任何一个作家,也没有写过相关著作,他的继任者公开表明他不会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所以科隆虽然之前有二三十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但现在这个历史已经断了。波鸿以前的那个教授已经离开波鸿,因为他不喜欢波鸿这个城市,临时有人替代他,但是他们的爱好是否在当代,我并不清楚。苏黎世大学有一个教席专门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特别喜欢莫言,写过一本关于莫言和余华的书,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做大量翻译工作。所以说无论是波鸿、科隆和苏黎世,他们都不是系统地研究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周奕珺:在德语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是否要好一些?
顾彬:现在德语国家也没有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德语国家的汉学之前强在专门介绍翻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是我们前一辈的汉学家退出历史舞台后,没有人能够继承他们,现在德语国家连一个专门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教席都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跟我的学生,以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些研究汉学的人一样,放弃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跟他们一样来华赚钱,或者转而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可能大学或许还会有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做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或许没有人能够替代我的工作。我的爱好根本不在当代,而是抱着一种为现当代文学牺牲的精神来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时常翻译,经常请中国作家来德国的话,就没有人来做这个工作了。总是有很多人甚至包括中国人劝我别做这个工作,说是浪费时间,这些破作家连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所以这句话不是我在吹牛,而是反映出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担当,我为此而牺牲我自己。因为我翻译的时候通常不能同时写作,我是一个作家,我写诗同时还写小说和散文,已经发表和出版了12本书,我需要很多时间来写作,但是我却从中抽出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来献给中国当代文学。我从来不会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牺牲我自己,因为那是我的兴趣和爱好所在。
周奕珺:在您看来,德语国家有哪些您所认同的汉学家呢,包括老一辈和现在的?
顾彬:上一辈有三个我非常尊敬的汉学家,第一个是劳尔夫·特老策特尔(Rolf Trauzettel), 他是思想最深的汉学家,第二个是隆格·特拉福马(Runge Traphma), 他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方面非常有见地,第三个是君特·德·波恩(Günther De Bonn),他是世界上除了韩国日本以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得最好的,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因为他自己也写诗,熟谙歌德的诗歌,所以他可以把唐诗翻译成真正的德语诗歌,他翻译的诗实在是太棒了、太好了。然后就是我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霍夫曼(Alfred Hoffmann),很可惜,他很少写作,但是他上课上的特别好。他四十年代到过中国,是胡适的朋友,向中国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学习过,回国后在波鸿大学上过课,主要教授唐朝的诗歌,宋代的词,周朝的孔子、孟子,讲课的时候讲的特别深,很可惜他出版的书不多。我继承了他的思想以及分析诗歌的方法,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完全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写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在学术上是他的“儿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由我完成了,我将他的观点全然呈现在读者面前。如今这一批人都是老一辈了。年轻学者或译者中,有不少人德文水平非常非常高,但是他们不一定在国际上很出名,或许因为他们比较谦虚或许因为别人觉得他们只是译者,一个是马克·海摩尔(Mark Hemmer),他是我的学生,现在大约四十多岁,可以说汉学界他的德文是最好的,因为他以前不是汉学家,而是日耳曼文学家,有一天他从上海来找我说要跟我读博士,我说你没有学过汉学,先跟我学汉语吧。他跟我学了十年并做我的助手,因为他的德文水平很好,所以我时常请他帮我校正我的翻译,这一类年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现在还没有退休的汉学家大部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感兴趣,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研究政治和经济,有一部分人研究汉朝,不知道为什么汉朝在德国汉学界非常火,对此我觉得非常奇怪。也有不少人,他们专门写中国古代哲学的书,反正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应该承认他们的成绩,比如海勒儿·劳茨(Heiler Rotz),沃尔夫冈·波恩(Wolfgang Bonn)等。
周奕珺:您刚才提到很多人最初研究中国文学,有些人后来不再进行相关的研究,另外一些人转而研究政治经济,而您却一直坚守在文学领域,最终成为知名的汉学家。用中国的俗话说,您如今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您还打算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吗?
顾彬:首先我自己肯定不会跟这些人一样,我一辈子都会从事翻译研究工作,我不可能退休后什么都不做。有不少人特别是中国人对我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你还写书吗?我们都不写了,我们玩去,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去吧,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想完成的任务。
周奕珺:请问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未来几年的规划是什么?
顾彬:现在最首要的是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丛书》,一共十本,然后再打算出《中国古典诗歌史丛书》,也是十本,还想写一本关于李白的书,如果我还有精力的话,我会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除此之外我当然几乎每天都会翻译当代诗歌、当代散文,我不会翻译小说,原因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靠这个过日子,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何况他们的翻译本身也很不错。
周奕珺:您总强调写作要慢慢写,而且时常举例说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写一页,还经常回过头去修改。但是如今这个社会节奏特别快……
顾彬:我讨厌这样一个社会,我不为这个社会写作。
周奕珺:您或许已经退休,这个社会对您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众多年轻的作家而言,这个社会的快节奏却无形中会影响他们,给他们带来压力,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他们应该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写作吗?
顾彬:他们不能迎合这个社会,不是说这个社会要求他们快点写就快点写,他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因为这一类读者非常残酷,你写的快我读的也快,读完很快就扔掉了。所以写作不是为了当代而写,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也不是为了出名而写,而应该为了永恒而写。如果一两百年后我们还会有读者的话,我们最初的坚持才是对的。
周奕珺: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写作的时候不应过多关注现在的读者想读什么样的书?
顾彬:根本不要为了大众而写,特别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和希望而写,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明天他们就把你忘掉了。或许你今天赚了好多钱,但是明天这个钱能够满足你的欲望吗?
周奕珺:那您觉得写作的时候,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顾彬:语言、形式、观点、世界观以及社会的发展、人性的问题。
周奕珺:现在普通的德国大众读中国文学作品吗?都读谁的作品呢?
顾彬:现在德国百分之四十的人都是大学生,所以德国的读者有一定的水平,莫言和余华的读者通常是一般的读者,但是通常都上过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的读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或文人,他们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周奕珺:在德国哪些中国的文学作品卖得比较好呢?
顾彬:莫言、余华,还有你们所说的美女作家,还有毕飞宇,还有格非。基本上中国最有名的小说,都有德文的版本。书评不一定会有,读者不一定会特别喜欢,但是他们会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好奇,二是为了消遣娱乐。
周奕珺:您在各种演讲中以及在上课时经常提到忧郁,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您,也感觉您浑身散发着一种忧郁的气息,您自己认同吗?
顾彬:(微笑点头)是的。
周奕珺:在所有的汉学家中,您在中国的互联网和媒体上名气非常大。因为您对于中国文学以及某些问题的犀利的言词,曾经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让人觉得您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而日常工作与您接触时,却感觉您是一个特别谦逊的人。比如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网络上时常引用您的这句话: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顾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人们总是误解我,他们完全不看我说有些话的背景是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自傲,我希望自己给人谦逊的印象。但是一个学者如果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应该公开表明出来,即使受到批判也无所谓。
周奕珺: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学德语的,在学习德语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不知不觉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受到德国文化、德国人的影响,那您研究中国文学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感觉到您的性格、做学问和为人处世方式也受到中国人的一些影响?
顾彬:当然。比如鲁迅就影响了我的性格,文人和学者应该敢说。我用中文和德文写散文,都向苏东坡学习,写诗的时候我时常向李白学习。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有所变化,一般德国人比较绝对,如果你不赞同我那就是反对我,如果我不赞同你我就反对你,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对,以前我也这样,但最终发现都未能取得好的结果。所以比如最近刘再复写攻击我的文章,如果放在以前我会写很犀利的文字来反驳攻击,但是现在我不仅什么都没写,反而到处都会说他的好话。我尊重他,对于八十年代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太好,希望他恢复。我上次在云南昆明参观了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我忘了,是东亚归来的华侨建的,村子里有不少格言警句写得非常好,比如“不要歌颂自己”,“不要说别人的坏话”,“退一步海阔天空”等。
周奕珺: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采访及整理人简介:周奕珺(1982-),女,湖南省衡阳市人,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的研究;包向飞(1974-),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支持,系“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项目成果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