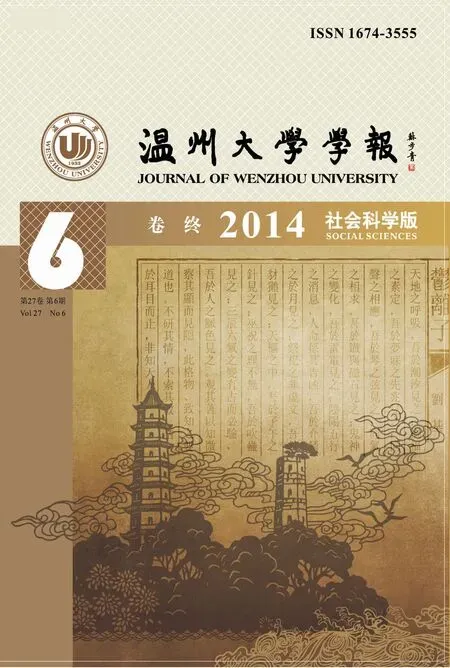“痛感”认知的开掘与审思
——鲁迅小说的创伤美学分析
2014-03-20吴翔宇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痛感”认知的开掘与审思
——鲁迅小说的创伤美学分析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鲁迅将国人的痛感认知理解为“人”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记。鲁迅笔下的人物用遗忘的方式消解现实困境,使得他们回避了基于痛感而衍生的反抗行为。面对着国民精神虚空的精神状态,鲁迅冷静地剖析了这种奴性人物的思维形态,建构了独特的批判视野,并将之纳入其思想改造的价值体系之中。
鲁迅小说;创痛话语;遗忘认知;精神死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痛苦灵魂”的鲁迅,其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是从“苦痛”的现代体验开始的。他认为,知识分子“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身心方面总是苦痛的”[1]。正是这种敏锐的感受苦痛的现代意识,使鲁迅对于自身社会角色和社会担当有着清醒的定位,能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获致反抗的持续动力。然而,当鲁迅将这种苦痛体验投射于国民时,他惊异地发现:国人对于痛感的认知存在着混杂和矛盾的现象。鲁迅将这种现象揭示出来,并希冀通过文化批判达到警醒国人的目的,这种努力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良知,也呈示了其现代思想的核心要义。
一、缺失痛感记忆的精神表征
鲁迅发现,国人对于自己的苦痛有着独特的消解渠道,“遗忘”就是其中最好的疗伤手段,“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2]58-59,而“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3]。鲁迅的这种认知均基于他对现实的深刻审思:当“五四”退潮,《新生》杂志的流产,鲁迅如立于荒原中“呐喊”却无人回应时,他采用了“麻醉自己的灵魂”的方式(如钞古碑)来消除这种痛苦的处境,遗忘“年青时候曾经做过的许多梦”。他意识到,一味地忘却会忽略和取消现实的反抗,也就是他所说的“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4],而这又是鲁迅不愿看到的。在其小说中,他深刻地揭示了国人不敢正视现实苦难的文化心理。具体而论,这种遗忘心理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当前痛感的忘却。在“铁屋子”这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鲁迅笔下诸多人物时刻有“被吃”的可能,他们的挣扎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人生的清醒认知。鲁迅发现,国人似乎有消解现实的困境和痛苦的先天能力,能使其迅速逃离现实的时间境域。阿Q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①参见: 鲁迅. 阿Q正传[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以下所引相关内容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这是一种典型的摆“祖先阔”,由于陶醉于对过去祖先的崇拜,阿Q才援引过去的家族来缓解现实的困窘。在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之后,阿Q“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正因为阿Q认为自己的辈分比中了秀才的赵太爷的儿子高,所以觉得自己也分享到了某种权力,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理,在阿Q看来,嘲弄和辱骂别人的祖先是极不道德的,当然也就具有很强大的话语力度。因此,当他遭到别人的侮辱和欺负的时候,辱骂别人的祖先是痛快地发泄内心愤恨的复仇手段,“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打老子”即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另一方面阿Q又将自己的时间思维投射到廉价乐观的未来中:他会用“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他离场的最后一句话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通过逃避到“过去”和“将来”的时间中,“现在”时间的焦虑和主体的反抗意识就自然隐退了。《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失去自己的宝儿时,其唯一的慰藉是希望借助“明天”的梦来和自己的宝儿相见,“现在”时间的苦痛为将来(“明天”)的梦幻期待所替代。显然,她这种将来(“明天”)的预设是没有意义的,文本结尾隐喻了这一点: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②参见: 鲁迅. 明天[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以下所引相关内容均出于此,不再一一作注.。总之,这些人的时间意识逃离了他们所处的当下语境,“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条所谓的“正路”上行走,结果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5]。
同样面对当下的困境,知识分子又何为呢?我们发现他们也未能免俗:在《端午节》中,鲁迅刻画了一个逃避到所谓象征精神自由的书本中,借此来忘却现实痛苦的人——方玄绰,他在现实世界的不公和生存压力下变得平庸圆滑,用“差不多”和“都一样”表达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失望与逃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纪的人”[6]。小说描写了他四次拿起《尝试集》来看的情形,这隐喻他在现实的挤压下,无选择也无作为,只是逃到无力解决现实生存困境的、象征知识分子精神解放的《尝试集》里,借以忘却现实和幻想解脱与自由。《伤逝》中涓生在痛定之后,在还不知道怎样跨出新的第一步时,他想用“遗忘”来作为自己开始新的生路的心理意识:“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7]133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这里的“遗忘”既表达了想忘掉过去那段痛苦的经历和虚空的记忆来面对新的人生,又体现了他在准备开始新的人生道路时无助和矛盾的精神状态。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遗忘。有感于“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鲁迅于1926年4月1日写了一篇《记念刘和珍君》的杂文,他不无感慨地说:“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8]。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写的杂文《空谈》中提到一件事,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四烈士坟中至今还有三块墓碑不刻一字,他悲愤地写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9]鲁迅觉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命运也和四烈士相似,他推想到黄花冈烈士的牺牲在民众心中引起的情感反应:“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10]1926年,从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厦门大学风景不坏,鲁迅却打不起精神来,而吸引他的是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道城墙,据说它是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建造的。但痛心的是:“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11]1933年,鲁迅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出发点是因为“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所以希望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左联五烈士”,等等。
从鲁迅在《药》中为夏瑜坟墓旁设计的萧条、冷清的气氛可以看出:“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夏瑜被人杀掉,血成了别人的药引,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在他的坟墓旁陪伴的只有缩着头的乌鸦,最后这只乌鸦也离它而去:“只见那只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12]前来上坟的人很少,即使鲁迅给坟顶上添加了一个红白相间的花圈,也遮盖不住夏瑜这位先驱者死后的孤独落寞。《风波》所揭示的是:辛亥革命只是剪掉了一根辫子,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临河土场没有留下记忆印记,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①参见: 鲁迅. 风波[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从临河土场的人们最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常态”可以看出,革命的记忆很快被人们淡忘了,也可以说时间并没有记录和保存这段历史。类似的事件在《长明灯》中同样在上演,当“疯子”被规训后,长明灯依然在社庙里亮着,人们似乎忘记了先前发生的一切:“未到黄昏时分,天下已经泰平,或者竟是全都忘记了,人们脸上不特已不紧张,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13]慢慢地社庙里的人迹越来越少,只有孩子在那里游戏和猜谜,“疯子”的行为和意义在所谓和谐和静穆的环境中淡忘。
二、创痛认知的含混与矛盾
遗忘意味着人对于过去记忆的缺失,由于遗忘,人既可以消解过去的痛感,也有可能中断过去的精神美德,这是遗忘行为所蕴含的必然结果。比照吕纬甫、魏连殳、子君等人现在和过去的精神状态,我们发现他们都遗忘和放弃了过去的先锋品质,走了一条自我否定的人生道路。吕纬甫忘记了过去和“我”一起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和拔掉神像胡子时的进取精神,在生活重压下,自动“缴械”。而过去那些温情回忆和美好品德在他心中也未留几分:“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14]魏连殳忘记和否定了过去特有的那份清高和道德标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15],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代替了过去“独异”的傲气和孤独清高的正气,最终使其走向从内向外妥协的悲剧道路。子君在过去是追求自由的进步女性,如她反抗父母和胞叔的包办婚姻,“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7]115但当生活堕入庸常后,变成一个耽于家务的家庭妇女,“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伺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涓生对子君的这种变化是有反思的,他经常说到自己“未忘却翅子的扇动”,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于,除了批判国民思想中存在的“遗忘”根性外,他还挖掘出他们思维意识中“遗忘”和“记忆”并存的矛盾状态,即对过去既有惯常的记忆又有刻意的遗忘。在鲁迅的思维中,一方面,中国人对过去是有很美好的记忆的,几千年历史习惯的惰力使国民难以摆脱与过去的精神联系,“复古”、“守成”的风气和思想盛行,现在人的身上持存太多过去的记忆。《风波》中的九斤老太念念不忘的是“一代不如一代”,赵七爷则云“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过去强烈的“记忆”而造成的悲剧,祭祀祖先是件威严而神圣的大事,由于祥林嫂的“败坏风俗”、“不干不净”,她做的饭菜“祖宗是不吃的”,四婶于是劝阻说:“你放着罢,祥林嫂!”[16]这给祥林嫂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然而,她通过捐门槛而获得的精神解脱,却并没有得到参加祭祀的权利,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将其推向精神崩溃的境地。因此,对祖先的崇拜、对过去某种风俗人情的强烈心理暗示和记忆合谋,将祥林嫂送上了绝路。另一方面,国民中又有“健忘”的根性,“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17]。“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18]读鲁迅的小说,经常能发现“记忆”和“遗忘”在同一主体身上并存的现象。这在文化反抗者和奴性人物身上都有体现,我们分别以狂人和阿Q为例来分析。
无疑,狂人对过去是有记忆认知的,他认识到“吃人”的历史没有年代,道出了古今一贯的“无时间”流动的社会本质,国民持存着“从来如此便对”的记忆。由此,既然古代有吃人的习俗,那么现在也可以吃人。从受害者间(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与“我”)的吃人到熟人间(狼子村与大恶人,大哥、赵贵翁、何先生、相貌不很看得清楚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与“我”)的吃人,从陌生人间(一路上的人与“我”)的吃人到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街上女人与她的儿子,母亲、大哥、“我”与妹妹)的吃人,无不表明:从过去到现在,“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并没有变。在这种时间惯性中,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流徙似乎凝固了,时序、时距被悬置,叙事时间的重复力也大大强化了。“狂人”在发病的时候是一个“文化反抗者”,与鲁迅早年倡导的“指归在行动,立意在反抗”和“摩罗之气”一脉相承,他道破了历史吃人的勾当。“狂人”身上洋溢着一种超越常人的理智和认知,而不是非理性,它不过是理性偏离了社会的常规思维方式,伸展到一种过于强烈的光照的中心里去了。但等他康复以后,就忘却了过去所坚持的文化立场和精神斗志,“赴某地候补”去了,这也意味着去做他以前所憎恨和反对的一切。狂人经历了从“记忆”到“遗忘”的心理过程,这是他现代意识退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与狂人相似的是,阿Q也是一个记忆矛盾的人,当他经历了屈辱后,“‘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就发生了效力”,用自轻自贱、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方式转移和忘却自己的窘境,如他以将自己比作虫豸、打自己两个嘴巴等方式来补偿和转嫁自己的痛苦,于是“他立刻转败为胜”,大笑而归。欺辱小尼姑后,他“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一切‘晦气’都报了仇”。小说中也特意描写了几次阿Q心满意足的得胜“睡着了”的情景,他的安然入睡,是没有梦魇出现的,也是隔绝记忆对当下主体的纠缠和折磨的一种好的消解方式。同时,阿Q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却有很深的文化记忆,他经常挂在嘴里的一句话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他会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来满足自己的情欲,虽没读过什么书,但传统等级观念在他心中也是根深蒂固。他的道德取向多有对古代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认同,如“男女之大防”,女人误国等等。当他被抓进了衙门,虽然革命之后已经不兴磕头,但他一到大堂,知道堂上坐着的都是一些有来历的人物,自然会想起“上尊下卑”,于是,“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可以说,阿Q内心并存的这种“记忆”和“遗忘”,体现了他时间意识的矛盾性和分裂性,主体无力也不会有意识地去平复两者的矛盾,在具体的语境中,阿Q只从于己最有利的角度出发,来记忆或遗忘。
在鲁迅小说中,将“遗忘”和“记忆”相互作用与纠葛书写得最深刻的小说是《头发的故事》。小说反映了N先生在“双十节”这一特定的日子里的精神状态与感悟,人们在“双十节”这一本该纪念的日子里却忘了纪念,从开篇的日历忘了纪念就有隐喻。说到“纪念”,N先生觉得很愧疚,使他“坐立不稳”了。那些为革命奔走甚至牺牲的故人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但记忆也有“不堪”的精神负担,N先生认为牢记理想家的所谓的“觉醒”和“解放”,只会徒增痛苦,他愤激地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因此,他认为:“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鲁迅一直认为不要随便预约和牢记“黄金世界”,否则代价是“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地腐烂的尸骸。”[2]167为了缓解这种记忆的痛苦,N先生想通过说些“得意的事”来摆脱这种痛苦,他围绕“辫子”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经历,从剪辫之举到无辫之灾,从装上假辫子到废了假辫子。然而辫子问题始终让他痛苦不堪,无奈N先生还是欲忘却而不能,最后,他才违心地劝阻学生剪辫子。N先生在“遗忘”和“记忆”的双重痛苦下,陷入绝望的境地,感受到“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的罪犯般的痛苦。可见,由不堪记忆的痛苦到希望遗忘是能暂缓痛苦,而这种遗忘却潜在地加深和加长了痛苦的强度。
从上可知,有“遗忘”根性的国民同时也保有对过去记忆的深深体认,而单纯靠遗忘来摆脱痛苦记忆却在现实中成为空想。如果没有自觉的主体意识来选择和调整记忆认知,那么人只能成为被群体意识奴化的人,个人意识永难彰显。造成上述三种遗忘情形和记忆认知不自觉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方面来源于过去习惯性的文化记忆在全社会种植,是集体人的文化记忆。“鲁镇”(或者是“未庄”、“临河土场”、“吉兆胡同”、“吉光屯”等)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风俗人情、思维习惯,这些都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具有社会性,是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心态;还具有继承性和朴素性:它既蕴涵悠久的时间积淀,是当地人世代的生存方式的淤积,又是一种近乎日常的朴素社会意识,在当地人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中反映这种意识。正如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9]这种集体记忆形成强大的思维定势,剥夺了主体修改和涂抹自己以往记忆的认知自觉,要超越意味着背叛,而这种背叛所滋生的心灵重负势必会动摇主体的行动和思维意识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是国民不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缺乏自觉的记忆认知系统。在面对现实的窘境时,他们不能调节和整合自己的时间意识,导致对过去和现在两种时间进行取舍和判断时,他们的意识中会出现思维混乱、心理悖论和分裂的现象。主体的情绪、想象、体悟和话语在这种矛盾的张力场中受到极大的分裂重压,在具体的实现语境中,记忆和主体的行动之间只能产生实用性、本能性的关联,人只能不加选择地、盲目地去适应过去记忆的规范和不自觉地遗忘过去的某些困境,在没有怀疑和否定的永恒常态中艰难地获取自我的生存保障,确立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人生选择。
三、痛感的发掘与启蒙的话语实践
在鲁迅的小说中,鲁迅并非一味展示国民被吃或虐杀的事实,而是将重心放在对人精神死亡的揭露和剖析上。在鲁迅看来,这些人是没有痛感认知的,尽管肉体存活着,但其精神早已死亡。
从精神死亡中体验虚无的程度来看,小说《示众》无疑揭露得最为深切。可以说,《示众》并未关涉“死亡”,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写的“幻灯片事件”的再现和引申。看客们热衷的是热闹的场面,正是通过将现实的示众转换成“戏”,他们不仅获得置身事外的安全感,同时也使自己能够保持心理平衡:“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20]在“看”的空间位置的动态移动和时间流动中,“看客”根本不明白自己为看的对象是谁?看的目的是什么?看的意义何在?基于一种毫无目的行为集体地加入这场“示众的盛举”。当一个工人似的粗人低声下气地请教秃头老头子:“他,犯了什么事啦?……”时,秃头老头子、粗人及旁人的举动透露出“看”背后的本体精神虚无:“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由此,“看”本身的意义被抽空,在看客群体(由胖男孩、秃头、胖大汉、小学生、长子、老妈子等组成)的冷漠无情、于己无关的“看”中,鲁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精神世界虚无几近死亡的“意识圈”。“看”的意向行为成了叙述者在其中体验精神虚无、生存荒诞的“闹剧”。
对于别人的死,旁人要么集体性地来“帮忙”(《明天》)、“观瞻”(《孤独者》、《在酒楼上》);要么表现出厌恶、反感、冷漠等情绪(《药》、《祝福》、《阿Q正传》)。宝儿死后,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盖上”,冷酷无情的王九妈“等的不耐烦,气愤愤地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可见,旁人对于单四嫂子及宝儿的死显得很冷漠,缺乏必要的同情和理解。当阿Q被游街、示众、上法场时,两旁到处是张着嘴的看客的喝彩声,吴妈麻木而出神地看着士兵们背上的洋炮,对阿Q置若罔闻,同时人群中也发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的议论,国民人性中最残忍的冷漠和无情的精神图景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最可悲的是,阿Q根本意识不到是非善恶,死到临头想到的居然是:“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看客们则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看者”与“被看者”都丧失了现实的是非曲直,国民中的精神虚无被表露无遗。当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讲述阿毛遇害的故事时,围观的人“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她的述说并没有得到同情,只能成为旁观者无聊的谈资。
应该意识到的是,当存活的个体与死亡相遇时,对生和死所引发的时间终极思考就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21]。“死”与“生”既是时间段中的两极,同时又对立统一、密不可分:探讨死亡问题虽名为谈死,实则论生,或毋宁说它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延续和扩展。这其中明显地渗透了现世的生命关怀,同时不放弃对现世人终极意识的叩问。因而“知死”实为“知生”,由生与死生成的文化意义及生死之间的转化关联是时间意识重要的哲学内涵。鲁迅小说的时间意识绝不是简单的悲剧人生体验,而是在“死”的“临界处境”中反观“生”的存在与意义。关于“临界处境”,雅斯贝尔斯认为,它是人面对痛苦、绝境和死亡时的一种意识状况,是必然的、最后的和绝对的状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的存在处境才使人们有体己的震惊,因为“在我们的实存的边缘上被感受到、被体验到、被思维了的处境,把实存的内在矛盾、二律背反统统展现出来了”[22]。可以说,这种“临界处境”就是时间重要的中介点,处于这一关节点上的主体面临着重大的生命转折,其思维意识在这一特殊瞬间、场景中被释放和播撒。
在鲁迅的小说中,当那些下层庸众面对“死”之将至时,也不免对“生”有本能的感触和发现。阿Q临刑前,最初的反应是死的不可避免:“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临死前对自己“出风头”的自鸣得意以及其无师自通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是他先前充当过“看客”的心理佐证。同时,“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他在“死”的突然惊觉中产生了本能恐惧。一句底气不足的“救命”,道出了他的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其屡试不爽的“精神胜利法”在死亡的临界点也发挥不了作用了。祥林嫂的“死”是她在“生”中逐步绝望、怀疑最终驱成的。她对“我”的“临终询问”表明了她对“生”的虚无的极大怀疑,从不愿意改嫁到丧夫失子,最残酷的是“想做奴隶”而被别人剥夺了,耗尽自己尽一年的工钱捐了门槛,然而仍然没能改变她绝望的命运,鲁四太太依旧不让她摆放祭品。所以当她的“临终疑问”在“我”这里得不到答案时,等待她的就只有死的结果。陈士成最终溺水而亡同样来源于生的绝望,连续十六次考不中秀才的他陷入了无穷尽的失望和虚无的精神状态中,小说并没有写他死亡的具体过程,而是放大了其临终前的精神状态和对残酷人生的感悟,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眼前飞舞的杂乱异样的阵图、回荡在他耳边的“这回又完了”冲击着他的神经,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这种虚无的“临界处境”始终蚕食着陈士成,模糊了生的意义,也失去了人生的航向和选择,“生”的反抗和抉择被“死”的解脱所搁置,“死”成为其摆脱绝望处境的唯一手段。
福柯认为:“在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在死亡缓慢和半隐半现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变成了某种个体性生命。”[23]即是说,主体在逼近自己死亡之际,能对生有相对深刻的思考。然而,这种死亡临界点上“生”的发现对于庸众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最多不过是本能的反应或是加快其死亡到来的心理要素罢了。同时,作为见证他人“死亡”的当事人(或旁人)也没能产生“生”的主体思考。对于“夏瑜缘何而死”、“死的意义在哪”等问题,夏四奶奶完全不知情,当然我们也很难苛求她能彻悟到儿子的死亡之于生的意义,毕竟她的思想意识难以达到这种境界。让人痛心的是:在上坟的时候,她依然迷信地希望乌鸦飞上坟头来证明儿子是屈死的;孔乙己的死,留给周围人的感受是“还欠十九个钱呢”;阿Q的死只是让旁观的人留有“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的印象;宝儿的死除了给单四嫂子在梦中留有念想外,至于说到死亡的感悟和意义她一无所知,“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他能想出什么呢?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祥林嫂的死对于那些麻木的旁人来说毫无意义,旁人也不可能推己及人地将祥林嫂的命运与自己联系起来,置身事外的于己无干的想法是旁人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她宛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里,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惊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如果说“下层庸众”是被社会现实无情地重压而精神死亡的,那么“文化反抗者”的“死”却多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鲁迅让生性充满叛逆和“狂妄”特质的文化反抗者最终走向死亡或幻灭的道路,体现了他对生死转换的理性沉思。他们的“狂”既源自世俗的偏见(传统将其视为“狂人”),同时又是现实逼迫的结果。他们的“死”带给我们更多拷问现实、反观“生”的启示,这其中以魏连殳的死最为典型。在魏连殳死前给“我”写的那封长信里,意味深长又发人深省地道出了他对生的感悟和认知。这封信可以看作他在死亡“临界点”的自我否定,其中渗透出主体深深的“负疚感”。尼采认为,负疚的产生来源于人的自由无法向外发泄,只好转向内部,是人的内向化:“由于有了这种内向化,在人的身上才生长出了后来称之为人的灵魂的那种东西”[24]。魏连殳的这种内向化的反省是对生的压抑的释放,当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时,将仇恨、破坏、残害对准自己。他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反抗者,最终却选择给军阀做参谋,最终他用一种“自戕”的方式复仇这个世界,借以毁灭包括旧我在内的黑暗人间。在文本的最后,“我”听到魏连殳的“死”,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如果说魏连殳的“生”让“我”认识到什么是虽生犹死,那么他的“死”反而让“我”意识到了获得解脱和新生的愉悦。他的死让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他的死亡既是他反抗社会的一种方式,也是我获得理性认知开启自我人生道路的感悟。
通过展示国民精神死亡的现象,鲁迅洞悉了病态社会中群体的虚无本质,他们的肉体虽然存活,精神却已经死亡。在虚无心理和本质的支配下,他们的痛感意识也都终结了,其反抗的可能被抽空。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现实的痛感能催生人抗争的“意力”,在与“黑暗”与“虚无”实力的“捣乱”中,彰显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这既是鲁迅“立人”工程的逻辑起点,也是鲁迅“反抗绝望”哲学的思想催化剂。
[1] 鲁迅. 关于知识阶级[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27.
[2]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C]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 鲁迅. 导师[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9.
[4] 鲁迅. 《呐喊》自序[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40.
[5] 鲁迅. 论睁了眼看[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54.
[6] 鲁迅. 端午节[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61.
[7] 鲁迅. 伤逝[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 鲁迅. 记念刘和珍君[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3.
[9] 鲁迅. 空谈[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8.
[10] 鲁迅. 黄花节的杂感[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27.
[11] 鲁迅. 厦门通信[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87-388.
[12] 鲁迅. 药[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72.
[13] 鲁迅. 长明灯[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8.
[14] 鲁迅. 在酒楼上[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1.
[15] 鲁迅. 孤独者[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03.
[16] 鲁迅. 祝福[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
[17] 鲁迅. 老调子已经唱完[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22.
[18] 鲁迅. 十四年的“读经”[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38.
[19] 露丝·本尼迪克. 文化模式[M]. 何锡章, 黄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2.
[20] 鲁迅. 随感录·六十五[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84.
[2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315.
[22] 雅斯贝尔斯. 当代的精神处境[M]. 黄藿,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175.
[23]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M]. 刘北成,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93.
[24] 尼采. 道德的谱系[M]. 周红,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63.
Digging and Reflection of “Pain” Cognition——Analysis of Trauma Esthetics in Lu Xun’s Novels
WU Xiang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1004)
Lu Xun regards Chinese people’s pain cognition as an important mark of the awakening of“huma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 resolve the realistic plight through oblivion which enables them to avoid the resistance behavior caused by the sense of pain. Facing people’s spiritual vanity, Lu Xun calmly analyzed the thinking modality of the servile characters, constructed a unique vision of criticism and brought it into his value system of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Lu Xun’s Novels; Trauma Discourse; Oblivion Cognition; Spiritual Death
I206.6
A
1674-3555(2014)06-0009-09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6.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4-03-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62)
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