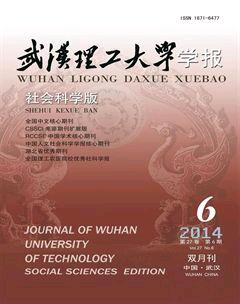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再认识——重读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论断
2014-03-19岳磊
摘要: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其中十分关键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家庭社会学发展的推动.费孝通对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进行了敏锐的观察思考和讨论,指出了中国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提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呈现出“反馈模式”,还认为中国家庭受到了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较大影响.而费孝通的微型社区研究方法、比较方法及注重传统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 i.ssn.1671-6477.2014.06.014
收稿日期:2014-06-12
作者简介:岳 磊(1983—),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
费孝通是我国社会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文革后他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费孝通有着丰富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经历,同时又受教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通过«江村经济»等著作,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盛誉.费孝通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尤以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小城镇建设研究影响巨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恢复工程,重建学科和研究体系.其中就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来讲,费孝通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在重建社会学人类学的过程中,费孝通也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在中断20多年的研究之后,费孝通重新开始对中国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并结合他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对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且出彩的论断,其中就包括关于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等家庭社会学问题.本文将着重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论述入手,探索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并就费孝通研究家庭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
费孝通在文革之后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之时,陆续发表了多篇对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文章和言论,其中非常重要的有三篇,分别是«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①.这三篇文章(以下简称“家庭结构三论”)逐渐深入讨论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别是从对江村的追踪调查中,更是从一个时间序列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费孝通还在多种场合就文革之后中国家庭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发表了言论,对于早期恢复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并促使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展开家庭社会学研究,影响颇大.
一、家庭社会学的恢复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这本书展示了当时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高水平状态.此后,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文章及专著不断涌现.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社会学学科也不例外,并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在中国开始恢复重建,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也在中国逐步得到恢复.与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之同时,家庭社会学也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成立家庭社会学研究机构、出版家庭社会学研究专集并展开多地城乡家庭调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5大城市的4000余户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即有名的“五城市家庭研究” [1].这项研究在家庭社会学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就基本确定了“从经验研究入手这个方向” [2],同时社会学界抓住机会学习了国外能够学到的方法和理论,锻炼了一大批研究人员.而正是这批早期的研究者,在此后家庭社会学逐渐走向正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2年,费孝通接受记者访问时,对中国当时的家庭结构就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国家庭大体可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由鳏寡孤独构成的不完全家庭;二是由夫妻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三是加进一个老人或一些亲戚的扩大家庭;四是由两代夫妻(父、母、儿子、儿媳或者女儿、女婿)以上组成的大家庭.现在是大家庭多了呢还是小家庭多了呢?结论是小家庭在增长.” [3]此时,费孝通关于家庭结构的论断,还处于一个大致判断的时期,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经过革命年代的冲击,中国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由于研究人员的断层,对这个变化的研究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未得到有效展开 ②.费孝通、雷洁琼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这个问题及其研究价值,并促使当时的研究人员关注家庭结构的变动.自此,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家庭社会学也逐渐成为社会学领域中十分热门的一个分支.
二、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
改革开放不久,在经历了许多运动与建设后,家庭结构必然发生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不同于费孝通当年写«生育制度»时的情况.因此,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家庭,在新的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而费孝通等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必须重新开始.
在“一论”中,费孝通从江村的情况入手,介绍了他最新的调查资料,并着手对家庭结构变动进行探讨.他首先阐述了“家”的观念以及中西对家的不同看法,然后对家庭进行了分类探讨.这个分类开始并非十分完善.1986年根据最新的调查资料,费孝通在“三论”中对家庭结构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其主要确定为“核心家庭”、“残缺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四类,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讨论.从“一论”中看,费孝通对江村的资料只是一种质的处理,大体上对家庭的结构作了分类和探讨;同时,费孝通还选择了一个街道作调查以观察城市的家庭结构的变动,并指出“城市正在发生偏离父系和从父居的传统体系,而出现女儿结婚后与父母同居,形成实质上属于女系性质的扩大家庭” [4].在“一论”中,费孝通着重论述了“核心家庭”这一家庭结构形态的变化.费孝通在这里初步地作了城市和乡村家庭结构的比较,正是这一点对于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因为城乡差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越来越大,这导致了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乡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凸显出来.
“二论”的发表是在“现代化与中国”研讨会上,费孝通着重从老年人赡养问题开始来论述中国家庭结构的不同与变动.而这一次的研究,直接来源于费孝通在上一文章中谈论家庭结构变动后又到江村进行的调查情况.在“二论”中,费孝通对中西家庭代际模式进行了简明的比较:“如果我们承认中西文化中确是存在着这种差别,我们是否可以用下列公式来予以表示:西方的公式是F1->F2->F3->F4.而中国的公式是F1<=>F2<=>F3<=>F4(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在西方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简称‘接力模式’.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对父母赡养这一种义务.” [5]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和西方在抚育和赡养问题上的区别:一个是“接力模式”,一个是“反馈模式”.并由此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进一步追究为何中西存在这样的差别?费孝通在这里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给出了提示,即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可靠的依据.
“二论”中,通过对中国家庭中子女对父母赡养问题的进一步阐述,费孝通接着便论述了引起家庭结构变动的一些较为关键的原因:工分制的影响;房屋关系带来的冲击;亲子关系的变化;婆媳关系的影响等等.这些看似具体的原因,其背后都有着时代的烙印.在经历了集体经济后,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集体经济时代,“工分”使得家庭成员的劳动得到了计算,即实现了劳动的“计算化”,这让青年劳动力能最好地展示出自己的优势,导致原先大家庭中不分你我共同劳动、财务由家长掌控的形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年轻人逐渐有了自己的支配空间,这个空间的不断扩展进而影响了家庭中的关系格局,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可能出现兄弟分家问题.在过去,房屋紧张则是兄弟同住、约束家庭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房屋较少而不能分开,这样联合家庭就可能继续存在.联合家庭在革命前是中国家庭中十分广泛的结构形式.
但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革命的介入,传统的伦理价值也遭到巨大的冲击,即便在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较多的传统价值观念,但新变化仍然影响了亲子关系.空间的变化、观念的转变,都导致家庭内部关系发生变化,集中表现为亲子关系的变化,而亲子关系的变化则会促成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动.如我们常听到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对家庭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内在的影响.虽然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但因为传统价值观念的强力约束,因而并未对家庭结构的变动产生太大的冲击.但经历了革命的冲击,已有价值观念在革命中被作为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遗留物而饱受批判,最终大部分瓦解或者被冲淡.
费孝通在“二论”中还讨论了“法”对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并结合前面提到的“反馈模式”,费孝通指出:“由于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反馈模式可以说是中国亲子关系的特点.作为一个伦理的规范,至今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它是当前的立法原则,而且写入了«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如果以这个反馈模式为基础,加上父系的亲属体系,可以推论出父母和已婚的儿子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是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形式.但事实上在农村,以江村的具体例子来说,不仅当前,而且过去,大家庭并不是占多数的家庭形式.农村里过去不仅是以扩大了的家庭为多数,而且已有大量的小家庭.小家庭在解放后已成为多数,虽则从60年代后期起比重有所下降.这说明反馈模式的亲子关系是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中体现的.家庭结构在不改变这一模式的条件下,还可以有不同的类型.”这可以看出,反馈模式在家庭结构中的存在并不是仅在逻辑上进行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认识的,在现实中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费孝通指出,在反馈模式中,子女赡养老人从简单物质上的反馈逐步进入到了精神反馈的阶段,老人不仅需要的是物质帮助,还有来自子女的照顾等精神上的慰藉,而这又在婆媳关系上造成了新的问题.费孝通的这种从细致的观察入手进而结合中国的传统伦理,考虑现实社会变化的影响,并纳入中西比较的视野,在阐述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的同时对家庭结构的变动展开了初步的解释,能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学还处于恢复期,费孝通的论断对于家庭结构的研究是发挥了指路作用的.
费孝通的“三论”则是在1985年首次发表.在笔者看来,“三论”是费孝通对前几年关于家庭结构探讨的一个总结和修正.这一次,费孝通再次到江村深入调查,并结合前两次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不小的修正.首先是对家庭结构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和解释,他写道:“因之,我同意在分析中国家庭结构时,不妨把两代重叠多核心家庭合并在三类里,而称之为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或大家庭则保留给原来四类里的同胞多核心家庭.修正分类法的目的在于突出中国家庭以亲子为主轴的特点.” [5]在调整家庭结构分类的同时,费孝通重新整理了所收集的江村的数据,从时间跨度上展示了江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这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的数据,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村庄的数据,但是在笔者看来,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一个村庄家庭结构的变化,而更是一个时间段内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既是在时间上进行了历时性对比,同时也是费孝通历时追踪研究方法的一个体现.
在“三论”中,费孝通特别指出了“核心家庭的稳定和主干家庭的起落”这一个变化,其中主要体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另外,对于新时期出现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现实,费孝通适时地关注了这种新变化对家庭的影响,并指出“主干家庭稳定性增加的趋势和当前鼓励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是相适应的” [6].这样的工业化并不显著冲击已有的家庭结构.而如今,中国大量农民工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动不再如费孝通当年看到的乡镇企业带来的影响——曾经是“离土不离乡”,如今是“离土又离乡”,这对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但费孝通关于乡镇企业发展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则仍然值得我们参考.
在“三论”的最后,费孝通指出:“江村目前的情况可说是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究竟事态的发展会导致那一方面的偏重而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现在还不易预测.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对于中国农村里主干家庭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可以说有所增进,同时也看到了农村体制改革对家庭结构已造成深刻的影响” [6].从“三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家庭结构变动的分析框架.费孝通以江村为案例,通过多年亲自采集的数据向我们说明了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变化在家庭结构上的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家庭结构的形态变化、养老方式变化、代际关系、家庭价值等多方面的内容.相较于他的“一论”和“二论”而言,“三论”可以说更加有概括力和说服力,是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中国家庭结构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一个总括性分析.
费孝通在家庭结构问题上的探索并没有随之停止,结合他早年在云南所做的社会调查,以及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对家庭问题的调查和思考,费孝通逐步完善了他关于家庭社会结构的思想,比如提出特别重要的“家庭三角理论”,对后来的家庭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潘允康在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时指出:“费孝通先生的家庭三角理论,不仅包含着结构稳定的思想,而且还有延伸的结构更新理论.在他看来,在父母的抚育下,家庭中的孩子终究要长大,世代间的隔膜客观存在,亲子间继替必然发生,在原有的家庭三角中会产生和分裂出新的家庭三角,这是人种传递中的新陈代谢规律.” [7]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随着后来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逐渐完成及家庭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逐渐发展,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也逐渐科学化,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多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展中国家庭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在回应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关于中国家庭的各种问题.
三、对费孝通家庭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三篇论文,直接反映了费孝通先生在文革之后其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端和发展历程.通过这三篇论文,费孝通敏锐地将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呈现出来,在革命时代占据主流的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模式开始受到影响,而与此同时,核心家庭数量不断增加,这样的家庭结构变化,既影响了代际关系又影响了家庭价值的变化.在代际关系中,中国家庭的抚育和赡养呈现出反馈的模式,这显著地不同于西方家庭.这些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现实中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流动增加、革命时代价值观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通过不断的调查和反思,费孝通以家庭结构变动为中心,不断讨论并在调查中不断修正其观点,将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建设带入到一个良性的恢复进程中.在“三论”中,我们还看到了费孝通的研究方法和特色.费孝通既有西学经历,同时对中国社会又有深入的了解,在中国社会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其有标志意义.在对费孝通家庭结构三论的讨论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来谈一谈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方法.
费孝通认为,首先“实地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实地研究的方法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要求;实地研究的方法是社会科学获取资料的基本方法 [8].从家庭结构三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研究方法的精神,费孝通多次访问江村并利用实在的数据说话,而且也是历经多年的不断追踪和调查.虽然在家庭社会学这一领域中他并没有过多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但是从方法上却给后来研究者以启示和引导.对江村家庭结构的调查,也反应了费孝通的微观社会学——微型社区研究的方法,“费孝通用微观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和观察,学术贡献巨大” [9].
其次,在社区内部调查时,他着重于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要有定性研究,要在定性的基础上开展定量分析,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抽象思维的能力” [10],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学界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时表现出的过于崇拜定量研究方法是一个提醒.比如,在对江村家庭结构的分析中,费孝通从“一论”中直观感性展示江村家庭结构到“三论”中在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家庭结构分类的修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当下,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离,笔者认为,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作用对于真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是不利的.这两种工具必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是目前社会学界关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使用范围的争论已经牵涉到了中国建立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宏旨,并常常被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喜欢定性方法的研究人员倾向于指责定量方法无法有效呈现中国问题,而定量方法的追随者则认为定性的方法过于随意,导致对问题的认识千变万化而随心所欲.例如,谢宇曾在阐述定量研究方法时说:“并不是我认为只有quantitive才能做社会学,而是说这方面中国是空白.” [11]实际上,费孝通在这一方面则更显包容,他善于使用多种方法,并将主要的精力放置于问题之上.笔者认为,在方法问题上,二者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过度的定性定量之争则只会将中国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最终会丧失研究的客观价值.不仅在具体方法上,而且在理论问题上,费孝通都十分清醒,他认为“理论问题十分重要,没有社会理论做底子,社会研究也无从入手”,但同时,他并不是以理论为主要追求目的,“他追求的是有用的知识” [8].从这一点看,费孝通更倾向于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将主要目光放在问题本身,放在知识上,而不是将精力耗费于方法的争论和理论框架的选择中.
费孝通在关于家庭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其经常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因为人类行为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找出其中的同质因素,通过分类的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类型比较来认识同类的特点和类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深入地认识社会.笔者认为,类型比较方法存在的优点在于对同质性的聚集和对异质性的分离,以达到“一种知性和理性之间的过渡”,从而形成知识层面的东西.费孝通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现象比较层面,他还将比较延伸到文化传统层面,他“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 [12].由此,费孝通的比较意识不仅在方法层面展开,还在认识论层面展开,这一点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提示.
费孝通立足中国社会,在学术表达上,他也是独有特色,他以研究方法作根底,让事实来说话,表达时所选取的语言平实简练,通俗易懂,这一点在“三论”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而且他多以第一人称写作,不拘泥于形式,随兴而作,读起来没有晦涩的感觉,而是在事实的阐述中让读者感受深刻.
费孝通还有另一个标本意义,即告诉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对于一个研究者是否可以研究本乡文化,即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们中间进行研究,或者说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这样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本民族人也能很好地研究本民族的社会文化” [13].从这一点看,费孝通本身即是一个符号,即意味着在中国本土研究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同样可以突破各种已有观念和思维范式的束缚,有效地、深入地认识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建立中国研究者的学术自信.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费孝通的“家庭结构三论”更大的意义在于其在家庭社会学研究重建之时的引导意义,他的努力对于后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今天,中国学者对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范围也不局限于一个村庄、一条街道,而逐渐进冬入了更加宏观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家庭结构,“从总体上看,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为基本结构的状态将持续,仍呈现出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居次、单人家庭作为补充的格局.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14].在这个主要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也逐渐在各个方向展开.可以预见,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法的不断创新,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①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1982年3月费孝通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学术演讲,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文中简称“一论”;«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费孝通在香港“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讨论会”演讲,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文中简称“二论”;«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文中简称“三论”.
② “文章”中,作为“资产阶级伪学问”的社会学受到重大打击,“文革”之前中国社会学界主要的研究人员在文革中遭受各种灾难,并逐渐丧失研究机会和研究能力.文革之后,恢复社会学时期,能够有能力重新工作的研究人员已经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