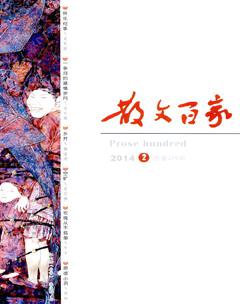中秋,在故乡
2014-03-19汪少飞
汪少飞
什么都有可能暗淡的,唯故乡的月儿永远明亮;什么都有可能变味的,唯故乡的亲情永远香甜。
——题记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到了苞谷须喷红吐紫的时候,故乡的中秋便来临了。今年,在这个时节里,我终于回到了故乡。故乡的房屋依旧,山水依旧,蓝天依旧,只是,看不见一个年轻人了,更看不见在河边浣衣的肤若白雪的山妹子了,他们都出去打工了,中秋是回不来的。这里,成了茫茫大山里的一个空着的村庄。
我就是在这个空着的村庄里,我就是在这个空着的村庄里留守的花甲、耄耋之年的老人的脸上,寻找着关于故乡中秋的那些芬芳的记忆的。
我的山村地处皖南太平县与黟县毗邻地,故过中秋既承袭了古黟繁缛浓烈的风俗,又沿传了太平丰实随和的习惯。全家人早上起床后,各自泡一杯自产的黄山茶,围桌而坐。这时,父亲便把几个月饼放在桌心,用菜刀有规则地一切四块或八块分给大家。这些月饼风味各异,型小馅美的是古徽州黟县产的,个大馅丰的系靠近长江水系的太平产的。除月饼外,还有脆爽的茶食片等。吃了月饼后,家里殷实的,还有茶叶蛋上桌。我家苦,只有闻香解馋了。白天,若逢日头大、气温高,准会有人下河药鱼,这天可就热闹了,中午直至傍晚,村里的男女老少携着鱼网、脸盆什么的,都往小河里奔,不时传来捉住石斑鱼或红肚子鱼的惊呼声……
晚上是正餐。记得我在离家二十多里山路外的郭村中学读书时,尽管路远、住校,但中秋的团圆饭还是要赶回的。本要走两个小时的陡峭山路,我们一个小时多点便赶到了。这时,初秋的夕阳还留有一点儿影子在西山顶上摇晃,村里还飘着最后一缕炊烟。但不同的是,往日炊烟中弥散的腌菜的奇酸味,被红辣椒炒肉片、青椒炒河鱼的香味取代了。那时苦,但晚上的饭菜还是较为丰盛的,全家人都要喝点儿散打的太平白酒。
我家是“桶匠世家”,我的祖辈、父辈都是做圆木的,从出生地江西都昌一直做到皖南,在太黟两地颇有名气。而这喝酒,也是祖传的“世家”。祖父那时虽年已古稀,但半斤酒还是能喝的;我父亲每餐喝酒虽不多,但一日三餐,平时喜欢在厨房里他的那张破旧的小桌子上独饮,惟中秋这晚例外,作为主人和全家人一起喝,很难得的;兄长那时已是大小伙子了,风华正茂,是喝酒的主力;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小子,酒,苦而辣,但我已开始红着脸从中寻找那种飘飘然的神仙般的感觉了;弟弟那时尚小,不能喝,没想到的是,后来,他竟然成了我家的酒仙“李太白”。那时,一斤太平散酒是七毛钱,这对常吃“红锅”的我家来说,是十分珍贵的。
喝着喝着,中秋的月亮便升起来了。
我的名叫扁担铺的小村子,落在太黟分界的来龙山的山嘴上,两山夹峙,山高林密,故能见的蓝天不大,月亮便显得尤为大而亮,仿佛就顶在屋顶上。好在两条小河在村前汇合,清流环绕,河风习习。吃罢团圆饭的村里人各搬个小凳子,聚坐在我家门口看月亮,也有坐在村前的小木桥上看月亮的。但在大家的脸上,似乎看不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愫,因为那些年小山村还没有一个人走出山门。当然,早年走出山门的,是有的,如我远在江城芜湖的姑父刘国平。他和队里的国兴、顺信等几个年轻人于1948年参加了黄山游击队,之后,就很少回大山了。大伙儿也没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兴致,因为村里人几乎都不认识大唐的酒仙李白,只有过年时常为各家各户写春联的长久叔知道一点。他说李白好酒,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喝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倒在哪里,就写哪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他的诗歌都是这么写出来的,只是,最后,他喝死了……说完,他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然,我也是知道一些的,还能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只是这晚坐的时间很长,聊老虎笼的山上种的苞谷,聊队里即将砍伐的竹木,聊正在打的太黟公路的羊栈岭隧道,聊过冬的口粮、衣被,有笑声,也有轻微的长时间的叹息声。几个酒喝高了点儿的平时常翻看报纸的年轻人,还聊起了我平时很少听过的一些新鲜事:队里的那个长得最好看的、黄梅戏唱得最好的女知青要回城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年底要嫁到山外去了,重又复出的邓小平上黄山视察了,队里的山场可能要分到户管理了……
对故乡中秋月的忆念,是在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益强烈的。我是1986年开始离开故乡的小山村的,1993年则离得更远了,到了驻黄部队的一家单位工作,虽仍在黄山之境内,但与地方少有联系。此时,我的父母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年龄虽不算大,但一辈子的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已使他们发如霜染、病痛缠身,尤其是母亲,先是胃病,后又是尿毒炎、高血压、左心衰,但这些,除了病发时我专门回去安排治疗外,平时,我爱莫能助,只能在晚上望月兴叹。九十年代的10个中秋,我几乎没有在故乡过中秋的记忆。而这一时期,正是父亲母亲进入老年后最困苦、最无助、最伤感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我的时候。而我呢,则远在异地谋生,将自己一生中最璀璨的生命朝阳廉价地零售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只有在每年的中秋之夜,独自一人从紫陌红尘中溜出,找一个能看见蓝天的僻静之地,看月亮。我知道,顶在我头上的月亮,还是少儿时在故乡看到装有“吴刚”和“嫦娥”的月亮。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生起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迷惘。我怀念少儿时故乡的中秋,怀念那条白天捉鱼的清流环绕的小河,思念故乡像泥土一样质朴的父老乡亲。这时候我才体会到,他们在中秋月夜下的闲聊,就像一支远古的歌谣,将一个贫穷的大山和一群贫穷的人们摇得亲切、温馨而甜蜜。我更思念我的父母,对他们,我开始怀有深深的负疚。我知道,我又一次让盼我回去的沧桑之父和多病之母失望了。每年,他们都是从7月15日盼到8月15日,可是,总难见儿影儿、踪儿……
进入新世纪后,我已从部队单位调回地方工作,离家近了一点,本可以常回故乡看看小时候和我一起捉鱼摸虾、砍柴挖药的伙伴,和他们喝杯酒、叙叙旧,尤其是看看我白发苍苍的父母,哪怕默坐着不说话,让时光在我们的心中静静地流淌。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已到了风烛残年。逢年过节时,对于早年外出飘泊的我,其心灵深处有了犹如胆怯、弱小、无助的孩子对大人般的依恋和渴望,可是,还是被我疏忽了。生存的艰难,竞争的压力,还有那些虚荣的所谓的帽子、面子、房子、车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年三节的概念已在我的脑海中淡化了,尤其是端午和中秋两节,我几乎已回味不起故乡腊肉粽子的香味了,也似乎忘记了故乡或“型小馅美”或“个大馅丰“的月饼了。故到了苞谷须喷红吐紫的中秋,我总被种种事儿缠着,依然难回故乡,只有长久地站在我住的海安花苑的二楼阳台上,望着明月发出“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的感叹,只有将异乡的中秋月,当着故乡的眼睛和父母的心灯自我安慰。这个时候,我的眼角开始有泪水溢出,开始是热的,然后却像冰一样的冷……
现在,中秋和端午都有假了,我可以回我的故乡,回我那个现在已觉得很遥远的名叫“扁担铺”的小山村,和我的父母一起过中秋节了,与我的大山人聚一聚了。可是,我的父母,我的一辈子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父母,早已长眠在村西坟岭的茶地里了。父母的坟墓朝东方,一弯清流从其脚下缓缓东流。
现在,我终于已经回到了故乡。我在我这个空着的村子里,漫无边际地转悠;我在我家空着的老屋的前后,漫无边际地转悠。
家里的土墙老屋还在。说是老屋,其实并不老,也就三十多年吧,却承载了我生命中最年轻的岁月和我多个过中秋的记忆。只是自父母先后离世后,已多年没人住了,长年锁着,显得很老了,里面堆满了兄长做竹艺品用的锯成段的毛竹,多处漏水,霉迹斑斑。开门见河的后门及通往河里的一步宽的小路已被芭茅覆盖,杂草丛生……这扇后门和后门外的一小块菜地边,就是我父亲经常长坐的地方。听邻居巧珠叔母说,每年中秋节的那天,我母亲都要到村头的公路边等太黟两地的往返班车,看下车的人中可有我的影子,有时在路边一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形只影单,花白的有些零乱的头发在秋风中轻舞。巧珠叔母还说,无数个中秋之夜,盼不到我回来的父亲和母亲也就是坐在这老屋的这扇后门和后门外的这一小块菜地边,轻叹,然后各自背过身去,悄然落泪……
听毕,我,无语凝噎。我极力憋着,控制着,可一滴泪,凝重如铅,还是打糊了宁静的河面,也打碎了故乡那玉盘一样的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