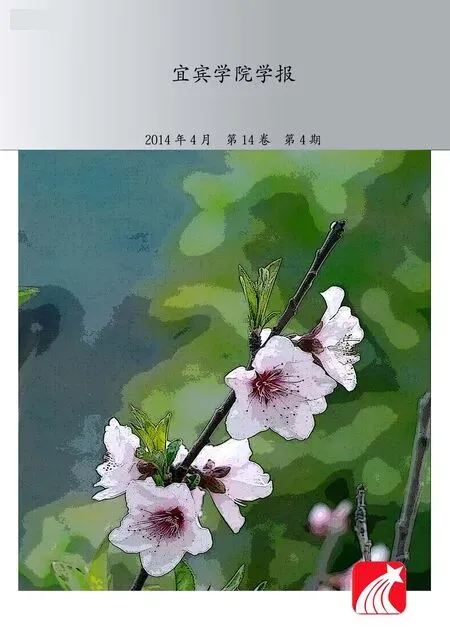晏殊词论三条材料之辨
2014-03-12张中秀
张中秀,邓 雷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晏殊作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其《珠玉词》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对宋词的繁荣兴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历代对晏殊词作出评价的论者都不乏其人,然而可能因为词论辗转流传的原因,有些材料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含义,从而导致未被完全的理解甚至误解。以下将对宋代有关晏殊词的三条材料进行辨析。
1.刘攽: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中山诗话》)[1]292
刘攽《中山诗话》中所记载的关于晏殊词的条目,是一条非常值得注意的词论。此条关于晏殊词的论述之所以应该被看重,其一是论述的真实性。刘攽虽然晚于晏殊近三十年,然而其生活的年代与晏殊大致相当,而且身居官位有风闻晏殊逸事的可能。同时“(刘)攽在元佑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2]98,作为北宋有名的史学家,其笔下文字也应该承袭史家严谨的特点,这就注定其论述文字的可靠性以及材料的真实性。其二是此条词论的广泛影响性。在宋代另外两部诗话中,《潘子真诗话》和《诗话总龟》都引用了此则材料,但是所述内容与《中山诗话》稍有不同。
江南冯延巳善为词歌,晏元献公所为歌词,不减冯也。乐府《木兰花》句都是七言。晏诗云:“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潘子真诗话》)[3]299
江南冯延巳善为歌词,晏元献尤善,公所为歌词不减冯也。乐府《木兰花》句都是七言,晏诗云:“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诗话总龟》)[4]406
这两部诗话的引用材料都遗漏了一个《中山诗话》中所述说的一个事实,就是晏殊非常喜欢冯延巳的歌词。两部诗话的作者均为北宋人,潘淳曾师事黄庭坚,阮阅亦生活在北宋末期,二人当为同时期人。此二人所著诗话都遗漏此处事实,当非有意为之,而再从二人所录文字来看,则二人的诗话材料可能有承袭的关系。除却宋人对此条词论的重视外,嗣后的词论家也多有注意,如清代冯金伯的《词苑萃编》也收录此条材料,文字类于《中山诗话》。
然而正是这样一条颇为有名的词论,至今却一直在被误解。关于《中山诗话》此条论述一般都被理解为:晏殊颇为喜欢冯延巳的词,而且自己所填之词也颇受冯延巳的影响。直到刘熙载的《艺概》中“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5]3689一出,近世论者在论及晏殊词风受冯延巳词所影响之时均用这两个例子。然而《中山诗话》中关于晏殊词的此则材料,真的是为了表明晏词受到冯词的影响吗?其实不然。
近世学者在引用《中山诗话》此则材料之时,几乎都是摘取前半句“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罕有整条材料全部出现的。即便是如孙克强《唐宋人词话》这般收录宋词人评论的集成性资料也只择取了前半部分。然而若从《中山诗话》的前半部分来看,上述所作的解释,晏殊所作之词受到冯词的影响当无可疑问,但是若从《潘子真诗话》、《诗话总龟》此条材料的记录来看,却没有这种意思,冯延巳擅长填词,晏殊也特别擅长,晏殊所填的词“不减”冯词。这里的“不减”二字从文字意思的走向来看并不能说明晏词风格受到了冯词的影响,至少在潘淳、阮阅摘抄此则材料之时,其二人并没有将这则材料理解为这个意思,而应当是晏词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减”冯词的。那么此种因素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看材料的后半部分了。而后半部分的材料各诗话词话均无异议,说的是晏殊一首七言《木兰花》词中两句“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这两句词中“重头”、“入破”都是音乐家的行话。《潘子真诗话》、《诗话总龟》为冯延巳擅长填易于歌唱的词,晏殊也同样擅长,晏殊所填词的音乐当行性不比冯词的少,如晏词《木兰花》中便涉及了音乐家的行话,可见其对音乐了解颇深。《中山诗话》为晏殊特别喜欢冯延巳便于歌唱的词,他自己所作的词,其中的音乐可歌性便不下于冯词。如其《木兰花》一词便涉及了音乐家的行话,可见其也是深谙音乐之道。而这点也是非常符合晏殊一贯的行为。
晏元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尝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避暑录话》)[6]292-293
在那个歌舞升平的上层社会中,做了半辈子优哉游哉的太平宰相晏殊,带领着一群文人士大夫,从事娱宾遣兴、应歌合乐的诗词创作活动。[7]3而晏殊长期浸淫于这样的歌舞场合,对声乐有相当了解,填写出来的词也必定是交由那些红粉歌妓所演唱,此点正与冯延巳相类。由此也可知,《中山诗话》中此条关于晏殊词的材料并不是对晏殊词风继承冯延巳词风的阐述,是对晏殊词中富有本色当行的音乐性的记载,而这种音乐性也与江南冯延巳便于歌唱的词相似。
2.晁无咎: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评本朝乐章》)[8]469
现今关于晁补之论词的专著《骫骳说》已经散佚不见,只有篇章《评本朝乐章》存留在宋人载籍之中。而此篇章中关于一条与晏殊有关的词论却颇有疑问,《能改斋漫录》所录:
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
晏元献指的是晏殊,前面评价的是晏殊,而后面所举例“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诗句却是晏殊的儿子晏几道的。那么这条评价到底是针对谁而发,是晏殊还是晏几道?
晁补之《评本朝乐章》根据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中所言“元佑间,晁无咎作《乐章评》”,可知此篇章作于元佑(1086~1093)间。[9]410之后在赵令畴所作的《侯鲭录》中“晁无咎评晏叔原”条记载了:
晁无咎言: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10]184
赵令畴去晁补之未远,而《侯鲭录》成书也在《能改斋漫录》之前。赵令畴的这则材料与《能改斋漫录》的材料有两个不相同的地方:一个是将晏殊的名字改为了晏几道,并多出“自是一家”四字;第二个是“此人不住三家村”与“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从字面上看,若是生字,则晏殊不可用,因为晏殊出生之家并非高门大家,若是住字,则晏殊、晏几道皆可用。从这条材料的记录似乎可知,晁补之所要论述的对象是晏几道而不是晏殊,然而赵令畴所记载的文字才是晁补之文章中的原话,《能改斋漫录》中所记载的此处文字是误记吗?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在《能改斋漫录》此处文字出现矛盾外,《雪浪斋日记》中更是明确记录了一段话:
《雪浪斋日记》谓: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不愧六朝宫掖体。无咎评乐章,乃以为元献词,误也。元献词谓之《珠玉集》,叔原词谓之《乐府补亡集》,此两句在《补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词情婉丽。[11]253-254
这里明确指出了晁无咎的错误,而且从《能改斋漫录》中录用了《雪浪斋日记》的材料可知,《雪浪斋日记》成书在《能改斋漫录》之前。所以《雪浪斋日记》的作者不可能是读了《能改斋漫录》所记载的矛盾文字之后,才发现晁补之出现的错误,最大的可能是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原文本就如此。而赵令畴《侯鲭录》中之所以记载为晏几道也是因为他看出了此处晁补之的错误,将其径改为晏几道。同时此处,《雪浪斋日记》的作者也认为晁补之把晏几道误写成了晏殊。
在后世引用此篇文献中,基本上都是将此处材料归为晏几道,如《唐宋人词话》认为晁无咎误笔将晏几道误作晏殊[12]222,少有将此则材料划归晏殊的,如《历代词人品鉴辞典》则将此则材料作为晏殊的[13]57。然而事实到底是此则材料应属于晏殊还是晏几道?
从逻辑上看,晏殊字同叔,晏几道字叔原,如果文章中记录的是晏同叔,那么还有可能是晏叔原的误笔,但是文章中记载的是晏元献,元献是晏殊的谥号,用起来就比较庄重,下笔也不太可能与生者晏几道混淆,而元献与叔原也相差甚大。同时,一个人物名字即使初稿出现错误,在校读之时,也很容易发现晏元献与晏叔原的误笔。所以错误不应该是出现在晏元献上,也就是说此则材料所叙说的对象就是晏殊而不是晏几道。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此句词上,对于现今学者来说,也许可以很快将这句词划归到晏几道身上,但是在北宋元佑时期晏几道的词尚未十分风靡,而且晏几道词风与其父晏殊词风颇有几分相似,或言“几道为殊之幼子,词有父风”[12]227,那么晁补之在记忆中误把此首词当作晏殊所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晁补之印象中已将此首词当作了晏殊所作,所以他即使校对文章也不可能发现此处错误。再者,从整篇《评本朝乐章》来看,晁补之所进行论述的主要是针对词人而发,偶有提及词句也是作为自己论述的证据,所以论述的重点在于词人而不在于词句,因为关于词人的观点是不变的,但是词句却是可以换动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晏元献这个词人名字是固定的,而“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此句词却是可以变动的。
从内容上看,“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首先是“不蹈袭人语”,晏几道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就是直接袭用五代时期诗人翁宏的诗《春残》,而《玉楼春》一阕中“织成云外雁行斜,染作江南春水浅”也袭自白居易的《缭绫》“织为云外秘雁行,染作池中春水色”,其他化用诗句不知番几。其次是“风调闲雅”,“雅”之一字上二晏皆足称之,而“闲”之一字,晏几道如冯煦所言为“古之伤心人”,其词作多写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男女悲欢离合之情,用“梦”来追忆他所钟爱的“莲、鸿、蘋、云”四位歌女,且一生境遇不佳,很难用“闲”来形容其词。而晏殊的词却是“盖大君子之用心,不汩汩于嗜欲,政事之暇,寄闲情于词赋,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松陵”[12]174,完全可以称得上“闲”。同时,与晁补之同时期的词人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中也叙及晏殊的词风“风流闲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再次,“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个例子述说的是极尽欢娱的歌舞场面,也正是晁补之要论述的词有富贵气,不是那些三家村的学究可以写出来的。这不仅仅符合晏殊“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的作风,同时也暗合其本人的富贵审美以及一贯所引以为豪的富贵气词风:
晏殊云:“‘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归田录》)[14]21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撰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青箱杂记》)[6]293
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也基本上可以看出,晁补之的此处文字确实是在评论晏殊词,只不过后面在论述晏殊词中富贵气之时,误将晏几道的词作当作了晏殊的词作。而后世论者都是从词作的方向来看,只认定词句,从词句来判断晁补之所要论的词人,认为其只是误将人名写错了,而没有想到从词人方面着手,是词句误记罢了。
3.李清照: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词论》)[15]267
这段话首先赞扬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学识渊博,才大如海,作词不过是在海中取一瓢之水而已,极言其仅以余力为之。[16]198其次批评了三人的词其实就是句读没有改好的诗句罢了,而且往往又不协音律。这里批评了晏欧苏三人词“以诗为词”的手法和词不合律。李清照对晏殊、欧阳修、苏轼词的批评有几点问题:
第一,李清照何以将晏欧苏三人共置一处而并提?从时代、年岁、风格无论哪一者来看,晏殊、欧阳修都与苏轼相差甚大,晏欧二人同属于一个时期而年岁相差不大,而苏轼比晏欧二人则晚一辈;晏欧二人同承花间词风,分属婉约派,而苏轼则被归为豪放派。如此看来晏欧共论当没什么疑问。而晏欧苏三人之所以如此共同提出就是为了批评他们词中所共有的缺点。
第二,晏欧苏三人的词是不是确为句读不葺的诗?关于这点,苏轼的“以诗为词”当是无甚疑问。自陈师道于《后山诗话》中提出苏轼“以诗为词”此论后,学界不仅多有附和,而且认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17]66那么主要问题是晏欧二人词是否是句读不葺之诗?从现存晏欧二人的词作中,确实存在“以诗为词”的现象,如晏殊《胡捣练》小桃花与早梅花,尽是芳妍品格。未上东风先拆。分付春消息。佳人钗上玉尊前,朵朵秾香堪惜。谁把彩豪描得。免恁轻抛掷。[7]108欧阳修《盐角儿》增之太长,减之太短,出群风格。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倾城颜色。慧多多,娇的的。天付与、教谁怜惜。除非我、偎著抱著,更有何人消得。[18]322-323二词都沾染了诗中以“以文为诗”的气息,而颇失却了词味。如果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是有意识地提高词体的地位的话,那么晏殊词中“以诗为词”的手法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而这种不自觉的“以诗为词”在晏殊词中又表现为运用对句、化用诗句、运用典故这三个方面。据统计,运用对句方面,《珠玉词》140首,120首运用了对句,对句数量达到230对[19]199;化用诗句方面,《珠玉词》有118句[19]246-252;运用典故方面,《珠玉词》有98处[19]202,数量均不在少数。所以,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这句话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仅“批评苏轼的词”而晏、欧只是“牵连偶及”。[20]
第三,晏欧苏三人是不是多有词作不协音律。关于此点,苏轼词作的不协音律在同时代人之中早有人提及,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故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21]469而晁补之恰恰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至于晏欧二人词作是否不合音律,“宋人只言苏轼词或不合律,未有言及晏殊欧阳修者”[22]200。之所以未言及晏欧之词不合律,一者可能二人确实未有不合律的词作,二者也可能是因为二人词作不合律情况较少,只是偶现,故而不予强调。在词乐逐渐消亡的今天,词的音律体系已难以考证,人们对词的音乐形态知之甚少,仅从刘崇德先生《燕乐新说》、《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等书中可窥见一斑,可以说如今词已变成了一种文字的艺术,因此我们无法确切考证二晏词是否协律,无法对李清照的评价做出准确判断。[23]16然而,从一些侧面可知,晏殊词应当协律可歌,如上文所说的《中山诗话》中就提及晏殊的词作中具有音乐性的行话,可以表明晏殊熟稔音乐之道。同时少时就作为神童的晏殊,又长于歌筵舞席,没有理由不精通音律,而自己所作小词,拿出来与歌妓一唱也是花下樽前之乐事一件。而且词自出现起便是为了供人歌唱,发展到宋初,尚未沦落到案头之物,所以晏殊词应当协律可歌的。
至于李清照《词论》中何以将晏欧二人之词与苏词一般皆定义为不协律,原因可能有三:一为李清照此段评论主要是针对三人词中“以诗为词”的手法进行批评,而不协律则主要是根据苏轼词而发。但是因为本身就不是特别严谨的著作,便未予以考究。二为李清照此段评论的原话或许未必如此,在转抄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遗漏或者舛误。原本的李清照《词论》并未流传下来,《词论》是附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所流传下来的,所以这种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三为李清照所言的词律(音律)较之一般的词律则更为严格,划分得更为细致,在这种情况下,晏殊词是不合律的。
参考文献:
[1]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九十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3]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 (清)刘熙载.艺概[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
[8]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王兆鹏.词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宋)赵令畴.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3]吴湘州,王志远.历代词人品鉴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宋)欧阳修.湎水燕谈录·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8]邱少华.欧阳修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1.
[19]唐卫红.二晏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20]胡学琦.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J].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1(1).
[21]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2]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3]张琛.宋代二晏词接受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