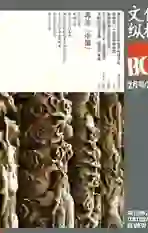再造“中国”
2014-03-11
何为中国?从周代开始,这就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无论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还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几千年来,中国都是文明的中心,被四夷和化外之民所围绕簇拥。中国人于兹土安身立命、歌哭生聚,虽有朝代的兴废,但却没有文明的断绝。
直到四夷和化外之民,不但动刀动枪,还携其文明鼓荡而来时,中国人对自身的理解才被彻底敲碎,惊叹眼前的世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期间,从不分你我,到迟疑犹豫,再到藕断丝连、彻底唾弃,现代中国和古老中国,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苦恋剧。然而,分手的决绝之后,如何理解自身的问题,虽然经过几轮尝试,却并没有最终解决。
当前,何为中国,更进而不再是中国人自身的问题,还是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大国的疑问。在张志强的笔下,中国之为中国,必须回到中国文明形成的源头去找寻,它和中国成为一个统一政治体之后,为了解决“中国”规模的问题,更和这一统一政治体之上生成的价值秩序和价值观念相关。在这一视域下,来反观现代中国,“共和”的出现,并没有解决明代以来政治基础的稳定和扩大问题,也没有打造成功一个更稳定的政治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在推翻皇帝制度的同时,也连带推翻了这一制度背后的文化象征系统。这是现代中国痛失所依,面目不清的根本原因。
说到底,理解中国的问题,根本还是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而中国在现代的遭遇,最核心、最繁难的地方,莫过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曾几何时,“大一统”下的多元共生,一直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然而在近代,民族问题对“中国”的挑战却最为巨大和严重。傅正从晚清的脉络中,详细梳理了这一困局,特别指出,在西方叙述的冲击下,用阶级来克服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改革开放之后遭遇了挑战,在今天我们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号召来凝集各民族的共识时,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作者认为用“宪政主义”或者“国民身份”等空洞的观念无助于此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托于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史的重新书写。
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更多的人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本源性的大文明体,自身的问题,最终还是必须落实在自身文明的基础上解决。它的体量,决定了不可能像日本在近代那样,完全泯灭自身、舍己从人。秋风和任锋的文章,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以儒家为核心的现代中国秩序构建的历史过程。他们从现代转型伊始儒家所遭受的重创入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认识儒家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价值地位入手,描述了儒家在面临近代挑战时,所做的回应,既有政治实践,也有理论设想。一个呼之欲出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必须有全新的焕发和提振,才可能再造文明、再造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新领导人上任后对曲阜的参访,被解读为应和了民间“文明复兴”“文化复兴”,乃至“继承道统”的呼声。似乎经过百余年激烈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重新回归传统的风潮,已经从学界重新刮回到政治层面。这充分说明,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理解,已经逐渐走出过去那种单一、否定的视角,而现代中国的面相,也似乎在这种视角之下,才能逐渐清晰起来,坚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