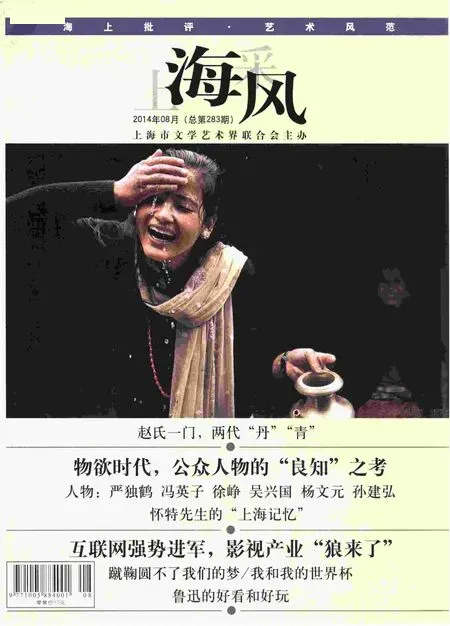被神化的俄罗斯文学
2014-03-07文/张闳
文/张 闳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批评家
三套车、白桦林、伏特加、手风琴、马祖卡、喀秋莎……这里是俄罗斯!这里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祖国!这样的宣告是多么令人迷醉!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它几乎等同于在宣告天国的降临。
的确,就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同俄罗斯相提并论。那个广袤的被冰雪覆盖的国度,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有过一个“俄国梦”,而且,这个梦并未因苏联的崩溃而破灭。因为这样的梦实际上更多的是关于19世纪俄罗斯的。被神话化的19世纪,加上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俄罗斯,这就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时空想象的全部。1980年代的时候,我常常跟几位兄长辈的朋友谈论起19世纪俄罗斯文化,每一次,朋友们都会激动不已。有时,他们的眼里还会泪光闪烁。他们对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诗人作家,比对本土诗人作家还要熟悉。数算着那些光芒灿烂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一串串冗长拗口的俄文在舌尖上翻滚,还要不厌其烦地加上父名,以示正式。他们会事事以俄罗斯为参照,检点本民族的劣根性,全然不顾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斥责。被茫茫白雪覆盖着的俄罗斯大地,一切污秽、邪恶,都被掩盖得干干净净。在那个贫乏时代,读书人是那样地迷恋着19世纪的俄罗斯,就好像穷小子保尔·柯察金迷恋林务官的漂亮女儿冬妮娅一样。
对于我而言,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谜。它从来就是一个怪异的、自相矛盾的混合体。它是那样忧伤,又那样奔放;那样诗意,又那样粗鲁;那样圣洁,又那样邪淫。一边酗酒放纵,一边孩子般地痛哭悔罪。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即便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优秀儿女来说,俄罗斯也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一百多年前吟唱道——“俄罗斯母亲啊,你贫穷,又富饶;你强大,又衰弱!”俄罗斯常常表现出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从版图上看,它占据着无与伦比的辽阔空间,但它却始终对土地有着一种难以遏制的贪婪和热爱。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充满了无家可归的焦虑,徘徊于广袤的大地之上,同时又在抬头仰望天国。它是一个最关注灵魂的民族,创造的艺术能让灵魂震颤,但它的灵魂却没有稳定的形式,只有一种单纯而又热烈的情绪来当作粗糙的替代品。同俄罗斯在一起,是令人兴奋的,同时又是危机四伏的,总好像是一场冒险。它是令人费解的,又是令人迷醉的,正因为令人费解,才令人迷醉。诗人丘特切夫在提到他的祖国时,这样写道——
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
通用的尺子无法度量她:
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
——对她只能信仰。
是的,俄罗斯确实成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他们相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俄罗斯精神”或“俄罗斯灵魂”。可是,即便从文学上讲,这样的一成不变的俄罗斯并不存在。普希金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布尔加科夫的俄罗斯、普拉东诺夫的俄罗斯,是完全不同形态和不同性质的国度。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会比中国人跟俄国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然而,对于做“俄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自恋”的产物。他们愿意相信有一个那样的俄罗斯存在在那里,像传说中的美丽的公主,永远美丽,不会老去,即便有某些令人不悦的传闻,那也是被恶魔施了魔法而变成了天鹅的少女,只要你不懈地去爱它,就会恢复美丽的人形。
毫无疑问,一代人需要一个精神乌托邦来寄托自己的梦想,当他们在自己的现实中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尤其知青一代人,在那些寒冷、空虚和无望的漫长冬夜里,聚在一起吟诵普希金,讲述契诃夫,哼唱《三套车》,这样的精神慰藉胜过温暖的炉火和家园。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曾经计划写一部小说,讲述几个知青在乡村的夜晚,唱着《三套车》,对几位村里的少女所到来的精神和情感的双重震撼,以及几个人一生命运的改变。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部小说依然没有完成。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写这部小说,它不是文学,而是生命。面对这位朋友的精神追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事实上,他所挚爱的,早已不是什么俄罗斯、三套车之类,而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世界。这位孤寂地生活在偏远小镇上的文学朋友,他需要自己的文学蜗壳来抵御外部世界的风雨。喧嚣、狂暴、自私、冷漠的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诸多伤痛,或许依然可以从那位身穿农夫长袍的老托尔斯泰那里,找到精神的镇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