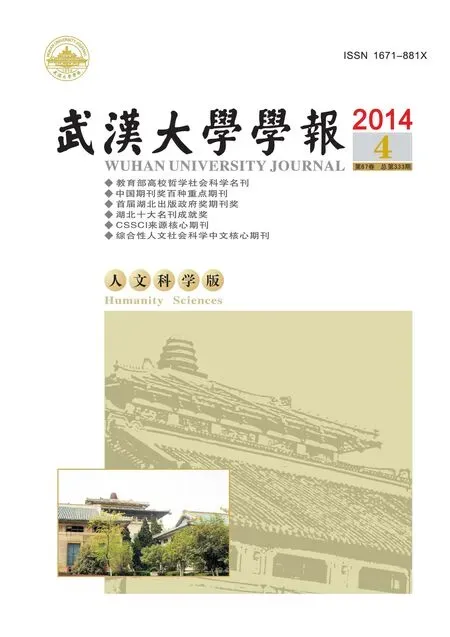易学研究的纯化与泛化
——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问题申论
2014-03-04萧洪恩
萧洪恩
以易观之,易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中较为独特而普遍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学习中域文化的进程不同,中域易学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有的民族易学尚处于原始形态,而有的民族易学则经过传统易学而走向了近现代形态,出现了易学文化转型。另一方面是各少数民族由于心同此理之故,发现了自己的“易”学,后来又结合中域易学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独特易学,虽然各民族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不同,但却在易学发展中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体验,因而易学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的“多元一体”格局。从目前已经得到阐明的布依族、水族、土家族、阿昌族、瑶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普米等民族的易学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丰富的易学文化,正如太史公所谓:“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因而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并不着眼于对“多元一体”的中国少数民族易学进行全面介绍,而只是就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申论,并进而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的一般特点与研究重点。至于各少数民族易学的系统研判,则另专文推阐。
一、 易学泛化:少数民族易学研究中的超载与局限
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少数民族易学”概念的提出却是较为晚近的事。如1995年杨宏声、华铮等于《中国少数民族易学通论——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的易文化》中即特别提出了“少数民族易学”的概念,并相应地提出了“少数民族易学”“是由汉族易学典籍和思想在少数民族那里传播和影响而有易学呢,还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易学自有渊源?或者,多源、多元的少数民族易学实际上是在和汉族易学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文章中同时还提出了“易”的“原型”构成问题,追问“原生态的对立观念或二元观念究竟为何、原发性的图式化形式究竟怎样才能加以辨认和阐释”等等所谓的“易学”问题,并提出是否“凡涉及占卜(占卦)、阴阳、五行、太极、河图、洛书的种种观念、思想和范式,皆纳入‘易学’的范畴”的问题*杨宏声、华铮:《中国少数民族易学通论——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的易文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事实也正是这样,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易学”范围的不清晰,因而出现了易学研究的泛化现象,笔者把这种泛化现象叫做易学的超载,即把一些不属于易学范围的文化现象“强为之名”地进行易学研究或过度地进行易学阐述。
(一) 推易及文——把诸少数民族文化现象易象化
在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有一种将少数民族文化泛易学化现象,其代表或即是由江凌撰文、李辉绘图的《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该题目前已在《中国民族》2013年第1期至第12期上共发表了12篇文章,据刊物开栏语说是其“2013年特别推出的一个系列专题”,其宗旨有二,一是“通过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现象的易学解读,揭示少数民族文化与易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在文化层面上进一步佐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二是在 “学术层面,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具体内容是“运用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的思维方法,来解读少数民族有关的神话、节庆、礼仪等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其宗旨并无不对,而且,作者对其所谓“易学视野”也有特别说明,即“所说的‘易学’,并非指狭义的有关《周易》文本的研究,而是指广义的‘易学’——即围绕《周易》文本所发展出来的整个易学体系,包括易学的思维方式、基本理论、方法等内容”。作者还特别强调“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都可以从易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作者所“关注的范围,仅限于那些与易文化有较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论文首篇即作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宣判,即把“中国易学文化的基本原理、方法”“总结为三个要点,或称为‘三定律’”,即“天人同易”、“观象系辞”、“神道设教”。由于他运用此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因而首题即宣布“‘易学’来了”。于是,12篇文章下来,盘瓠神话,苗族的“接龙”习俗与“椎牛合鼓”祭祀、“略比倮”葬仪,端午节、“刘三姐”、火把节、泼水节、多民族的射日神话,满族的“大清宝藏”和“索伦竿子”的传说,金瓶掣签,黄帝四面、舜目重瞳、孔子圩顶等都在易学文化体系“三定律”下,通过易学易象“得到”了说明,把极具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化现象简化为“易”象组合。或许作者本身心有所虚,因而在专题末尾虽然说“主旨是从易学文化的视角,说明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与中华易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紧接着即强调“通过努力,至少可以说,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从新的视角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框架”,但最终并不是为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而只是为“具备一定易学基础的读者,已经初步认识到了这一视角和方法的独特价值”*江凌:《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1-12),载《中国民族》2013年第1~12期。。正是由于此,虽然文章中言之凿凿,但也不泛“可能”之词。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研究活动,我们尊重这种研究的权利,但却很难同意研究者的观点。因此,我们把这种研究叫做“推易及文——把诸少数民族文化现象易象化”。
(二) 推己及人——把中华易学文化泛化为世界文化之源
在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另一种将少数民族文化泛易学化现象也值得注意,其代表或即是由黄懿陆先生《从共同的易学理念看人类文明同源——人类文明同源研究》,该同题论文发表在《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期、第3期及第4期上,更早的则是其《大王岩画的易学阐释——文山岩画的宗教内涵剖析》之同题论文,分别发表在《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和第3期上。黄懿陆先生从易学的角度,认为云南省麻栗坡县城以东发现的大王岩画,既不是什么“侬智高留下的身影像”,也是不什么“傩舞的代表作”或“母系社会的女神像”,而是盘古阴阳夫妻或伏羲女娲像,“实乃阴阳易学抑或鸡卦的产物”。因为“图案中出现了‘▽’符号、鸡骨卦象、易学常用的‘▽’字和‘十’字、生殖器崇拜以及‘◇’形符号和‘龙’等图像。此外,反映了鸡卦的形式、功能、作用与易卦的关系和巫者对鸡卦的思考和‘龙’因鸡卦而有形的过程,从而凸现出‘龙’的起源等理念”*黄懿陆:《大王岩画的易学阐释——文山岩画的宗教内涵剖析》,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3期。。在此基础上,黄懿陆先生更进一步研究了云南抚仙湖水下远古遗址,认为“人类文明起源模式为远古中国阴阳易学”,具体地点为原壮族地区,因为“从壮侗语支民族后裔之一壮族把‘天’和‘太阳’叫做‘干’的语言切入,通过中国云南抚仙湖水下远古遗址所见文字符号、图案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所见文字符号、图案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地远隔千山万水,但注重阴阳易学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并且,原始的易学观念以数字“十”和三角符号的形式出现,普遍见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及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更进一步,黄懿陆先生对比了甲骨文、金文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有关王权的记载,认为其同样体现着阴阳易学哲理。据此,他特别强调“殷商、西周时期的金文,无不蕴藏着‘干’的读音分别是‘太阳’和‘天’的两重内涵,这种读音和语义分明是壮侗语支民族后裔之一壮族语言中的意思”。于是,不仅易学,而且人类文明,都在云南初始地发生了,“因为,易学观念和易学的考古证据、还有阴阳哲学思想,远古时期就诞生在云南,现在我们要寻找易学的源头,还得从抚仙湖水下去找,具体易卦数字和图案就在抚仙湖水下的古建筑当中”。在系列论文中,黄懿陆先生具体研究了欧洲考古学上的“▽”符号及其意义、近东及苏美尔人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结论当然是一致的——易学文明、甚至人类文明起源于云南抚仙湖地区。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同样要说的是,我们尊重黄懿陆先生的权利,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因而我们将他的研究定义为“推己及人——把中华易学文化泛化为世界文化之源”*黄懿陆:《从共同的易学理念看人类文明同源——人类文明同源研究》,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4期。。
(三) 易蕴通观——把心同此理所得泛化为易学文化之流
从人类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说,在相类的环境条件下,会大致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观念出现,比如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面对的宏观宇宙基本相同,因而在原始初民那里都大致发生了三层宇宙结构说——天神世界、人间世界和地下世界,因而“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我们发现类似的宇宙观念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2005年,第42页。。笔者曾就土家族的三界宇宙观作过深论,后来更及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并关注了世界多元文化的这一观念现象。与此相类,认识对象的二元模式,如男与女、善与恶、中心与边缘、自然与文化、上与下等,也都会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再现,这样即导致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模式,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判断,人类文明在发生之际以前,本来就是‘趋同’发展的——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再到青铜文化……人类文化的第一次‘趋同’,主要出于原始文化心理的共同性,是一种平行发展的‘趋同’。”*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262~263页。
正是由于有这种“趋同”问题,才为研究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提出了哲学解读的任务。对少数民族易学研究自然也是一样。不过,同样研究易学,却会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差别,并且这种差别不是“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而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比如,20世纪易学哲学研究得以展开,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于是即有学者以易学哲学观为参照,将少数民族哲学中的同类思想归入“易”蕴名下。代表作即有宋野草的《云南少数民族哲学中的“易”蕴探寻》*宋野草:《云南少数民族哲学中的“易”蕴探寻》,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一文,该文有感于“少数民族易学一直以来都未被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因而“以云南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为例,通过对其民族文化中蕴涵的唯物思想、辩证思想、阴阳、五行等进行分析,系统阐释了云南少数民族哲学中的易学思想”,文章中所论述的内容,有些自然可以认为是所谓的易学内容,如阴阳思想、五行思想等,但唯物思想、辩证思想就很难将其归入易学门下,把它作为易学的专利。而且更进一步,即使是“阴阳”思想,作为一个符号化语言,其所表示的哲学文化观念却极具普遍性,只不过好多民族没有用“阴阳”来表示而已,就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更多的也是借汉语“阴阳”来“格”以己义而已。至于“五行”,也完全可能是各民族心同此理一般,正像西域各民族有“四素”说一样。从理论上说,这种研究方法有些类似于人类学上的元语言或哲学上的元哲学研究法,即把某种哲学还原为元语言或元哲学,然后据此来判定其他哲学或语言,凡相同者,几乎都是此元语言或元哲学之流。而实际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来说,并非此例者甚众,因此笔者将其认定为“易蕴通观——把心同此理所得泛化为易学文化之流”。
二、 一体两面——中国少数民族易学中的信仰与学术
目前,中国易学明显地呈现出所谓“学术”与“运用”两面。所谓“运用”,实际上是部分易学人士利用民间信仰的市场来经营易义,于是有多种多样的“堂”、“坛”、“公司”等等出现,我们把易学这一部分归入民间信仰系统。而所谓“学术”则主要是学者从事的易学研究。在这方面,历史上即产生了多种学术派别,如划分为“尚辞”、“尚象”、“尚变”、“尚占”等;或划分为《易》《老》兼治者,发明图书易者,以佛陀解易者,仿圣拟经者等。通常的划分是所谓汉易与宋易,或言象数易与义理易……可以这样说,易学历史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体两面——基于学术的一面与基于信仰(运用)的一面。
就信仰而论,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以来即曾有过自己的可比类于易学的文化形式,后来中域易学文化传入以后又得到合理嫁接,以至于现在根本无法也无需去判别谁先谁后、谁源谁流的问题,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汪宁生先生即作《八卦起源》*汪宁生:《八卦起源》,载《考古》1976年第4期。一文,文章通过考察西南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的“数卜法”,如苗族木片或竹片卜(一正一反、两正或两反)、纳西族的“卜”、西盟佤族的“司帅报克”卜、阿坝地区藏族的牛毛绳、羌族的数麦秆、云南西北部傈僳族的“赛萨”卜等,特别是认为四川凉山彝族的“雷夫孜”占卜法,更与中国古易卜法相类。这些卜法,如果以易观之,则无不属于易学,若此的结论即是易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曾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运用,除民间广泛用于风水、命理、风俗仪式外,就目前所知的卜卦即达数十种,占卜的法具甚多,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均可,如竹卦、米卦、水卦、磨钩卦、纱钩卦、木梳卦、茅草卦、蛋卦等,并且与中域易学“动则观其占,居则玩其辞”相类。即使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也实行梅卜、剑卜等多种卜卦方法,如土家族知识分子田甘霖即在《甲申除夕感怀和家大人韵》其三中有“观梅灯有艳,看剑水无波”之说*陈湘锋:《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诗中的“观梅”、“看剑”都是占法,其他如字占,其法为任取一字划数,以八减之,余数得卦;再取一字,以六减之,余数得爻。然后,依“易”理,以断吉凶。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若以易观之,则都有易学,只不过不宜妄言为中域易之流而已。这倒有点像庄子《秋水》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一般,只是参照标准不同而已。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涉及到了普米族*章虹宇:《普米族的“八卦图”》,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苗族*吴心源、雷安平:《苗族九卦寻踪》,载《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建设实践研究》(会议论文集)2009年。、彝族*刘明武:《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载《中州学刊》2009第3期;冯利、覃光广:《八卦哲学与彝族》,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王路平:《试论古代彝族的八卦哲学》,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水族*唐建荣、任睢阿闹:《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载《三峡论坛》2011年第6期。等民族的易学。诚然,这些研究并不是从信仰的层面进行的,而是从哲学文化学方面进行的,是一种文化哲学研究。从易学发展形态上讲,普米族*章虹宇:《普米族的“八卦图”》,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的易学尚处于图画阶段,因而更为原始;水族*唐建荣、任睢阿闹:《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载《三峡论坛》2011年第6期。的易学在水书中表现,显示了向文字形态的过渡,与此相应,纳西族的易*李国文、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学亦处于此阶段;而苗族*吴心源、雷安平:《苗族九卦寻踪》,载《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建设实践研究》(会议论文集)2009年。、彝族*刘明武:《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载《中州学刊》2009第3期;冯利、覃光广:《八卦哲学与彝族》,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王路平:《试论古代彝族的八卦哲学》,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的易学文献都已具有成熟的文字形态了,可以说已是比较成形的易学文化形式了。
就学术而言,中国少数民族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了自己的易学精英,其中不少精英还提供了易学经典。像土家族至少在两汉魏晋时期已有以易名家的学者如范长生;至少在宋代已形成了影响全国的“涪陵学派”易学;至少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已将易学列为学校的“学位”课程,大家“研易似少陵,祗为吟诗瘦”,并明确地提出了“画前有易”的观点*[清]同治版:《来凤县志》第31卷。;至少在19世纪的土家族地区有了易学哲学专论——长阳土家族学者谭大勋的《气运论》、李鼎三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义》……在其他民族中,像回族,瞻思是元代后期一位博通经史和易、道之学的学者,著有《易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李贽著有《易因》六卷解释《易经》六十四卦象;此外,从王岱舆以降,中国的回族学者在系统研究伊斯兰教义并刊行其汉文译著过程中,易学始终是其重要的运思工具,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刘智的《天方性理》、马注的《清真指南》、蓝曦的《天方正学》等都可以作为易学著作进行研究。又如,在明清时期,不少白族学者都对《易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尤以高奣映、王崧的成就最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有杨宏声、华铮的《中国少数民族易学通论——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的易文化》*杨宏声、华铮:《中国少数民族易学通论——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的易文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一文进行论述。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耶律楚材*王冉冉:《耶律楚材与易学》,载《周易研究》2012年第2期。、保巴*陈少彤:《关于〈易源奥义〉一书的哲学思想》,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12期;陈少彤:《保巴生平、著作及其哲学思想》,载《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唐城:《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载《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李秋丽:《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载《周易研究》2011年第6期;秦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2~149页。、康熙*袁江玉:《康熙与易学》,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蒋湘南*问永宁:《蒋湘南与伊斯兰哲学》,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问永宁:《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易学观》,载《唐都学刊》2008年第2期;黄黎星、崔波、丁四新:《黉门菊灿——萧汉明教授七秩华诞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问永宁:《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易学观》,载《唐都学刊》2008年第2期。、蓝曦*问永宁:《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载《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等少数民族易学精英都获得了广泛的研究。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学术易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政治适用与文化融合得到多方面影响,回族、蒙古族、白族易学在这方面的特点都表现鲜明;二是借易学以明志,并综合运用易的各种流派与各种文化形式,如宝巴易学即象、数、理兼用等即是。
在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的一体两面中,信仰的一面通常体现在民间的宗教信仰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民间宗教。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对“民间宗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如有主张两层次说的学者强调宗教的“寻常百姓的层次”即是民间宗教*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湾文殊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有主张两种基本形式者认为普化型宗教即“民间宗教”*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有的则认为“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等。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民间宗教包括信仰(神、祖先和鬼)、仪式(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和象征(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等体系*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笔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上述这些方面差不多都可以以易观之而被视为易学文化。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主要并不是作为易学文化进行研究,而是作为民俗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的研究对象。作为易学文化研究的少数民族,如彝族、纳西族、水族、苗族等,通过对民间信仰的挖掘整理,不仅形成了汉译文献,而且形成了与中域易学的有效沟通、对比,如形成了彝族刘尧汉及陈九金、卢央等在《彝族天文学史》*刘尧汉、陈九金、卢央:《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对彝族易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河图、洛书与彝族十月历结合起来,甚至说墨西哥土著印第安玛雅人所使用的十月历即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其根即在云南省楚雄洲大姚县昙华乡的丫古埂彝族村。而刘明武的《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刘明武:《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则不仅认为彝族文化里有阴阳、五行,也有图书、八卦,强调这些在彝族文化里是解释宇宙起源与演化的基础理论,是解释时间与空间的基础理论。而且强调了解彝族文化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头。吴心源、雷安平等在《苗族九卦寻踪》*吴心源、雷安平:《苗族九卦寻踪》,载《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建设实践研究》(会议论文集)2009年。中,根据湘西苗民杨老七真传,田仁美与龙玉六口授,田彬传承制图、释义、讲解和奉献,田彬与龙炳文翻译、整理、校正和注释的“中国苗族九卦易经”,探讨了该苗族易学的卦名与卦象、卦文与卦义、卦理和卦势等方面内容,具体涉及到了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人居、器物,甚至包括医学和哲学等知识,认为“中国苗族九卦易经”“是苗族先民对人类自身、人与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科学总结”,它体现了苗族“一分为三,三位一体”的生成哲学观,“万物有灵”的能量观,“三生万物”的生命观……唐建荣、任睢阿闹的《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唐建荣、任睢阿闹:《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载《三峡论坛》2011第6期。则认为水书是水族的“易经”、“百科全书”,文章中还分析了水书中广博的阴阳五行、对立统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观念,而蒙耀远、文毅的《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唐建荣、任睢阿闹:《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解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载《三峡论坛》2011第6期。则认为水书的本质与核心是阴阳五行,并就水书中阴阳五行与汉文化的阴阳五行进行了对比,对“水书与汉文化同源共生”问题展开了讨论。李国文曾有《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李国文、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并有《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李国文、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对部分少数民族也有深远的影响。而纳西族的《东巴经》中就有大量记述五行的内容,在书中专论有“原始青蛙八卦”、“原始精威五行思想”等,认为“五行”、“八卦”思想与纳西族的宗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纳西族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认为,目前易学研究进行得较好的民族,主要都是从民间信仰中发掘材料,然后进行思想内涵的挖掘。甚至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易学文化研究,正是从民间信仰研究走入学术殿堂的。
在民间信仰中的易学文化被揭示出来的同时,一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易学精英也被抬上了学术研究舞台,土家族祭出了苌弘、落下闳及蜀才易学与涪陵易学,蒙古族祭出了保巴,满族祭出了康熙,白族则祭出了高奣映、王崧等,回族更是祭出了大批人物,应该说,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易学史也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
三、 纯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先师萧萐父曾提出“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问题*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载《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羼入许多非哲学思想资料时会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因而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但进一步的思考则表明,应考虑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关注作为哲学赖以生长土壤的文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排除泛化哲学文化的研究对象。
根据这种研究思路,李维武教授曾提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正确地处理了“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关系*李维武:《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事实上,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易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易学,应当进行一定的研究对象的泛化,从少数民族的全部文化现象中去厘清其中的易学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在土家族先民关于人类起源的“卵生”说中看到“卵生下无极,无极生下太极,太极生下两仪,两仪有阴阳,就像两个人”之类的易学范畴;在阿昌族开天辟地神话中看到由混沌而生阴阳,并进而产生天公和地母的二元思维;在瑶族盘古传说中看到有乾坤之说,而在其《过山榜》则说“昔时上古天地不分,世界混沌,乾坤不改……”。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中的确有众多易学现象。如果说上述只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传说(唱)所存,那么一般民众日常话语中的“行是差,梦是想,打卦佬在烧得讲”,则提供了与前面所谓“数卜法”不一样的以火烧观察裂纹的另类占卜法,诸如此类,的确反映出中华少数民族易学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泛易学研究。但是应注意,这种泛化既不是对任何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进行泛易的解释,而是去探寻其中确实的易学内容,也不是用中域易学观念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过度的易学阐释,例如在彝族重要文献“《西南彝志》的汉译本中,经常把‘父母’译为‘阴阳’,……这样做恰当吗?我们认为,《西南彝志》中的‘父母’概念确实比之《梅葛》中的‘雌雄’概念要更抽象一些,并且有了更为丰富的哲学含义,但是它与汉文的‘阴阳’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因此,不应急于将彝文的‘父母’等同于汉文的‘阴阳’,否则就会忽略了彝族思想史的特点。”*伍雄武、普同金:《彝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此外,“从《西南彝志》全书来看,所谓八卦主要还是作为空间方位的概念,其次才是作为万物本原的概念。……在《西南彝志》第四卷《论四象变八卦》篇中,以‘八卦’作为方位概念就十分明确。”*伍雄武、普同金:《彝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泛化中国少数民族易研究应有一定的限度,我们甚至据此而主张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的纯化。
为了纯化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我们根据各民族发展实际,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学术上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精英文化成果,可简称精英或经典易学文化,蒙古族、回族、满族、土家族、白族等民族历史发展中都大量存在,而且这些精英在阐明易思想时,并不只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甚至是自己讲。二是民间口承文化中的易学,可以称之为口承文化易学。这通常是通过民间口耳相传承继发展的文化形式,如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这方面的口承文献已有不少整理翻译成为文本文献,如《崇搬图》《阿细的先基》《彝族古歌》《牡帕密帕》《仡佬族古歌》《盘王大歌》《苗族古歌》《密洛陀》《傣族古歌》《论傣族诗歌》《查姆》《梅葛》《侗款》《遮帕麻和遮米麻》《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彝族诗文论》《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等,但仍然有待更进一步的整理的东西。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它们都包含有口承文化易学内容。三是仪典文化易学,仪典应作广义的理解,比如节日文化、哭嫁仪式、丧葬仪式、祭祀等等,这部分应从其实在的仪式中去理解和研究,与此类仪式相联系,人们的行为其实也应纳入此类文化中来研究,如出行必看期或卜卦等,即是一种典型的易学行为,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即隐含着其易学观念。四是物态文化,这类通常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在这类易学文化中,大到城市建设,如唐宋时期易直接影响了南诏、大理国都的城市建设,在南诏、大理国都城的王都选址、整体规划布局及建筑格式与风格等方面,都反映出易学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王朝都城建设和规划的影响*杨周伟:《论唐宋时期易学在南诏、大理国都城建设中的运用》,载《周易研究》2011年第2期。。而伊犁特克斯八卦城的选址规划,更是与易学紧密相联*杜殿卿:《周易明珠——八卦城》,载《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杜殿卿:《易学对伊犁特克斯八卦城选址规划的影响——八卦城“风水”浅析》,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至于人的行为,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最直接的反映莫过于元朝,不仅朝代以“元”命名,而且元代皇城——元大都城门的名称完全根据《周易》卦象取名:南垣正中为丽正门,东南为文明门,西南为顺承门,东垣正中为崇仁门,东南为齐化门,东北为光熙门,西垣正中为和义门,西南为平则门,西北为肃清门,北垣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王玉德:《试述元代易学与文化》,载张涛:《周易文化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至于小的如居住的房舍,埋人的墓葬等,甚至生产工具的变化及所反映的文化形态,都或多或少地与易学文化相联系。应该说,中国少数民族易学文化即完全可以从中进行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除了一些重点问题而外,还有一些难点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域易学与少数民族易学的关系问题,而目前最大的难点问题就是所谓贵州荔波水书《连山易》的问题,目前已发表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潘兴殿:《水书专家认为:水书或为失传已久的〈连山易〉》,载《贵州民族报》2010年11月3日,第A04版;阳国胜、陈东明、姚炳烈:《水书〈连山易〉真伪考》,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阎朝科:《荔波泐睢连山易连山神农故里书——贵州荔波水书〈连山易〉历史渊源大解读》,载http://29938690.blog.163.com/ blog/static/3182482320089691854,2008-10-06。,基本上是肯定水书《连山易》即是失踪的《连山易》,“水书”被水族称为“泐睢”。泐,源于古汉语,是“文字”的意思。“睢”是水族自称,合起来就是水族文字或水家书的意思。学界对照历代有关《连山易》的评说,认为水族文字比甲骨文更古老,并根据古册反映出的信息在湘西地区找到了《连山易》原创地。据研究,这部新“发现”的手抄水书厚达350页,且抄录者的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字迹清秀、稳健、工整,把很多水族文字翻译为汉字,消除了不少水书象形字符。抄本还对传统的《水书·明晰分割卷》进行了改编,按照天干、地支年份等进行编排。学界甚至认为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连山乡,就是《连山易》的原发地,并且在其周边还相继发现了反映《连山易》的连山八卦庙……无论如何,像这类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易研究中还有不少。其他一些问题如在土家族地区传承的问易诗即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圣人同民患,贞晦谁发覆?” “吉凶悔吝生,何以明兆繇。”这些问题是易学内容自身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中应逐步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曾有“易学为中华文化之源”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否对中国各民族都具有普适性?从民间信仰层面研究,各民族在自己的信仰文化中,都有与易相通的文化现象及相应的文化观念,并且是各该民族的基础文化观念——行为、事业本身的前导观念,甚至对作为主体的人本身也作相应的易学形象分解,如掌上五行、面上八卦、骨相结构等,这些现象说明,易学确实为各民族文明之源——一系列文化行为都据此而生,一系列文化现象都可从中探寻其源。但是,从文化即是人化的层面说,在这类易学文化观念产生之前,人类却早已创造了自己的多样文化,因而从人类学、民族学甚至文化学的层面,却不能说易学为文化之源。因此,我们可以否认上述说法所具有的普适性。不过,从易学学术的层面,中国不少民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或早期阶级社会,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精英、经典易学,因而根本无法用易学来超前解释那些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即使按照象—数—理的发生顺序,以最初始发生的易象来解释也做不到。因此,在今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中,不仅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论建设,而且还应厘清研究的重点、难点和范围,并且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