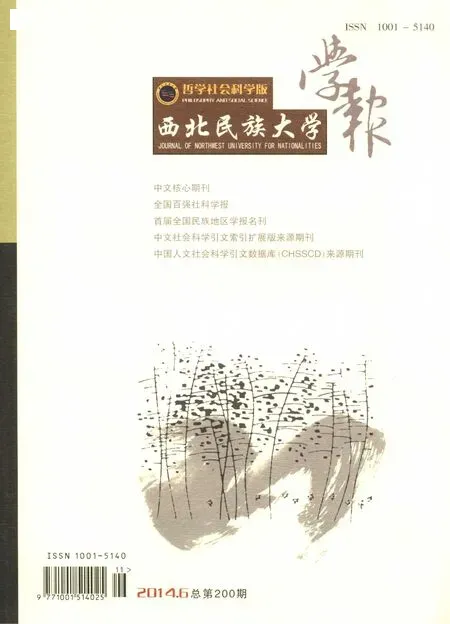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2014-03-03赵翠翠
赵翠翠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200241)
一、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地对于炎帝信仰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的炎帝信仰及其祭祀,也在这种祭祖热潮中不断地得以重构。尤其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的到来,使得该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深刻地体会到炎帝及其祭祀传统重构的重要性。为此,经过20年来炎帝祭祀及其信仰传统的发展,A地已经大致形成了以炎帝祠、炎帝陵和神农祠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与此同时,“就该地区而言,同为一种炎帝信仰,但却因为其组织力量、参与人员、资金来源、祭祀仪式、信仰虔敬与否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信仰类型及其信仰表达方式”[1]。
首先是民间峪泉村神农祠的恢复。峪泉村神农祠的炎帝祭祀,即地方民间的炎帝信仰方式,主要以庙会的形式举办。由于固有的神农庙早已不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峪泉村村民自发修建了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神农老庙。此后十余年,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不断前来祭拜,加之国家“310国道”修建,使得当地村民不得不考虑新神农祠(新庙)的修建。于是,在村民的热心支持及其村民组长的带领下,由峪泉村一组村民集体出资,同时收集四方民众捐款,在原神农祠旧址距离九龙泉30米的“310国道”北侧,建起了一座高大宏伟、巍峨庄重的新神农祠。新祠占地约6亩,殿堂坐落在九龙泉之北,据地基平面高十多米,望之高大而宏伟,气魄不凡。祠内供奉有炎帝神农氏、神农父少典、母任姒以及太阳神、太阴神等神像,以供人们祭拜。每年正月十一炎帝诞辰之日,该地还举办有隆重的庙会及其祭祀活动。
其次,为官方炎帝信仰模式的重构。但这种重构又与民间炎帝祭祀的恢复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民间老百姓对于炎帝信仰的崇拜及其祭祀,尤其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的拜谒、祭奠,使得A地政府逐渐体会到炎帝祭祀对于该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借助于炎帝信仰及其祭祀,A地可以更好地向海内外宣传炎帝故里,从而推动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1991年,A地政府将原神农祠的“神农庙”迁移至市区中心的河滨公园,后改为炎帝园。与此同时,市政府还将传说中炎帝忌日,即农历七月七日,作为“炎帝节”,并于1993年在炎帝祠主办了隆重的首届公祭活动。在举办了三届炎帝祠公祭后,A地政府将炎帝祠公祭的时间改为每年的清明节,迄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
与此同时,作为官民共建的炎帝陵,也在A地神农乡①修建炎帝陵时,该地为神农乡,目前为神农镇。和宝桥厂的联合主导下,于1993年顺利得以修建。这种信仰类型,缘起于1992年台湾民道院一个百人祭祖团到当地祭祀炎帝之后。当他们来到峪泉村九龙泉那座面积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祭祀炎帝,“屋狭器小,来人潸然伤心落泪”[2]。如此情形,迫使当地的地方官员萌发了要在神农乡常羊山修建一个炎帝祭祀场所的想法。作为官民合办的祭祀类型,炎帝陵的建设,既有神农乡政府在修建炎帝陵前期论证中的行政投资,也有民间乡村社会中的集资。在民间集资中,又以宝桥厂为主要投资者②据访谈,宝桥厂当年投资修建炎帝陵时花费近三百万,其社会影响力大为增加。。炎帝陵重修后,每年的炎帝忌日,即农历七月七日,常羊山都会举办有祭祀炎帝的活动。在这其中,既有官员的参与,也有民间自发的民众祭拜,此为官民共建基础上的官民混合式信仰表达。
至此,A地炎帝信仰祭祀的三大格局正式得以形成,并由于其信仰资源、组织力量、祭祀主持人、资金来源、参与人员、祭祀仪式等要素的不同,这些炎帝信仰大体可划分为民间祭祀、官方祭祀和半官方祭祀三种类型。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一个有机的信仰整体,即以信奉炎帝为信仰基础,在同一个区域内、依据其不同的资源、权力、社会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二、权力关系中的炎帝信仰
尽管炎帝信仰在陕西A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达模式,但他们的信仰基础及其核心内容,却都为一个“神性”的炎帝,这是三种信仰类型的交集部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又因为资金来源、参与人群、权力关系、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3]等因素的不同,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关系分殊。
(一)被边缘化的民间庙会
从A地炎帝信仰的复兴及其发展过程来看,老百姓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主要以庙会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具有民族心理特征的信仰,逐渐在地域化的日常生活中,被老百姓演绎为了具有地方“保护神”的信仰角色。为此,炎帝信仰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都存在着神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神农”不仅是人们心中的“老祖先”,是农业之神、太阳之神、医药之神,还是峪泉村的地方“保护神”。
A地峪泉村九龙泉及其古老的“神农庙”,③神农庙,是民间老百姓的叫法,又名神农祠。不但赋予峪泉村神农祠以历史事实的合法性,更是A地唯一遗留下来的能够证明自古至今延续的对于炎帝祭祀的庙会传统。“因为那里原来就是神农庙,几十间房,后来被占了办公,毁坏了”。④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1日。“1993年之前,在峪泉村,后面有个炎帝小庙,就是九龙泉那个碑址,现在是半截子了。那一年,台湾人还来到这里来祭奠炎帝”,⑤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这些不但触动了当地老百姓,更是让A地政府深刻体会到炎帝祭祀的重要性。
然而,九龙泉炎帝小庙没有成为复建“神农庙”地址,神农祠更没有因此而获得资金等方面的权力支持。对此,有人指出了其中的缘故,“那个地方太小,310国道也在那里,环境不好,不适用了”。①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5日。可见,峪泉村当时的一间小庙及其九龙泉,虽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只属于民间庙会性质。每次庙会主要基于峪泉村及其周围村落民众的参与。虽有仪式承包者、庙管会的全权负责,且有小组集体资金在重大事件上的某些支持,但大多数时候则只能依靠于民间集资,其影响力有限。
更为重要的,在炎帝信仰的神圣性建构方面,政府通过对“神农庙”的迁移,重建并以其公权力认可了炎帝信仰的正统,从而在新的场所中建构出了政府公权力所定义的炎帝祠。尽管如此,九龙泉之神圣的遗址,还是受到A地政府的重视,只是他们在这其间忘却了神农庙,而只在乎炎帝赐予的“圣水”。因而,在A地政府主导下的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典期间,地方政府就有专门通过民间理事会成员,在九龙泉及其神农祠前举行过盛大的“取水”与“合水”仪式,并恭读祭文,借用九龙泉之“圣水”②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3日。的名义,以炎帝信仰的显圣与灵验,为炎帝陵祭祀建构其信仰的神圣性。
在此不得不说,九龙泉之“圣水”,是地方政府建构炎帝陵祭祀大典的合法性依据而已。对于神农祠而言,取“圣水”和“合水”的过程,他们还需要召集人群,配合相关工作。所以,峪泉村神农祠那里,“纯粹是民间的,政府不在那里去。遗留下来的主要是以村上为主体的,镇上也不参与。现在民间的话,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了”。③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6日。从根本上来讲,九龙泉及其神农祠,只是A地政府举办炎帝祭祀大典的调味品,处于配角地位,其影响力也只能局限于一地一隅,处于被边缘的地位。
(二)炎帝祠公祭的正统化
作为市政府主导下的炎帝祠祭祀,无疑是公祭性质。在此祭祀礼仪中,市长主祭并代表全市公民宣读祭文,朗诵的都是四言诗句构成的祭文,象征着政府公权力对炎帝信仰的最大认同。因而,炎帝祠祭祀场面宏大而庄重,成为炎帝信仰正统之体现。
在权威性资源的整合度上,炎帝祠祭祀因为公权力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从而走上了一条政府建构的道路。其祭祀规格、资金、规模、参与人群等都有组织化的保障及其安排。其模式已经程序化。
炎帝祠是市区内的旅游景点。炎帝祠祭祀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从仪式过程来看,有击鼓鸣钟,统一着装(黑色或蓝色),有锣鼓队,唢呐队,彩旗飘飘,龙飞凤舞。有56面红旗,代表着56个民族。在祭祀的内容上,炎帝祠祭典不光是一种单纯的祭祀,它还融入了很多现代性的纪念祖先的方式和元素,比如“用鞠躬替代了民间的那种九扣八拜,献花篮后三鞠躬,最后围绕着炎帝大殿瞻仰”。
在仪式承包者方面,炎帝祠祭祀有专门的承办单位。每年的清明节公祭,炎帝研究会和炎帝园相关人员具体负责落实。炎帝研究会属于具有法人资格代表的社会团体,政府给予专项经费支持,且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以供日常事务的处理;炎帝园则为国家级重点公园,“炎帝祠”属于事业编制单位。
炎帝祠公祭纳入到了公共财政预算中,属于专款专用。从参与人员上来看,炎帝祠公祭虽有学生群体参与,但大多为市级、区级、县级工作人员。
炎帝祠祭祀的本身是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传承炎帝文化及其信仰建构中,希望提升该地的知名度,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三)炎帝陵祭典的流动性
虽然,炎帝陵和炎帝祠于同年开始举办炎帝祭祀,且炎帝祭典已成为国家“非遗”,但炎帝陵实乃桥梁厂和神农乡的官民合办性质,是国家2A级旅游景区。20年间的祭祀历史中,炎帝陵祭典既有最初以民间为主的祭祀模式,也有2003年十年大庆之时,公祭与民祭的合二为一;在此基础上,更有三次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典期间,以A地政府为主导,区级政府承办的公祭形式。
可以说,炎帝陵祭祀的信仰表达方式及其性质,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既不同于官方主导的公祭,又不同于纯粹民间庙会式的信仰表达,它处于一种官方与民间的中间状态,其性质在“公祭”与“民祭”之间,“不是私办的,也不是公办的。算是合办的,自负盈亏”。①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1日。由此也体现了炎帝陵祭祀之极为明显的流动性色彩。
虽然,炎帝陵的修建,乃官民合办性质,但由于炎帝陵祭祀内容丰富,及其对A地重构“炎帝故里”的重要性,为此,区级、市级政府在炎帝陵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使得炎帝陵的面貌焕然一新。由此,炎帝陵祭祀能够借着区级、市级政府的支持而建构了官方化祭祀的表达形式。
但在炎帝陵具体的管理事务上,政府与炎帝陵之间却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具体运作则以桥梁厂和镇政府两家为主,且桥梁厂占据主导性,属于自负盈亏单位。在炎帝陵的祭祀仪式上,虽然祭祖大会期间,官方对比较复杂的祭祀礼仪细节做有部分删减,且加入了很多提升文化内涵的现代化表达形式,如音乐、古筝等,但炎帝陵祭典总体还是保持了民间祭祀的原汁原味,如唢呐迎亲、沐浴圣水、幡旗阵、农祭、乐祭等民间祭祀环节。
仪式承包者方面,虽然早期民间理事会②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4日。在炎帝祭祀仪式的编排及其祭祀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官方性质的不断参与,民间理事会也逐渐淡出了这一祭祀系统,成为地方政府随时可以支配的民间资本。这一力量的淡出,甚至出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炎帝陵祭祀对于信仰炎帝的社会大众之吸引力。
另外,随着地方领导的换届、退任、调离等,炎帝陵祭祀也陷入一时的停滞状态。就连曾经投资修建炎帝陵的宝桥厂,现今也因为厂长换届、上市等原因,而停止了投资。
可见,地方权力关系及其资源动员体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炎帝陵发展前途的黯淡。因此,炎帝陵的发展规划筹划多次,却总是不了了之。
三、炎帝信仰表达的内在逻辑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三种信仰类型的表达及其实践,虽然基于同一个炎帝信仰,但却具有不同表达特征,其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信仰同一个神性:即炎帝信仰,但却具有实实在在的分殊呢?
(一)灵验为特征的民间崇拜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信仰在中国人的信仰结构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虽然史学家关于炎帝之称谓争议很大,有炎帝、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等。但在民间老百姓看来,这些区别似乎并不重要。尤其是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A地,由于深受炎帝“生于濛峪、长于瓦峪、沐浴于九龙泉、成于姜水、俎于天台”历史故事的熏陶,民间老百姓们对炎帝的传说及其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对老百姓而言,炎帝不仅是人文始祖,更多的是发明医药、粮食和创造交换贸易的伟大神,他们亲切地称炎帝为“神农”、“神农爷”或“爷爷”。这点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都具有神化的信仰特点,且大多以灵验为特征。
一个村民这样说道,“一间小庙的时候,里面的地母娘③“地母娘”在峪泉村村民那里,即为炎帝母亲,且有专门的庙会。每次庙会时,“神农经”和“地母经”都深受峪泉村民所喜爱。画像是他画的。他好像把九龙泉里的太湖石伤了,后来生病了,害怕得不得了,人家给他托梦了,他就画了像给人家放在庙里,现在病好了”。④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1日。“有一些私家老板来祭祀,祭祀之后他觉得生意兴旺,越兴旺就越是来拜。还有外地大老板,买的那种香,又长又粗,一大股。还有一些企业老板也来祭祀”。⑤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4日。“基本上我有啥事情,都会实现的,都是非常灵验的”。⑥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4日。“七月七日毕竟是炎帝祭日,除过烧香叩拜,拿点膜,面,拿点水果,有些人还做些衣服,给炎帝搭红。这些都是把炎帝神化了,把炎帝当作神来看待。”①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4日。可见,对于信仰炎帝的社会大众而言,灵验是民间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倾向于将这种信仰与生活结合起来。对于那些经常“跑庙”的人来说,即使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灵验的事迹发生,但也会因为经常“跑庙”或做“功德”而受到炎帝的护佑。比如,“我家里各方面都挺顺当的,我觉得在庙上干事情,家里也平安”。②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7日。“我在炎帝陵这里身体很好,没生病。两年了,我没有吃药,要说好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好处”。③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4日。“天台山办庙会,红头绳,拿回去之后吉利,不生病么。挂个红腰带,各人都安全。但不能做对‘神’不好的事情。你看我没有打过吊针,没有住过院,一般没有什么大病”。④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9日。在此,平安、健康、吉利等也是灵验的表达特征。在此,炎帝信仰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因为炎帝信仰,而获得了某种内心的安定、超脱与世俗的利益。
(二)神圣资源配置与合法的炎帝信仰方式
所谓神圣资源,是所有资源中的最基本的资源。而神圣资源配置,就是对神圣资源进行的分配。这里的神圣资源放在具体的民间信仰个案中,就是那些占有合理的、民间信仰形式的拥有方。在某种情况下,神圣资源占有方,甚至就是建构信仰及其信仰方式的主体。
从此角度来看,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之构成,无疑是由于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而形成的产物。具体而言,谁占有的资源越多,谁在此神圣资源分配中就占据主导地位,谁也就越具有分配神圣资源的权力。炎帝信仰的三类信仰类型,占有的是同一种神圣资源,但他们各自所占据的资金、人群、权力关系、仪式承包者等却不同,这些都是影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方式的重要因素。
作为占据神圣资源最多的A地政府而言,它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分配神圣资源的能力。虽然A地政府一开始考虑到神农祠开发对炎帝祭祀的重要意义,也顾及到神农乡政府和宝桥厂联合修建炎帝陵的作为,但基于公权力的考虑,它最终还是以“神农庙”的迁移建构了炎帝祠及其祭祀的合法性。因而,当民间致力于修建炎帝陵时,A地政协、市委就已经决定在炎帝园内修建了炎帝祠。
这种官方化的信仰建构方式,不但说明政府对神圣资源具有先天的占有优势,而且它在建构神圣资源的合法性上具有绝对的象征权力。为此,炎帝祠祭祀在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体现了极为明显的官方化特点。
作为三种信仰类型中,最具特色的炎帝陵属于原神农乡与宝桥厂的联合修建,乃官民合办的股份制性质。因而,与政府主导的炎帝祠公祭相比较,它占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同时,炎帝陵最初的修建,也有其自身合法性:即炎帝生于濛峪所在的常羊山。传说炎帝的母亲“游华阳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为此,常羊山为炎帝托孤之地。此外,依据民间说法,炎帝虽然俎于天台山,但其埋葬地应为出生地濛峪,因为按照“生于此,葬于此”的选择也是合情合理。
然而,这种官民合办的炎帝陵祭典,仍然无法与政府主导下的炎帝祠公祭相媲美。虽然,在20年间的祭祀历史中,由于仪式承包者的身份及其所占据的可支配性资源,炎帝陵祭祀曾经出现过一度辉煌,影响力极度上升。但随着权力支持系统的变更,炎帝陵祭典一时间也陷入了沉寂,甚至回到了最初的祭祀形态,祭典本身体现了极为明显的依附性和流动性。
与前两种信仰类型相较,民间庙会式的表达,其拥有的资源就更少了。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邱氏集团的人最早来寻根问祖,认为最早的是峪泉村九龙泉”。⑤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9日。炎帝陵举办全球华人祭祖大会时,地方政府也曾专门在九龙泉举行过盛大的“取水”与“合水”仪式。但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存在方式,峪泉村神农祠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视野中,处于被边缘或非正统性的地位,似乎只是民间乡村社会的信仰习俗而已。
这就是说,一种神圣资源一旦纳入到公权力的配置资源内,它便能够表达出炎帝祠式的公祭模式,祭祀规格及影响力大为增加;一旦没有被这种内在的关系格局所整合,便会呈现炎帝陵式的信仰表达困境,甚至只是民间神农祠的信仰表达模式。
(三)炎帝信仰与权力关系的整合
从A地炎帝信仰的社会建构过程来看,无论是炎帝祠、炎帝陵,还是神农祠,都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权力关系格局。这不但导致三种信仰类型呈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还使得他们在这个关系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就此而言“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5]。“这里的权力概念,就其与信仰的深层关系而言,是一种‘象征权力’或‘符号权力’,是通过权力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垄断而展现出来的象征权力。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构成,并存于社会权力的建构之中。神人关系的背后,蕴藏的是‘权力’”[6]。
所以,当权力关系及其动员的资源,成为炎帝信仰建构的必要条件时,炎帝祠祭祀就成为正统信仰的象征。因而,炎帝祠祭祀有专门机构从事炎帝祭祀的组织活动,且有专门的经费来源。在此“正统信仰”的光环笼罩下,官民合办的炎帝陵祭祀和民间神农祠等祭祀,就只能视其为非正统的民间信仰,是民祭模式。
为此,在资源的分享及其权力关系对于炎帝信仰的定义与定位过程中,炎帝陵和神农祠祭祀,无疑处于民间非正统地位。尽管对于炎帝陵而言,曾经由于A地对炎帝故里之打造,在炎帝陵十年大庆及其三次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典前后,炎帝陵祭典获得了市级、区级最大力量的资金支持,炎帝陵祭典也曾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公祭形式。但这种阶段性的被纳入官方体系的信仰形式,并没有由此而获得某种稳定而持续的发展。相反,一旦利益无法被公权力所分享,失去的便是公权力的支持,甚至会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与此同时,炎帝陵的自负盈亏性以及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炎帝陵祭典的祭祀形式、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等受到了很多影响。
总体而言,虽然炎帝信仰在A地呈现三种不同的信仰表达模式,但却都是基于一个炎帝信仰而来。官方之所以能够建构出炎帝祠公祭那样常态化的运作模式,其最初便源自于民间神农祠庙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首先恢复;炎帝陵的修建,亦是同步于炎帝祠。只是在建构主体上,当时的神农乡借助了这样的恢复性契机,和A地宝桥厂进行了联合式修建,从而呈现出官民合办式的信仰表达模式。至于民间神农祠的庙会式表达,则由于没有和这种权力关系进行某种有效的整合,只好呈现一种信仰的地方化特色。
它说明,“一种信仰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大多是权力、资源、人群、利益与地方力量之间的整合。一旦这种整合形成强大有效的力量,便可以促成某种信仰类型的建成。反之,这种整合形式一旦失效或出现了某种偏离,则会促使信仰本身遭遇一种多种利益关系、公共权力和地方利益难以平衡的困境,最后酿成如炎帝陵陷入困境的那种僵局”[7]。
然而,一旦官方需要民间给予其神圣性资源的供给,这种民间信仰的表达逻辑也会被加以整合。也就是说,“正祀”与“淫祀”,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的转换,只是这种转换会呈现出民间信仰表达的不稳定而已。它与官方所建构的常态化运作模式相比,具有一定的临时性边界。同时,它的“兴与衰”,也更多地建立在是否获得“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
四、炎帝信仰的两种话语体系
就A地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及其表达特征而言,炎帝信仰虽然体现出三种不同的信仰类型,但其背后却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种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都是在祭祀炎帝,但其炎帝观却有明显不同。官方在祭祀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民间则在祭祀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它们是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两种话语体系。
(一)隐喻官方权力公祭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上的炎帝,对于A地来说尤为重要。它不仅在近年来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建构了一种文化及其旅游上的品牌,还使得A地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炎帝故里。
对于A地而言,炎帝祠公祭不但为公权力所主导,还为官方权力所建构的炎帝信仰类型,其关注点在于炎帝祭祀所带来的地方经济、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此,炎帝祭祀无疑就是一个文化品牌,是一种能够带来诸多利益和资源的象征符号。所以,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清明节公祭不但是A地开展的一项重大庆典活动,也是要通过祭祀这样的形式,来宣传“A地乃炎帝故里”的历史事实,从而带动和宣传A地。因而,三次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举办之时,每次祭祖活动就是与招商洽谈会结合在一起,这就完全不同于民祭形式。
因此,炎帝信仰及其表达,因为官方权力的建构而得以复兴。“A地的炎帝祭祀活动已经持续20年了,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多次大型集会和研讨会的举行,天台山、炎帝园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重点公园的批准,大型电视连续剧《炎黄大帝》外景拍摄基地在A地的落户,在某种程度上,亦得力于祭祀炎帝典礼活动的连续举办”,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完善清明祭祀炎帝典礼,使其成为A地的一张文化品牌、名牌,在彰显炎帝故里、华人老家的同时,促进A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8]。由此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
因此,官方主导的炎帝祠祭祀,无疑是公权力的象征符号,隐喻的是官方化的权力结构及其地位。相比较民众所信仰的炎帝而言,“官方没有把它当作祈福,而当作一个大的活动来宣传A地,打造炎帝文化品牌,打造A地知名度,增加A地影响”。①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因而,“炎帝祠修好了,当时就是为了增加炎帝园人气,增加门票收入”。②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5日。“有了发展经济意识了,就想办法招商引资,引进项目”,③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7日。并非出于一种信仰上的考虑。
对于政府来说,只要你没有干扰我的公祭,也就最大限度地容忍不同于公祭的“私祭”[9]。这就是说,那种民间所谓的炎帝祭祀,不但在官方权力的眼中处于“私祭”或“淫祀”地位,而且正是出于这样的权力格局,民间神农祠祭祀等,并不影响官方所建构的炎帝祠公祭。即使是炎帝陵祭祀,“都是民间性的,也没有啥形式了”。④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5日。在其祭祀性质的认定上,“显然是民间的,是神农镇和宝桥厂合修的,这个和政府不粘关系,原先政府还有些不承认呢”。⑤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此外,“政府还把炎帝陵作为景点来接待,算是政府有个接待办了”。⑥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7日。
在此情境下,一方面,炎帝陵由于自身所面临的体制不顺,经营不善等诸多问题,希望A地政府能够与其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摆脱其发展困境。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整合所需资金庞大,炎帝陵的性质又乃宝桥厂和神农乡联合修建性质,因而,A地政府始终没有参与炎帝陵内部的管理,只是在祭祖大会期间,借用炎帝陵的万人广场,同时也借用民间峪泉村九龙泉之“圣水”进行祭祖而已。
另外,在近20年来的祭祀历史中,炎帝陵还为地方树立了形象。政府从旅游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搞公祭,并非出于信仰的考虑。
为此,炎帝祠公祭才显现出诸多特征。受此影响,炎帝祠内部的设置及其管理无疑也带上了官方色彩。在其信仰的仪式表达中,也凸显了国家“正统化”的符号象征。所以,官方所公祭的炎帝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炎帝,且掺杂有经济、旅游发展等利益考虑,此乃官方权力公祭之隐喻性表达。
(二)神灵应验为核心的民祭
尽管在公权力的眼里,炎帝是一个具有打造炎帝故里,提升A地经济实力的文化象征符号,但对A地的老百姓而言,炎帝则是具有神性的人物,他能够为民众的身体疾病、家庭和睦、发财致富等实际需要,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安慰。这也就是为何民间峪泉村神农祠的祭祀和进香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一批老太太的带领下逐渐恢复起来,而作为官方主导下的炎帝祠公祭则晚至1993年才得以恢复的根本原因。
因为“普通民众最关心的并不是政府公祭中的先祖,而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10],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中的信仰所需,且这种需要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是普遍存在。虽然炎帝在官方看来,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很容易将其神化为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神灵。这就将民间信仰和对始祖炎帝的敬仰,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为此,峪泉村村民常常称炎帝为“地方保护神”。
这就是说,作为正统信仰及其价值系统,炎帝是华夏始祖。为此,炎帝祠每年都举办有隆重的公祭仪式,以纪念炎帝之丰功伟绩。这套仪式及其理念,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炎帝是伟大的人文始祖,并非神灵。所以,炎帝祠公祭的仪程安排中,并没有敬献三牲五行等仪式,只有所谓的敬献花篮等环节,祭拜礼仪也并非民间仪式中的磕头、烧香,而是一种毕恭毕敬的鞠躬仪式。
然而,这套仪式和标准并不会成为民间老百姓对于炎帝的祭祀礼仪。在当地村民的观念中,炎帝之所以值得去祭拜和祭祀,并不是所谓血统或是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先祖及其认同,而是他们心目中所定位的那个“神”。这位“神”不但曾经为人类社会做出过贡献,如创造粮食,发明医药、首创贸易等,还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信仰需求。
在民间老百姓看来,炎帝是“一位高尚的很有道德的人。他受人尊敬爱戴,所以人们尊为神”。①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峪泉人对于神农炎帝都比较重视。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好像神农(即炎帝)会惩罚。因而,炎帝的神像应该是独立的,没有任何第三者,他是很独立的神像。”②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5日。“老百姓自古到今把炎帝看作一个信仰,当作‘神’来看待。他给人们带来农业、医药、太阳,A地风调雨顺,都是炎帝保佑着呢。每次烧香后,都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安静,给家里带来安康”。③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
为了更好地纪念炎帝,神农祠每隔两年唱一次大戏,平常时候以小戏代替,“以庙会为中心,为神而唱戏,唱戏的时候八方四邻的人都来,占神的光。为啥呢,他们认为这是给神唱戏呢,神就可以保佑村上今年平安,五谷丰收。所以唱戏的时候,人们就像过年一样,在外地的人也回来了”。④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27日。这样以庙会为中心的信仰表达模式,也是老百姓最为喜欢的信仰方式。
在民众的眼里,无论官方炎帝祠的祭祀如何隆重,场面如何壮观,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炎帝能够保佑的,能够求得平安、健康、财富等愿望的,便是他们最喜欢的。尽管炎帝乃祖先崇拜,但依着中国人对人神关系的宗教化心理,老百姓更喜欢将炎帝看成是能够保佑家庭幸福、和睦、生意兴隆、儿孙满堂、一方平安的神灵。
因而,民间在修建神农祠时,尤其是在神农祠的座底高度及其房檐时,就有很特别的要求。“为啥现在这个庙台子高于人大概两米呢?我嫌庙的台子低得很,土话就是说,神就是要高高在上,而且这个神是保护一方平安呢。所以庙应该高于310国道那样,还要四面淌水的那种”。⑤32MQY39访谈记录,2013年7月12日。在此,人们已经将炎帝神圣化,体现出了“神高于人,神尊于人”的信仰特点。
这种将炎帝信仰神圣化的表达,还表现在炎帝陵和神农祠的开光仪式上。“炎帝陵修成了,炎帝没有神气。作为道士来说就诵经,从这边拉些红线啊,然后沿着红线,九扣八拜,烧香磕头,然后诵经。沿着这个线走过去后,给炎帝点眼,当时还是红绸盖面,把光一点,这就算开光了。开始还是泥土,现在就是神了。然后烧香的,磕头的,敬献花篮的,就开始拜啦”。①民间理事会,1992年炎帝“移陵”之时成立。1993年改为“神农地区风景名胜理事会”,是神农乡政府认可下的,民间自发形成的理事会组织。每年炎帝陵祭祀大典之时,政府都要安排该组织进行祭祀方面的准备工作。近些年来,由于官方的不断参与、理事会成员年龄增大,该组织逐渐淡出,甚至已经出离。
可见,在中国人的信仰意识中,无论庙、祠修建后,只有经过了开光仪式后,似乎才会具有神性。在此,祖先、神灵的信仰交织在一起,但却并不影响人们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表达。
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权力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心目中所信仰的炎帝有着极为不同的表达逻辑。对于公权力而言,炎帝是伟大的人文始祖,是一个“文化建构资本”的象征符号,还有淡化其信仰内涵的倾向,是公权力的象征;但对于老百姓而言,炎帝则是人们求健康、求发财、求平安、家庭和睦、兼具佛道教信仰的神圣符号,是“信仰”和“信俗”的整合性产物。虽然“公祭”与“私祭”的目的不同,同一个神性的炎帝,却变成了两种不同的符号,虽不冲突,但却难以彼此整合与认同。
就此而言,“炎帝信仰的社会建构所体现出来的两大逻辑: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他们是‘同信但不同德’、‘信仰但不认同’的社会建构。在此,‘正祀’与‘淫祀’的信仰传统,已经被‘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予以替代”[11],它并没有直接转换为当代民间信仰类型的合法性要求。炎帝信仰能否被公权力所整合,“信仰的神圣与世俗、信仰能否构成一种社会认同的普遍性价值规范,不完全在于信仰的神圣与否,而在于建构信仰中的现实利益、权力关系与信仰本身的彼此整合。”[12]
在此情境下,恰恰是基于同一种信仰,经由人际关系、资源、权力、利益关系的建构结果,反而使得同一种神性的炎帝信仰,却因为建构炎帝信仰的多重现实关系,从而形成了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互不认同,最终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认同难以建构的挑战性问题。
[1][7][12]赵翠翠.信仰类型及其社会建构——以陕西宝鸡地区的炎帝信仰为例[J].民俗研究,2014,(1):150,150-151,151.
[2]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A地炎帝陵[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193.
[3][11]赵翠翠等.“仪式承包者”与民间信仰类型的建构—以陕西炎帝信仰及其精英关系为例[J].世界宗教研究,2014,(3).
[4][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Z].
[5]李向平.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5).
[6]李向平.两种信仰概念及其权力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2).
[8]霍彦儒.完善炎帝祭典彰显华人老家—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公祭炎帝典礼的构想[EB/OL].2012年4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3881a01014dol.html.
[9][10]黄剑波.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人类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