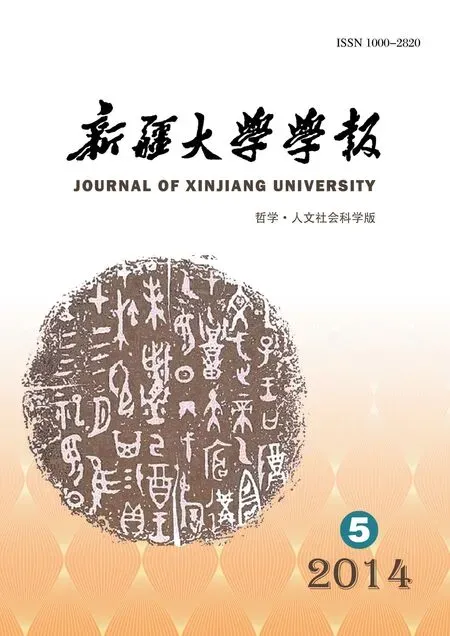阿拉提·阿斯木的超越与创新
——读《时间悄悄的嘴脸》∗
2014-03-03翟晓甜
翟晓甜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宁835000)
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坛上,阿拉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领军式人物。近年,他的创作走向了繁荣期与多产期。2012年6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蝴蝶时代》,其中选入了7部中长篇,反响很大,在上海专门开了座谈会。如果说,阿拉提早期的小说创作在语言上还带有比较生硬的“半维半汉”的特点,甚至还有许多不合乎汉语规范的言说方式,而今他的创作已经巧妙地融合了维吾尔语最通俗、最准确、最独特、最幽默的表现形式和汉语最优美、最含蓄、最清晰、最可爱的形式,把两种文化最精髓、最值得玩味的方面结合了起来。静心品味《时间悄悄的嘴脸》(以下简称《嘴脸》)①文中所引内容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时间悄悄的嘴脸》。,阿拉提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的标新立异的反常规的表现形式与他特有的语言风采!
阿拉提善写社会底层人物,展现的是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揭示人性中的不完美,将人性尽情展现,《嘴脸》也是如此。他设置的人物,常常是让其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然后让他们在人生“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浸泡、洗刷身上的污垢,慢慢地净化灵魂,一步步走向觉醒、顿悟、忏悔,最终让人性的光辉回照人自身。所以阿拉提小说中的“坏人”,最终都能悔过自新,改邪归正。这是阿拉提创作中一直固守的传统,《时间悄悄的嘴脸》在人物设置上仍然坚持了他的一贯风格,讲人性、讲人性的缺憾与人性的回归。在此基础上,这部小说有了新的突破,在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达上,都有了新的超越与创新。
一、直线型的情节设置,带给读者轻松、愉悦的美感享受
小说作法,自古至今,无论是文学理论家,还是小说家,讲究的是能否打动人心、震撼灵魂,可否引起读者的“共鸣”。崇尚的是经世致用。所以在情节上,追求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在事件选取上,力求离奇惊悚、在叙述方式上,讲究虚实结合、明暗交叉,或多条线索齐头并进铺展故事。追求的是让读者产生震撼人心、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使读者与小说中人物同喜同悲,阅读的过程成为了读者“背负”喜怒哀乐情感负荷的过程,读者承受着故事带来的“负担”,确实达到了“撄人心”的效果,这也是文学创作追求的境界之一。
与众多的小说家不同,阿拉提的创作决不是以动人的情节取胜,也不是以精彩的事件吸引眼球,更不是以猎奇的噱头哗众取宠。表现在情节设置上,他采取了平易、简洁的叙述方式,按照事件本身发展的顺序,娓娓道来,加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读者特别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阿拉提擅长揭示人性之美,写人的欲望,这应该是个有些沉重和严肃的话题,他写得也非常赤裸,非常直率,但又非常轻松自然,不压抑、不沉重,充满了飞扬的生命气息,读者能在极其平和怡然的状态下,认识和思考人的欲望。而不是简单带领读者去“窥探”欲望世界,
在情节安排上,这部小说分为三十五个章节,根据内容,篇幅有长有短。故事从主人公艾沙麻利“出逃”拉开序幕。情节依次展开:艾沙麻利误以为自己杀死了哈里,于是在一个黑夜里乘飞机逃亡。哈里并没有死,只是被艾沙麻利打断了一条腿。而远在上海的艾沙麻利并不知道,于是他“决定”易容,在他的肝胆朋友王仁医生的诊所做了一个精致的面具,并以米吉提为名,从此带着新的人造嘴脸出没。他在上海开始以艾沙麻利朋友的身份“遥控”家乡的朋友,托他们照顾好母亲米娜娃儿,同时在家乡,哈里害死了艾沙的弟弟开沙尔,并且霸占了艾沙家祖传的大宅院。弟弟死后的第五天,艾沙带着“别人的嘴脸”(米吉提)回到了家乡。在“朋友中间”,在“亲人中间”,怀着“贼心贼胆”,“请客吃饭”,在河边在城墙边,在昏暗的夜市,悄悄地谋划向哈里复仇之事。母亲米娜娃儿从气味上认出了儿子并洞晓儿子复仇的计划,于是规劝,艾沙有所触动“一切生命属于真主,他要迅速放下屠刀,在真主的阳光下忏悔!”艾沙回到上海,找王医生恢复了“自己的嘴脸”后返回故乡。
情节的大致安排上,阿拉提采取的是一种惯常的结构方法,即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清晰明了地叙述故事,当今读者在快节奏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对阅读更追求快捷、轻松、省力、娱乐,阿拉提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这一需求。虽然阿拉提用的是最常见的顺序安排故事情节,但是他却用最不惯常的表达方式来讲自己的故事。简单快乐,以语言的魅力征服读者、愉悦读者。阿拉提虽然不是写喜剧,但读他的作品,让人喜悦。他的叙说,已经形成了自己风格特点,他对汉语的运用虽然不能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但却是行云流水般自在自然。既能“阳春白雪”,又能“下里巴人”,雅俗共赏,充满情趣。
二、“时间”、“嘴脸”与“忽悠”:超长使用的惯用词语
综观阿拉提的汉语创作,尤其是近几年的汉语作品,给人最深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新奇,既平俗又雅致。从《蝴蝶时代》到这部《嘴脸》,一些阿拉提惯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不时跳入读者的眼睛。诸如:伟大的、亲切的、不要脸的、温暖的、民歌、西域河、抓饭、热包子、时间、嘴脸、忽悠、野罂粟等等。而在《嘴脸》中,“时间”、“嘴脸”、“忽悠”等关键词的繁复、变幻、超常的使用,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在《嘴脸》20余万字的文本中,“嘴脸”一词出现了216次。平均每一千多字就会出现一个“嘴脸”的字样。如此繁复、超常规的使用同一个词,原本是创作的大忌。但仔细品味,阿拉提对“嘴脸”一词的运用,灵活多变,诙谐睿智,形象生动,对汉语娴熟自如的运用,表明了阿拉提驾驭汉语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嘴脸”一词在汉语中,是贬义色彩很浓的词汇,阿拉提说:我所写的这个嘴脸,根据叙述对象的需要,在不停的变换。它的变化,是根据人物的变化,根据人物内心的需要来达成的。在静止的时间、流动的时间和精神层面的时间里,通过嘴脸的变换,我再把嘴脸应用到不同的形式和内涵的需要当中去。“嘴脸”一词在小说中,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含义:
1.表实指:即指人物的面容、脸面、面貌。
“嘴脸是美女,脾性是男人。”
“哈里绷着嘴脸说,怎么结账?”
2.表象征和抽象:
“嘴脸比较干净的艾买江老板站起来了······”(品德)
“如果我有那样的心,我会是现在的这个嘴脸吗?”(状态)
“善良了,才能有嘴脸和尊严。”(人格)
3.表指代和比喻:
“和那个人一起用掉几麻袋盐巴,才能了解他的嘴脸”(品德)
“我的灵魂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嘴脸”(德行)
“没有人能说清世界的嘴脸”(自然面貌)
“艾沙麻利掏手机停了几句,嘴脸紧张了。”(面部表情)
“最新的钱也不能收买他的嘴脸。”(人心)
“艾沙麻利灵魂和旧有的嘴脸安静下来后,开始用代表新嘴脸的名字活动。”(身份)
“但是他不能丢下母亲出国,只舒服自己的嘴脸。”(肉体与灵魂)
作者有意地、故意地将“嘴脸”一词用到极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时间悄悄的嘴脸》的题旨与意蕴。
小说中出现最多的还有“时间”一词,这是个抽象而带有哲学意味的词汇,我们会在不经意时,就被阿拉提带入了复杂的、诗化般的哲学迷宫之中。他的许多充满哲理思索的语段均与“时间”相关:“时间继续忽悠普天下的嘴脸”,“时间在很多的时候是多面人,它今天包容你,明天又忽悠你,看你的把戏”。“故乡是一个男人最后的时间。男人或贫穷或屁股上流油,他都要回到故乡来丢人或风光。”
阿拉提让时间成为高高在上的灵物,让人性在时间的舞台上尽情的“舞蹈”,最终却都逃脱不出时间的法眼。但谁见过无形无影无声无息的时间的“嘴脸”?阿拉提对时间的描摹和思考,使得这部小说更增添了哲学的玄妙意蕴。
三、诗化的议论与独白
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阿拉提小说中的议论和独白很多。《嘴脸》也是如此,文本中的议论和独白几乎占到1/3的篇幅,去掉这1/3,故事仍然成立、仍然完整,那么这些议论和独白存在的意义何在?这就不能不说到阿拉提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小说的散文化。散文可以抒情,可以描写,可以发议论。将其手法大量地运用于小说创作,阿拉提是勇敢的实践者。
阿拉提创作中的议论和独白,不露痕迹地、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创作中,与人物、事件、环境融为一体,似议论,又像是叙述,信手拈来,又收放自如,尤其是他将拟人手法引入议论和独白,新鲜活泼,悦人心境。这些议论和独白,有时是深情的诉说:“妈妈,你是能看得清我的灵魂的。我的错,是把简单的日子,变成了没有航标的河流,······妈妈,我要在干净的太阳下忏悔,在月亮下洗清我的嘴脸”。有时是蕴含哲理的人生警言:“时间是看热闹的东西,它在混乱的情绪里,检验人的理智宽厚。人是渺小无能的,真主给我们的时间是吝啬的”。文本中的议论和独白,更多的则是通过人与人、人与动植物、与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雪雷电,甚至是与一个酒瓶子的对话,来营造文本诗意的氛围,来表达作者想要“说透”的问题。这些对白,犹如呓语,给人梦幻般的感受:“······人能看得见天,天能看得见人吗?天怎么能看不见人呢?天甚至能看得见蚂蚁的心。······“它们(鹰)是羊杂碎的客人,而艾沙麻利他们是羊肉的客人,人是大地的客人,大地是蓝天的客人,蓝天是时间的客人,时间是风的客人,风是大地的浪人。此刻,从山顶上吹下来的风,正在窥视艾沙麻利的灵魂。”是呓语?哲语?还是胡言乱语?
这些看似与情节的发展并无紧密关联,也非情节发展所必须的对白,使阿拉提的小说既灵动活泼,又充满诗性之美。阿拉提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的议论与独白,已淹没于小说之中,成为其表达创作旨趣的主要手段。小说的可能性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排斥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和表述方式。阿拉提找到并步入了最适宜于自己的创作坦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阿拉提这部小说的对话描写,均无引号,也不分行,一气连写下来,但人物关系并不紊乱,这种简省的处理对话的方式,也是阿拉提的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
四、每一个绰号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各个民族都有给人起外号的习惯,比如汉民族大多根据人物的外貌特点、生理特点、技能以及品行行为特点给人起外号,《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每人都有一个江湖绰号,如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等等。维吾尔民族天性幽默风趣,他们也喜欢给人起绰号,并以拥有绰号为荣。
阿拉提善为自己的一个个人物取个充满戏谑俏皮意味的绰号。在阿拉提的小说人物画廊中,有绰号者总能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
阿拉提的小说中,人物绰号是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着眼于幽默风趣,也即以俏皮诙谐为旨。阿拉提给他的人物起的外号,往往淡化人物的品行特点,不管这个人物是好是坏,给他的绰号只要新奇有趣、滑稽可笑、让人开心、自然亲切就行,而且,每一个人物的绰号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应该是阿拉提的独创。《最后的男人》中的“阿不力米提面汤”、《蝴蝶时代》中的海沙乳房、玛利亚上海、玛丽克麻利、沙塔尔警犬等绰号的来历,都有一段诙谐的故事,而且往往带有一点“色”的味道,但“乐而不淫”,读之让人忍俊不禁,《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的艾海提老鼠,雅库夫走狗、居来提公鸡、尼亚孜国民党等外号的得来都十分有趣。艾海提老鼠是个最讲信义、最忠厚、最可信赖的人,是艾沙麻利的忠肝义胆的朋友,但“老鼠”的外号如影随形地跟牢了他,尽管他花钱大宴宾客,希望去掉这个不雅的外号,但这个丑陋的外号“只休息了三天,第四天又复活了”。走狗、公鸡也是略带有贬义色彩的称谓,但在阿拉提的人物身上,并不表明其品行的优劣高低。只是个幽默俏皮的绰号而已,小说一开头,就讲到主人公艾沙老板也被冠以“麻利”诨号,说他在艾海提老鼠办理酒店入住手续的“一会儿时间里,艾沙就和前台女经理海丽古丽一个鼻子呼吸了。艾海提老鼠说,哥儿们,你太麻利了。从此,麻利这个外号,就赤裸裸地跟随他了”。阿拉提人物绰号与汉民族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多将诨号放在姓名之后,极少冠于名字之前的。这些绰号都切合每一个拥有者的身份与经历,甚至还会引出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来。从这些绰号中,可以见出维吾尔人诙谐幽默的天性[1]。阿拉提笔下的人物绰号,不管是他刻意为之,还是自然表达,都给作品营造了欢快的氛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欢愉的阅读享受。
阿拉提文本中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议论,都充溢着欢愉色彩。诸如:“那些人······都是一些提好裤子不认美女的东西”,“九十岁的老贼还有未来吗?”“娶小老婆的时代已经睡到坟墓里去了,艾沙麻利说,如果你有心,我帮你叫醒那个时代。”“艾沙麻利和扎克尔地毯开始研究哲学,但是哲学自己不知道。”“我们是真理喂养大的。”“有老婆的人,身体不孤独,有朋友的人,心不孤独。”奇思妙语比比皆是,风趣幽默无处不在。这些鲜活奇巧的语言表达,营造出阿拉提小说的独特意蕴。
《时间悄悄的嘴脸》是一部综合展示阿拉提创作实力的长篇,尽管有些哲理性的议论似乎显得冗长了些,但毫无疑问它当之无愧地居于近年国内文坛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列。作为双语作家,阿拉提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眼界开阔。他既从传统的维吾尔文学中得其精髓,又从汉文学中汲取营养,他既从民汉历史与文学的厚重积淀中左右逢源,又能在当下的文学新潮里获取所好。他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民族。这部新作为新疆文坛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1]张治安,翟晓甜.阿拉提·阿斯木汉语作品创作述论[J].新疆大学学报,2012(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