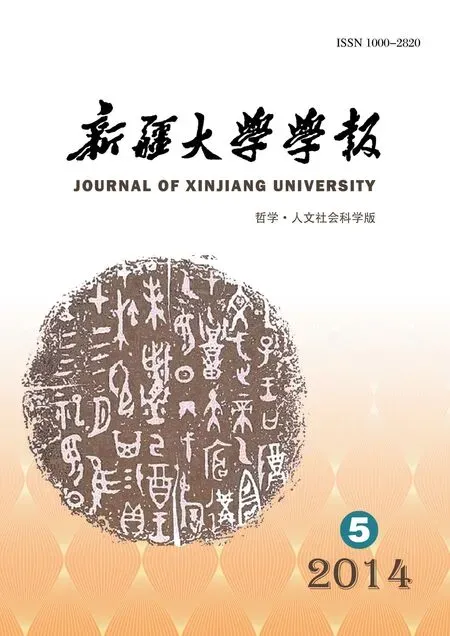乡土化: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创作审美取向的独特选择∗
2014-03-03何莲芳
何莲芳
(新疆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43)
一、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乡土化”内涵
(一)产生小说“乡土化”的丰沃土壤
社会发展或曰社会形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关,直接与三产比例、人口类型、城镇与乡村结构、个人收入来源、就业状况紧密相关。“新疆特别是民族地区,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速度上远慢于内地及沿海地区工业化程度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远低于东部发达省区。”[1]以上情况表明,新疆社会经济处于后发、边缘状态,而以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地区还没有进入以现代工业和服务流通业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折的初期。
新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绿洲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和以草原为中心的游牧文明两种主要的形式。新疆和平解放后,虽经系列社会改革,少数民族农牧区跨越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在民间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基本没有得到改变。新疆以兵团和天山北坡生活着来自关内不同地域以垦荒为主的各类移民,新疆移民社会人口的混成性也形成了新疆移民文化的特征:融合性。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原汉儒文明,另一方面又处于狩猎游牧文化圈内[2],移民文化重视农桑、讲究礼制、天人和谐、人伦有序。
(二)新疆新时期文学汉语小说“乡土化”的边界与内涵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应表现出地方的“土气息、泥滋味”[3]11−12,关乎作者的理想、家园、精神彼岸、是对现实思考的审美再造[4],“是作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审美观对乡土人事的现代性的文学想象”[5]。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乡土中国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作为解剖中国的一个视角,也有人认为“乡土”一词指的是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地域共同建构中形成的一个现代社会学与文化观念,它包括具有独特文化、历史和社会特征的地域上的乡村,也包括生活在这一区域中,受之影响的乡土存在者在现代性历史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形象及其历史命运[6]。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的“乡土”包含五种类型:以汉儒文化为主导反映新疆移民社会生存本相、世态人心和历史变迁;以回望的姿态,对兵团人亦军亦民的垦荒生活、事业、人性的历史反思;对新疆少数民族游牧及耕植生活方式的叙述所包孕的理想追求、故园之恋及自我内省;对乡土社区社会批判、人性反思创作取向指导下的乡土化生活写实;直面乡土现状,以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立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疆乡村现实的思考。
二、“乡土化”——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创作独特的审美取向
新疆对于移民“他乡”与第二故乡的双重性,使移民一方面作为客居者,不可避免追寻故土家园之根,另一方面也创造并皈依着新疆特有的文化,表现出对新家园的体认。
(一)以移民作家的身份写第二故乡(新疆)的乡土,揭示汉儒文化主导下新疆流民社会生存本相、世态人心和历史变迁
1.赵光鸣:以新移民身份,客观再现了新疆流民的命运沉浮与灵魂轨迹。
赵光鸣的中短篇小说对新疆底层走西口的流民缘起、生存样态、精神特点进行广泛探寻。如对新疆汉族流民渊源、构成和移民动机的揭示:流民绝大多数来自陇川陕甘宁湘豫,且流徙的主要原因是保命图存。如《乐土驿》、《绝活》、《西边的太阳》、《石坂屋》、《凉州客》、《三番的岁月》、《穴居之城》等。除此之外,流民迁徙还有政治流亡,文化探寻的原因。如《江尔巴依的金子》中的江尔巴依、《蚁王》中的越南志愿兵“蚁王”、《帕米尔远山的雪》中维吾尔族乡村清教徒式的游吟诗人、苏里坦叔侄等。
赵光鸣的中短篇小说中有大量流民社会生存样态的出色展示与描写。包括底层流民社会乡村生活的主要事件、生存关系原则、流民的审美追求,流民对“根”的寻找、“家园”选择等诸多方面[7]117。械斗、听墙根、奸情,饮食男女是其主要内容(《三番的岁月》、《远天远地》、《鬼村——一棵树》),乡村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权力、势力、性力(《绝活》《郎库山那个鬼地方》《大鸟》)。同时赵光鸣还对流民组成的乡土社群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行了客观再现。
赵光明的小说写出了流民社会的“乡土”情结,“赵光鸣的小说的乡土情结既表现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叶落归根、家族宗嗣观念也表现了对第二故乡的认同皈依这种矛盾而统一的心理······《西边的太阳》是其代表作”[7]118。新疆“她一改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荒寒、偏僻贫瘠的历史与文化指向,带着精神与生存家园的彼岸成了在自然与政治窘境中人们可以‘活人’的地方,成了生存与幸福的彼岸”[7]118。
2.李健:以家族盛衰,展现新疆近现代历史风云,揭乡镇人心奥秘。
李健出版于2012年的《木垒河》,接续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家族小说创作传统:将家族盛衰、人物命运沉浮、乡风民俗写实与新疆近现代历史变迁结合并赋予浓郁的新疆气息。
李健笔下的东天山木垒及周边地带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着弹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戏、吼秦腔的人们”[8],小说一语道出了新疆乡镇人口和文化构成的混成性、多元性,突出了边地特色。《木垒河》围绕“三鑫和”粉坊魏宗寿家族盛衰,通过日常生活叙述来表现移民社会的世态人心、民情习俗。既写出了走西口的汉族移民的日常生活风习如祈雨、打春、禳灾、占卜结婚、丧葬等,也写出了北疆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的习俗:如头生子送到父母处寄养、女儿出嫁习俗、宴饮待客讲究、男孩子割礼等。
《木垒河》鲜明的地域特色还在于写出了新疆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如金树仁时期的民乱麻匪骚乱、哈萨克牧民北迁、马仲英与盛世才的割据之战,盛世才的革新行政与反苏反共,北塔山战役,新疆解放初期吾斯曼匪乱等,勾勒出新疆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脉络,展现出新疆历史发展的些微面影。
(二)以兵团第二代的创作身份和使命感抒写垦荒事业的悲壮和爱情传奇
1.董立勃:以兵团第二代身份演绎追求真爱的母辈与乡土化的兵团社会冲突的悲情故事。
董立波以《白豆》著称于文坛,他因《白豆》《米香》、《清白》、《静静的下野地》、《烧荒》、《白麦》、《天边炊烟》“五部曲”而成为新疆新时期文坛引人注目的作家。
无论是白豆、白麦还是米香、阿布、小姨,作者都表现了一个在组织意志、行政领导、男性霸权当道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悲剧命运。白豆与胡铁的爱情及对命运的抗争,白麦传奇般的命运中的成长、堕落,《米香》中的米香传统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及自我放逐,《烧荒》中女兵阿布对真爱的追寻。《天边炊烟》小姨与右派吴之干的浪漫爱情和李拐子的婚姻选择等揭示了女兵对纯爱的追求以及与所处的下野地社会的冲突。除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规范抵牾外,更与兵团社会特定历史时期高度组织化、女性价值商品化、人性张扬与贬抑、封建性和男权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现实相关,董立勃演绎的兵团女性传奇爱情确乎具有鲜明反封建意义和人性反思意味。
纵观董立勃创作题材,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对烧荒时代兵团儿女爱情生活的着力表现是他创作的焦点。将当时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下女性为追求生命与爱的真谛,上演的一出出感天动地、特立独行的爱情大戏,作为叙事的重点。董立勃一方面写出了母辈们高贵美丽、真实丰富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写出了在兵团特殊的政治社会体制下人性的畸型、缺憾,个人与社会、女性与男性的矛盾。董立勃写出了母辈们追求真爱的浪漫、无奈、悲怆,也写出了具有特殊意味的乡村化的兵团的社会形态。
2.张者:为兵团垦荒事业泣血立言,赞一代人奋斗和成功,思垦荒事业功过得失。
张者的《老风口》在新疆“铸剑为犁”题材中无疑具有特殊地位。《老风口》的“传奇”性在于试图用史志的方式记录兵团垦荒事业的历史进程。如以南泥湾三五九旅为主体的10万解放军徒步进入南疆沙漠,剿匪、开荒,8000湘女、5000鲁女担负特殊使命上天山,下戈壁,上海支边青年支边及回乡运动,兵团建制的取消与恢复、塔河枯竭、河道改流······这些真实的关乎到兵团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都形成了小说的“史性”。作者以“历史书记”的身份为兵团第一、第二代人青春的热情、牺牲的伟大、奉献的神圣、创业的激情留下了十分壮美的一笔。
但小说又写了在戈壁沙漠上的特殊爱情:刀郎少女爱上解放军连长,为寻找幸福奔赴阿伊泉,成为神仙眷侣;浓郁馨香的沙枣花、一望无际的林带、壮观的沙漠之魂胡杨树,人羊大战、沙漠黑风、女兵奇异受孕等。这些都成就了小说的诗性。《老风口》将奇绝、广袤、粗犷、荒凉的大漠风光、戈壁胜景和兵团民情杂糅在一起,构成了特殊时空下的自然美、风俗美、人情美。
3.韩天航:兵团社会烧荒时代男女爱情悲喜剧和社会样貌叙述。
韩天航不多的兵团题材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他摆脱了习见的“创业加爱情”的叙事模式,借兵团生活的秘史,表达男性中心视野下的女性观、命运观、价值观,带着男性叙事者对女性的期待和想象,更加突出了以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联系着“乡土”的传统文化推崇与礼赞。如《母亲和我们》、《我的大爹》中戈壁母亲形象的传统美表现在守一而终、坚韧、包容、贤能,大爹形象:坦荡磊落、多情重义,敢于担当。这都是从人的精神美方面褒扬传统文化美。
(三)叙写百姓日常生活,表达对新疆传统文化或眷恋赞美或讽喻批判的文化反思
1.王蒙:以混成的文化身份,记述新疆边陲乡村,揭示维吾尔民族的精神面貌。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王蒙向文坛集束式地抛出了写新疆的系列短中篇小说——“在伊犁”,这些小说以其浓郁的边疆特色和对极左年代乡村社会人事的独特表达引起文坛侧目。作者以固有的汉族知识分子身份结合着已经“维吾尔”化了的现实身份、以“我看”他们和表现“我们”生活的混成性眼光表现乡村维吾尔人的生活与心灵。异质性、边地性、文化感成为“在伊犁”系列小说的突出特征。
从1979年的《歌神》开始到《啊,默罕默德·阿麦德》、《虚掩的土屋小院》、《爱弥拉姑娘的爱情》、《好汉子伊斯麻尔》、《心的光》、《边城华彩》、《最后的“陶”》、《杂色》等,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对乡村维吾尔族人的烤馕、拉面、饮茶、酿酒与饮酒、待客、宰牲、庭院布置,家庭起居、生死禁忌、年节习俗(封斋、宴饮)、婚礼、农田劳作、人伦秩序等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叙述,同时也写出了伊犁塔兰契们的质朴善良、因循保守、封闭自足,是非含糊、对极左政治的“塔玛霞尔”态度。作品中对世俗生活之乐之美的热烈追求,对艺术之美之真的渴盼情感,对世故现实的价值判断与浪漫朴野的精神欲求都进行了独特表达,赢得了文坛尤其是新疆文坛的高度认可。当然,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也以感同身受之心写出了极左时代北疆农村社会苦难,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判运动、虚报高产致使群众挨饿,破坏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举办所谓新式的革命婚礼,无限上纲上线批斗牛鬼蛇神,对美与善的破坏等等。但王蒙的重点绝不仅止于对极左年代社会批判,也不仅是对边疆人民人情和人性美的歌颂,他以16年的新疆生活阅历和对一个民族的知晓、热爱,以跨文化的思维写出了边地伊犁、维吾尔族农民伊斯兰化式的生存智慧与乡情民俗以及作者清醒的自我内省,文化的间离与“我”的融入感,使小说形成了特有的乡土化特点,而这一点,长期以来恰恰没有被关注。
2.寻找文化突围:红柯的抒情式歌咏
红柯来新疆是对迥异于中原汉儒文化的西域文化及西域这块土地的神往。他说“不管新疆这个名称的原初意义是什么?对我而言,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世界,就是新大陆,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诗意的生活方式”[9]。
阅读、体验与诗性想象,是红柯写新疆系列小说的建构与歌唱,在《阿里麻里》和《吹牛》中,人与自然浑融的环境,爱情的激越与美丽,友谊的纯然与简单。在《金色的阿勒泰》中,红柯将军垦战士屯垦戍边的壮举同人类创造生命的伟业联系在一起,将人与自然、大地母亲的相依相存写得神圣而诗化,庄重而威严。红柯以对新疆文化的夸饰性描述、表达了对新疆诗意家园、神性大地的思考。
3.对行进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少数民族情感心理的透视。
卢一萍以跨文化、跨民族的叙事者身份创作的“塔合曼草原”系列小说,围绕高原塔吉克人的生活、爱情、友谊,礼赞了青春的美好、友谊的纯洁、然诺的庄重以及高原塔吉克对“赛马”的骑士和英雄的崇拜。如《夏巴孜归来》、《七年前那场赛马》、《白马驹》等,反映出叙事者对“乡土”化的塔吉克传统文化的礼赞和向往,也表现出在现代文化挤压冲击下,塔吉克人的失落与尴尬。
其他如程万里《白驼》围绕农民巴克沙漠追逐吉祥物白驼的经历,体现了浓郁的维吾尔族生活方式:崇拜与迷恋白驼、训鹰的习惯和方式,世俗化的伊斯兰教日常生活等,反映出绿洲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心理及审美习惯。既揭示了他们淳厚美好、善良忠厚、重友爱亲的人性与人情,也讽喻了他们固守一处的保守与落后的习性。
(四)对乡村生活世相和民族传统文化深层心理的揭示
新疆汉语小说创作中还有一部分是双语作家的创作。他们表现出“前文化”积淀对创作的深度影响。如叶尔克西《黑马离去》,小说围绕一场婚宴是宰杀还是留用自然的精灵——南坡黑马,表现了哈萨克人对生命的体认、尊重和崇拜及其人伦血缘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等。阿扎提苏里坦的《死鹿》,围绕拜拉木杀鹿和捡鹿的言行与心理表现了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维吾尔信众对待生命的尊重及弃取不义之财的道德精神。这种文化心理、道德精神是伊斯兰教文化提倡的尊重生命、归于自然生命哲学的体现。
其他一些作家的创作,也有对乡村生活陋俗与社会现象、人性痼疾批判和讽刺的。如阿贝保·热合曼的《儿子娃娃》对乡村社会存在的官官相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阿拉提·阿斯木的《飓风》揭示乡村落后的观念、顺应命运的庸碌和软弱性格;艾克拜尔·米吉提《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呈现了维吾尔乡村社会的封闭保守、狭隘凝固的社会形态;傅查新昌《河边》叙述了基于人的欲望和生存所表现出的人性的恶与丑,表达了对背离传统道德的乡村社会生活的批判。
(五)抒写故乡独特的人生体验、表达变革中的失落与无措
刘亮程的奇特在于用一双自然之子的眼睛写出了与乡村紧密相关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虚土》基本无故事甚至框架。刘亮程通过乡村物象写出了新疆自流民的生命体验。如“一个村庄要是乏掉了,好些年缓不过来。首先,庄稼没劲长了,因为鸡没劲叫鸣,就叫不醒人,一觉睡到半晌午。草狂把庄稼吃掉。人醒来也没用,无精打采,影子皱巴巴拖在地上。人连自己的影子都拖不展。牛拉空车也大喘粗气,一头牛陷在多年前的一个泥潭。这个泥潭现在干涸了。它先是把牛整乏,牛的活全压到人的身上,又把人整乏,一个村庄就这样乏掉了。”[10]他以乡村思维将鸡、人、牛、泥潭、庄稼等物事与乡村的了无生机联系起来,将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结合,再现融合着表现,达到了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高超境界,成就了乡村哲学家的美誉。
《凿空》是一部思考新疆现代工业文明的推进与少数民族乡民生活关系的作品,作品以阿不旦村两件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坎土曼与毛驴来表现叙事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态度和认识。从阿不旦人传承千年的农具——坎土曼和毛驴的变化和遭遇,揭示现代工业文明与乡村农民、乡村生活的关系。南疆少数民族农民希望用坎土曼参与现代化建设,但“凿空”式的开采却与龟兹坎土曼人无关。作者在写这场现代文明建设时,也借乡村智者乌普阿訇之口说出了作者的思考:“胡大让我们守在这个贫穷的地方,胡大知道我们脚下有黑金子,有朝一日它会让我们变得富裕强大,可是我们没有运气,那些宝藏埋得太深,我们的坎土曼挖不出来,几千年来我们的坎土曼一直没变,能挖出石油的巨大机器来了,我们脚下的石油很快会采完,其他矿藏也很快会采完,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许多东西消失······当他们在村边打出石油,当石油被管道输走,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11]。
《凿空》中围绕坎土曼们挖石油管沟的梦想这一中心事件,十分严肃地表达了现代文明给乡村和乡民带来的深层思考。对黑石油和黑毛驴的不同态度,表达了作者基于人本的、历史的、现实的对待现代化的态度和立场,也是立于乡土的审美现代性表达,是对传统的一种回望。
三、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乡土化”特点的美学特征
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乡土化”特点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书写上。董立勃垦荒小说中的洪荒戈壁、漠漠胡杨,滔滔洪水;红柯笔下一望无际的金色阿勒泰、茫茫无边神秘的乌尔禾,葱茏无涯的大草原;赵光鸣小说苍凉寂寥的荒寒荒野;王蒙笔下巴彦岱的潺潺流水、无尽白杨;刘亮程笔下单调荒芜枯败的虚土村;芦一萍笔下巍峨的帕米尔雪山、无边的青草地;程万里笔下无边神秘、吞噬人生命的大沙漠,等等。新疆地域的自然都呈现出粗粝、荒凉、空寂、辽阔的特征,而在此渗透的进取精神、生命态度、人格特质、精神强度,又具有了悲壮美。董立勃女兵小说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追求;赵光鸣笔下流民为生存和自由所表现的坚韧、执着和隐忍;红柯小说向命运和大地抗争的创业豪情、骑士精神;李健小说人物在时代与家族命运的制掣中的奋斗抗争;张者小说逆转自然的戍边精神与伟大壮举,这些都在悲壮中充斥着奇绝之气,具有悲壮悲怆的特点。与此并行的是具有优美特质的富有田园生活气息的人事图景。芦一萍小说中的与雪山骏马、牧草故园紧密联系着的亲情、爱情、友谊,另类垦荒小说中人与自然相亲相生的和谐,伊犁河畔“塔兰契”平静悠然、恒久快乐的世俗生活,叶尔克西小说中对谙合自然法则的生命与生活的呼唤,这些都使小说具有田园之美、中和之美,使新时期汉语小说“乡土化”呈现出美的多样 形态。
[1]李瑞君.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42.
[2]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6.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赵允芳.寻根·扎根·拔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7.
[5]张丽君.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
[6]吴海清.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1.
[7]何莲芳.关于流民的底层叙事——赵光鸣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J].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1).
[8]李健.木垒河[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0.
[9]红柯.敬畏苍天·我与西去的骑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36.
[10]刘亮程.虚土[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115.
[11]刘亮程.凿空[M].北京:作家文艺出版社,201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