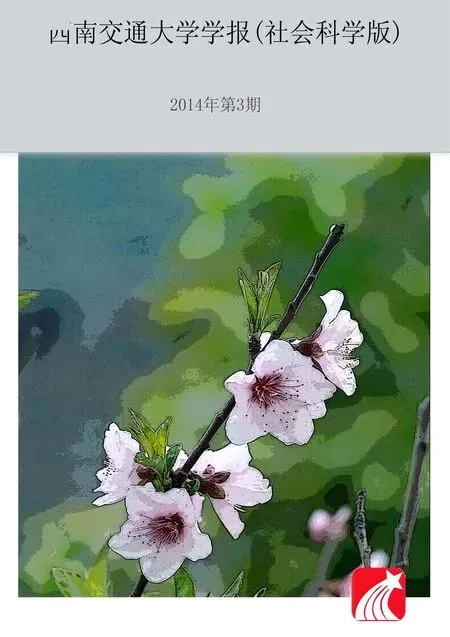严粲在宋元《诗经》学中的学派归属
2014-03-03周东亮
周东亮
(云南大学 图书馆,云南昆明 650091)
严粲,字坦叔,一字明卿,号华谷,福建邵武人,主要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两朝,曾官清湘令、浙东提举等职,著有《诗缉》。尽管其他生平事迹不详,严粲却在南宋《诗经》学领域中占有重要一席,对宋元时期《诗经》学在闽西、赣南地区的传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纳兰性德对严粲给予了高度评价:“宋元之际,闽之樵川儒学蔚起。若严粲明卿之于《诗》……予所见者,惟严氏之《诗缉》、黄氏之《尚书通考》而已”〔1〕。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宋元易代之际经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后世学者却对其学派归属产生了诸多分歧。笔者力图通过对其学派归属的梳理,还归其本来面目。
一、对于严粲学派归属的溯源
宋代以后至清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理学成为了儒学的正宗。由于严粲生活在朱熹之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为那些经学家所关注,所以关于严粲的学派归属并没有人注意到和提及。只是到了清代“汉学”复兴之后,他才又得以重新进入经学家的视野。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在清人的学术著作中,对于严粲究竟属于宋元儒学中的哪一派,却因为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产生了分歧。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严粲属于吕祖谦的东莱学派,以全祖望等人为主要代表,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大家所认可的一种说法;另一种则认为严粲属于林光朝学派,代表人物是清代学者李清馥,此说认可的人少。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观点,即将严粲归到东莱学派。这一观点源于明代人黄佐,其云:“华谷严氏《诗缉》以吕氏《读诗记》为主,而集诸家之说以发明之”〔2〕。但是黄佐并没有明确将严粲划入东莱学派。之后,朱彝尊在编辑《经义考》时将黄氏此语一并录入,亦未下按语。直到全祖望为其师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作《补遗》时,才第一次明确将严粲放在了《东莱续传》里,认为严粲是吕祖谦的后学①。朱彝尊和全祖望等人的这些说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界。由于《四库全书总目》里的经学部分大多直接来自于朱彝尊的《经义考》,而且四库馆臣在为《诗缉》写类序的时候又直接采入了黄氏的观点,实际上等于是认同了朱彝尊、全祖望等人的说法,即认为严粲属于吕祖谦的东莱学派。可见,如果说这种认识源于黄佐的话,朱彝尊和全祖望则使这一观点进一步为人广泛认可,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最终正式确立了严粲归属东莱学派的理念,从而深深地影响到了后来的学林,使得严粲《诗缉》是吕氏《读诗记》流亚的观念深入人心。
仔细分析这些人的说法,似乎没有疑义,毕竟他们都是从严粲《诗缉·自序》中“二儿初为东莱义”一句出发来考察的。然而再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严粲说的是他的两个孩子最初是读吕祖谦的《读诗记》,并未讲他本人曾受业于东莱之门。而且在严粲的交游中,我们也未见到其与东莱及其门人间有诗歌酬唱往来的记载,所以仅凭一句话就去勉强说他的学术派系,显然有点牵强了。
那么,黄佐究竟对严粲的《诗缉》和吕祖谦的《读诗记》作了多少对比和研究呢?黄佐本人学宗程朱,曾与王守仁辩难知行合一之旨,对于陆王心学是心存芥蒂的。朱彝尊则只是撮抄众书而成《经义考》,属于文献收集学家,他本人对宋元经学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全祖望虽汲取百家之长,“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②,然而“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于陆学则每致回护,涉及朱学,则必加纠弹。其语散见,不易觉察。治理学者每先窥此书,凭之入门,而不知其已引导入于歧途。非惟不足升堂奥,亦将无以窥门墙”〔3〕。由于明清两代朱陆后学党同伐异,学者们对待前代学者带有成见的多,对一些人物的学派归属存在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明清时期经学领域里的汉宋之争,深刻地影响到了学术界。诗经学界很多人在看待宋元人的学术归属时,都是简单地从存废序的角度出发。由于严粲在《诗缉》中存《序》,在形式上与吕祖谦《读诗记》相类,所以,很多学者就从形式上分类,将严粲划归吕祖谦学派了。对此,清人叶德辉有公允之论,其曰:“是书与吕祖谦《读诗记》并称,而即以《读诗记》为主,其中审定音训疑似,考订名物异同,皆非宋儒空谈六义者所能企及。而通志堂刻宋元以来经解书,吕、严两家均未之采入。因朱子于吕氏说诗,晚年多有不合,通志堂乃笃守程、朱之学者,以其派别同异故,牵连严氏此书亦摈而不取。然孤本流传,上登《四库》,至今说诗家有不取朱《传》而转取此二书者,毋亦是非之公不可泯灭欤!”〔4〕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李清馥的观点,他认为严粲属于林艾轩的光朝学派,在其所著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文节林艾轩先生光朝学派》里即列入了严粲。李氏在严粲小传之后的按语里,说明了他将严粲归入林光朝学派的原因:“林氏希逸撰严氏诗缉序言:‘华谷严君坦叔,早有诗名江湖间。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见,时出《诗缉》语我,其说大抵与老艾合,遂求全书而读之’”③。可见,李清馥之所以将严粲列入林光朝学派,依据是林希逸《诗缉原序》里的一句“其说大抵与老艾合”。但是在这里,李清馥显然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结论的得来是有前提的,即“时出《诗缉》语我”。而且林希逸只读到了部分的内容,并未读到全书,所以才有了“遂求全书而读之”的冲动。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另外一点,林希逸是林光朝的再传弟子,其理学渊源师承有序,他更多的是因为“理学一系的衰微及不为世人所重而忧心重重”〔5〕,遂借写序来为其“皆以布衣死”的老师们扩大影响的。由此看来,李清馥的说法就显得流于轻率和武断了。
另外,由于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体现的是“衍翼宗派,崇守家法”〔6〕的思想特点,而其家法就是“笃师承,谨训诂,终身不敢背其师说”④,所以他编写此书时就不免深深打上其家学烙印。李清馥之祖李光地是清初理学名臣,而“光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墟于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7〕。但李光地终究是一理学家,其门户之见在经学研究和学派划分上还是多多少少要留下痕迹的。李清馥受其家学影响,在这一点上也自不能免。
对于严粲的诗学轨迹,后人可能由于资料的缺失已经无法做出严格的考证了,但其在《华谷集》里的一首诗却为我们了解其诗学传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严粲生年不详,不过据其自述,可知其早年“从岭庵谢先生梦得游”。及谢氏移家江西,他也从邵武随至江西,“樽酒论文”,“如是者十载”。后来,严粲深情地回忆道:
乐平至鸣溪渡有山,与南丰军山同名者。余昔从岭庵谢先生梦得游。先生,于湖畏友也,豪于诗,悦军山之峭拔,畅其吟怀,自邵武徙家于市山,筑室曰“西窗”,以朝夕对焉,尝命余记之。余时从西窗樽酒论文为乐,如是者十载。今先生已焉,感而赋诗。⑤
谢尧仁字梦得,张孝祥门人,建宁蓝田保人,以文词诗律游江湖,有诗集行世。其《题金山》诗云:“半夜鬼神朝水府,五更鼓角动扬州。”大为张孝祥所知,以国士畏友待之,谓其文“如觞滥岷山,不舍昼夜。其为荡云沃雨之浸,夫何疑?仆但得望洋而叹耳”⑥。也就是说,严粲从谢尧仁游学十年,实得张孝祥诗学之传,而非如后世学者所言,应归宗吕祖谦或林光朝。
二、严粲《诗缉》与吕祖谦《读诗记》及朱熹《诗集传》的比较
通过追溯以上两种学派划分的渊源,我们不难发现其划分依据都经不起认真推敲。如果想充分说明严粲的学派归属,只能对其《诗缉》本身加以考察,这才是最为可靠的办法。
由于目前的《诗经》学“整个研究仍处于以目录和序跋为研究手段的阶段”〔8〕,所以少有专门论及严粲与《诗缉》的研究著作。而清代及民国年间的书目著作在论及严粲《诗缉》时,又多取朱彝尊《经义考》引明人黄佐之评价,认为“华谷严氏《诗缉》以吕氏《读诗记》为主,而集诸家之说以发明之”〔2〕。持这种观点的,以《四库全书总目》和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等为代表。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抹杀了严粲编纂《诗缉》的功绩及其影响,尤其是在整体上忽视了严氏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但如此,甚至关于《诗辑》如何“以吕氏《读诗记》为主”,各家也均无说解。而清人瞿镛则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称“其(《诗缉》)体与《读诗记》颇异,其说亦多自抒心得,不袭前人”,并谓“黄氏佐谓《诗缉》以吕氏《读诗记》为主,而集诸家之说以发明之,似不尽然”〔2〕。这一见解有别于黄氏的说法,显然有助于我们认清严粲《诗缉》的本来面目和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要明确此论,加深认识,我们还得更深入地进行对比研究。
(一)《诗缉》与《读诗记》的体例对比
严粲的《诗缉》和段昌武的《毛诗集解》都是继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之后解读《诗经》的集解体著作。与段氏近乎完全祖述吕祖谦《读诗记》的内容与形式不同,严粲在著述内容及形式上均融入了自己的特色。它既不同于吕祖谦的《读诗记》,更异于段昌武的《毛诗集解》。下面我们不妨举例加以说明: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
毛氏曰:兴也。孔氏曰:“《释鸟》:‘燕燕,鳦。’郭璞曰:‘齐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齐貌。 毛氏曰:之子,去者也。归,归宗也。远送过礼。于,于也,郊外曰野。苏氏曰:《礼》妇人送迎不出门,远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与之诀别,己留而彼去,稍稍更远,瞻望之不复能及,故念之泣涕。 王氏曰:燕方春时以其匹至,其羽相与差池,其鸣一上而一下,故庄姜感所见以兴焉。 广汉张氏曰:《燕燕》,以兴己与戴妫嫡妾相与之善欤。独言泣涕之情者,盖国家之事有不可胜悲者,晋褚太后批桓温废立《诏》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其有合于诗人之情欤?(吕祖谦《读诗记》)
燕燕于飞,曹氏曰:燕燕,两燕也。差池其羽。差,音钗,又音雌。○李氏曰:差池,不齐貎。○曹氏曰:差池,言其相先后也。之子于归,《传》曰:之子,去者也。归,归宗也。○《疏》曰:之子,戴妫也。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涕,音体,又音替。○《说文》曰:泣,无声出涕也。○《陈·泽陂》《传》曰:自目曰涕。
兴也。《传》不言兴,今从朱氏。燕以春来秋去有离别之义,故以起兴。庄姜抚戴妫之子,平时与戴妫恩信相亲。及庄公既没,嫡妾相依如双燕之飞,其羽差池相为先后而常相随逐也。今戴妫大归而己独留,不复得如双燕矣。我远送于野而与之别,稍稍更远,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倾也。风人含不尽之意,此但叙离别之恨,而子弑国危之戚,皆隐然在不言之中矣。广汉张氏曰:盖家国之事有不可胜悲者,晋褚太后批桓温废立《诏》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有合于诗人之情欤?○苏氏曰:妇人送迎不出门,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燕歌之燕,平燕鸿往来靡定,别离者多以燕鸿起兴。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燕歌之燕,平声,余并如字。“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谢宣城送孔令诗云:“巢幕无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严粲《诗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有不少相同之处:严粲的《诗缉》和吕祖谦《读诗记》一样,都很严谨,用“某曰”述其来源。而且二人都重视诗教,注重从情性方面解诗。不可否认的是,严粲《诗缉》的大部分材料源自吕祖谦《读诗记》,这主要表现在《诗缉》所引用的诸家说解上。关于这一点,严粲并不回避,他在《自序》中说:“二儿初为《周南》、《召南》,受东莱义,诵之不能习,余为缉诸家说”⑦,隐隐透漏了材料的来源。受东莱义即用了东莱本,而主要是使用其义;缉诸家说则表明不但用其义,而且用诸家说解,并有所补充完善,即已不是简单囿于东莱所引诸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严粲近乎全盘地抄袭了吕祖谦,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书“以《读诗记》为主”,那样就抹杀了严粲所做的工作。事实上,严粲对吕祖谦书做了很大的加工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两者在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读诗记》是将经文与注文分列,注文则“诸家先后以经文为序。或一章首用甲说,次用乙说,末复用甲说,则再出甲姓氏”⑧,即只是罗列诸说而已。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各家之说前后衔接不是很紧密,总有断续重复之嫌。而且诸家注释均采用同样字体,看上去颇显杂乱。《诗缉》则是“字训句义,插注经文之下,以著所从。乃错综新旧说以为章指,顺经文而点缀之”⑦,这样就将注释与章旨分开,注旨在疏通文字,章意在解说经文,显得浑然一体而又各自分明。而且“经文及章指并作大字,字训句义及有所发明并作小注,以经文为先后”⑦,字体有异,使人一看即有赏心悦目、条理清晰之感。
其次表现在对前人关于名物说解的处理办法上。《读诗记》只是简单的一一照录诸家之说,多数不加断语,这说明吕氏的侧重点不在名物制度上而是在义理上。严粲《诗缉》则不然,“凡草木虫鱼之类,旧一说分明者先著之;其辞繁及说不一者,称曰以断之”⑦。这充分显示了他谨严的一面,即不仅注重从义理上解《诗》,而且注重从名物上入手,借助名物的辨析来探讨《诗》文字之下的本义。可见,严粲不是简单地盲从前人,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再次,是在说解方法上增加了解经的角度。吕祖谦是位理学家和史学家,这就决定了他在解经时主要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把经书作为历史教科书来读的,而没有顾及到《诗》的文学色彩。严粲是位诗人和经学家,他一方面也把经书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但同时也注意到了《诗》是诗歌,要从文学角度加以阐释,“要在‘以意逆志’,优而柔之,以求吟咏之情性而已”⑦。比如上面这一段,严粲就增加了以雁这个意象起兴述别离的部分,并且引述诗歌加以佐证,这和那些诗话的评点就较为接近了。
第四,严氏《诗缉》修正了吕氏《读诗记》的一些明显错误。比如上面一段中,吕氏《读诗记》说:“毛氏曰:兴也”,严氏《诗缉》却说:“《传》不言兴,今从朱氏”,这就是在修正吕氏之误。我们翻检今天的《十三经注疏》本《诗经》,于此诗下并未见有《传》言兴之记载,看来当是吕氏误记。严粲则依据当时他所见到的本子,修正了《读诗记》的这类错误。
第五,在字的音释上,严粲遵循时代有变化语音亦有变化的观点,采用时音来为《诗经》注音。《诗经》的文字之所以能遭秦末焚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的缘故〔9〕,结果使得后世《诗经》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假借字。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语音也在流变,原本押韵的诗变得不押韵了,给学者们造成了很多困惑,故而字音问题就成了读《诗》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吕祖谦《读诗记》并不注音,严粲《诗缉》则对一些字作了注音。而且在注音时,他采用了诸如直音法、形训法、反切法、《温公指掌图》等多种方法,尤其是广泛使用了反切法注音。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像朱熹那样采用当时流行的吴棫的“叶韵说”,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可贵的。因为严粲之书在“便家之童习”外,已经注意到了地域和时代所导致的音变,所以在学术上没有盲目追随朱熹等当时的学术大家,而是从学术的继承与流变上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严粲的这种客观态度也影响到了明人陈第、杨慎等,启发了他们从语音流变上去研究古音声韵问题。
最后,《诗缉》和《读诗记》对引述材料的剪切和重新安排方面详略不同。吕祖谦《读诗记》重在注解,汇集众说而取法其意。尽管陈振孙说它“剪截贯穿,如出一手”〔10〕,但毕竟只是像是出于一人之手而已,注释文字和章解还是出自不同人之手,需要读者去贯通融汇。而严氏《诗缉》则有着双重面向:一方面将注解名物训诂放在诗句之后,为疏通诗意作准备;另一方面融汇诸家之意而成每章的章旨并放在章末,力图揭示出诗之本义。《诗缉》中的每章章旨,才是真正的“出于一手”,毫无牵强、杂糅之感。
由此看来,严粲的《诗缉》除了“惟不废《序》与东莱同”外〔2〕;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对《读诗记》做了加工改造,算得上是“集解体中后出而转精者”〔8〕。应当说,严粲是用心在解《诗》,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真情真性。正如林希逸转述的那样,严粲“于此有年,非敢有以臆决,摭诸家而求其是”⑨。数十年的悉心体会,加上严谨的治学态度,终于成就了《诗缉》这部《诗经》学史上的全面具体公允的巨著,并引起后人重视,成为后学全面了解研究《诗经》的入门之书、不可或缺之作。
(二)《诗缉》与朱熹《诗集传》体例之比较
《诗缉》与《读诗记》都为集解体,关于两者的关系,历来各家书目几乎都有关注。相反,对严粲和与其生活最近的朱熹之间的学术关系,多数人则很少注意,尤其是对二人同为集解体的《诗集传》与《诗缉》的关系留意更少。虽然有少数著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邵武府志》和《福建通志》均认为朱熹《诗集传》“多采其(《诗缉》)说”,但又把时代先后弄错了,以至于误导后人。那么,《诗集传》与《诗缉》在体例上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不妨也举例说明: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翶将翔,弋凫与雁。《郑风·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翶将翔,弋凫音符与雁。
赋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际也。明星,启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缴射,谓以生丝系矢而射也。凫,水鸟,如鸭,青色,背上有文。 ○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朱熹《诗集传》)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诗记》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时也。《列子》曰: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传》曰:言小星已不见也。将翱将翔,今曰:翱翔,雍容和缓之意。弋凫与雁。弋,音翼。凫,音符。○《笺》曰:弋,缴射也。缴,音灼。《疏》曰:谓以绳系矢而射也。缴,谓生丝为绳也。○曹氏曰:《凫鹥》解曰:凫,野鹜。○解见《凫鹥》。
此诗述夫妇相警之辞。始妇警其夫曰:鸡鸣可兴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妇又警其夫曰:子宜兴而视夜之如何,盖小星已不见,唯明大之星烂然,天将晓矣。方将雍容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早则从容,晏则忽遽,起不可以不早也。○苏氏以“明星”为“启明”,盖今俗所谓晓星也。毛氏谓:天将晓则小星不见,惟明大之星烂然。虽不指为启明,然将晓而明大者,惟启明耳。至《陈·东门之杨》“明星煌煌”但言夜深,则星明又不必专为晓星矣。(严粲《诗缉》)
显然,严粲法朱子之意的地方很多。据笔者统计,《诗缉》全书标明注引《诗集传》的地方近乎《读诗记》四倍,且在书中明确标明从朱说或以朱意为长的近十几处,更不用说其章旨中那些暗用朱说的地方了。但严粲《诗缉》在形式上比较注意注明自己书注所自,以示不敢掠美之意,彰显出其严谨的一面。朱熹则不然,他为了突出其弃《序》的革新精神以及与汉、唐旧说的不同,在作注时全不注明出处,对《传》、《笺》、《疏》更是这样,以致后人误以前人著述为朱熹所自创,这在学术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⑩。严粲出于对朱熹的这种机巧作法的不满,遂以《读诗记》为基础,吸收了吕祖谦和朱熹的说解方法与观点,编成了《诗缉》。不同于同时代那些动辄就是撰、著的说经著作,严粲编《诗缉》时祖述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之意,态度审慎而谦虚。这种严谨还体现在著书的用语上,该书味经堂刻本每卷卷端均刻有“朝奉大夫臣粲述”字样。
除了这些细微的不同外,《诗缉》在体例及解经态度上还是有不少地方袭用了《诗集传》。
首先,两者均有文字音释。这说明朱熹、严粲两人都对《诗经》的韵读十分关注,力图用时音来读《诗经》。朱熹在《诗集传》中用直音法注音,但采用较多的是南宋人吴棫的“叶韵说”,忽略了时、地的差别。在今天看来,这种注音方法实际上是极不科学的。严粲则充分注意到了音声的时代、地域之别和文字的变化,并运用反切、直音、形训等多种方法来注音,这要比朱熹相对科学得多。
其次,两者在注经态度上都是十分审慎而严谨的。朱、严两人在注经时都遵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不去强不知以为知,对于自己弄不懂的名物注解,也多是存而不论,仅备众说而已。如朱熹解《卫·芄兰》时就说:“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诗缉》卷十一《齐·山有枢》一诗中对于“山有栲”的“栲”,由于《尔雅》和郭璞注及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说有异,严粲对此又无考,就说:“今曰:姑两存之”。
再次,两者都有引证,只不过是在详略及位置安排上有所不同而已。朱熹《诗集传》是先列经文,在经文后注音,然后释字析物,次论六义,再加引证,最后综述串讲章旨大义。严氏则是在经文中夹注字之音义,然后引证论说。在经文之后专门连缀诸家说解而成章旨,分章讲解。
第四,两者都不拘门户,博采众长。朱熹《诗集传》虽名曰废《序》,实则从《序》者亦不少,其间多采毛、郑、孔等旧派的说解,只不过没有明确标注出来而已。而严粲《诗缉》则明确标明所用何家,其中既有尊《序》的毛、郑、范处义等,亦有主废《序》的新派欧阳修、苏辙、朱熹等。
最后,两者在解经时都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性,这是两人有别于同时代各家的地方。朱熹在《诗集传》中就充分注意到了《诗》的文学性,无论是在读诗还是在论诗、评诗时,也多注意从其文学性上生发观点。严粲的《诗缉》无疑受了朱熹的启发,也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性,并偶用文学手法解《诗》。比如其解《陈风·月出》一诗,就把月下美人写得轻盈静美,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严粲的《诗缉》在内容上是兼取吕祖谦《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并法其意;而在先释词后串讲文义上则更多的是在学习朱熹的《诗集传》。所以,简单的一句“以《读诗记》为主”并不能真正揭示《诗缉》的本来面目,反而会误导读者。准确的来讲,我们还是应当说:是书“因吕氏《读诗记》而作”〔11〕,并多采朱熹《诗集传》,集诸家说解并发明之,有所不安则加己意而成。严粲对朱熹的《诗集传》应当是研读较深的,不然也不会有“人琴无处问,空想考亭诗”(11)的感慨与遗憾了。
三、《诗缉》引述文献
清人焦循曾对编述文献与著作文献的区别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之,而作者之意复明,是谓之‘述’”〔12〕。用此标准来衡量判断,《诗缉》无疑是一部“述而不作”的编述文献、集解体著作。
作为一部编述文献,《诗缉》虽杂取南宋后期以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却建构起了一个完全属于编者严粲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诗缉》中,严粲经常会结合南宋的现实与历史,把经义的解读指向当时社会政治,从而使得其解读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据笔者粗略统计,其所明抄暗引之书,遍及先秦至作者生活的时代之著作,从《诗经》学文献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种类多达110家,这要比吕祖谦的《读诗记》多出近20家(12)。而且这多出的近20家中,有些今存者寥寥,后世也多赖此书而得知其内容之一二,如曹粹中的《放斋说诗》和范处义之《解颐新语》等。
严粲《诗缉》引书,有明引,有暗用。明引多见于夹注中,暗用则多出现在章旨及考辨中。如其解《杕杜》“独行踽踽”时,直曰:“朱氏《孟子解》云:踽踽,独行不进之貌”。这是明引朱熹的注解来解释字义。而在解《干旄》时,则说:“贤者来自他国,若季札聘郑,子产如晋之类。季札告子产以谨礼,子产告叔向以实沈台骀之事,皆闻所未闻,是以善道告之也。”是为暗引《左传》来辅解章旨。无论明引还是暗用,始终都是围绕着经文展开的。
据笔者统计,《诗缉》引经部书凡72家(由于有些不详其书,故只称家不列其具体数目种类,下同),范围遍及全部十三经。在这些经部引书中,种类最多的是《诗经》类著作,约有30多种,可能实际数量还不止于此。因为严粲引书多不标书名,对作者仅称姓氏,而有一部分又为今存之其他《诗经》类书所不载,加之原书亡佚,故无从查考。在部分可考的《诗经》类著作中,又以《传》、《笺》、《疏》这些汉、唐《诗经》学的精华为主,占到了引书条数的近一半。而所引用的宋代《诗经》学著作,又以朱熹、曹粹中、李樗、钱氏、苏辙、吕祖谦、王安石、范处义8家为主。在引用宋代《诗经》学著作时,既取以存《序》而著称于世的范处义、吕祖谦等人的书,也取疑《序》的欧阳修、苏辙、朱熹等人之书,同时还取兼采持平的曹粹中、李樗等人之书。
从这些《诗经》类引书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严粲是兼容并取、毫无门户之见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引用的条数上来看,引用宋人之说解最多的是朱熹,有591条,其次是曹粹中,再次是李樗,吕祖谦之说仅排在第五位,也就167条,引朱说近乎引吕说的三倍还要多。于此可见,严粲并不是株守吕祖谦之说,倒更像是在申述补充朱熹之说。
在《诗缉》所引的这些经部书中,有些极其珍贵,因为其引文或为他书所不载,或可补它书之缺文脱句。如其引曹粹中《放斋说诗》的文字数量要远远大过其他诸家书所引;引范处义《解颐新语》的文字也多是现存其他各书所不载的,其引文数量是王应麟《困学纪闻》的三倍;而其引的南宋钱氏之说,也为现存其他各书所不载。
《诗缉》经部引书位列第二的是小学类著作,有14种,其中以《尔雅》、《经典释文》和《说文》为主。这些小学类书多是解释名物训诂,音义兼备。严粲所见者是宋本,并且多为原本,转引者少,所以,又可用它来校补今书之脱误。
《诗缉》引述的经部文献除《诗经》类书外,引述较多的是三礼及“三礼”注疏和《左传》。《左传》多是用来揭示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三礼及“三礼”注疏则多用来说明《诗》中的礼数和对器物的要求等,以此实现教化学人的目的。从《诗缉》引述的经部书来看,总的文字数量差不多占据了全书的近百分之九十还要多。
《诗缉》引史部书8种,主要是以《汉书》和颜师古注为主。《诗缉》引这些史部书,主要是引其《地理志》及人物传记中涉及到的一些地名等来疏证《诗经》注解中出现的地名之类。这体现出严粲谨严的一面。
《诗缉》引用子部书8种,数量虽不多,但却涉及到儒家《荀子》、道家《老子》、《庄子》等。严粲之所以引这些子部书,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书成书年代距《诗经》的时代不远,语言文字上多可互通的缘故。
《诗缉》引集部书13家,其中唐、宋人的诗文著作占7家。这是以往解经之书少有的情况,尤其是引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来解经,更为他书所罕见。严粲引这些唐、宋人的诗文著作,数量虽不多,却有着重要作用,多是来印证一些旧的诗说的正确性。严粲引用诗文来解经书,与宋代诗话类著作勃兴当有一定关系。对此,还是清人王宗柟说得好:“严氏解《诗》,间引唐宋之作,退谷所訾,此或其一端。董子云《诗》无达诂,如其与经旨比附,即以凡情证圣解也可。矧汉魏已来称诗者,类皆鼓吹风雅,性情一也,顾可画古今而二之耶?前贤持论,各有所主,平心味之,得失自见”〔1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诗缉》和吕祖谦《读诗记》、朱熹《诗集传》一样,是宋代诗经学中集解体的著作,书中所反映出的是严粲采纳百家、不偏不倚的中肯解经的严谨态度,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严粲既不应属于吕祖谦学派,也不属于林光朝学派。他应该和吕祖谦、朱熹一样,是学术上的兼综派。
注释:
①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五十一。
②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
③见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见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见严粲《华谷集》,载于《两宋明贤小集》卷329,《四库全书》本。
⑥见嘉靖《邵武府志》、《于湖居士集》前序、《宋元学案》。
⑦见严粲《诗缉条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见吕祖谦《读诗记·条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见严粲《诗缉·自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按:清人姚际恒对朱熹的这种做法表示极度不满,在《诗经通论·诗经论旨》中说:“(朱子《集传》)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姚氏还对《集传》作了统计:“《集传》从《序》者十之有五,又有外示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能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盖深刺其隐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62册第11页。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亦曰:“自来说《诗》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从《序》,非不知其两者有所失也,盖不能独抒己见。”详见李先耕点校本第1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见严粲《华谷集》之《乐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按: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称,吕氏《读诗记》引书80多种。
〔1〕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38.
〔2〕瞿 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49,49,49,49.
〔3〕钱 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25.
〔4〕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9.
〔5〕孙 红.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J〕.北方论丛,2003,(5):10-13.
〔6〕何 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64.
〔7〕永 瑢,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799.
〔8〕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95.
〔9〕班 固.汉书(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8.
〔1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
〔11〕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66.
〔12〕焦 循.雕菰集(卷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3.
〔13〕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