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喀拉峻杯·第三届西部文学奖授奖词 受奖词
2014-03-02本刊编辑部
小说奖
弋舟:《龋齿》(载《西部》2012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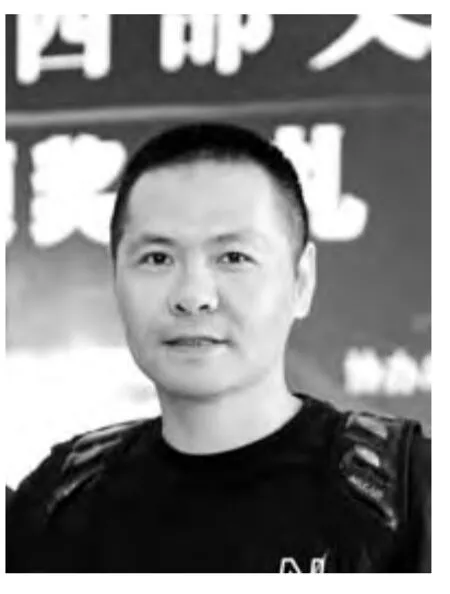
授奖词
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弋舟是近年来西部活跃的小说家。《龋齿》以冷静节制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离婚多年的女人因一颗龋齿被牙医男友发现,在治疗过程中因心脏病突发而昏厥的故事。娴熟的叙事技巧,不露痕迹的推进方式,收放自如的转接过渡,赋予小说独特的阅读吸引力。女人被施救过程中的“臆想”内容,堪称神来之笔,以潜意识的方式表明她内心深处从未忘记过去,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尽管过去留给她的是伤,是痛,是“细菌性疾病”,却像那颗龋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行文的主旨和意义彰显于此,记忆与真相亦隐藏于此。
受奖词
我祖籍江苏,父亲一辈来到了西部。而我,比父亲往西跑得更西了一些。我们父子的生命轨迹,就是一个不断远离故土、向西复向西的图景。由此,当我在西部成为一名写作者时,我很难如我的西部同侪们那般举重若轻,迅速找到自己言说的立场与根基,从而获得某种相对轻易的叙述策略;当我每每试图也以那种“西部经验”来策动自己的表达时,我便会首先被自己内心的羞愧所阻挡——是的,我的这些“西部经验”无力转化为我的文字,因为,我缺乏那种呈现自己“西部经验”时所必须的“西部的情感”。身在西部,我总有一股寄居者赝品一般的虚弱感,我觉得在这块土地上,我难以理直气壮,难以不由分说,甚至,难以从根本上给予自己一个确凿的身份认同感。于是,即便在热泪汹涌时,我也往往习惯性地藏住悲伤。如此种种,令我被迫维护住了一个小说家所必须的“他者”的态度,同时,也必然使我丧失了那种写作者同样不可或缺的“讴歌”的热忱,它使得我的写作常常表现出寒冷有余而温暖不足——这当然是一种缺陷。
所以,今天《西部》授予我这个奖项,于我而言,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我不惜一厢情愿地将之视为这块土地对于我这个异乡人的收留与认领,不惜自以为是地将之视为西部文学对于我的一次矜重而庄严的首肯。从此,我或许便可归家。
感谢《西部》!
流瓶儿:《小说二题》(载《西部》2013年第7期)
授奖词
流瓶儿是新疆新生代作家榜“十佳作家”之一,执着追求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个性书写。《小说二题》的《启示》和《阻止不了的生长》虽是其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却以缜密的构思、从容的叙述、以小见大的视角显示出她创作的未知潜力。两篇小说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非健全者”,他们因生理或心理疾患而产生惧怕感,却从未停止观察、思考。作者用极其经济的笔墨将这种观察、思考以不同视角细微而真实地描画出来,传达了无可选择境遇之下无以言说的生命痛感,并触及了“健全”与“非健全”的生活悖论。
受奖词
必须说感谢。也必须说说三年前。
三年前因为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入选了新生代作家十佳。我很意外能得到那样的荣誉,同样让我意外的是它带给我的伤感,远大于喜悦。
因为那是一部畅销小说,一些人很隐晦地表示出了不屑。钱钟书在《围城》一书里写:“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写作的人,是一群敏感的人,尤其是专攻人物内心、探索人性的这类写小说的人。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并不好过。当时另一部长篇已写过半,但是没法再写下去。
我不甘心,我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写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小说。我要证明自己。
三年前在领奖台上,我说一定要努力,要对得起那个奖,我想今天的这个奖,可以算作是一个交待。如果说,荣获新生代十佳有一些运气和其他因素在里面,这一次的西部文学小说奖恐也难免会有。必须说,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遇到了一群肯帮我的好人。
我希望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能道出几句惊世骇俗的话,结果却像一个怨妇中了奖,用画外音回赠砂砾和鱼刺。我们是作家,但也是寻常的普通人。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没有了这些虱子,生活就会少了很多乐趣。
拿到小说奖,意味着披上了另一件华美的袍,将面对新的一群虱子。还是那句话,我要对得起这个奖,我会继续努力。
诗歌奖
冉冉:《冉冉的诗》(载《西部》2013年第11期)
授奖词
若隐似无的生活印记,求真求善的心灵诉求,对周遭事物的独特体察,使冉冉的诗具有温暖、透明的品格与底色。简约、纯粹的语言,增添了诗句的清澈、精准之感。对于“觉”的自觉追求,对于“奇迹”的拥抱姿态,对于生活现象的超脱之心,常常有意无意流泻出来,佐证了她对诗歌这一“祈祷形式”的认同。冉冉的诗是复调的、多声部的,并将自己的思想锤炼统一;对美的追求,接近至善之真,在自我认知中领受诗歌和启示的双重光照。
受奖词
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并沉浸于写作状态的诗人跟置身催眠过程的人有几分相似,譬如其间的专注、放松、自由与喜乐,就跟深度催眠中的功态接近,其结果也同样改变、塑造、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与精神。而作为完成状态的诗歌,则是写作者经验(或超验)的析出,是可以存留和反复回放的幻境,是化装抑或是伪装的白日梦,是我们祈愿的尚未看见的看见,抑或是,我们暂时无法实现的祈愿之愿的替代。
在此我要坦白从诗歌中获得的利益与力量——诗歌的阅读写作回溯并重塑了我的生命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反刍、观想、体察身心的景象际遇。通过看和见,我得以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她和他们——尤其是她,她的自省自律、隐忍担当、柔韧旷达、幽默笃定,让我对自性的显现葆有信心。她隐身在他们之中,深藏于每个人的身内,在这哀伤苦厄的时代给了我们自净的勇气和爱的希望。我曾在《雾中城》里写道:“这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也是今生的大事。”——是的,是诗歌写作让我走上了寻求觉悟的道途,尽管这道途曲折漫长,几乎是永无止境,但最初的一步毕竟已经迈出。
谢谢各位评委,你们将两年一度的西部文学奖诗歌奖颁发给我,或许表达的正是对一个同道的关注与看见。真正的爱诗者并不孤独,经由阅读写作,我们不仅见证着相同的命运与境遇,还将以切实的努力去创造和抵达理想的生命之境。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石头里的天空》(载《西部》2013年第4期)
授奖词

太阳、眼睛、光明、爱情,这些张扬青春活力并具永恒光芒的字眼,屡屡出现在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的笔下,成为他诗歌的主调。由此开掘表象后的本质及其潜藏的哲学意义,使他的诗歌具有维吾尔传统诗歌中的抒情元素和哲理色彩。结构的反复,意象的差异性指向,语言的澄澈、质朴,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感受。麦麦提敏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近、认知、欣赏维吾尔青年诗人和边疆新生代诗歌的有效途径。
受奖词
大概在小学五年级,我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初我认为字数整齐、二四行押韵,就是诗;当时我也认为,从古到今,有那么多诗人,写了那么多诗,我还有什么东西可写吗?在不断地成长、探索过程中,我对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想法多么幼稚。诗歌是没有界限的,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人都去写诗,依然有东西可写,诗与人息息相关,正如德国伟大的诗人策兰说:“诗是人身上最人性的东西。”
我是双语诗人,用汉语写本民族,这种创作方式承载着太多的沉重的东西,对我的冲击力很大。而发生在现实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使这种沉重的写作方式更加沉闷。诗,将带我到何方?我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得知自己获得了西部文学奖诗歌奖,我很高兴,这意味着对我汉语创作的充分肯定。在这里,我要感谢诗歌,感谢《西部》文学杂志。 黄金草原,文学盛会,同诗的约会将会永存于记忆里,使我们富有。
散文奖
汗漫:《小叙事》(载《西部》2013年第2期)
授奖词
汗漫是诗人出身的“新散文”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散文写作,将诗歌语言的精约、准确、深刻运用其中,兼具细节的丰富、情绪的饱满、想象的丰富、铺排的舒展、行文的从容。《小叙事》将诗化的情怀、小说化的叙述引入散文写作,将新闻事件作为写作动因,打破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通过“乡村新闻”、“台币”、“灭门案”、“水库暗蓝”四篇文字,以敏锐的笔触叙述从文革临近结束到改革开放过程中,村镇受到外来冲击后,时代变化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影响,每一个小人物都携带了时代的精神基因,也是时代镜面上的小小折射点。
受奖词
在伊犁获得“喀拉峻杯”西部文学奖散文奖,非常荣幸!
在喀拉峻,绿草涌上天边的山顶就转化成了白雪,这,也是一种从绿到白的“跨文体写作”。
《西部》文学杂志在新疆,就像是处于尘世的尽头,反而有可能获得超越和开阔,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实际上,每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不管身处金融中心、政治中心、话语中心,都应当让自己的书桌成为远离中心的一小块西部——只有一种地方性、个人化的写作,才有可能水穷云起,通向广大的世界和灵魂,像希尼的爱尔兰沼泽地、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沈从文的长河湘西。
我的散文写作实验始于九十年代。我把散文看成一种不分行的长诗。而诗的本质,我以为就是对生活和心灵的真相进行独到的发现,就是除去种种遮蔽,反对虚伪的、陈陈相因的、懒惰的、没有难度的思考和表达,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充满了那么多的疑难。
这些年,一批诗人介入散文写作,使这一文体渐渐呈现出一种混血的、跨界的、全新的语言面貌,而这恰恰与我们当下的复杂处境相互贯通、映照。
我的散文写作,聚焦于当下南方经验和故乡中原记忆。这次获奖的《小叙事》,涉及到了若干乡村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命运里困顿、绝望、挣扎、失败,像病理切片一样,有可能透视出一个转型中的动荡不安的时代。
我知道,我的表达远远不够开阔、有力,所以我要向喀拉峻草原学习写作——让文字的绿草,一涌而上,抵达稿纸的顶端、人的心尖,成为白雪。
感谢《西部》杂志,感谢伊犁,感谢特克斯!
辛生:《母亲》(载《西部》2013年第10期)

授奖词
散文写作讲求以情动人,辛生深谙此道。《母亲》一文语言简洁、节制,行文平实、素朴,字里行间充盈着对母亲的无尽思念。不仅于此,我们更多地读到母亲传奇般的过往给予作者丰厚的人生滋养,以及作者心中潜藏着的对母亲深深感恩之情的独语。“母亲”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从怀念母亲进而延伸至对“死亡”这一终极命题的思考,增添了辛生行文的深度和厚度。“没有终止,难求遗忘”,既是写给母亲和自己的,更是写给天下和人世的。
受奖词
感谢《西部》和西部文学奖各位评委给予我这样的殊荣。
这么多年钟情于文学,没想过要得什么奖,只为能通过阅读和写作,在今天这样一个满眼浮华的物质社会,为自己的心灵寻得一方安静而怡然的所在,让自己能够远离人世的狭隘与堕落。
文学于我,是一个缘分。因为工作,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写得好、写得有想法,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就这样,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的最爱。写公文终归是一种被动的、有约束有程式的文字活动,时间久了不免枯燥,我便去寻求文字自我表达的快乐。于是,我与文学不期而遇。
文学于我,是一份情怀。文学阅读和写作,经常使我沉湎于自己的感动,这使我的情感变得丰富而敏感。文学滋养了我的情怀,让我懂得理解和包容人与人性的复杂,进而引我看清人们内心的憧憬和希望。
文学于我,是一种信念。文学描绘的众生相和由此构建的精神世界是迷人的。文学独有的审美追求使我相信,真善美的力量是永恒的。这个世界从来不乏像土地一样淳厚的担当、像稼穑一样朴实的崇高。我坚信,文学的清醒与温柔,将给予我们的心灵宁静而温暖的抚慰。
我深知自己写作的局限与肤浅。我会把西部文学奖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努力不辜负《西部》对我的培养和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厚爱。
祝根植新疆的《西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增光添彩!祝西部文学奖更加不同凡响!
康剑:《禾木纪事》(载《西部》2013年第12期)
授奖词
康剑多年来纵情于喀纳斯山水,用眼睛观察,以心灵体悟,借镜头和文字表达,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喀纳斯的可信文本和无穷想象。《禾木纪事》中的三篇文章,以三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曲开老人、喇嘛、老村长为题,叙述了现代文明及其旅游开发对“神的后花园”禾木村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不动声色地传达出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迅速改变的隐隐担忧。康剑的文字和影像,记录、流传、复魅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图瓦人独特的文化景观。
受奖词
首先我要感谢喀纳斯,没有它,我不可能写出今天这么多的山水散文。我很庆幸身边有这么好的山水,让我看到它后,经常能够浮想联翩。山水的美给了我很多的灵感,也给了我很多山水以外的感受。山水的美是直白的,又是充满奥妙的,所以山水难写。况且古往今来,文学大师们已经把山水之美写到了尽头和极致。两汉文章里有山水,唐诗里有山水,宋词里有山水,甚至连明清的小说里也有迷蒙的山水。当代散文大家笔下的山水,更是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但面对眼前的山水,我们的确又无法停下笔来。于是,我就努力透过山水,试着表达山水之外的东西,尽管这种表达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些山水,是它教会了我,在山水面前,人类只有跋涉和攀登,没有跨越和征服。山水是人类永远的老师,它能使人变得宽容、善良、博爱和谦和。
其次我要感谢的是,在这方山水之中生活的人们。这么多年来,这些人们给了我太多的喜怒哀乐。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他们对这方山水的热爱。曲开老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人,因为一个能拯救自己也能拯救故乡的人,是多么的美好。禾木村喇嘛的故事告诉我,人不能口袋里越来越有钱,而内心却变得空空荡荡,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的内心要保留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更多的人们让我想起了心存已久的问题,自然风貌的保护或者文化特色的保护对当地人到底是否公平?所谓强势文化介入较小文化是否不道德?受时间的影响文化会不停地被改变,是否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后果是否一定是自然屈服于人类?这些,让我成为了一个大大的矛盾体。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我还会不停地和这群人一起喜怒哀乐下去。
我还要感谢《西部》。我知道,《西部》的前身是《中国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的前身是《新疆文学》。三十年前,从她的音容笑貌里,我认识了周涛、杨牧、章德益,以及更多的我们的前辈。从那时起,立志在这座文学殿堂里让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梦想。
最后我要说,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获奖对于我,是额外的收获。
评论奖
泉子:《诗之思》(载《西部》2012年第9期)
授奖词

写诗,办诗歌民刊,用诗的方式思考、探究周遭世界和心灵世界,已然成为泉子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之思》的写作持续多年,断片式的思考以“诗歌”为母题,关涉诗与传统、诗与时代、诗与心灵、诗与人等话题,“思”的整体性推进是为了确保“诗”的精进,因此是对“诗”的一次“护航”。在泉子那里,思考的深度和诗歌的日常实践是一种彼此砥砺,一位日渐成熟的70后诗人为我们提供了对“诗人”的另一种体认,或许这种体认才剥离了喧嚣沸腾的诗坛雾霾,道出了“诗人”沉潜的真相与本质。
受奖词
感谢《西部》杂志社,感谢各位评委,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诗歌之外的奖项。任何一个严肃的奖项,都是一次相互的辨认,而今天,我正是因一种相互辨认中的喜悦而站在这里。
《诗之思》的写作迄今已逾十年,或许,这将是一首永远不可完成之诗。它伴随着一个诗人的成长,以及那注定永远不可抵达的征程。它立志于成为一个人、一种语言,以及这尘世永远无法克服之局限性的见证。
我曾在一篇访谈文字中谈到:“《诗之思》写作起点是2004年的夏天,或许,它会与我的余生相伴始终,并与我写下的其它被命名为‘诗’的文字一道,作为一个不断得以完善的生命留下的痕迹。《诗之思》之于我的重要性,并非是它从同行中为我赢得的掌声,而是在于它为我提供了一种内心修炼、悟道求真的稳固通道。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持续的写作与修行中,我才得以真正地理解‘生命是一次澄清的过程,是一次次澄清的过程,是从一团混沌抵达澄澈与通透的过程,是从一块岩石通往白玉的过程。’”
再一次感谢《西部》杂志社的同仁与评委们,感谢你们的慧眼与洞察带给我的深深的温暖,也希望这些文字最终没有辜负这样的一种信任,希望这样的一次相互辨认最终完成的是一次共同的见证。
王敏:《巴扎里的时间》(载《西部》2012年第11期)

授奖词
巴扎和麻扎,是维吾尔文化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和终极指向的日常事项,是研究维吾尔人价值观、生死观乃至民族文化的神秘钥匙。青年学者王敏敏锐地抓住“巴扎”这一如今带有时尚表征的古老事项,引入对“时间”的分析,全方位展示出巴扎里的时间与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经营活动、人生态度等诸多方面的紧密关联。概括周全,说理有据,论证充分,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王敏集学者和作家于一身的综合素养与出众才华。
受奖词
感谢《西部》和西部文学奖的评委们,将这份殊荣给了我,在我得知许多也被提名的作家,并没有获得此项奖项的时候,我的确感到我并不能够心安理得地领奖而不感到受之有愧。我深信我是那许多被提名获奖的作家中“今年有幸”的那一位。
在特克斯的草原上领受这个奖项,被群山与草原环拥,让我想起我在喀什乡村巴扎与老乡一起赶集,体会时间流失的片刻,那是一种全新的主体性的赋予与设计,它让我能够成为我的参照,进而能够思考出一种扎根于新疆乡野的时间谱系。回想起来,仿佛我只有扎根向我所生活的土地,才能取得抵抗时间洪流的一点精神力量。
我想,是文学赋予我们这样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情感的痛苦、知识的荒僻与表述的焦虑,它让我们置身其中能够找到一种妥当的、重新设计的主体性,使我们最终成为我们,使我们最终能够拥有自己。我要感谢文学的这种力量,它让我通过它对我的设计,在自己身上不只看到边远的目光、偏僻的角落、复杂的地域文化境遇、纠结的族性与性别差异。它让我居于自身而不被缩减,放之世界而不至被流散。它以它全部的话语结构、时空坐标,设计、发明了另一个我,一个相对于现实经验而言,或许更完整的我。
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时曾说:“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的确,如果生命有一个意义的话,那就是生活在其中。如果文学有一个命运的话,那就是写作在其中。我只是有幸地生活在写作中,以期与更完整的自己相遇。谢谢大家!谢谢西部!
翻译奖
松风:“英美自然诗文”小辑(载《西部》2013年第6期)

授奖词
松风既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又有厚重的国学涵养,对待译事用力、用心。他的译作既能深刻把握原作的精髓,又能融入自己的学养,精准细致,充满韵味,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文主义气息。“英美自然诗文”小辑汇集了英美十几位著名作家自然主题的佳作,田野、河流、树林、花朵等惯常事物在他们笔下充满神秘的气息和蓬勃的生机。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和内心需求。松风优美、贴切的译笔,让我们不仅赏读到原作的独到情思,更心领神会译者“桥梁”作用之重要。
受奖词
第三届西部文学奖组委会和各位评委们,所有因对文学的爱而相聚在伊犁那片美丽土地的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获悉荣获西部文学奖翻译奖的那一刻,我正在万里之外享用英伦下午茶。望着眼前漫向天际的碧野,我的心里充满感恩。西部文学奖将首次设立的翻译奖授予“英美自然诗文”小辑,也许是对一种生存方式的呼唤和鼓励。
我们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其几何级数的线性发展,颠覆了人类的时空观念。面对越来越萎缩的时间和日盛一日扁平化的空间,我们几乎忘却了“宇宙”,再也不知何谓“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来不及拂去物质文明尘屑的我们,双脚已迈进了“大数据”时代。必将彻底颠覆既有生存方式的“大数据”,虽可准确跟踪我们每一个显性或隐性欲求,却无法慰藉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来自我们生存现实日渐物质化。我们与自然搏斗得太久,与自然的脐带早已被一代又一代人貌似合理的现实利益诉求所切断。要修复人与自然的本原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软化人的心灵。而软化心灵的最佳药物是文学。让更多的人浸淫于文学,并非不切实际的奢望,而是我们不得不为的选择。用文学去冲刷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在我们体内积聚的污垢。通过文学,我们感受周遭一切生命的喜怒哀乐,重建与一切生命的联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幸福地栖居在大地上。
授奖词对我翻译的褒奖,我将之视作对我的扶掖与期许。我深知,翻译与原作,就像隔着银河相望的一对恋人。我想做一名渴望抵达的译者,但我到不了彼岸。我唯有洞开自己的感官与心灵,将在原作里感受到的韵律、悸动、情愫,最根本的,对自然的关切和对生命的尊重,复制进自己的母语里,让我的同胞们倾听。
谢谢西部文学诸君。此刻我在米沃什和辛波斯卡的家乡克拉科夫祝福各位。我们热爱文学的人,就是要用触及心灵的方式,确保每天面对升起的朝阳和西去的夕阳,能够发出由衷赞叹:“万物静默如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