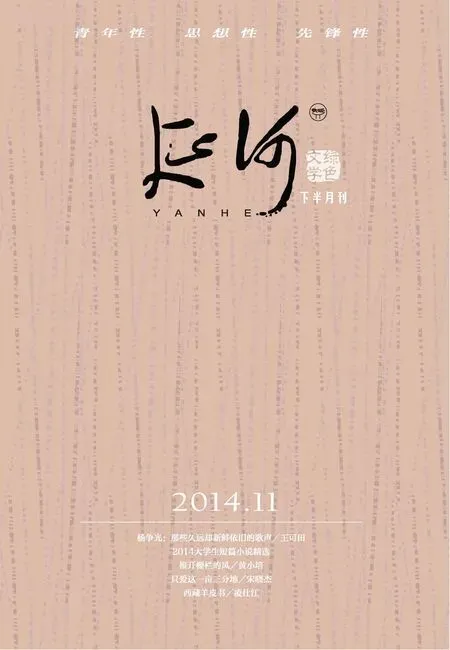秋到上林湖
2014-02-24付秀莹
◇ 付秀莹
秋到上林湖
◇ 付秀莹
去慈溪之前,便听说,要去上林湖看看。当时心里一动。
上林湖的名字,是早有耳闻的。然而,总觉得,远在浙东的上林湖,之于我这个京华倦客,更仿佛一个渺远的传说,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心里念里都有,却终究是一种审美的遥望,或者机缘的等候。
在慈溪,我们喝酒,闲谈。酒是黄酒。到了浙江,黄酒是必然的选择吧。大约只有黄酒,在这晚秋时节,才能够让我们内心炽热,让我们在暗夜中有勇气去捕捉生活的微光。旧雨新知,我们推杯换盏。私语,大笑,忘情,忘形,即便沉默,都是好的。岁月飘忽,一生中,我们能够有几次这样的欢聚?而上林湖的波光,在黄酒的迷人的呼吸间隙,在隐约的不安的期待中,明明灭灭。
终于抵达上林湖的时候,是近午。
一段极平凡的小路,连接着两个迥然各异的世界。一端是熙攘的俗世,一端是静谧的内心。从下车到上林湖,这一段路途,竟然是如此的切近,而又如此的遥远。
当一片湖水在我们面前慢慢敞开的时候,喧闹的人群忽然间便沉静下来。一种巨大的温柔的气息扑面而来,顷刻间把我们湮没。十月的金丝银线从远天倾泻,宛若金色的细雨,密密交织着银色的水滴,在水面上溅起斑斓的光。而郁郁苍苍的绿意,从四周的山上,跌入水中,那倒影经了湖水的浸润,更有了一种不可测的神秘,幽深的,丰富的,驳杂的,一言难以道尽的,仿佛一篇小说,拥有了宽阔的纵深的幽微的向度。
这便是深秋的上林湖了。
湖水饱满,明净,丰沛,有水鸟从湖面上掠过,倏忽便不见了。天空是那种澄澈的蓝,映衬着湖水的光影,以及四周的山色,仿佛墨色未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直教人疑心,这究竟是天上亦或是人间!远远地,有一只木船,暗沉的色调,有些破旧,在岸边孤独地横着。似有所待,又仿佛无所用心。浩大的湖面,唯独这一条小舟。这一条早已弃之不用的小舟,在水边依傍着,连同岸边的芦苇,以及芦苇的飞白,水鸟滑翔的姿势,执拗地同这泓湖水一起,构成某种诗性的复调。
乘坐的却是机械船。总觉得,这样的机械船,它的马达声,它冰冷的质感,于这上林湖是过于唐突了。然而,世间的事,缺憾是难免的。泛舟湖上的时候,风带着凉意,迎面而来,便也渐渐释怀了。船头仿佛一把硕大的剪刀,把丝绸般的水面豁然剪开,试图识破隐匿千年的心事。阳光照下来,淡淡的透明的烟霭,在湖面上浮动,且聚且散。周围是黛色的山峦,大多深秀的苍莽的调子,秋天的林木,绿得更见深沉了。新鲜的湿润的水气氤氲上来,淘洗着我们的肺腑,也淘洗着我们斑驳的铅华与风尘。风是微凉的,而阳光温热。这样的水上光阴,心无挂碍,渣滓全无,是上林湖的馈赠吧。
湖边的坡地上,便是越窑遗址了。
草丛中,落叶间,浅水里,随处可见青瓷的碎片。朋友递给我一块,笑说让我带回北京,或可换一栋房子。我看着掌心里的瓷片,边缘清晰,质地光滑,梅子青色,有着若有若无的纹理。这样一枚瓷片,它碎了,它不完整,然而,它却经历了千年前烈火的淬炼和美的碾磨,在时间的飞尘中,把一个时代的风华悄悄留念。有谁能够猜出,这小小的瓷片,是出自李白饮酒赋诗的杯盏,还是苏轼雪夜晴窗的笔架,是出自宋词中蛾眉婉转的素手,亦或是大江东去气吞山河的金樽?这遍地的瓷片,是文化的碎片,审美的碎片,是时间飞刀之下遗落的美的痕迹,是破碎,也是完整。
说来真是神奇。今年,从初夏到晚秋,我的生活,竟莫名地与青瓷生发出密切的关联。先是到丽水,见识了龙泉青瓷的清雅风致。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手边正是一只青瓷杯,大朵的牡丹,凹凸出恰到好处的手感。从丽水到北京,这杯子倒完好无损,而回家的第二天,杯口的边缘,却被杯盖碰了一个小的豁口。是不是,太美好的东西,总是易折易碎?我遗憾着,但执意不换。觉得,这有着缺口的青瓷,仿佛更接近生活本身。
从慈溪回京不久,又到宁波。离别时,老友竟然送了我一套越窑青瓷。倏忽间,仿佛又回到那一个晴好的近午,深秋的上林湖,千年的越窑,遍地的青瓷的碎片,在秋风中诉说着千年的沧桑。我抱着那一套越窑青瓷,从宁波到京城,一路辗转,小心翼翼,仿佛怀抱着一个稀世的宝贝。总以为,那一次上林湖之行,我无意间错过了青瓷的碎片,错过了千年文化的片言只语。谁能够料到,时隔半月,我竟然又重新捡拾起那个失落的传说。破碎的完整,完整的破碎。新的青瓷,旧的历史。旧的碎片,新的灵魂。这是青瓷的语言吗。
丢失什么,我们便捡到什么。获得什么,我们便失去什么。青瓷,以近乎文学的方式,浸润了我的日常生活,修补了我关于历史、文化以及美的思维逻辑。
上林湖,四周的山上,是繁茂的林木。这林木,曾经在千年前的越窑里燃烧。而这上林湖的水,以及湖畔的泥土,都曾经亲历和见证过,那一个时代的美的蜕变,以及诞生,当然,还有灰飞烟灭。
我们来了,又走了。我们匆忙的脚步,会不会惊扰了这片山水的千年旧梦?
我们来了,又走了。而上林湖,依然在那里。
走读西吉
对西海固的想象,最初来自张承志的散文。
从银川到西吉,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旷野寥廓,沟壑纵横。斜阳如醉,在天边热烈地燃烧。扑面而来的,是粗犷雄浑的塞上气息。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见惯了大平原的单调与平和,这奔涌如马的连绵群山,这大西北的漠漠黄土高原,究竟是怎样的胸藏崎岖呢?
踏上西吉的时候,已是黄昏了。向晚的西风,带来微寒的凉意,才恍然惊觉,这里已经是气候学意义上的秋天了。秋风过耳,把京城的浮躁与戾气轻轻拂去。葡萄熟了,枣子熟了,马铃薯熟了。炊烟袅袅,大地安详。有女子从街上走过,神态宁静,衣袂翩然。这是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吗?
“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自然,我们只是过客。对于西海固,对于西吉,我们的惊鸿一瞥,看到的或许只是它们平静的表象,而内心的沟壑与精神的陡峭,是潜伏在葫芦河的流淌中,还是隐藏在六盘山的褶皱里?是栖息在汉代古城的砖瓦上,还是逶迤在丝绸古道上最美的丹霞间?
在西吉数日,吃的最多的,是马铃薯。这西吉的宝物,这三个换命的兄弟:土豆,洋芋,马铃薯。它们喂养了一方子民的肠胃,也喂养了一方水土的灵魂。谈的最多的,是文学。西吉,位于宁夏南部山区,是人们常说的西海固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贫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不生长庄稼,却生长文学。或许,文学是这片土地上最为茂盛的庄稼——这是一种怎样的隐喻?
我不知道,西吉的马铃薯和文学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通道。是马铃薯喂养了文学,还是文学滋养了马铃薯。亦或者,它们在西吉的土地深处,共同孕育了西吉坚韧不拔的人民,从世俗到精神,从沉湎日常到超越日常。
沉默寡言的农民,白天在田野里劳作,而夜晚,他用满是老茧的双手,建构着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时候,他叱咤风云,他一字千金。他是文字王国里的王。在木讷笨拙的外表下,谁能够窥见他们隐秘的心灵花园——草木葳蕤,鸟语花香,这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抚慰,亦或是对苦难心灵的补偿?朴素的乡村知识分子,在干旱的季节里,内心的大雨滂沱,而此时,菜蔬繁茂,万物花开。谁能知道,在文字中自由行走的他们,究竟亲手触摸到了什么,才使得他们在乡村的鸡鸣犬吠中热泪盈眶?那些稚嫩的孩子们,那一页页渴望签名的作业纸,忽然让我满怀羞愧。我们这些来自京城的匆匆过客,在世俗的尘网中浪得虚名,是什么赋予我们指导人生的资格和权利?被浑浊斑驳的人世劫持已久,我们是否能够以最初的纯净,真正走进西海固,走进西吉荒凉而丰富的内心?
在中国文学的精神地形图上,有冠盖云集的繁华都城,有耕书承传的富庶乡村,江南的郁郁秀色,北地的亮烈奇崛,中原的旷达开阔,边塞的萧瑟苍茫——这是中国文学的丰富表情。然而,在中国的大西北,在这个被誉为文学之乡的地方,在西吉,这片并不丰饶的土地上,竟然有着如此丰美的精神的绿洲,这是一个奇迹。干渴的土地,为何偏偏能够孕育汁液丰盈的生命?这是一个谜。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如此强大,以坚韧的精神,自由的想象,近乎执拗的不懈,在现实人生的缝隙中,努力追寻和探求心灵世界的广阔和幽深?

治印 左权
这一回西吉之行,见到了很多宁夏本土的优秀作家。季栋梁、漠月、李进祥、了一容、火会亮……他们无一例外的沉静少言,气质从容。在热烈的宴会上,在喧闹的旅途中,在活跃的会议上,他们都不卑不亢,安之若素。季栋梁是活动牵头人,沉稳大气,指挥若定,有他小说的话语风度。漠月,我们曾同赴宁波领取十月文学奖。进祥是我的鲁院同学,新获骏马奖,他是民间的高手。而了一容和火会亮,都是西吉这片土地孕育而出的小说家。在西吉的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戴蓝色包头的女子匆匆赶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金莲。我能够想象,她怎样放下案头的工作,放下怀中的婴儿,放下繁琐的家务,一身风尘赶回西吉。西吉是她的故乡。在回程的车上,从她轻轻的讲述中,我隐约看到了她从乡村到城市,一路走来的艰辛劳顿。她认真地同我闲话家常,认真地同我探讨小说。焦虑是认真的,关切是认真地,淳朴也是认真的。有作家朋友同她玩笑,照例是极认真的神情。仿佛一把紧绷的小提琴,稍碰琴弦,便铮铮作响。这位坚韧的回族女子,素面朝天,在繁复的日常生活中辗转,想必,她没有闲情亦没有闲心,染上所谓女性作家的坏毛病罢。窗外山岭逶迤,阳光跳跃。她侧着身子,一一指点给我看——这是她的家乡啊。无论在市委书记的会客厅中,还是在家乡父母官的欢宴上,这位八零后的女子,都行止从容,言语有状,静如秋水……我是在回京的飞机上,才认真阅读了他们的文字——随身有一本《朔方》,西吉籍作家专号,看似平静的文字之下,有丘壑深藏,有激流奔涌。
一位宁夏诗人说:有了爱,才会在乡村的屋檐下梳理忧伤/有了爱,才会在西海固的痛苦里痛苦/怀揣荒凉的人世,对着寂寞的蔬菜/让西海固感知:我有多么爱你——
我相信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