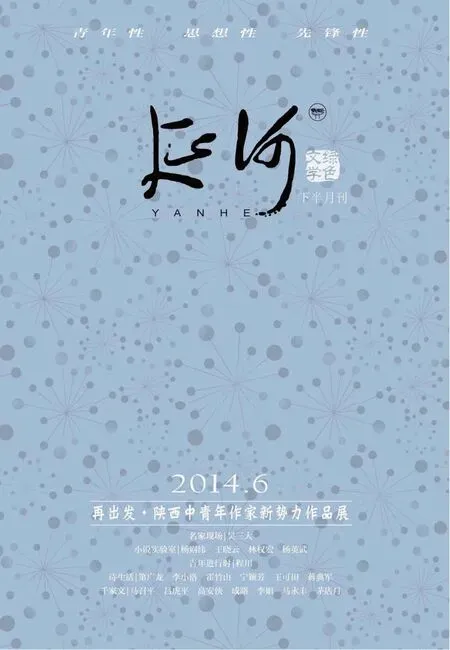画 面
——图画作品内质的艺术指向札记
2014-02-23◇成路
◇ 成 路
画 面——图画作品内质的艺术指向札记
◇ 成 路
成路,1968年6月生于陕西洛川。著诗集五部。诗集《母水》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备选作品,荣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第十九届“文化杯”全国鲁藜诗歌奖、中国首届地域诗歌创作奖等。出席诗刊社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散文诗刊第二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诗歌委员会委员,陕西文学院第二、第三批签约作家。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延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关于廖哲琳的写生画
“自我的陕北”
台湾和陕北是汉语文化系统下的两支具有差异性的另样文化。廖哲琳的生长文化背景是南岛文化、儒家文化和欧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混生文化体系,而她这次展出的速写画的画面语言是以陕北文化为主体的符号。当然,我们已经发现她在实现这些画面的时候,已经把陕北文化给了新的指认,使之得到了再次的繁衍。
这时,我在想:廖哲琳一个另样文化背景的画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画布上如何完成“自我的陕北”?这个问题在“漫步中的速写”的开幕式上她给了我答案,那就是如同村妇劳动,如同村妇生活,还有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故事。《男人的背后》是一个大女人的背影,面前空旷,生动的双腿处于奔跑的状态,使人不由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温情与感动;而大女人的壮实是支撑男人的柱子。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老表演艺术家,为了在银幕上逼真地演出疼,他在自己的十指上反复扎竹签后说,疼是倒吸凉气的,不是喊声。廖哲琳也一样,她“自我的陕北”不是用欺骗人的眼睛临摹的,是在劳其身躯和心智后融到生命里的,陕北和她之间消除了夹生和隔膜。
物象记忆
陕北主题画,自然物象山、河、羊、窑、人等等是入画的一个传统,廖哲琳也不例外,甚至有笨拙的嫌疑,正如对陕北,她自己的深刻印象是笨和大,其实她的这份笨拙是淳朴,这些看似不成熟的符号是她用自己的个体经验在彻底颠覆以往的惯法。换言之,就是超越了陕北现实的物象,运用物象记忆在画布上创造了另外的一个真实的“自我的陕北”。廖哲琳的《夜里火炕上》没有炕,只有主体人物的梦想和探究,而炕是海,也许是辽远的宇宙,这样的陕北在今天有的人看见感到突兀,或者说不成立,如同佛家纪念锁骨菩萨的延安宝塔能够成为革命的红色记忆,它需要时间。
在这里我不是有意回避美术教程里的绘画科学,是想说画里的艺术经验。科学是规律,艺术是想象,但规律的前身是想象,牛顿从一只苹果落地开始想象之旅发现了地球引力,那么绘画科学之外还有什么,画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天可以是绿的。这样说,是因为一位画家告诉我廖哲琳的画里“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把天画成绿色的了。我说,惯用的往往不是画家丰富经验的产物。

安天富 临·明·张岱《快园道古句》 行书
哲学想象
画,颜料堆积的物象。这些物象如果和现实物成了孪生子,那就是物质的势力。在这里,我想用“哲学”这个词,对于画家的画面进行文字阐释的时候,用到“哲学”这么一个词,可能感觉到有点玄,其实我是想用哲学的源出意:“爱智慧”。专业的画评人谈画,会给画家一个定位,那就是流派和主义的归属,或者按照绘画材料分类。而一个成熟的画家,在完成一幅作品时,会因为需要,采用各种方式、手段、材料来服务于自己的表达。也就是说成熟画家是各种流派和主义的邻居。
《黄土坡上的演唱会》,群山上演唱者沐浴在亮黄色的光芒中,近景山上三颗火焰树,是大山充满了活力和宗教。另一幅作品《雪天》,漫天的雪压迫着陡峭的山,山下牧羊人、羊群是一个点缀物,而恰恰就是这个点缀物里,牧羊人的身体和拦羊铲构成的“十”字,以及牧羊人头顶雪花泛的亮使观者看见了佛性,而离人不远处一颗孤独的树,正是佛的召唤,当然暗色的天压着一切。廖哲琳的画,就是用这种写实和想象聚合的语言,隐藏了她质疑人本质失却了的传统,这是她“爱智慧”的结果。“爱智慧”——哲学想象,使她的画面重建了陕北文化意象的序列。
廖哲琳的一个“自我的陕北”正在形成,并将会辽阔。
具实的判语
血色的象征群
阅读画,对我来说,往往会跳过绘画技术从画面的象征势力开始。
一群黑色的幽灵在墓穴里游荡,或者是在墓穴里争夺物质的胶着状态,而悬在幽灵头顶上的是血色的土地和土地之上的黄色块状物质。这是袁惠娟的油画作品《拜金》的画面叙述。我与这幅画对视的时候,看见了画家的哲学暗指——当下的“幽灵化人群”。 袁惠娟在画里述说的是人类灵魂的劫难,也在质问观者,你可否也行走在这群幽灵中?这质问,是画家在生活感受中分拣出来的“从恶”之源的发声。
作为观者,我心抖动。她的画布上血色颜料和景象隐含了社会状况,用象征手段在历史感的担当中表达了画家自己对社会的犹豫思考。
袁惠娟的血色意象是从一幅画中所描写:大海、山峦、山峦后半隐的血太阳,头偏向右的女子观看血色的海水,随着女子的目光延伸,一条线性血色路径延伸开始的。她说,“这是梵高画中的亢奋,似火山爆发的感力和能量”给自己留下的影子,其的影响仅这一幅作品。但在我一个观者看来,这个影子给了她一个绘画的象征群——血色。
是的,这时候更应该摆脱技巧而从本体上观察袁惠娟的作品了。她画的《山水人相连》,人这一主体金发女子,亦然右侧目沿着铺展开来的血色路径依山目触太阳。她画的《罂粟花》血艳扎眼。画家释放出来的这些血色象征群,在笔触的力量下违反常例,轻盈和笨拙的表现手法同时在画里应用,开始直接指向了生命与灵魂。在组画里,《交错》,血太阳在交错的流水下,那流水上的两个女子就是天使了,而动人之处是流水和天使之间的三块黑——飞行物向画面外翱翔,这是生命的望。《离骚》,我不知道这幅画是否与屈原的诗歌有关联,单看其画面,它符合了屈原诗歌的“遭忧”或“牢骚”之意。三个层次的女人,正面的黑色女子和裸体的血色女子同时右侧目,投向瞭望月亮的背影的白色女子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世界——以裸体的血色女子为中心构成了生育、理想、浪漫的世界。《挣脱》,这是血色的另一种表达,面部平静、闭目的血色裸女在绿色的背景下伸展肢体,看不见她的欲望,可从她半隐的生育之门看见了心灵的出口。
袁惠娟在绘画中制造了血色的象征群,她给血色没有赋予暴力,而是生育和犹豫。这就是我喜欢她这组象征秩序的原因。
执鞭着
袁惠娟“幽灵化人群”的造型,假如观者向深处看,其实画家自己就行走在这群幽灵中。她是执鞭者,鞭打血色的土地。为什么呢?袁惠娟,从南京移居到挪威,居然发现自己母性的黄色土地在被兄弟们涂上了另外的颜色,她49岁开始用颜料和线条混合成鞭子,含泪鞭打手足。
袁惠娟,中国清秀的江南人,绘画从挪威西画传统开始。可是她努力把“秦俑”这一中国西部粗狂文化元素作为自己一段时间的独立主题创作。在本质上,她把旧元素这一实质加入绘画,是按照旁观者看到事物和经验的观点来组合,通过自己幻与实的灵性视觉语言,或者说符号,表达自己质问的发声和内在的情感。
关于《战士》系列组画,袁惠娟说,这是一个致敬“兵马俑”——这幻般的两千年前中国历史和艺术形象。这句旁白其实道破了画家这一主题创作的本意——向被遗弃、异化的传统文化致敬的同时,强调华夏的文化血脉,也是鞭打背叛者。
《战士》组画,每幅作品里笨拙的、孤单的、眼睛不协调的俑人,按照俑人的各种态姿配以《孙子兵法》的术语,形成了一个多维的文化链条。其中一副画的描述语言是:一个俑人与歇鞍的战马相对,画家把想象中的草地、天空等各种元素移植在画面上,象征了杀戮的末日,协调绘画世界与不协调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战士》组画是在符合写实和记忆的景象中完成的,那《忙于闲中》组画是画家想象的真实了。落注:“枝头秋叶,将落悠然峦树。”的画,树根裸露在大地上,凋零的黄树叶有绿意的存在。落注:“又分功名,自是梦中蝴蝶”的画,夜色中断裂的壁岩上趴着根须,显然是在地下的境域里开放着一簇黄花,两只蝴蝶飞舞着。这两幅画共同完成了生对根性的眷恋和回望。在这里,观者把根性和华夏的始源文化是应该联系在一起的。
这时候,我想到袁惠娟画展海报上的一幅画,四座依次纵向溢满粮食的囤,地下散落的颗粒向远山延伸,皴裂的山体横向的肌理、金黄和微绿交混、山后的光。而《山中的秋》,多云的天空开了一个透亮的口,把人的视力点从大地的金色中援引走。《高淳固城湖》,五彩斑斓的湖畔,水面六只舟,稍远四棵树,远处的树林、山峦使观者向深处走。这似乎是风景画语言,是旅人看见宁静的风景。那观者若从逻辑语言上来看,就不难发现画的重心点是中国的平衡美学和宗教里援引生命的哲学了。
袁惠娟的绘画作品,在多文化的渗透里,已经模糊了地理分布,而她的艺术观念是强调本源的,她总是用写实、写意、抽象等复合语言,给这个流动的世界一个具实的判语。
暖记忆的造型
暖记忆
观察一个画家的作品,通过色彩和笔触看他们在创作时对文化元素的应用和把握,以及外露的文化思考是关键的。作为观者说出这样的一句主观话语,是建立在当一幅画进入观者的视角时,画和人在一个场中所产生的互动力,这力源是文化做了媒介的节点。那么,叙说一个画家的作品,其实是在梳理他的作品形成的文化流。
冯颜明的油画是以家乡——陕北场景为主要绘画材料的,偶尔也有外域材料的作品。1982年,他在画布上实现的《正月十五》,灯笼群、观灯人群构成景象,灯是多彩的色团,人群是用色彩间隔开来的重色竖笔。这是画家在记忆中恢复的生活印象,也是生活感觉——陕北节庆的环境、季节风、倒影的红这些元素形成了文化链条,是本已经成了静物的画面动了起来。我的视野里,这是冯颜明用纯粹的意象语言完成的唯一作品。这幅画对画家的重要性是“暖记忆”造型的展开,而且持续至今。关于暖,他说,冬天雪落后,在黄土上行走有暄热的感觉。陕北俗语:下雪不冷,融雪冷。在这样的记忆下,2001年,《冬雪》是凤凰山土红黄色的山体皱褶和台阶上飘落的雪,雪像固化的棉絮,山体的顶阶和二阶上的植物带动了整幅画的活力。2005年,《初雪》是画家站立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对这年第一场雪的主观画。这幅作品里他在处理目击的现有实物时是妥协的——把看见景物宏达,但显得空洞的全景剪成局部——残部,一片雪覆盖在半个物体上、冰溜子悬挂着,画面顶部的一缕红和画面底部黄色物体上的一个红色“慢”字构成了呼应关系。这个“慢”字的出现,画家是想告诉什么?是期盼融雪再多呆一些时日,还是告诉这个总在喜欢新而拆旧的乱象来的迟一点呢。这是一个诉求词,一个在日常中呼唤,或者遗忘的细节。生活就是在于发现这些细节变得生动。
冯颜明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他对人的幼年印象是祖父,他对村庄的幼年印象也是祖父。这种印象的影响之深、之远形成了他崇祖色彩浓厚的画风——土地是质体,植被是沙曼。《葵花塬》,这里的葵花是正在生长的绿色植物,开了点点纷乱的黄花也没有全向太阳。植物延伸到接近画面的四分之三时,突然绿色成了浮色,亮黄色明喻悠远的生命迸发。据画家自己说,那天带的减色的白没有了,就用画刀刮过去出现了这种效果。而在观者看来,这是符合绘画创作允许在科学技法上进行改写,加入画家自己的想象元素和手段,符合自然习惯,或者颠覆自然习惯都是可以的。
激活静物场
延安的画家有一个共性的创作素材,那就是中国红色经典的遗址场景。画家的笔触如果以自己对这些场景的目击物进行绘画,那就缺乏了与观者的公众记忆,看上去除过材料以外就是静物画了。画家对事物持续观察、持续写生,把自己的多项经验组合在一起,才能表现出这个事物内涵的冰角。同时,对于古地这样的静止事物场,是需要画家去激活的,就是组合活场。冯颜明有多幅经典遗址场景画,他在创作时努力把自己对场景的记忆和另外人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增加外物的介入。《枣园之春》,画家用多色彩流动的象征语言叙述大地,喻指了在河流里对昨天与今天的沟通。而飘逸的三个现代女子与远处的中央大礼堂遗址对望,叙述了痕迹上的精神不可磨灭性。
冯颜明有美术专业学院的绘画技术功力训练,现在是传授绘画技术功力的副教授。这个典型的学院派画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服从物象的真实,常常充满野性——创造力。《塞山奇峰》,油画上的这座山峰是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将军学习和战斗过的遗址,若干块状是他创作这幅画的语言策略,黄红块状、褐红块状垒山,画的力量就存在了整个画布上。山压下来,其的重量让河流和土地难以支撑,连同生机勃勃的毛头柳树也被山的颜色吃掉。关于这幅画,但愿不再附有其他暗喻了,它只是停留在艺术手法上,那就是通过夸张的语言叙述使画生出了张力。《斜阳》,从静态的树看见是一个无风的绘画环境,生长树的土地喧嚣、翻滚,还有一些血色的红藏在其中。选择这样的矛盾描绘语言,画家的企图明显是想画出以前没有过的经验,强调某种特定现实中的混乱和无序。当然,也可能是斜阳散乱的光源制造的现象,画本身并不包含其他深远的意义,只是画家自己目睹的物象与世界本质存在的一种纯粹性巧合的结果。这两幅画都是2012年的作品,它们抗争、呐喊之后呈现出了暖象征,和30年前《正月十五》的暖有相同点——温存触动了观者心底柔软的部分。
讲述
先觉者,是吟诵谶语的巫师,或者通灵者,当然自觉的艺术家在作品里也往往暗合。
圣女——祷告女——讲述者,这是一个用覆盖的方式完成的系谱。2008年,冯颜明创作130×160cm大幅作品《讲述》的时候,画的主体造型经过祷告女覆盖圣女,讲述者覆盖祷告女的过程,确立了讲述者这一主体造型,她的手势和身姿更像是合唱指挥者。倾听者、或者合唱者是万象众生,他们的面容表情激动、愤怒、沉思、吼叫、平祥、空洞,这些表情集合在一起本身就是混杂的曲乐。那讲述者,或者指挥者的这一长发女子,画家给她的负担就显得尤为沉重了。
冯颜明说,画家的每一个成长期,绘画语言和思考都会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他创作《讲述》时是在自己的青年旺期,这个时期正是一个人的思想从活跃向成熟过渡的苦闷期。那他的苦闷是什么呢?生命的苍凉与脆弱,灾难与恐慌。画家把他的苦闷需要倾诉,讲述者便是他的代言人了,倾听者是他虚拟的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众生,这些众生相里有那么几个背向讲述者,是对这一现场逃离的姿态。这时,画家用冷色调构成的整个画面世界,他突然借用的外力光源散落下来,光的出现给苦闷的众生寻找到了解决思考的通道。光其实是画家在渴望知道现实中的未知事物,他的作品是一种指向的艺术形式——顶上的追光——暖记忆。
这幅作品,在我的阅读中是冯颜明少有的冷作品之一,但就是在这冷中,画家把自己的生命借给了想象,创造出摄人的重感觉。
《讲述》作品完成后不久,四川省汶川发成了8.0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地质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