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古元
2014-02-19徐冰
徐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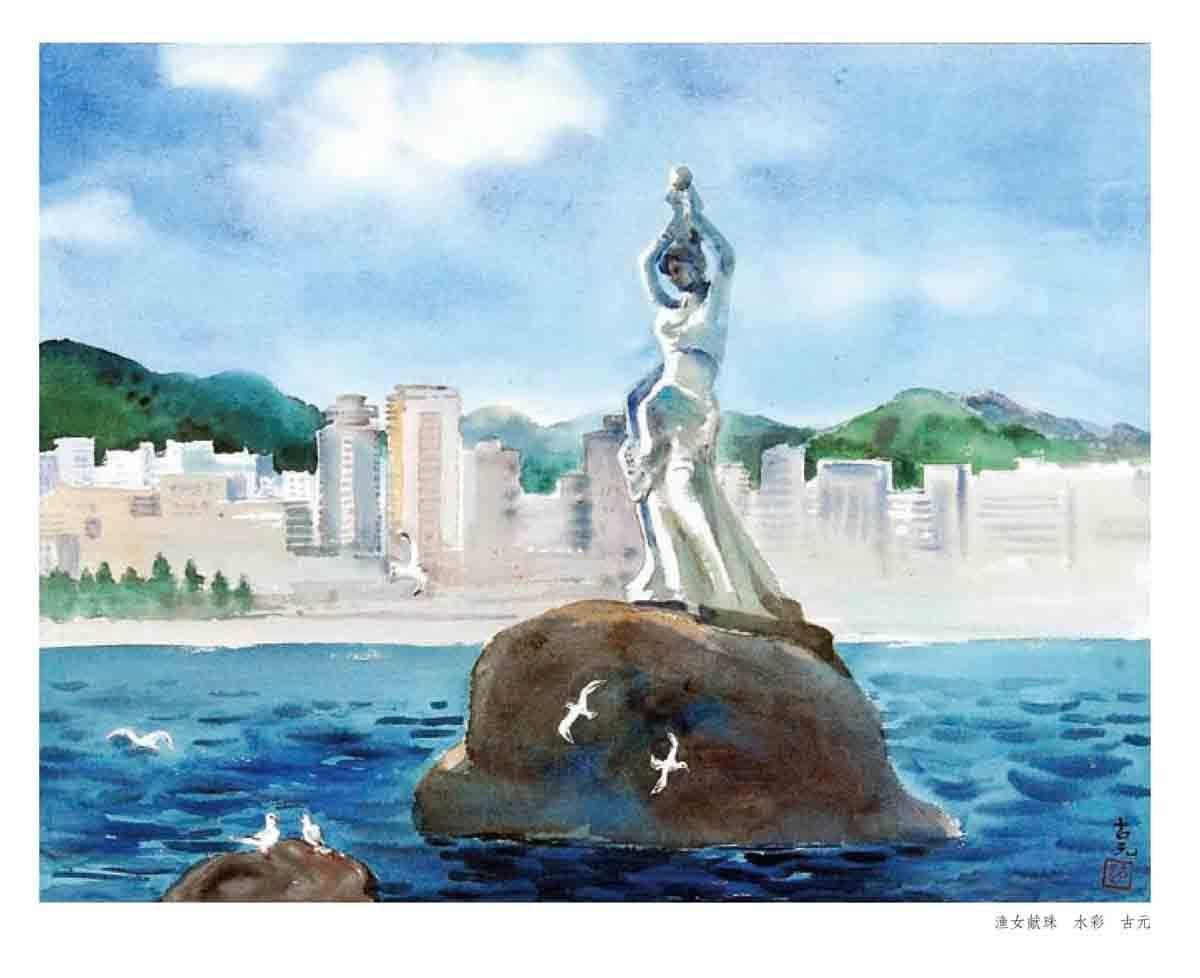


在我看来古元是少有的了不起的艺术家,而且我与他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事件和艺术上的影响,确切地说古元和他的艺术在我思维的网络中是一个座标,这就像棋谱上的几个重要的“点”。在我前前后后寻找的几个大的过程中,在我需要“辨别”时,总会遇到它,作为一个问题和参照,我必须面对它而不能绕过去。
还在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我爱古元的画》。因为当时的作文选中有一篇范文叫《我爱林风眠的画》,所以我就模仿了一篇,模仿是最省事的。我可以把古元的《京郊大道》《玉带桥》与春游的感受联系起来,当时古元的画吸引我的是那些大圆刀,我觉得一刀一刀刻得很利索。这,是艺术。
我家在北大,文革中我是个“狗崽子”,但也因祸得福。一些先生为了减少麻烦而清理旧物,知道我爱画画,便把收藏多年的艺术书籍转给我。其中有德国、俄国的绘画和解放区大众美术工厂的出版物以及鲁迅编的《新中国木刻集》等。我开始看到了古元早期的木刻,只觉得比后来的显得粗糙些,但刻得老老实实的和画中的人一样。
又过了很多年我去插队了,在北方的一个山村里,那地方很穷,但人很纯朴。也许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的举止动作都很慢,很简单,也有意思,穿戴、说话、办事都没多大变化。因为就这么几户人,谁家怎么回事,说不说从根上都知道,所以也就一是一、二是二的。当然也有政治和党的领导,但都是被“乡里乡村”化了的。那时带在我身边的一点宝贝中,就有那几本画册和我自己剪贴的古元的木刻与其它的一些版画。当时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个村子的一切真像古元木刻的感觉。这一点我印象很深。
1977年我从农村来到美院,开始学习艺术。杨先让等几位先生讲得最多的就是古元了。当时的最高追求就是表现好生活气息和人物的味道,特别提倡古元式的味道。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文化上有缺陷,但也有长处。比如说,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切切实实地理解古元的艺术,因为我在古元木刻的环境中生活过。我开始学习古元,试着把那些记忆中打动过我的细碎的情景,用木刻的语言表达出来。古元先生也肯定我的艺术追求。但我后来发现,我寻找的一种东西似乎是总也抓不到,这小到那村口的一个土坡坡的感觉。我可以从古元的木刻中找到这个土坡,但当我试着刻画它时,一经转印出来却已经不是那个土坡了。这时我已经开始觉得古元的了不起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是不可企及的。也许黄永玉先生的木刻是可以学的,因为它是“知识的”,但古元的木刻是没法学的,因为它是没有技法的,是“感觉的”。这是我刻了几百张木刻之后才体会到的。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让我们懂得我们这“种”人根上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画家能和古元比。中国古法不善画人,即使画人也多是文人意境之代替物。后来学了西法,又太会画人,太会把人物安排在自己的技术中。如果说古元给我们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那王式廓《血衣》类的作品则是话剧中的中国人。我曾经和古元的农民一起生活过,但我绝不敢胜过在王式廓的农民中。总之他们两人的农民不一样。
后来我留校了,因为我“学”得好。1982年前后,我自己有一些机会可以出国学习。但这大的变动无疑会影响到我的艺术,我拿不准,当然要征求古元的意见。他说:“你的路子适合在国内发展。”这话对我像是得到了一次艺术上的认可,从而满怀信心地继续着我要去做的事情。任何事只要你一个劲地钻下去,都能悟到一些或升华成另一种东西,我很庆幸的在那个节骨眼上,这个建议导致的后来的结果。
事情过去了才会清楚。我当时迷古元的艺术,其实并不懂得古元,或者说只懂得一部分的古元。也许是因为太爱一个东西,你看到了就足够了,不必再去问里面的东西。和许多同行一样,只看到古元那一代艺术家从生活到艺术的方法和朴实风格。以坚持深入生活模拟一种方式弥补达到古元境地的不足,而在愿望上对这种方式及风格模仿和继承的不走样,反倒使这种经验变异,退化为一种标本捕捉和风俗考察。以对区域的、新旧的类比把握作为把握生活最可靠的依据,似乎谁找到了北方鞋与南方鞋的不同,谁就发现了生活。这种对局部现象和趣味的满足,使创作停留在表层的、琐碎的、文人式的狭窄圈篱中,反倒失去了对时代生活本质和总体精神的把握,与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所思所想离得远了。又由于对这一经验的信赖,而只顾忙于形式效仿。一方面,不对这一经验作规律及方法论的探讨,深入到艺术文化学、社会学层次的研究,不能将其精髓有效地运用于新阶段的创作和对待又出现的新的艺术变革现象。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曾经参与过这批优秀创作的部分艺术家本人身上,这确实也是一种局限。
在美院读书时通过李树声先生讲授的《革命美术》这段艺术史课,我们了解了古元艺术的背景。但当时除了应付一门课外,与自己的画并没多大关系。在美院有先生讲艺术史论,有先生讲艺术技巧,但我总觉得中间还缺少一个环节,大部分学生毕业了也不能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不懂古元是因为我不懂这个关系,不懂这个关系也就不懂艺术是怎么回事。把古元的艺术放在这个关系中才能找到更多的信息。
古元那个时代之前的中国艺术之陈腐不用说了。西学东渐,社会动荡,到30年代艺术界更显出纷争的局面(和现在差不多)。借西开中的一支,讨论焦点大体限于借西方古典还是西方现代之争。汲古润今的一支部分继续海派变法,部分作点西法中用的暧昧试验。两支的共同弊病在于学术与社会脱节,陷于东西新旧之法所占比重多少之争。岭南画家多有投身社会革命,虽然作品时有某些新物点缀和政治暗示,使其政治与艺术身份基本是分离的,画画时既是雅士,出现了少有的政治上激进、艺术上温和的分离现象。发生在国统区的木刻运动,以为大众、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显示出特别的参与力量。这一支又与艺术目的直接和紧迫,方式上的“直刀向木,顷刻能办”基本上直接挪用外国木刻技法为时下的革命所用。实际还没有真正顾及艺术自身语言问题。丁聪等文人对社会时弊作了犀利批判,基本属于用通俗手法表示其政治态度的个别现象。在众多的赏识与努力中,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的一代艺术家,却在不为艺术的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最有效的进展。艺术的根本课题不在于艺术样式与样式之关系,也不在于泛指的艺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艺术的本质进展取决于对这一关系认识及调整的进展。
解放区的艺术来自于社会参与的实践,而不是知识圈内的技法改良。它不是政治实用主义的艺术,对艺术自身问题做过细致的改造和建设。它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个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这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的,一批艺术家在一个时期共同工作的结果。作品也许还不精致,便观念却以极其精确和深刻,它具备了所有成功的艺术变革所必需的条件和性质。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魅力的秘密,原来这魅力不仅在于它独有的智能及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社会革命与动,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称为这种精神。把古元与“前卫”放在一起谈人们会不习惯,但说法不同,核心是一个。即:对社会及文化状态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
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时,我才开始懂得古元,才开始懂得去考虑一个艺术家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的,他的根本责任是什么;才懂得试着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并问自己怎么去做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像古元他们那种明确的观念的落脚点吗?有他们对社会和对艺术的诚恳吗?我没有把握去回答,而仅有的把握是我知道了去思考它。这时我的艺术才开始有了变化和进步。看上去离一种东西远了,却与它的灵魂更近了。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倒像一篇思想汇报了。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结果可归结为一句话,也就是如何“继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这句话被说得已经很多了,但事情却还没有做好,有时忠实的、情感的、样式的继承也许是背离精髓的。用旧的师承方式来对待前人的或一个新的成果,这是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历史的循环好让我们把前辈的业绩梳理得更清楚,但历史的深度却在于这循环的似是而非中永远留着一个谜底,测验着人们的弱点和浅薄,以把锐敏与平庸区分出来。
古元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我终末成熟的艺术观说不定哪天又会陷入一个迷雾中,而我思维网络中的那个座标在我需要辨别时,我一定还会遇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