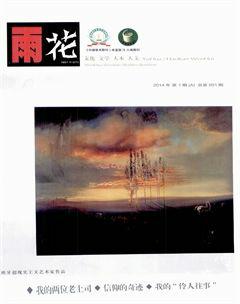坠落山坡
2014-02-17赵树义
●赵树义
坠落山坡
●赵树义
乡村的夜,乡村独坐山梁的孤寂把你的软弱之根赤裸裸地凸现出来,你生存,便适应,你适应,便冷漠,直至残酷的现实成为你生命的一种组成。
与生俱来的悲剧,与城市无关,也与乡村无关。悲剧的源起,犹如一枚果实的内核,无论麻辣或苦涩,终归与果实生长的山坡或院落无关。时间像一枚硕大的太阳,光线一瓣瓣地凋零,它却依然那样庞大,那样遥无尽头。果实一日日饱满,一日日占有自己的风味,而它生长的过程却是悲剧的全部。回望乡村,一种时间般抽丝剥茧的物质,渐渐浸入血液,侵入骨髓,芸芸众生草一样的衰荣便由此衍化而成。
比如黑夜。
城市的夜是孤独的,因为城市华灯如星河,因为城市高楼如蜂房。然而,城市独步窗口的影子,虽然落寞、窒息,却总显出踌躇满志和很有头脑的姿势。城市总企图凌驾在夜的上面。城市总企图沉溺于白昼之中。
乡村的夜却很空旷。一片浓重的黑无声地栖落肩头时,兽的利爪开始四处出没。夜风是很野性的呼吸,因而一种恐惧便成为乡村流淌在血管里的液体。你坐在油灯下或炉火旁,摇曳的亮光把你放大在墙上,你的恐惧便暴露无遗。透过这堵墙你研究山林和野兽,因此你对乡村有一种刻骨的仇恨。乡村的夜,乡村独坐山梁的孤寂把你的软弱之根赤裸裸地凸现出来,你生存,便适应,你适应,便冷漠,直至残酷的现实成为你生命的一种组成。你接纳着自然,自然也就收藏了你;自然亘古沉默,你无语地生长和死亡。
童年是一面山坡,一面鸟兽出没和结满野果的山坡。关于兽,人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瞳孔底便深藏着一种恐惧和憎恶。因而,童年最有作为的事,便是捕鸟和采摘野果。
鸟是一种自由的生灵,无论怎样的季节,它都选择天空作为生存和表现的最好场所。因此,要想击中甚至捕获它,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时机和圈套。果子却不然。相对于飞鸟,果子唾手可得,但如此轻而易举的事件却并非发生在所有的季节。获得果子需要时间,需要等待,像赢得爱情。鸟因天空而风头出尽,鸟却因了天空而被击中;果子因季节而成熟,果子却因了季节而凋败。这是一种命运,一种无法摆脱更无法抉择的命运,犹如上帝握在掌心的骰子,谁能告诉我,究竟骰子的哪一面才是运气蕴藏的所在?
黑暗之中,麻雀这种长着两只眼睛的生灵尤其显得悲哀。它龟缩屋檐下浑如一团泥巴,翅膀仿佛在白天丢失;而孩子们却像猫一样,蹑着脚在夜色中出没。孩子们握着一只手电筒和一根长及屋檐的木杆,好像握着一个阴谋。他们沿着墙脚悄无声息地搜寻,一旦发现目标,一束强光便骤然照射上去。麻雀似乎被光明照耀了,一动不动,随即便是木杆凌厉的一击,麻雀应声落地。麻雀不是被坚硬的物质击中的,而是被灿烂的光线击中的,它生命的最后挣扎仅表现为几根飘零的羽毛和一声无奈的哀鸣。
最悲哀的事件发生在深秋连绵的雨季。孩子们把活捉的麻雀用泥巴裹起来,投入火中徐徐烧烤,肉香四溢开来。与其说这是美餐鸟肉,勿如说是美餐勇敢。这个时候,怯懦如我者只有躲上阁楼,听脚下断断续续的水声。木水桶咚、咚、咚地承接着檐水,声音仿佛从峡谷飘荡上来,充满空洞的叹息。目光被屋檐压迫着平直地投射出去,没有天空,没有山,甚至没有树,雾湿的粪土气息、腐败的谷草气息和厚重的空气在眼前的世界弥漫着,庄稼开始在田间腐烂。
山坡上生长着很多故事。狼是羊们世代的对头,村民们却说那独行者是山神庙的守护神。羊们“咩咩”叫着走上山坡,走下山坡,它软弱的叫声似乎早已宿命地认定,自己只是别类口中的食物。
一只野果,弃之山坡平凡如一茎草、一抔土,不名分文,跻身城市却身价百倍。对野果而言,究竟是应该庆幸抑或是感到不幸?显然,野果无须计较这些,也从不计较这些。野果的悲剧与市场无关。野果刻骨铭心的是季节。
或许仅为证明勇气,我曾模仿同伴在山坡上进行滚动表演。山坡很陡很长,与地面构成45度角,直抵河沟。我伸展四肢,翻板一样缓缓滚动。我试图掌握节奏,但惯性和地心引力很快就把我的信心击为齑粉。天像漩涡,地像转盘,凭借一棵树的阻挡我才幸免跌入沟底。听着同伴的笑声,我知道我是一只受伤的鸟,我不能到天空飞翔;面对时间和重力,我知道我是一只坠落的苹果,无法在枝头炫耀。
这个事件埋葬了我的童年。我是一枚行将凋零或弃之山坡的果实,我喜欢移栽树木的行为,或许就是意识深处对再生的渴望。我把刚破土的杏树、破裂的核和它本生的泥土一起挖出来,移到我家的院落。我在树的四周围起一道土塄,每日按时观察和浇水。我盼望它长大。然而,当嫩茎快要长成枝干模样时,它却总莫名其妙地枯萎,或者横遭猪、狗甚至鸡们的践踏。树总在突然间死亡。一年又一年,我总一无所获。
在北方,在所有季节的果实中,青杏最早地出生,最早地上市,因而也最早地逝去青春。我未能让红杏爬出墙头,我的院子里没有一棵树过早地结果,没有一棵树过早地遭受攻击,也没有一棵树待到秋风初临时,就变得一无所有。望着山坡上那些早已干净了的枝干,我不知道,我该为我的失败遗憾呢,还是庆幸?
秋天的山坡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野果,故乡人都叫它杜梨。杜梨学名棠梨,属落叶乔木。杜梨的果实很小,如孩子的拇指肚;杜梨的果实很密,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布着褐斑的青皮经阳光久久地照射才呈现出淡淡的黄来。即使深秋时节,杜梨吃起来仍很涩,人们只得把倒牙的杜梨采回家中,贮藏砂锅,埋放炕洞,任其自然腐烂。待到果实稀少的隆冬,浑身已黑透的杜梨终于释放出独特浓郁的味道,像醉梨。这时候,杜梨才仿佛出阁的少妇,真正地成熟起来,也珍贵起来。
梨与杜梨在同一季节生长,同一季节坠落。梨与杜梨比,可谓族类中独秀的一支,纵然村野之人把称为杂种看做是最大的侮辱,但每年春天,却依然有人热衷于把杜梨从山坡移栽到院落,热衷于在杜梨的枝干上不厌其烦地进行嫁接。这仿佛一个游戏,一个老人们教导我的生活常识:如果你走路时,左脚总不断地踢右脚,那你就任选一个十字路口,垒一个石摞。石摞垒作塔的模样,庙的模样,不管谁有意无意地踢倒它,你都能把这个坏习惯传导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