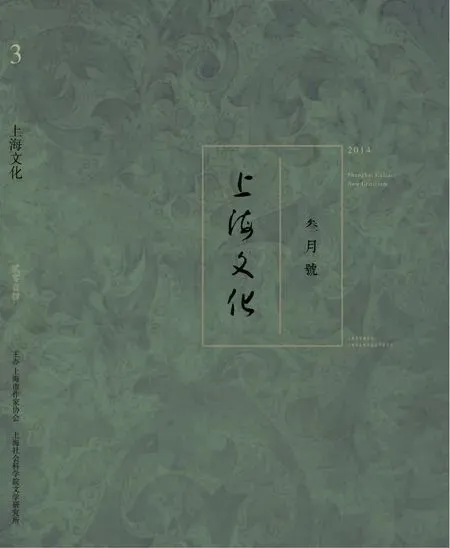《悲剧的诞生》中的动物问题
2014-02-12庞红蕊
庞红蕊
《悲剧的诞生》中的动物问题
庞红蕊
人们对这一界限的强调是为了从虚构的差异中捕获“人之本质”的概念,从人为的划分中确立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从暴力的切割中去除混沌状态所带来的恐慌
动物问题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哲学家们在探讨“人”的问题时,总是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有关人之本质的结论。希腊人将人定义为zōon logon echon(具有逻各斯的动物),这一规定是比较流行和通用的阐释。从此,逻各斯(以及从之而来的理性、语言、灵魂、精神等)被规定为人的原初本质,并垄断着整个哲学传统。动物是人的对立面和参照物,从而也被相应地定义为“非逻各斯(非理性、语言、灵魂、精神……)”的存在。动物本是与人类最为切近的绝对他者,然而,在哲学领域中,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们通过审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来捕获人性。人们在探讨动物问题时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有的哲学家认为是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有的认为是语言,有的认为是劳动等等。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发生了无数次的偏转,然而不管怎样,人们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在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一条天然的界限。因此,有关动物问题,人们的分歧在于“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划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至于“是否存在这一界限”问题,人们的答案从来都是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动物问题的探讨只是在复现和巩固人与动物之界限而已。人们对这一界限的强调是为了从虚构的差异中捕获“人之本质”的概念,从人为的划分中确立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从暴力的切割中去除混沌状态所带来的恐慌。人从动物这一镜像中来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可以说,如果去掉动物他者,“人性”就成了一片虚无的暗夜,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人性”这一概念是由动物他者来填充的。尼采开始反思“人性”、“动物性”以及“人与动物之界限”等传统哲学命题。《悲剧的诞生》一书是尼采思索动物问题的起点,它为以后尼采探讨相关问题奠定了基调,并影响了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对动物问题的看法。
酒神之醉——人与动物之界限的消解
在《悲剧的诞生》开篇,尼采指出阿提卡悲剧(Attic tragedy)是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相互激发的产物。日神和酒神是两种不同的生理现象:日神是梦,酒神是醉。他们又分别管辖两种不同的艺术世界:日神是个体化原则的神圣化身,他掌管优美表象,是造型力量之神;酒神则打破个体化原则,将个体拖入毁灭的深渊,使之融入原初的存在,他是一种载歌载舞的音乐情绪。日神和酒神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是相反的:日神在造型艺术的凝神观照中间接解决矛盾;而酒神则在意志的音乐符号中、在痛苦的再生中直接解决矛盾。然而他们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对立面,狄俄尼索斯是背景,而阿波罗是这背景之上的华美表象。“希腊的阿波罗主义必须从狄俄尼索斯的土壤中产生,……狄俄尼索斯式的希腊必然变为阿波罗式的”,悲剧是日神与酒神的和解,是由酒神主宰的神奇联盟。可以说,酒神精神是悲剧的本质。那么,什么是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与动物问题又有何关联呢?
酒神乃宙斯与地母神塞墨勒之子,出生后不久便遭到了提坦诸神的追杀。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他能变幻成公牛、狮子和豹等各种形状。他走遍了希腊、叙利亚乃至印度。一路上,他传授人们葡萄种植和酿酒术。尼采指出,酒神的本质乃是醉。在酒神之醉中,大地复苏,人们进入浑然忘我之境。
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重新修好,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与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慷慨地奉献出它的献礼,危崖荒漠中的野兽也安静地向人类走来(approach in peace)。
在狄俄尼索斯状态下,野兽“安静地向人类走来”,与人类和解
狄俄尼索斯精神是陶醉的世界,是异教的节庆,是“自豪、忘情、放纵”,是“对各色各样的严肃性和市侩气的嘲弄”,是“一种出于动物般的充沛和完美而达到的对自身的神性肯定”。在陶醉和节庆中,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被摧垮了。不再有专制和压迫,奴隶成了自由人。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与周围人和解了。在醉的战栗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被摧垮,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被冲毁。人与野兽之间不再是敌对的关系,在狄俄尼索斯状态下,野兽“安静地向人类走来”,与人类和解。会直立行走和使用语言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而此时的人类忘记了怎样走路,忘记了怎样使用语言。可以说,他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优越感,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抹去了。人、动物以及人与动物之关系都在狄俄尼索斯这里被重塑。尼采的酒神世界就如同本雅明所说的“救赎之夜”(the saved night),传统的哲学和人类学话语在这里都失灵了,人类不再是动物的命名者和救赎者,不再是动物的认知和改造主体。相应地,动物也不再是“有缺陷者”,不再需要人类的修补和拯救,不再为人类所利用。动物摆脱了人类的桎梏,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可见,酒神之醉并不是如传统哲学思维那样将人和动物对立起来,它从根本上摒弃了这一思维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与动物之关系的别样景观,为我们开启了思考动物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酒神之“醉”中,人们失去了理智,将压抑已久的、更为原始的动物性力量释放出来;在“醉”中,人们打破了个体化原则,摧毁了二元性的僵化机器,僭越了所有人为设立的界限。狄俄尼索斯的“醉”与苏格拉底的“醒”相对立。苏格拉底指出,城邦的护卫者“必须避免酩酊大醉(keep away from drunkenness),他们是天底下最不应该酗酒的人,因为一酗酒人就会忘乎所以(not to know where on earth he is)”。酒醉会让人丧失理智、纵情狂欢,会让人僭越界限、忘乎所以。苏格拉底强调界限的明晰性,他将正义定义为“做自己的事”(the practice of 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从个体层面上讲,个人的正义就是坚守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之间的界限。其中,理智是引导者,而激情和欲望是被引导者。一旦动物性欲望逾越界限,人就会兽性大发、害人害己。从城邦层面上讲,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不越俎代庖。“城邦中的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卫者这三个阶级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便是正义,而这也会使城邦成为一个正义的城邦。”
此外,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家力量与苏格拉底式的理论家力量相对立。对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家而言,动物性本能(instinct)是创造性、肯定性的力量,意识(consciousness)只起批判和告诫的作用。而对苏格拉底式的理论家而言,动物性本能成为批评者,而意识则成了创造者。苏格拉底式的理论家“始终不动声色、冷眼静观(remains a calm,unmoved gaze)面前的形象”。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他们以一种鉴赏者或批评家的眼光来审视对象,与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分即属于这种看待物的方式。在笛卡尔看来,人是“我思”的主体,而物是“我思”的客体。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动物处于“被注视”的赤裸状态中。正如德里达所说,“动物由这样一种原理组成,即:它可以被观看,却不能观看别人。人与动物相互注视的经验从未纳入到相关的哲学或理论话语结构中”。由于人类对动物主观能动性的极力否认,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永远都是单向的:人类能注视、思考乃至利用动物,动物却不能反过来注视、思考和利用人类。主客体的思维方式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狄俄尼索斯的艺术家力量取缔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he i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ubject and object)。这种力量不仅使人与人之间重新修好,也使敌对的(inimical)、被奴役的(subjugated)动物与人类和解。其次,苏格拉底式的理论家主张在审视物的时候应“不动声色、冷眼旁观”,康德的“无私利性”审美观即属于这种看待物的方式。在康德看来,“鉴赏力不带任何私利性(apart from any interest)。它是这样一种能力,即通过愉悦或者不悦而对某个对象或者某个表象方式作出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使人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他将审美行为看作“不带任何私利性的”,“无私利性”的意思是对某事或某人无动于衷、无所意愿。尼采反对康德的“无私利性”。他提出质疑:艺术家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怎会无动于衷呢?艺术并不是无私利,它从来不“悬置”欲望、本能或意志。恰恰相反,艺术是“权力意志的刺激物”,是“激发意愿的东西”。“无私利性”的康德仍然把自己摆在观察家的位置,而没有从艺术家(创造者)的角度来看待美学问题。观察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缺乏创造性的天赋,“像一条肥虫的躯壳,体内空空,缺乏自我体验”,只会以不含私利的态度来对待美。与观察家相对立的是艺术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他雕刻的少女像激起了他的情欲,他为这座雕像着迷,并像情人一样拥抱它、拥吻它。可见,在尼采看来,艺术并不是“无私利”的,它并不弃绝欲望,也并不净化心灵。相反,艺术激发欲望、刺激心灵。在陶醉的艺术家状态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生命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动物性本能在这里是一种创造性、肯定性的力量。而在无动于衷的观察者(理论家)状态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生命力的虚弱和贫乏,动物性本能在这里得到最大的抑制。
生成—萨梯里
酒神狄俄尼索斯具有变形的力量,他可以变成公牛,变成狮子。他旺盛的生命力可以使他突破现有生命形式的界限向动物生成。酒神的变形是对生命形式一元性的突破,使生命向着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不仅酒神具有变形的力量,他的信徒们也被这种力量所传染,弃绝自身而幻化成他者。
看到自己被一群精灵所围绕,并感到内心与他们融为一体,这是一种艺术天赋。狄俄尼索斯的兴奋情绪能够将这种天赋传输给一整群人,悲剧合唱队的这一过程就是戏剧的原初现象:看到自己在自己眼前变形(transformed),人好像真的进入另外一个身体,融入另外一个角色。这一过程乃戏剧发展的开端……在这里,我们舍弃了自身而进入另外一种天性。而且,这种现象以一种传染病的方式呈现出来(occurs as an epidemic):整个人群都感觉自己像这样神奇地变形了。
悲剧合唱队不同于行吟诗人和画家,因为后者总是和他们的人物形象保持距离,总是用静观的眼睛来审视外在的事物;悲剧合唱队也不同于其他合唱队,因为后者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名字和现实身份,他们从不舍弃自身,从不进入另外一个身份。悲剧合唱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拥有变形的力量。整个群体都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舍弃自身而进入到另外一个异己的身体。悲剧合唱队是一支变形者的合唱队,他们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名字,忘记了身份和地位。他们超离了自己,超离了社会现实,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那么,他们获得的这一崭新生命形式是怎样的?
悲剧合唱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拥有变形的力量。整个群体都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舍弃自身而进入到另外一个异己的身体
迷醉(enchantment)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前提。在这种迷醉状态中,狄俄尼索斯信徒将自己看成了萨梯里(Satyr),而作为萨梯里他又看见了神,换言之,他在变形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幻象,这一幻象外在于自身,是他的状态的阿波罗式完成。戏剧便随着这一幻象产生了。
在迷醉状态中,狄俄尼索斯信徒们变形为酒神的侍从萨梯里。萨梯里是怎样一种形象?博尔赫斯在《想象的动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中这样描述萨梯里:“(他)好酒、好色,下半身是山羊,上半身有手臂和人头。他披着厚发,长着短角,尖耳朵,钩鼻子,眼睛东溜西溜的。他随侍酒神,闹闹笑笑,不流血便征服了印度。他们伏击山林女神,与她们调情起舞,他们的乐器是笛子。乡村的人对他们尊敬,将首批丰收的水果供奉他们,羔羊也是祭祀他们的祭品。”萨梯里人头羊身,载歌载舞,酩酊大醉。他类似于卢梭笔下的野蛮人形象,没有理性,没有智慧,服从自己的动物性本能。在文明人和知识人被塑造之前,他便存在着。他是文明人和知识人的祖先。尼采强调萨梯里并不等同于进化论意义上的人类祖先猿猴。在生物人类学意义上说,猿猴到人类的转变是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的进化过程。猿猴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低级阶段。然而,尼采将萨梯里看作人类的祖先是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来说的。萨梯里绝不是人类的低级阶段,恰恰相反,“他是人的本真形象,是人最强烈冲动的表达,是因为靠近酒神而欣喜若狂的迷醉者,是与酒神共患难的伴侣,是大自然心灵深处之智慧的宣告者,是大自然性之万能力量的象征”。在尼采眼中,萨梯里既是文明人的祖先,也是文明人的对立面。萨梯里真实,文明人虚假;萨梯里强大,文明人虚弱。从萨梯里到文明人的转变不是一种进化,反而是一种堕落。萨梯里的半人半兽形象逃脱了柏拉图道德图解的世界,他呈现出生命的秘密本质
萨梯里上半身是人的形象,下半身是山羊,他是半人半兽的混合体。在柏拉图的隐喻世界里,半人半兽的形象具有一种说教性的力量。“这种形象被用于告诫人们,被欲望驱使的人类是如何变成野兽的俘获物”。他以一种嘲讽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为了唤醒在荒唐罪恶中精神堕落的人们。如果说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半人半兽是作为一种否定性形象出现的话,那么在酒神的世界里,半人半兽的萨梯里是作为一种积极肯定的形象出现的。他以一种奇异的魅惑力体现了生命的强度,他以混合体的形象跨越了物种界限,突破了固有的生命形式。萨梯里的半人半兽形象逃脱了柏拉图道德图解的世界,他呈现出生命的秘密本质。萨梯里的兽性层面在这里不是遭到排挤和嘲讽,而是受到肯定和褒扬。
萨梯里使用的乐器是笛子,他吹出的是“奥林匹斯狂欢纵欲的笛子旋律”(orgiastic flute melodies of Olympus)。这种音乐“具有动摇我们根基的力量和奔流直泻的旋律,具有和声的销魂境界”。人类的根基之所在乃逻各斯,而狄俄尼索斯音乐动摇了这一根基,将动物性的混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放纵、酒的狂饮等动物性本能都在萨梯里的笛声中得到了彰显。与此相对应的是苏格拉底的音乐。为了培养勇敢节制的城邦护卫者,苏格拉底对乐器和音乐曲调进行了精心择选。他“选择了阿波罗及其乐器(Apollo and Apollo’s instruments)而不是马叙阿斯及其乐器(Marsyas and his instruments)”。马叙阿斯是弗律基亚地区的萨梯里,他使用的乐器是长笛。而日神阿波罗使用的乐器是七弦琴。长笛是所有乐器中音域最广的乐器(the most many-stringed of all),其他多音调乐器都是对长笛的模仿。长笛能够创造出复杂的节奏和多样的韵律,如果城邦的护卫者长期沉溺于此种音乐中,会放纵情欲、喜怒无常。相应地,阿波罗的乐器韵律和谐、节奏单一,护卫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理智、节制的品格。复杂的音乐让人放纵,朴质的音乐让人节制。阿波罗的七弦琴代表着理智,代表着理想的人性;马叙阿斯的笛子则代表着情欲,代表着放纵的动物性。苏格拉底将长笛的制造者和演奏者赶出城邦,这也意味着他将动物性放逐出城邦之外。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尼采的酒神音乐是对苏格拉底音乐的反驳。尼采肯定萨梯里的音乐,而苏格拉底则坚决否定这类音乐。尼采通过肯定萨梯里的音乐来肯定情欲、肯定动物性,而苏格拉底则通过否定这类音乐来否定情欲、否定动物性。
狄俄尼索斯的信徒们在迷醉状态中“看到自己在自己眼前变形”,变形为半人半兽萨梯里。变形(transformation)不是对萨梯里的模仿和再现——即“像萨梯里一样”,而是通过达到一个近似区域变成萨梯里。在这一区域中,人们再也无法将自我和生成物区分开来。在人与萨梯里之间,在两种异质生命之间,架构起来的不是一种相似性,而是一种极度的接近,一种绝对的相邻关系,一次滑移,一种生成。生成-萨梯里完完全全是真实的,但这里的“真实”并非是人“真的”变成了萨梯里,而是说人脱离了原有的领土,向异质之物逃逸。人在这里发起了一场脱离领土的运动,他脱离了现有身份和地位,甚至脱离了人这一物种,将自己带入一个强度场,带入一场不可抗拒的生成之中。生成不同于进化,进化总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实现的,而生成是通过传染来实现的。狄俄尼索斯将放纵、陶醉、狂喜等动物性因素传染给信徒们,信徒们又以相互传染的方式扩展为一个集群。“这种现象以一种传染病的方式呈现出来(occurs as an epidemic):整个人群都感觉自己像这样神奇地变形了。”狄俄尼索斯信徒向萨梯里生成,他们指向的是半人半兽,一个混种。萨梯里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秩序,任何一个领域。他摆脱了二元性的僵化机器,而介于人与动物之间。他触及了人类认知范围的极限,是不可分辨之物、难以感知之物。萨梯里的混种形象使人与动物之间的明晰界限变得不可能了。
悲剧的再生——人与动物的和解
苏格拉底用理论概念替代了悲剧图景,从而宣告了悲剧的死亡。然而,“伟大的赫拉克利特教导我们,万物始于火,又向火回归,往复循环。今日我们称作文化、教育和文明的东西终有一天要接受公正的狄俄尼索斯之审判。”尼采指出,“我们正在经历悲剧的再生(the rebirth of tragedy)”,德国音乐作为一股反苏格拉底的力量正大放异彩。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他们的音乐像一阵狂飙席卷了当代死气沉沉的文化荒漠。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的第二十节末尾为我们描述了悲剧再生的图景:
我们的目光茫然注视着那已然消失的东西,却看到仿佛有某种东西从金光灿灿的深渊处升起,它繁茂青翠、生机盎然、充满渴望。在这过剩的生命、苦难和快乐(superabundance of life,suffering,and delight)里,悲剧端坐中央,体验着极度的狂喜,聆听着那遥远而忧郁的歌声。歌声诉说着存在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和痛苦。是的,我的朋友,像我一样信仰酒神的生存方式和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已成过往。请戴上常春藤花冠,拿起酒神杖,如果有虎豹愉悦地躺在你腿旁,请不要惊讶。从现在起,要敢于做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因为你必会收获自由,必会得到拯救(redeemed)。你会随同酒神欢快的游行队伍一路从印度漫游到希腊!准备迎接一场艰苦的斗争吧,但也要坚信你的神必会创造神迹!
当酒神狄俄尼索斯被苏格拉底放逐,世界就陷入了荷尔德林所说的“贫困时代”。冷静清醒的理论家们统治着这个贫困的时代,他们崇尚知识、理智、审慎以及静观,将陶醉、狂欢、欲望乃至痛苦驱赶出去,生命因此变得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尼采指出,既然万物始于火又归于火,那么悲剧从酒神中诞生也必将从酒神中再生。当悲剧再生时,贫乏的生命又将“繁茂青翠、生机盎然、充满渴望”。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将《圣经》中的“义人必因信耶稣得生”置换为“人必因信酒神而得生”。酒神取代上帝成为“公正的审判官”,“悲剧式的人”取代“义人”获得永生。当酒神再次降临之时,当悲剧再生之时,威猛的老虎和豹子变得温顺起来。人与动物之间将不再疏远、不再敌对。而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也会在酒神的迷醉力量下被重新塑造,向半人半兽萨梯里生成,向异质生命生成。
一个多世纪以后,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敞开:人与动物》(The Open:Man and Animal
)一书中的开篇描述了义人(the righteous)在末日审判时的具体形象——Theriomorphous(兽形)。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收藏着一部13世纪的希伯来文《圣经》,该书中的一幅插图引起了阿甘本的注意。这幅插图描绘了义人在末日审判这天举行弥赛亚宴饮(the messianic banquet)的场景。这一场景既是整部《圣经》的末尾,也是人类历史的终结。阿甘本对这幅插图进行了细致地描述:在天堂树的树荫下,两个乐手正在欢快地演奏乐曲,头戴冠冕的义人端坐在铺设华丽的桌旁。义人的一生都遵守着摩西五经的教义,然而在弥赛亚的日子里,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利维坦(Leviathan)和比蒙巨兽(Behemoth)的肉,而不必担心这一杀戮是否符合犹太教的法规。这种观念已为拉比犹太教传统所熟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还未曾提及的一处细节:微图画家所描绘的义人形象并不拥有人类的面庞,这些冠冕下方其实是动物的脑袋。此处,右侧有三个形象,即:锋利的鹰喙、红色的牛头以及狮子的脑袋,我们能够通过这三种形象辨认出三种末世动物(the eschatological animals)。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图像中的另外两个义人呈现出驴子的怪诞特征和豹子的轮廓。两名乐手也长有动物的脑袋,最为醒目的是右侧演奏小提琴的乐手,他长着一张受到神启的猴脸。
画中的义人在分食利维坦和比蒙巨兽的肉,而丝毫不顾虑犹太教的教规,这是因为他们身处于弥赛亚的时间,法律和教规被悬置的时间。令阿甘本惊奇的是画中义人的形象:他们拥有人的身体,却长着动物的脑袋。“为何人类终结时的代表长着动物的脑袋呢?”有很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都没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答。Zofia Ameisenowa试图将瓦尔堡学派(Warburgian school)的方法应用于犹太教文献。她指出,兽头人身的义人最早可以追溯至诺斯替教(Gnostic)的占星术。在诺斯替教的教义中,星座的形状像动物的脑袋,义人死后升入天堂变成星辰,所以就有了人身兽头的形象。阿甘本认为Zofia Ameisenowa的解释并不符合犹太法师传统。因为按照此传统,义人应该是弥赛亚降临时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不会死去,更不可能变成星辰。在阿甘本看来,半人半兽的义人形象指涉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崭新关系,而这一崭新关系也隐含在《以赛亚书》中的弥赛亚预言部分,即:“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安波罗修图书馆手稿的艺术家给以色列余民安插了一个动物的脑袋,他们想借此说明,在末日这天,动物与人的关系将呈现出崭新的状态,人自身将与其动物本性和解,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末日审判的时间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在这一刻,人类被重塑,变形为半人半兽的全新形象。一方面,在人类内部,人类不再将理性与欲望、语言与声音、政治生命(bios)与赤裸生命(zoē)等严格划分开来。另一方面,就人与动物物种的关系来说,人类不再是动物的认知主体,动物不再受人类的奴役。人与动物之间将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关系。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
)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头,它是人身上最神圣的部分,也是其他一切部分的主宰”。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围绕着头部建构起来的:为了防止头部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来回翻滚,诸神将躯干赋予头部,作为头的运载工具;为了让头部可以四处行走,可以攀援和支撑,诸神又将四肢赋予头部。在柏拉图看来,头部是诸神模仿宇宙的圆球形状制造出来的,里面承载着不朽的理性灵魂。这部分灵魂使人类从地面飞升,趋向天堂。爱智慧的人仰望天空,关注身上不朽的部分,珍视神圣的灵魂;而耽于欲望的人靠近地面,关注身上生灭的部分,玷污了自身的神性。动物是由后者转化而来的。以较为高级的爬行动物为例,它们总是盯着地面,从不仰望天空,从不使用头部的神圣灵魂,所以“头部变长,并且有各种形状”。在《圣经》中,末日审判要区分义人和恶人。“信上帝”的义人进入天国享受永生和富乐,而“不信上帝”的恶人则难逃刑罚的厄运。义人与柏拉图的“爱智慧的人”相对应,他们趋向天堂、追求不朽;而恶人与“耽于欲望的人”相对应,他们放纵欲望、腐朽堕落。在这部13世纪的希伯来文《圣经》插图里,义人有着人的躯干,却长着动物的脑袋。动物的头替换了人的头意味着无理性替换了理性、混乱替换了秩序。可以说,义人的兽首形象是人之本质的消解。可以说,义人的兽首形象是人之本质的消解
尼采和阿甘本,一个探讨悲剧之再生,一个探讨末日审判之场景;一个探讨异教神——酒神,一个探讨犹太教;一个是诞生-死亡-再生的环形时间结构,一个是时间之终结的线形结构。虽说他们的探讨有诸多不同之处,然而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尼采和阿甘本都从根本上摒弃了人与动物相互对立的传统哲学思维,他们都希冀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人与动物能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和谐相处,这为我们开启了思考动物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此外,尼采“悲剧式的人”在悲剧再生时向半人半兽生成,阿甘本的“义人”在弥赛亚时间里也变形为半人半兽,这两类形象都从根本上取缔了人,取缔了人与动物之界限,向混种生成。
❶Matthew Calarco,Zoographies: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3.❷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7页。
❸尼采:《权力意志》,第4部分,转引自《尼采与哲学》,2001年版,第17页,注释2。

❺尼采:《权力意志》(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36页。
❻Giorgio Agamben,“between”,The Open:Man and Animal
,trans.Kevin Attell,(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81-82.❼❽❾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Second Edition
,(Basic Books,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403e,82;433b,111;434c,113.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