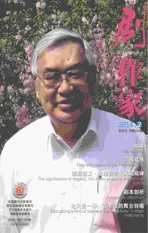论风景一种:百老汇的舞台转喻
2014-02-07濮波
濮 波
音乐剧的景观化和伦理真空地带
当今的舞台,是一种情境主义者德波所言无奈的景观,剧场化已经渗透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而生活的实质漏洞百出,离希望的空间渺远。舞台,或者像舞台戏剧一样的景观,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和视觉记忆。舞台,它再现或者表现社会的真实图景。所谓舞台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喻,就是指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而日常生活的剧场化,则是另一种生活对应于舞台的转喻系统。)
这里所说的是前一种舞台转喻,舞台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喻。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1)、一个瞬间转喻一段社会时间的(比如萨特的《禁闭》、品特的《生日晚会》、布鲁斯·诺里斯的《克莱伯恩公园》);(2)一个相对较小的时空转喻另一个相对较大的时空的(比如老舍的《茶馆》);(3)两个空间完全对等的置换(比如标榜在时空结构上等同的自然主义实验作品。这些作品在理论中存在,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一个理由是,百分之百的即兴创作和在场,以及取消再现的努力几乎都是不成立的)等等。相对于转喻的修辞,舞台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粒沙中见到的世界”,或者一个片断(横剖面)中获取的社会全景。这种尝试的审美基础就是“舞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或者“舞台是社会的转喻”。
舞台转喻本质上是一种典型化的或者非典型化的再现,它与另一种修辞:“表现”的模式不同。表现类戏剧几乎认为戏剧可以是完全创造自舞台上的,艺术高于现实和社会。社会又可能模仿戏剧。而当代被表现的戏剧,不是从社会风景中截取的。
这种舞台修辞的不同,使得当今的剧场依然呈现出幻觉和反幻觉的两种图形和风景。比如说,选秀是表现,游戏式的、开放式的先锋戏剧是表现,它不模仿现实。而通过排演的戏剧,无论荒诞剧还是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都应该是再现剧,它的审美对应就是幻觉剧场。今天,在百老汇演剧区,幻觉剧场和反幻觉剧场的争执,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阶段。尽管阿尔托和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吸引了一大批实践者,但是在剧场上,那些最能获得票房的依然是幻觉的剧场。如在最近的《纽约时报》戏剧版里所上榜的最热门戏剧中,除了品特的《背叛》等少数几部话剧之外,几乎清一色都是音乐剧的天下:这十大热门是《女巫前传》(Wicked)、《狮子王》(The Lion King)、《魔门经》(The Book of Mormon)、《蜘蛛侠》(Spider-Man: Turn Off the Dark)、《长靴妖姬》(Kinky Boots)、《玛蒂尔达》(Matilda the Musical)、《安妮》(Annie)、《背叛》(Betrayal)、《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和《摩城》(Motown: The Musical)。可见以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和盛大的舞台景观为吸引观众手段的音乐剧,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幻觉剧场的模式。
这些以炫耀场景效果的剧作,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之观念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戏剧观格格不入,相差甚远,然而这就是当今百老汇的现实。全球化导致时空的分延和景观化效果的加强。于是,在这种景观化的舞台伦理下,道德屈服于景观。虽然这些音乐剧最后都通向一种光明的主题,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的主题,在舞台上需要营造巨大的光影工程。而且,这种工程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
因此,虽然过去的舞台革命,用剧场性去对传统以模仿和剧情再现的戏剧性进行颠覆的实践做得非常到位。比如在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剧场上演的实验作品所昭示的。这些作品不再依附于文本,不再召唤“不在场”的现实,而是直接诉诸感官,表现动态思想的深厚潜力,并与进行当中的个别而具体的生命经验同步。它取消观演间的界限,让演员和观众在每个戏剧当下融为一体,体验共同的精神焦虑。通过在场,反对一切再现的手段,也反对斯坦尼、契诃夫、亚里斯多德。
可是,实际情况是,幻觉剧场不可能消失。因为我们称为戏剧的每一个关注的框架都是虚构的,没有纯粹或真正的“在场”。任何一次排演和演出都是一种“再现”,一次“再生产”和“复制”。因此,它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戏剧和表演观念:所有的表演都是幻觉。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舞台存在,就不外乎是再现剧场和幻觉剧场。它依靠一遍遍的重复来获取市场和观众。因为,过去的几十年剧场实验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但没能呈现人类强烈情感的精髓,实现观众和戏剧的交流,反而陷入形式主义、自我重复和极端混乱的状态。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的失败之说,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才成立的。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延续了剧场的幻觉性这种姿势,虽然它也在内部支持像阿尔托的叛变和革命,也支持像随后的布鲁克(戏剧导演)、特纳(人类学家)和谢克纳(环境戏剧倡导者)的综合和妥协(仪式)观念,可是,在百老汇的剧场里,真正获取大量票房,维持资本主义江山的是那种大型的感官秀。借助剧情的旧亚里斯多德戏剧观的痕迹,当代的票房冠军们都知道,要让观众掏钱来观看戏剧,话剧俨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断然不是重头戏。所以,这里的策略是那种巨型化的演出:《狮子王》、《歌剧魅影》、《妈妈咪呀》、《魔门经》、《猫》,在这些音乐剧里,道德和伦理被开放至一个接近极限的程度。在这些以德波所言的“景观”——而不是一个道德故事,一个生命经历给人的冲击的——剧场里,一切都是有着诡秘的内在逻辑的。
当代百老汇或者伦敦西区、芝加哥、东京、首尔、温哥华、多伦多剧场区域,一条可见的逻辑就是:一切大型的演出必须将道德的宽容度提高到最大。全球化时代幻觉剧场在伦理道德领域一个最大的挑战是,这些大型秀需要克服一个矛盾,自由、性欲、身体的展示和阳光主题的巧妙统一。比如说《歌剧魅影》的主题,是对光明战胜邪恶力量必然性的讴歌,和对纯真爱情的提倡……因此,这个戏剧中,女演员投身于以歌剧演员的事业作为维持生计手段的剧情(其中的场景显然是历史性的,有不道德成分,女性身体的展示成为了一个时期剧场的噱头。剧情要再现历史,就得尽可能再现这样的壮大色情场面)就显得为广大观众接受了。观众还顺理成章得以窥见到剧院的后台——那些演员们随便更换衣服的地方,暴露着身体的隐秘之处。这样的场景设置,舞台的艳舞和虚幻的景观,就这样与正在上演的音乐剧的声光效果,统一了起来。观众以在投入剧情的方法参与了舞台景观的营造,成为了现场的一个元素。虚幻景观的流行,还与一种剧场的分裂行为有关。在视觉上,观众包揽声色舞蹈(剧情空间所展示的);外表上,又以在“观看一台人道主义的戏剧和音乐剧为名”的伪装下正襟危坐,甚至还可以风度翩翩、绅士味道、批判味道十足。
身体和幻觉构成了当今百老汇剧场时空的主要元素。在剧间休息的时候,观众们纷纷涌出剧场,去设在剧场十米开外(或者紧邻的地方)的酒吧痛饮一杯,仪态万方、道貌岸然地与同性或者异性朋友寒暄、交际。大多数时候,男士们为了遇见一个心仪的异性这样的目的去酒吧。休息时间一般为20分钟,中场休息时间过后,剧院进入下半场。你再次回归到一个安全的观演地带。这样的伦理真空地带,其实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本质上身体和精神断裂的事实,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里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断裂”的症候。也许,资本主义剧场让你掏腰包的伎俩就在这里:让你充满幻觉,既沉浸在故事中的幻觉,又希望自己获得超越庸常生活的能量的幻觉。
剧场裸露,作为一种百老汇景观,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遥相呼应。它也与资本主义的戏剧制作方式,观演契约的达成,都有关系。它显然广为流行。如在外外百老汇剧场的一个代表性LA MAMA剧院(这个剧院上演过纽约著名的先锋戏剧家杰•苏伦(John Jesurun)的作品《空月亮里的张》(Chang In A Void Moon)系列[1]),正在上演《黑场淡出》(Black Out),它的观演极为典型,是观众从高处的黑匣子四周边框,看笼子般的黑匣子里的三个只穿着内衣的演员的表演。在2013年,伦敦西区的约克公爵剧院里,我第一次欣赏表现大文豪奥斯卡•王尔德同性恋题材的话剧《犹大之吻》(大卫•哈尔作品),其中男性的裸体在舞台上持续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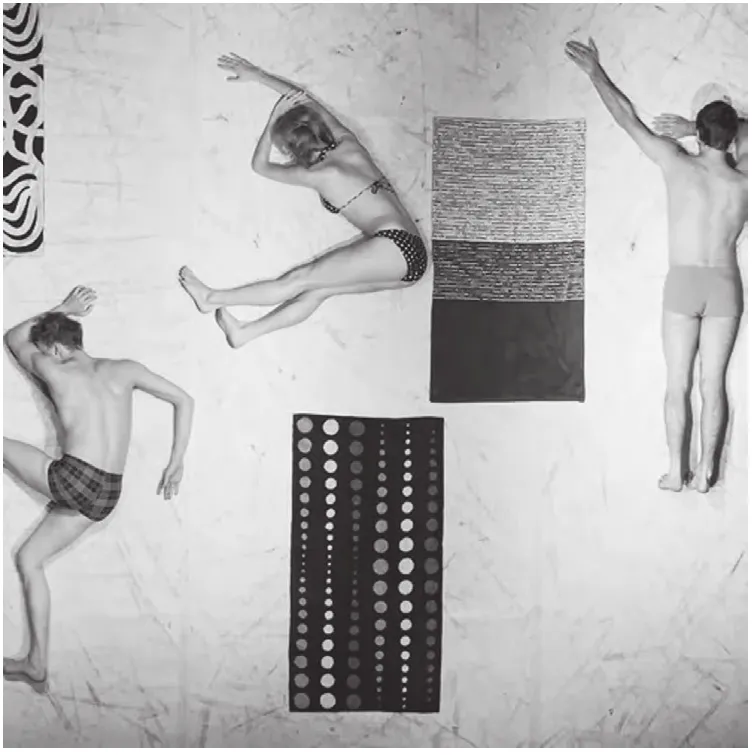
《黑场淡出》(Black Out)之剧场效果
这样,当代音乐剧的幻觉看见,与全球化时代的景观效应是统一在一起的。景观的流行背后,揭示的是当代人一种对待剧场的态度——它是建构道德同时又是身体和道德不可通览的场所,一句话,即是道德诉求明显,又是道德伦理的混沌之地。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身体的快速来不及修正道德的措辞和话语。
策略和话语
身体和道德的速度感的问题,引发出另外的思考:即不管在百老汇,还是在国内的剧场,策略在戏剧制作中的位置突出了。这是社会的时空演变对应人的精神面貌的另一种修辞转换。
比如,在当代戏剧越来越频繁地表现了一种话语的策略而不是对话的策略。对话在戏剧中的位置,越来越渺小,而将主旨让位给了话语。如上海话剧中心宁财神改编的金庸作品《鹿鼎记》,就是以话语策略代替了对话的丰富和文采。宁财神在原著剧情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加料和重构。而对话,却被评论家批评为这个戏的弱项。[2]这个戏剧,经过与原著写作时间几十年的跨度,在当下要表达的是一种超越狭隘社群和政治划分的那种机械性给人的窒息,它要表现社会阶层的第三空间(一种模糊空间)而不是界限非常明确的一种空间。这个戏剧的改编者顺着金庸的路子,其实想要达到的是对政治的一种瓦解和救赎,对于我们当代人压抑人生的一种痛快的宣泄。它这样的策略,带起的情感结构是被观众认同的。因此,刘剑梅这样评价:“在这个戏剧里,韦小宝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身便是一个杂体,而他又能轻易地平衡社会上的所有杂体。这杂体不仅对所谓的男性‘理想人格’提出质疑,也对任何固定的本质化的写作立场提出质疑。”[3]《鹿鼎记》的改编,说明在全球化时代进程和与之相关的话语系统里,一些超越二元体系(现代性体系)通则的强调。对介于事物边界之间的杂体的正面表现,对于边界模糊这种主题的呈现,证实了戏剧策略的存在,而对话的作用在淡化。
当代几乎所有的剧场观众,都非常熟悉当代的戏剧更多的是关于话语的。它的背景是对话的表演性的普遍,以及对主题和题材捆绑的无意识的反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主题,正如黑格尔所言,是两股理性力量(不分上下的原则)的交锋与对峙导致的悲剧性。它折射一种不能两全的高尚法则。而在台湾戏剧家王墨林参加澳门艺术节的《安蒂冈妮》中,其戏剧的策略又有所不同,表现如下:
舞美:倾斜的坡台,看似稳固,却也象征着倾斜的正义,可以倒向国王Creon,也可以倒向安蒂冈妮;
剧情:再经过重新诠释之后,正义之神阿波罗在这个剧本里已经隐隐退位了,少却了神性色彩,甚至连盲眼先知Tiresias都不是太明显,更少了宿命论的成份;与此相反,Creon转为绝对的主角,掌握此空间的权力,也掌握了权力的空间。
演员表演:白大铉经常以高亢、清亮、严厉的说话口气,来强调此一王者印象;相形之下,洪承伊所饰演的安蒂冈妮,身形虽然稍微柔弱,但却表现出坚毅、据理抗衡的神情与态度。两人用韩语吵起架来,各自显得正气凛然,目光炯炯有神。
舞美灯光:红光、白雾、黑背营造剧场空间氛围。
几个剧场的元素,让王墨林版的《安蒂冈妮》充满了戏剧能量。这出戏的策略之一便是主题当代化的转移。重新编写与诠释的剧本,除了引录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原著台词之外,还引用韩国木刻画家洪成潭关于光州5.18民众抗暴事件的诗作,以及小说家黄晢日英《悠悠家园》段落,最主要还是回应东亚的戒严历史,更为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女性形象与当代亚洲的情境建立起具体的连结(这一直都是王墨林多年来的主题关心与批判坚持有关,在其《军史馆杀人事件》、《荒原》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控诉)。《安蒂冈妮》则是更融入了这些年与韩国戏剧交流后的东亚戒严观,不再只是往内钻探戒严的国家暴力体制之核,而是往外连结亚际(inter-Asia)文化的批判之网;倘若解严初期是重新阅读与认识台湾的开始,那么千禧以来应该是重新阅读与认识亚洲的开始,至少我所感受的知识界与文化界,是有这么一个趋向的。[4]
德国戏剧理论家汉斯•雷曼在其《后戏剧剧场》这本书里点明了在当代的后现代的某些剧场作品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策略,就是类似路易•阿尔都塞把社会辩证时间和主观经验时间之间不可或缺的“相异性”转化成了每件“唯物主义”批判性剧场作品的基本模式,皆在动摇在那种主体中心接受和现实误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我理解所谓“批判性剧场作品的基本模式”,即资本主义的空间里,有一种技术时空的增强,对于传统的时空,就产生了一种挤压和淘汰。这也可以从以“速度学”著称的法国思想家保罗•魏瑞利奥指出的“技术速度代替机械速度,是后现代景观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后现代的景观冲突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时间的冲突”[5]之论断中得到应征。同样,两者速度的差异,与斯丛狄认为的“传统剧场和当代剧场,在本质的上冲突——所谓的戏剧危机是一种时间危机”[6]的逻辑一致。经验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分野,还体现在:“传统的观剧时间概念是分离的,而当代的剧场作品打造了精巧的合金。”[7]异质性的时间层汇合在剧场经验的唯一时间之中。因此,自然科学创造了新的世界图像——相对论、量子理论、空间时间理论相继出现。在大都市中,混乱的经验以不同的速度和节奏发生。对于这种早已产生的经验,和那些无意识的复杂时间结构,自然科学的新进展造成了一种新的认识。柏格森把经验时间作为一种“绵延”,从而将其余客观时间区分开来。社会过程时间与主观经验时间的区分越来越清晰。
在田纳西的《欲望号街车》里,女主角白兰琪的主观经验时间是绵延着南方种植园气息的那种带有巴洛克、封建腐朽色彩,然而又是在内在呼唤着绅士风格的那种老时间,它与现代社会的时间格调(以斯坦利为代表)格格不入。于是,两种时间在戏剧中产生了冲突。相比之下,斯坦利的时间观念就比较符合社会的进程:资本主义的机械化进程,具体表现在碎片、断裂、道德的淡化和不相关的不可通览的事实增多。这些不断以合法名义出现的事件碎片(体育、劳动、社会休闲、社区暴力、家庭维护)以资本主义赋予的平等化的形式一股脑儿出现在斯坦利的时间经验里,产生一种与南方种植园文化不相容的丛林法则经验。这样,戏剧的冲突就是两种时间经验的冲突。
在一般被认为适合表现“三一律”时空感的剧场中,营造时间速度的非常规化或电影化,则是纽约的波多黎各裔艺术家、剧场实验者杰•苏伦作品《空月亮里的张》的策略。汉斯•雷曼指出,他的这个系列作品中充满了冷静与意义中纯几何的结构,舞台空间往往是这样的:多不设布景,因为灯光层次已经结构得非常精细,这一类别的剧场作品可以说是体现了剧场艺术与电影之间的联系。电影对话在稍加改造之后,引入到了剧场之中。剪接的原则被加以极端化地应用。虽然一个故事的芽端和片断在作品中不断闪烁,但如想找出亦条情节主线,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杰•苏伦的舞台空间中,技术时间(社会性的时间),替代了人们过去的经验时间,使得这个戏剧先锋作品对应了后现代社会的视觉特征。包括它的台词——完全超越了幻觉剧场的再现原则,而是“以一种近乎机械性的、急促、快速的言语方式使得个人性、性格、寓言等戏剧概念都荡然无存。这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视觉、语词所组成的多棱镜。观众首先感知的是拼贴、剪辑组合而成的影像画面、电影、叙事印象,而并非戏剧逻辑”。[8]
从戏剧时间的角度上理解杰苏伦,他建构的是与观众的观赏同步的时间体验,一切都在这个剧场中属于原生态。而没有经过演员“先经验一遍”—再“通过重复的彩排和训练”—再“一次次重复地展现在舞台”上的过程。
这种人物的内心冲动直接可视地展示给观众,达到了剧场时间和表演时间的同步。
时间危机的延伸
剧场体现了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经验的冲突,它恰如其分地用剧场转喻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图形。这就是当代剧场审美的来源。在反映诸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问题:经济问题(危机)的时候,剧场依然大有可为,并乐意用再现的手法,并试图抓住这样的经济问题之于人物精神的对应关系。比如,2012年普利策奖、托尼奖和2011年奥利弗奖的三料冠军《克莱伯恩公园》,便是在老房子的周转和经济问题之间展现,继而带出社区的其他问题:种族、意识、家庭、国家。家、国家、天下在这部戏剧里有着另一层“转喻”的修辞对应。可以说,《克莱伯恩公园》里的社区,对应了五十年美国社区的变迁。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有类似之功效,它以男女(家庭)的经济关系折射了社会本质和时代图像。易卜生的作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初期或者还远未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的时候,那种对于资源的利用和竞争,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紧张。戏里,海尔茂为了获得职位,必须非常精明,而且势利,才能保住江山。而恰巧妻子诺拉做了一件看起来有点傻的事情,一件受制于人的事情。诺拉没有与海尔茂商量与人交易的事情。易卜生没有交代这是属于家庭内海尔茂的默许还是假如知道可能会拼命阻止的道德性。似乎看来海尔茂是会拼命阻止诺拉干这件事情的。诺拉与海尔茂在这件事情上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易卜生似乎赞成诺拉的仗义的做法,于是他站在诺拉的角度来替她打抱不平。而事实上,海尔茂可能会有另外的办法——如果他知道诺拉为治愈他的疾病铤而走险,将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形势的话。
海尔茂老成、对于社会的残酷比较领悟透彻。诺拉则亲信别人,显然属于浪漫主义类型的女性。这导致家庭被人敲诈的风险。在江山和美人之间,海尔茂很自然地先选择了自己的江山。而不顾诺拉在自己经济危机的时候,曾经做过仗义的事情。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的负心郎形象,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美狄亚》的丈夫所表现出来的为了显赫的王位而不顾伦理道德底线,可以随意践踏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生活的伴侣。《美狄亚》表现了王位的那种反人伦的特征)。相对《美狄亚》来讲,海尔茂是真实的。这么一件小事,然而它牵动了当时北欧的观众,继而在二十世纪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这其中的奥秘在哪儿呢?
在海尔茂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北欧时期,资本主义的制度对于成功人士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海尔茂潜意识里非常清晰,如果江山保住,不怕没有像诺拉一样体贴的女人来到身边。而假如失去自己的职位,则在这个险恶的社会里,有可能什么都失去,甚至最后也会失去诺拉的爱。这是从男性的想象和经验出发的对于海尔茂这个角色的合理性思考。海尔茂是一个事业成功者的典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几乎都会如此干的角色。这样,这个戏剧的问题其实不是家庭伦理的事情,不是男女平等的事情,而是社会伦理强加于家庭伦理的那种对应关系。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务实,浪漫主义和情义已经退居到了第二线。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易卜生没有讲到即将来临的欲望和性的巨大的能量。在这部戏剧里,资本主义的绅士风度,好像都已经失去。不仅海尔茂看起来像一个从牟取利息差的银行生意里刚刚脱身的疲惫男人,诺拉也从浪漫和怡然,慢慢地走向了焦虑。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刚好美国的电影全球奖揭晓,澳大利亚演员布兰切特凭借《蓝色茉莉》中的表演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她由于在电影中演一个类似白兰琪的女子,被封为影后。《蓝色茉莉》改编了田纳西的《欲望号街车》,但是它的语境和主题则完全变了。用路易•阿尔都塞的原理,我们将这种改编中携带的主题性转喻应用到当今许多领域,就会发现,操作、运用、消费经典杰作中的剧情和主题,已经是当下编剧和导演一个十分不错的权宜之计——在一个全球化对景观的控制社会中。因为某种程度上,社会就是剧场,对经典的主题改编就是时间性的一次舞台转喻。我们再来回顾田纳西的《欲望号街车》中的转喻:它呈现了一个冲突的社会风景。符号化的人物和对话的转喻,支撑起了剧情发展的逻辑。在田纳西的这个戏剧作品里,白兰琪是欲望的符号。她拥有一段被资本主义规范和所谓的历史意识指认为淫荡的历史。因此,她被描写成举步维艰,没有出路。她的特异性在于欲望的控制体系与别人不一样,别人听从庸常社会的建议,按照今天的科学术语来讲,今天的大部分人不会与一个“性取向异常的异性”谈恋爱,这表明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然而,白兰琪天真的地方在于,她突破规范去做了;别人在现代社会里迅速获得生存的基本伎俩(技巧),她没有,无论是恋人的选择,还是在选择以后的处理,都没有什么生活的经验可言。在那个时代,相信社会的公共性信息平台是缺乏的,社会上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性学指南机构,让白兰琪可以去倾述和咨询一下。她的天真还在于,失去了丈夫之后,开始在小城镇堕落,与非常多的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请记住,这是田纳西对女性堕落的标志性指认——他没有去责怪那些不负责任的男性,与白兰琪一夜风流之后消失无踪的那些男人。他的剧场修辞停留在机械转喻的阶段,时代局限性比较明显。田纳西的剧作里,也没有标明在美国社会,与多名男子保持性关系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这就非常令人疑惑。难道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会遭遇驱逐?这是讲究人权的美国啊。唯一一个可以想得到的事实是,白兰琪遭到学校的除名,可能为了维持生计,在酒店与人随便发生性关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这等于是卖淫。于是,在掌握了一些证据的前提下,小镇的司法机构,将白兰琪的继承一处房产的权利也剥夺了?这好像也说不过去。剧作里没有说白兰琪遭到判刑之类。于是,最好的解读本剧的办法只能将之读成一个现代寓言或者现代仪式戏剧。在被家乡剥夺了继承权和几乎是驱逐之后,白兰琪保持着过去被当下人指认为非常不合时宜的生活和言语方式。
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许多的戏剧理论和历史书籍里,都将这个戏剧的主题界定为南方情调的破落。所以,白兰琪的性格是封闭的,也就是在戏剧里她不得不走向崩溃。这既是主题决定的人物命运,也是田纳西的戏剧观念(观念图形)。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再来看《欲望号街车》,发现里面的结局是单一的,就是它没有升华为两套语言的冲突这样的戏剧主题。比如,今天我们会认同白兰琪的遭遇是通过两套语言系统(阿尔都塞所言的两个时间的相异性)的冲突造成的。戏剧应该关注这两套语言法则的冲突和后果,构建一种关系式的戏剧模式。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神话和寓言模式。寓言模式屏蔽了某些真实。今天,我们假如再改写《欲望号街车》,那么主题其实就会集中在两套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不相容。而不会局限在让白兰琪无路可走,而是在批判过白兰琪之后要批判斯坦利。这个戏剧在今天可以写成喜剧。相反,斯坦利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丛林法则里生机勃勃的强盗,虽然还没有获得成功,但是野心十足,十分活跃;白兰琪代表了南方的破败、南方的失落。她的那些语言方式和行为模式既是南方的种植园社会模式的:寄生特征明显。由于时代和经济模式造就的局限,那个地域的女性在经济上从属于男性,交际花围绕着男性的富翁转悠,天经地义。而浪漫主义色彩的幻觉组成了女性生活的全部心理图景。
在改编的《蓝色茉莉》中,女性的困境依然存在,源自于性格和历史的双重影响。但是《蓝色茉莉》的主题却是自强不息和寄生生活两种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冲突。《欲望号街车》揭示了白兰琪和斯坦利的时间经验冲突,而《蓝色茉莉》则对比了姐妹之间的生活方式之冲突。相似的人物故事和命运,但是主题完全不同。这就是今日艺术家消费经典巨作的秘密所在。改编法则还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不改变原作品的主题,何以成立?不转喻其内涵,怎样在今天成为著作权的主人?
相比之下,电影《安娜•卡列宁娜》的改编是一个反向例子。安娜在电影中,是一个直率的女性,她按照自己的欲望法则生活,而不是婚姻法。不过按照当今人的观念来看,她事先应该与丈夫有这方面的契约会比较好。安娜在今天可以生活得很好。原则是必须在结婚之前与未婚夫进行双方权利的沟通:是不是可以在结婚后有另外的性生活?这是很重要的部分。相信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两个人的观念和事实之间就不会分裂。婚姻的要害之处在于,双方都期待从中得到好处。而双方都不愿意将这种好处和利害关系事先说明白。另外一点诡秘的地方在于,婚姻和欲望的关系问题。婚姻不可能消除完全消化欲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一般需要超乎物质的力量才能将这种欲望控制得恰到好处,不伤及脾胃。双方的欲望机制的达成也需要事先沟通。这都说明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国社会,这种“通奸和婚姻”的二元对立,既缺乏沟通,又缺乏透明性和疏导性。言下之意,这个戏剧在俄国背景里除了悲剧式结尾就别无他法。单向度的社会,导致关系的破裂和愈演愈烈的惩罚游戏。这出戏在当代应该停写了。而汤姆•斯托拍改编的电影则依然在老旧的主题套路里折腾,所以这个电影最后的升华部分不精彩。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如果不改掉故事的结尾(主题),怎么可以成功呢?
注释:
[1]《空月亮里的张》(Chang In A Void Moon),首演于1982年的Pyramid Club,2003年10月曾到LA MAMA剧院上演其中的第53、54、55集。
[2]杨申,《教授明星盛赞〈鹿鼎记〉 丰富想象受肯定》,新浪娱乐,网络资料,网址:
http://ent.sina.com.cn/j/2009-04-09/01512462311.shtml,登入时间2014年1月10日。
[3]刘剑梅,《狂欢的女神》,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66页。
[4]于善禄,《〈安蒂冈妮〉的当代转喻》,《牯岭街小剧场·文化报》 2009年第9期。
[5]杨子博士论文《家园的踪迹:全球化上海的剧场与艺术空间初探》,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5页。
[6](德)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7]同上,第198页。
[8]同上,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