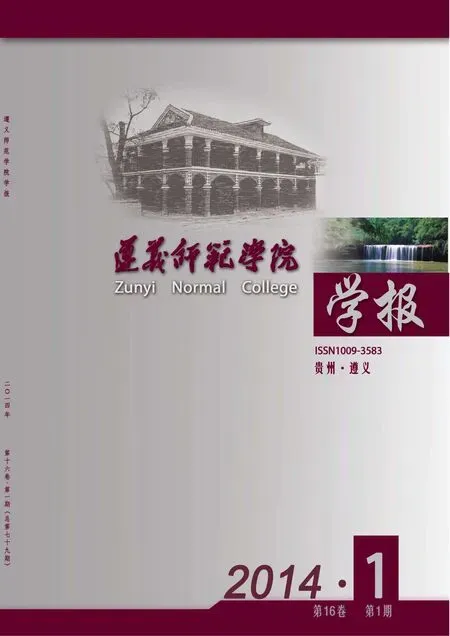解读《论语》的“仁富”思想
2014-02-05郝永
郝永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解读《论语》的“仁富”思想
郝永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论语》的“仁富”以“仁”为本质,包含着富而能义、富而能礼、富而能信、均富、乐富等内容,是一有机严整的思想体系。就当下而言,它对富裕起来后的少数人于伦理道德上出现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贫富不均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有警醒和纠正的积极作用,并在“均富”和“乐富”层面上具有世界意义。
《论语》;仁富;当下意义
《论语》作为儒家基本经典,是以对社会人伦的关怀为中心建立的思想体系,代表了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其中的“仁富”思想直到今天仍然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说《论语》的“仁富”思想今天还具有借鉴意义,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1]国情的认识。阶段性特征、新情况新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而整体富裕后关于“仁富”的思考也应属于“阶段性特征、新情况新问题”的内容。
一、“仁富”的本质
“富”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关于社会的思想体系都要涉及的论题。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学术思想,大多有关于“富”的论述。就中国古代而言,我们仅就和《论语》大约同时代的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关于“富”的理论做简括的考察。
先秦春秋战国时期争鸣的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几家思想体系,都有自己关于“富”的观点。道家的《老子》从其“道法自然”价值观出发,提出了“我无事而民自富”[2]的主张,因此它关于“富”的观点可称为“道富”论。墨家从它思想体系的逻辑源头“兼爱”出发,主张要实现国家富的目标就要“兼相爱、交相利”[3],故它关于“富”的思想是一“兼富”论。法家在治国用兵上主张法本论,其思想体系的逻辑依据是“法”,故法家关于“富”的理论可以称为“法富”论。就“法”和“富”的关系,法家突出强调了“富”的物质基础地位,它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4]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于春秋战国后是一农业为主的社会,故农业生产的好差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富贫。《商君书》把农业称为“事本”,将农业看做国家的根本。关于这一点,《农战》篇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4],《算地》篇有“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4],《去强》篇有“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国富者王”[4]的论述,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富”的国家根本意义。道家的“道富”论强调精神的富足、平和而不重视物质生活的富足;墨家的“兼富”论强调无差别的绝对平均主义而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不符;法家的“法富”论强调法本基础上的富国强兵而使“富”缺乏人性的关怀。总之,从中国古代尤其先秦看,各个思想体系关于“富”的理论都以其自身思想的逻辑源头为依据而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不足,这些不足成为它们最终没能由理想变成社会现实、即使变成社会现实也不长久的原因。就西方而言,和中国的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它的商业社会属性,它在关于富的理论上突出地表现为“商富”特征,这一点为中世纪以前直接的商品经济和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所共有。商业的核心理念是对“利润”的追求,故“商富”的基本点即在于其“求利”性。马克思等人看透“资本”的本质而强调政府干预前提下的社会均富,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其根本上的“求利”性,西方的“商富”尽管可以造就国家社会的整体富裕,但贫富不均和对外争夺依然是其长期存在的特征。儒家以“仁富”为代表的思想,适合人类生活的现实,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盛世。
《论语》就其“仁富”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论语》关于“富”的表述,除了直接用“富”字外,还用到了诸如“用”、“奢”、“简”、“贵”、“衣”、“食”、“利”、“聚敛”、“足”、“货殖”、“稼”、“圃”、“庶”、“玉帛”等语汇。对“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论语》认识清醒,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论语》把物质的富足看做国家生存的重中之重,关于这一点,下引这段内容可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5]
尽管《论语》这里是在强调国家建立和治理过程中“德”的地位高于“力”,但其中的应有之义也可以是:国家建立和治理的过程中,军事强大的基础是物质的富足,否则就是穷兵黩武。关于富足在国家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在《颜渊》篇中也有表述。该篇列举了国家生活的三个基本要素——足食、足兵、民信,足食列第一。《论语》还认识到“富”在人格修养上的积极意义,“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5]它将“富”看做人类的基本欲求,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5]的表达。孔子还将“富”看作职业选择的基本要求。《述而》篇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执鞭”在当时是一低贱的职业。我们一般认为,儒家是反对具有投机特质的商业行为的,但《论语》在谈到该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一点表现在它关于“货殖”的论述: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5]
我们虽然不能说孔子的“屡空”、“屡中”是在叹惋学道而贫的颜回、赞赏“货殖”而富的端木赐,但我们从中实在也读不出他批评端木赐的意思来。总之,《论语》不但没有回避富的问题,而且在大量地谈论富,它谈论富也不是在贬斥富,而是将其看做国家存在的基础、人本性中的应有之义。《论语》认为对富贵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它又强调人们在追求富贵时要遵循“仁”的准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5]“仁”即为他人着想,如作为国君,他关爱的对象是天下百姓,故对于饥荒之年财物不足时国君的态度和做法应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自己的富足以百姓的富足为前提,这就是国君的“仁富”。相反,如果国君的富足是暴敛和与民争利之富,则是“不仁”,而应接受讨伐。《先进》篇曰: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5]
总之,就“富”的本质而言,《论语》的主张既不同于同时代的道家、墨家和法家,也不同于西方的以“利”为本,而是它思想体系逻辑起点的“仁”,故其关于“富”的理论可以称为“仁富”理论。一言以蔽之,《论语》在讨论仁与富的关系时主张“仁”是“富”的依据,富是关爱他人前提下的富,是不损人利己之富。
二、“仁富”的内容
众所周知,《论语》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仁”即“爱人”,“爱人”即爱他人,故“仁”的学问是要求人们思想和行为以他人为出发点的学问。从伦理道德修养层面看,“仁”还逻辑地包含了义、礼、信等。由于“仁”有以上内容,故富和义、礼、信等的有机统一也是《论语》“仁富”思想的应有之义。
富而能义。“义”,《礼记·中庸》释曰“宜也”[6],指的是合乎道——“仁”的行为。如果说“富”与“仁”的关系是要求人们在富贵时思想上以他人为出发点,那么《论语》中“富”与“义”的关系则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符合“仁”。行为上是否以他人为出发点,是判断该行为是“义”还是“利”的依据。《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同样是追求富贵的行为,如果是以他人为出发点,则是君子之“义”,否则则是小人之“利”。《论语》认为如果人们追求富贵不是为他人着想的“义”而是为一己之私的“利”,则会招致人们的不满:“放于利而行,多怨。”[5]《论语》对不“义”而“富”贵的行为持的是反对态度,它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故从富与义的关系看,《论语》不但主张“富”,而且要在思想和行动上以他人为出发点。
富而能礼。在儒家的伦理范畴中,“礼”的义项具有多重性,而它的核心义项则在于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论语》强调“礼”与“富”关系时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5]文,可见它主张的“富”是在遵守“礼”的基础上的“富”,如果秩序乱了,“富”也将不复存在。基于“富”的秩序即“礼”的规定,那么民富之后教之以礼则是逻辑的结论: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
孔子的时代,人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口匮乏的时候要发展人口,人口众多之后要使民致富,而富足之后则要教民以礼,否则富足就不会长久。再者,《论语》还认识到“富”和“礼”一体两面不可分的一而二、二而一关系。它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帛”即“物”,“物”代表“富”,故“玉帛”与“礼”为一即“富”与“礼”为一的意思。从“富”和“礼”的道德修养和外在表现关系看,《论语》将其分为富而骄、富而无骄、富而好礼三个层次,并认为前两者“未若……富而好礼”[5],把“富而好礼”看做最高的境界。其实,富而骄作为“富”的一种心理因素和外在表现,就连反对儒家礼义道德的道家也将之视做负面的东西,《老子》就说过“富贵而骄,自遗其咎”[2]的话。如果说《论语》主张“富而好礼”的基础是个人修养的话,那么墨子则认为它的基础是爱它人如爱自己的“兼爱”思想: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则富必侮贫,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富不侮贫。[3]看来,无论儒家、道家还是墨家,它们都是主张富而能礼的,只不过其逻辑依据不同而已。
富而能信。“信”《说文》解为“诚”:“诚也。从人从言,会意。”[7]故“信”即讲信用和重然诺的意思。富和信的关系,《论语》主要是从治理国家的层面讲的,如它将富足和人民的信任看做治国理政三个基本要素中的两个: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5]
就“仁富”的理念来说,《论语》尽管有分富和仁、义、礼、信来讨论它们关系的情况,而实际操作上它们又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如《论语》还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5]的表述。《论语》的“焉用稼?”并非是不搞生产创造财富,而是说如果管理者能做到考虑问题以“仁”为本,以百姓为出发点的话,则义、礼、信、富当是其中应有之义。
富而能均。《论语》的“仁富”内容上还包含“均富”。逻辑上,“均富”是“仁富”的必然结果,因为“仁富”即是以他人为出发点的“富”的追求,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则这个社会必然是一“均富”的社会。关于“均富”,《论语》是这样说的: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5]
这里《论语》认为,“均富”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内容,而国家社会的“均富”和长治久安,是“修文德”使“远人”“服”,进而“来之”、“安之”的前提和基础。其实,《论语》这里的“均富”理论并不是将财富完全平均地分给社会成员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是强调人伦前提下的相对平均主义: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5]
可见,《论语》的“均富”是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是一秩序的“均富”观。
富而能乐。物质生活的富足并非“仁富”的全部,《论语》的“仁富”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一严整的体系,还在于其包含了人的精神生活层面,或者说,《论语》认为“仁富”不仅仅包括了“均富”在内的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人的精神生活的幸福、快乐、平和与否,也是衡量是否实现了“仁富”的指标而且是最高指标,这一最高指标可称为“乐富”。关于《论语》的“仁富”——“乐富”思想,表现在《先进》篇孔子对四子所明之志的态度上。孔子认为国家生活的最高境界不是其他弟子如子路等的国富、民强、民礼、民祀等,而是包括国富、民强、民礼、民祀等基础上的如曾子所表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5]的理想。其实,曾子所表达的这一理想是一种精神愉悦、平和即“乐富”的境界。关于曾子的理想,宋儒们如朱熹就曾专门讨论并称其为“曾点气象”[8]。关于“曾点气象”,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孔子不把国富、民强、礼仪包括“均富”等“仁富”理念的物质层面看做最高境界,但不等于他不重视这些内容。事实上,孔子非常清楚“仁富”物质层面的基础意义,这一点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实质上孔子的意思是不要仅仅只注意到“仁富”的物质层面,还要更深刻地体会到其精神层面。“仁富”的精神层面要求,就是心态的愉悦、平和——“乐富”。就“富”的精神层面讲,当时的道家也主张这一点,如老子就有“知足者富”[2]的说法。但分析起来两者又有所不同:作为《论语》的包含于“仁富”理念的精神上的“乐富”是和富国、强兵、均富融为一体的精神愉悦、平和,而《老子》的“知足者富”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所谓的小国寡民。可见,两者尽管有相同的表现形式,却有不同的逻辑基础。
总之,在内容上,《论语》的“仁富”思想包含了富而能仁、富而能义、富而能礼、富而能信、均富、乐富等元素,是一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修养等层面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理论。
三、“仁富”的当下意义
当下的中国在“富”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阶段性特征,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累了巨大的财富,GDP已世界第二。但贫富不均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的富还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没有实现精神上的“乐富”。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富的问题上出现了为富不仁、唯利是图、贫富不均等种种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论语》的“仁富”思想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就“仁富”的伦理层面讲,我们已经富裕或行将富裕起来的人们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借鉴《论语》的“仁富”理念。关于富的伦理,首先要富而能仁。在致富的过程中和富裕后,都要尽量做到考虑问题以他人包括国家和民族为出发点——富而能仁,而不是相反——为富不仁。实际上,在当下的中国,为富不仁恰恰是一较为多见的现象。如发表在《河南税务》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名人·富人·偷税人》[9],将名人、富人和偷税人并列就可为证。富而能“仁”还要求人们在自己富裕的基础上要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慈善事业,而不是靠国家政策发起来的有些巨富在国家危难时严格要求他的员工每人只能捐十元钱。其次要富而能义。要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正当致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甚至钻法律空子而致富所得都是不义之财。富而能义还是个人人格定位的依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故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全由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再次还要富而好礼。“仁富”虽然不是建立在墨子“兼爱”基础上的“兼富”,但它却不排斥关爱他人。故富裕起来的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不应“以富侮贫”,这是富而能礼的内在要求。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富得太快,有些人被富冲昏了头脑而忘乎所以,骄横跋扈、趣味低下。新浪网转引浙江电视台《寻找王》栏目2009年5月份发生在杭州的富家子弟飙车造成浙江大学毕业研究生惨死的案例就是明证。[10]这和《论语》“仁富”主张的“富而好礼”是不相符的,说明我们在富而好礼的道德要求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还要富而能信。基于追求利益的特质,人们称那些狡猾、欺诈、不守信用、不重然诺的商人是“奸商”。和“奸商”相反的是以儒家“仁”德作为自己经商指导思想的“儒商”。而逻辑上,“儒商”一定是富而能信的商人。就个人来说,做“儒商”还是做“奸商”全在自己。
就“仁富”的“均富”层面讲,尽管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的整体富裕,但我们还没有实现孔子主张的“仁富”目标。因为孔子的“仁富”不但要求整体上富裕,而且还要求“均富”,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一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贫富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均富”的社会,政府的认识和努力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中央层面是清楚的。但中央政府的理念却不见得为地方执政者所认识和实践。近期有地方政府的处级官员公开讲出了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两分的话:据新浪网转引中国广播网的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栏目报道,当记者采访某省会城市规划局分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对某一信访处理意见时,“这位副局长却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1]故可以说,使“均富”理念成为地方政府乃至全民的意识和行动,是我们当下就要做的。
就“仁富”的“乐富”层面讲,它是当下中国应该立即践行的理念。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论语》的“乐富”观,在文明后应该加上“幸福”。因为“幸福”是一表述精神生活的范畴,它内蕴了“愉悦”的心理感受,故“幸福”可以代表《论语》中的“乐富”理念。它在国家生活层面大致和我们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是一致的。《论语》的“均富”和“乐富”的理念,不惟在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上有重大意义,在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上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论语》在提出“均富”的理念后继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文”即“人文”,“安”则“安乐”,“文”而“安”逻辑上当为“乐富”的应有之义。完全可以说,一个“均富”、“乐富”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那么当下中国民众的“乐富”或者用今天的术语——幸福指数观照,是一怎样的情况呢?据英国“新经济基金”公布的2009年《幸福星球报告》全球国家幸福指数,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高踞前10名的其中9席。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12]通过上述材料,分析国家富强程度和幸福指数的关系后不难发现,人们幸福快乐与否和物质上的富裕不但不成正比而且似乎呈现反比。从这一角度看,《论语》的“乐富”观也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我们不但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还要建设一个幸福快乐的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实现全社会的大和谐。
综上所述,《论语》的“仁富”是以“仁”为依据而有别于古今中外其他思想体系关于“富”的理论的思想,它逻辑地包含了富而能义、富而能礼、富而能信以及“均富”和“乐富”等内容。就当下实现了整体富裕的中国社会来讲,它能够起到警醒或纠正为富不仁、唯利是图、贫富不均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的作用。由于“仁富”的“均富”和“乐富”层面具有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它应该成为中央、各级政府、全民的意志;由于西方没有“仁富”理念,故早已整体富裕起来的西方大多国家还不是“均富”和“乐富”的社会,从这一点看来,《论语》的“仁富”思想还有世界意义。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09-27].http://www.gov.cn/jrzg/2009-09/27/content_1428158.html
[2]李耳.道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1,4.
[3]墨翟.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5.
[4]商鞅.商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07,1103, 1105,1104.
[5]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91,92,27,45,74,27, 80,73,27,28,27,46,80,86,7,79,85,107,80,75.
[6]孔颖达.礼记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570.
[7]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0:52.
[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28.
[9]孔国强.名人·富人·偷税人[J].河南税务,2002,(16):29―43.
[10]刘兆亮,王真,冯云浓.年轻男子驾三菱跑车飙车撞死路人[EB/OL].[2013-05-08].http://news.sina.com.cn/s/p/2009-05-08/033417768110.shtml
[11]任磊萍,何岩.郑州经适房土地建别墅记者采访被质问替谁说话[EB/OL].[2013-06-17].http://news.sina.com.cn/c/ 2009-06-17/075115803313s.shtml
[12]杨建.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国内地居第20位[EB/OL]. [2013-08-30].http://news.sohu.com/20090830/n266321359.shtml
On The Analects’Thought of“the Benevolence Prosperity”and Its Present Significance
HAO Yong
(The Literature Academy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The benevolence prosperity of the Analects as an organic and neat system contains justice,courtesy,confidence,even prosperity and happy etc,but its essence is still benevolence.At present,i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rectifying the wrong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ethics such as being rich and cruel,seeking nothing but profits and too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and it has world significance on the sides of even prosperity and happy prosperity.
The Analects;the benevolence prosperity;present significance
B82-053
A
1009-3583(2014)01-0047-05
2013-10-09
郝 永,男,河南永城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