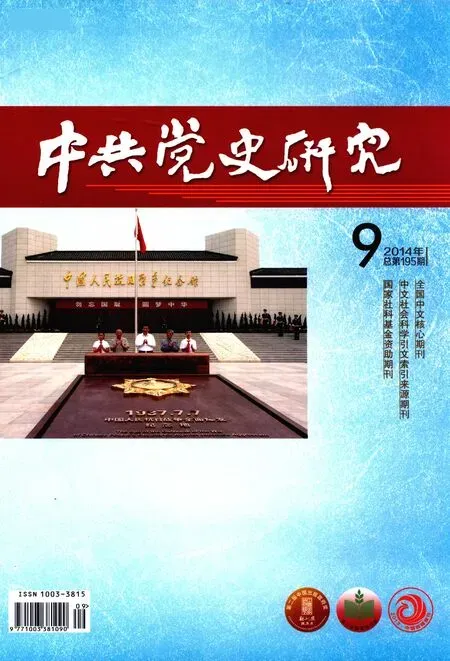关于党史研究者的专业修养问题*
2014-02-05欧阳淞
欧阳淞
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党史学界关注已久,近两年来,我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
第一,党中央历来重视党史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了党史作为历史教科书和“必修课”的重要性,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营养剂”。展望未来,党史重大纪念活动将接踵而至,纪念建党95周年在两年后就会到来,纪念建党100周年在七年后就会到来,要把这些纪念活动的党史宣传工作做好,就需要我们党史研究者有新的作为、有大的作为,不能吃老本、炒冷饭,就需要把深化党史研究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出更多、更好、更新鲜的研究成果。而要深化党史研究,就必须总结党史研究的经验,探索党史研究的规律,把握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就必须关注党史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我自己来党史系统工作时间不长,我深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史工作者,对于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应当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因此,我在实践中注意以学习服务研究,以研究促进工作,对党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第三,我注意到,党史研究队伍中有很多同志对党史学的基本问题有兴趣、有基础、有成果,但也有些同志本身并不是党史专业出身,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有点先天不足,因而,通过研究党史学基本问题提升专业素养,对这些同志来讲可能是填补空白,而对学过这方面课程的同志来说则可能是与时俱进,是更上一层楼。
从这三点考虑出发,我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经过与有关同志的讨论和切磋,陆续写出了关于党史学基本问题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党史学基本问题而言,也许只是破了个题,而对于构建完整的党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而言,则相距更远。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是想作为“引玉之砖”,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并为后来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索引和基础。大家手里都有这本小册子了,所以今天我的发言不想再简单地重复这几个问题,而是想谈一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党史研究者的专业修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思考,提出来和大家交流讨论。
第一,史学研究者要走向成功,就应当提高专业修养。
学术领域浩瀚无垠、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尤以史学得天独厚。也正是因为这样,诸多学人虽皓首穷经,也未能尽其于万一。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知识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需要深厚的专业修养。为了获得这种专业修养,那些最后成功的史学家们都坚持走博通之路,日积月累,进而在学术上打下了宽厚而坚实的基础,最终达到大器晚成的境界。
研究宋元史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古文献方面的功力就令史学界同仁非常钦佩。他把史学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特别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为了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他收集的史料、积累的稿本就有3尺之厚。而经过删繁去复,最后写成的文章也就2万多字。他认为,“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沉潜深入、厚积薄发,确实做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研究近现代历史的著名学者邵循正先生,在外文文献方面的功力也令人折服。他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还学过波斯语、梵语等近乎消失的生僻语言,所有这些,都只为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和读懂第一手的外文史料。另外,他还十分重视晚清、民国私人笔记,尤其是来华外国人日记内保存的近代史料,并因此推动组织编辑《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正因为在外文史料挖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够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决前人无法知晓的问题。
我们党史学界的老前辈胡乔木同志也是自觉提高专业素养的楷模。胡乔木同志一生勤奋读书、善于思考,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在乔木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对知识的不懈追求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参加革命后,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工作多么忙碌,他每天都坚持读书学习。这已经成了他一日不可无的一种生活方式。每到一座城市,新华书店是他必定要去的地方。凡是他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书,总要想方设法一睹为快。他曾引用一句西方谚语“从容的赶快”来说明要把“从容”与“急切”结合起来、坚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学习的必要性。他曾说过: “学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事”;学习是为工作蓄积本钱,“不学习,不下本钱,工作是做不好的”。他一生博览群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还是哲学、历史、文学、法学、语言学、音韵学、逻辑学,也无论是古书还是今书、中国书还是外国书,他都广泛涉猎。数十年下来,他的大脑已经成为一个汇集各种知识的“海洋”,他一提笔、一想问题,积累的知识就会化作奔腾的文思,化作筹划解决问题的能力。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为之赞叹和称羡。这些能力不仅是一名党史研究者的深厚专业修养的真实写照,更是一位成功史学家的传世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二,史学研究者要提高专业修养,就应当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史家四长”的思想。
对于史学研究者专业修养乃至学术水准的考量,我国学术界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长”之说比较为大家所认可。总结和分析“史家四长”中蕴含的要素,可以看出遵循和借鉴“史家四长”,对于提升史学研究者的专业修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关于史德。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论著《文史通义》中,曾专门论述过史德问题,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和行为规范所蕴含的品德,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职业操守。历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永远是历史学的基石,也是历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尊重历史,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等,都是历史学家史德的具体表现。真正具备优良品质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探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
当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在总结当代史学发展史时曾说:“六十年来,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认为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处,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我们党史界的老前辈胡绳同志也说过:“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十分中肯而又重要的,但是,由于历史学家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的思想以及著述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命题有其合理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作为历史学家史德的重要内容具有不可须臾忽视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贵在据实而书,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所有论著都应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史料运用原则,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捏造和歪曲历史,做到不隐恶、不虚美,勇敢捍卫历史科学的尊严和价值。这些都是史德的内在要求。
关于才、学、识。史才、史学、史识,原被称为“史家三长”,后来加上史德之后就成为“史家四长”。一般认为, “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叙述事实、记载言语、撰写文章、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等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史学”是指掌握的丰富史料、历史知识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指的是史家独到的见解、观点、品质和精神。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回答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问时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这些论述可以说是道出了才、学、识的地位所在。
德、才、学、识四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史才中包含史识的因素,史识又以史才和史学为根基,而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史家四长”论体现了中国史家对自身专业修养的严格要求和对史学工作的自我认知,对促进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今,虽时过境迁,但“史家四长”的合理内核对于提高党史研究者的专业修养,仍有重要借鉴作用。鉴于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和时代的要求,党史学者的“史家四长”还应有新的时代内涵。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把党史研究视为一项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崇高事业,是第一位的要求。党史研究者应当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党中央对重大党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和重大结论,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在“求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解决党史研究为谁研究、怎么研究的问题。这是新时代对史德提出的新要求。同样,时代的发展也要求党史研究者适应多学科交汇发展条件下的历史叙事需要,提高史才;适应史料多元化的需要,扩展史学;适应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的需要,增强史识。只有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党史研究者专业修养的提升,才会有现实可循的途径。
第三,党史研究者要借鉴“史家四长”,就应当注重研究党史学基本问题。
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理论借鉴问题、布局和样式问题、资料准备问题、著述要领问题、成果转化问题等,事实上已初步涉及党史研究者遵循和借鉴“史家四长”的具体途径问题。
“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初步回答了党史研究者的史德问题,即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史学是带有鲜明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特点。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实现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才能提高党史研究水平,推动党史研究深入发展。
“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初步回答了党史研究者的史才问题,即要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根本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思辨的眼光,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宝库中,采纳和吸收一切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手段,从而进一步丰富党史学的理论宝库,提高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则从战略谋划、战略部署的角度,初步回答了党史研究者的史学和史识问题,即对党史研究内容应从哪些方向、哪些领域、哪些角度展开,作出宏观界定和整体谋划,对党史研究的成果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作出具体设计或实际选择。这既是适应史料多元化、成果多元化的需要,也是党史研究者学识的体现。
当然,涉及史学、史才问题的还有“党史研究的资料准备”问题和“党史研究的成果转化”问题。而“党史研究的著述要领”则对“史家四长”所包含的四个问题都有初步回答,因为党史著述是党史研究所有环节中最为综合、最为关键的一环。 “著述要领”中所讲到的“六个坚持”中,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时代和全局高度,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记述党的历史,就涉及史德问题;坚持写党的历史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就涉及史识的问题;坚持写伟大事业同写伟大工程的统一,坚持写“党怎么说”同写“党怎么做”的统一,就涉及史学的问题;坚持写宏观同写中观、微观的统一,既呈现出它的整体,又呈现出它的局部和细节,既要合理布局又要精雕细刻,把党的历史画卷完整地、生动地呈现出来,就涉及史才的问题。当然,“著述要领”的核心还是回答史德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在党史著述过程中,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以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认识历史和撰述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注和研究党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史研究者借鉴“史家四长”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借鉴“史家四长”,又是提高党史研究者专业修养的一条有效途径,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党史研究者要提高自己的专业修养,就必须重视党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实践。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今天的党史工作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党史研究者应该拓宽眼界、开阔胸襟,着力提高自身素养,努力拓展研究视野,为开创党史研究事业的新局面而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党史研究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