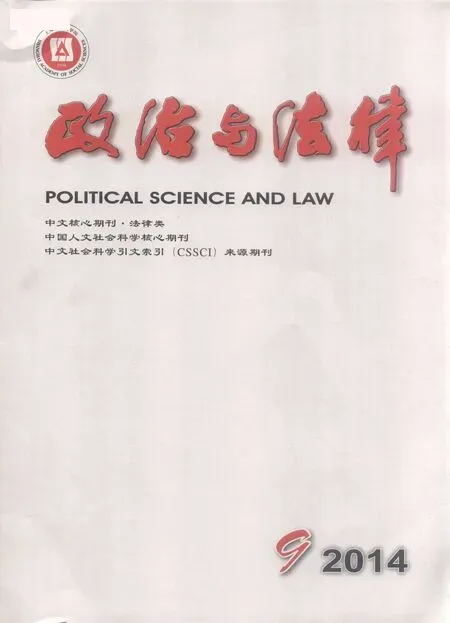矫正刑论:黑格尔刑罚目的理论的再定位
2014-02-03邱帅萍
邱帅萍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黑格尔以其哲学思想而闻名于世,刑罚目的理论亦是其整个哲学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内外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应定位于等价报应论或曰法律报应论,它是报应刑论的中流砥柱,甚至比康德的刑罚目的理论更富报应主义色彩。①如有国外学者指出:“黑格尔是一名真正的报应主义论者……他与康德立场一致,后者对报应主义的信奉是明显的,但是其对于报应主义的辩护仍至多处于初级阶段。”See A llen W. 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09.我国学者徐久生认为:“黑格尔……被公认为是法律报应论的鼻祖……黑格尔的法律报应论被学者们称为等价报应论。”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 页。类似观点还可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 页;周少华:《刑罚目的观之理论清理》,《东方法学》2012年第1 期;等等。当前的刑罚目的理论研究中,报应刑论饱受诟病,以报应和预防(尤其是一般预防)为基础的综合刑论成为主流,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亦随着报应刑论的褪色而被边缘化。然而,黑格尔的刑罚目的论形似报应刑论,实质上则应定位于矫正刑论。该理论为矫正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力推进学界重新审视刑罚目的,十分裨益于当下的刑罚目的研究。
一、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形似报应刑论
黑格尔主要是在探讨刑罚的性质和力度的过程中,阐述了其刑罚目的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表象上看,该理论具有典型的报应主义特征。
(一)刑罚在性质上是基于犯罪而对相应犯罪作出的绝对否定
黑格尔将犯罪定义为,“自由人所实施的作为暴力行为的第一种强制,侵犯了具体意义上的自由的定在,侵犯了作为法的法”,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8 页。犯罪是一种否定的无限判断。法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而由于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成为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对法的侵害,就表现为对自由的侵害。但是,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受到强制的,意志唯有达到了定在,它才有可能被侵犯,而意志在达到定在的时候是现实地自由的,是自由的存在,因此,受到侵犯的自由表现为一种具体的、现实的自由。由于概念上的法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它是不可能被扬弃的,因此,犯罪,这种否定了意志的定在的行为,是虚无的,它必定会被否定或者扬弃。因此,犯罪作为罪犯的意志,是一种特殊而非普遍的意志,虽然它表现为一种“肯定的外在的实存”,但是,由于这种实存是一种虚无,所以同样会出现“外在实存中的对上述侵害的消除”。③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0 页。这种对犯罪所造成的侵害的消除,在黑格尔看来,就是刑罚:“犯罪,作为自在地虚无的意志,当然包含着自我否定在其自身中,而这种否定就表现为刑罚”。④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5 页。如同力的对立面是反作用力,犯罪这种暴力性的强制行为,对其的否定或者扬弃只能是一种反暴力。亦即,刑罚也是一种强制,只不过刑罚借由反犯罪的正当性而成为是附条件并且合法的、作为对犯罪这种第一强制而施加的第二强制。
基于法的绝对必然性以及犯罪的虚无性,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其一,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必然性,有犯罪就必然有刑罚。法不可能被扬弃,一旦法受到了侵害,这种侵害必然要用刑罚来消除。犯罪的虚无性,也决定了犯罪是易破坏的,不是永恒的,要被刑罚否定;其二,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单向性、被动性,只有出现犯罪才会出现刑罚,反之则不成立。犯罪与刑罚都属于强制,但犯罪属于否定性的强制,而刑罚属于一种对否定进行否定的强制。如果刑罚上的强制缺乏犯罪这种强制的基础,那么刑罚就会变成一种否定的强制,进而沦为一种不法。犯罪能引起刑罚,刑罚则不能引起犯罪,这是概念上的必然要求,是刑罚之所以为刑罚的原因;其三,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相应性。刑罚是对犯罪这种侵害的消除,因此,有多少犯罪就应当进行多少次的消除,有多么严重的犯罪就应当采取多么严厉的消除措施。“只要量多些或者少些……正义会过渡为不义”,⑤[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05 页。不当的惩罚或者会使得犯罪得不到消除甚至使得犯罪被合法化,或者导致新的犯罪。这就如同是造纸厂在造纸的过程中会排放污水,排出多少污水就要对多少污水进行净化处理,污染有多严重,净化措施也就要多么严格;除污剂的量过少,污水的治理就见不到成效,甚至会使人误认为污染水源是一种合法行为,而一旦除污剂的量过多,则会使除污剂成为一种污染源。
(二)刑罚在力度上应与犯罪保持价值上的等同
由于犯罪侵害的是意志的定在、现实的自由,从而犯罪就“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即可以现实地被把握,因而,作为否定犯罪的刑罚,同样也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这就如同只有行为才可以现实地否定行为,否定行为的意志如果得不到现实表现就无法真正地否定行为。在质和量的范围上,作为否定犯罪的刑罚必须与犯罪保持一种相应性,这种相应性表现为价值上的等同,而不是形态或者特种性状上的等同。
黑格尔否定了追求刑罚在特种性状上的等同的必然性、现实性与合理性。
首先,法的概念对刑罚所规定的是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同一性,而非外在的同一性。具有质和量的范围的犯罪以及对犯罪的否定,都是属于外在性的领域,但“外在性的领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绝对规定”,⑥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5 页。犯罪和刑罚之间的等同只是内在同一性在外界的反映,而反映内在同一性的外界并不是固定不变或者唯一对应的,如同现象可以表现出事物的本质,而现象是多变的,本质可以透过多种现象表现出来,本质与现象之间不具有唯一对应性。
其次,外在性的领域是有限的,追求特种性状的等同,就会在现实中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情形中,如果行为人是一个独眼龙、瞎子或者牙齿已经全部脱落的人,那么他弄瞎了别人的双眼或者打掉了别人的牙齿时,追求特种性状的等同便不可能,会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尤其当特种性状上的等同还要与探究不同人的心理感受等的心理学相联系时,心理的复杂性便使得追求这种等同的困难程度更加凸显出来。⑦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5 页。
最后,如果无法认识到犯罪与刑罚之间自在地存在的联系,如果无法把握它们的内在同一性,刑罚就会成为一种祸害而丧失正义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结合便缺乏必然性而成为一种任意。由此,刑罚对于罪犯也就变成了一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恶,罪犯便很可能被降至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因此,“犯罪的扬弃是报复……报复就是具有不同现象和互不相同的外在实存的两个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同一性”。⑧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4 页、第106 页。
黑格尔认为,不同外在实存之间的内在等同是价值上的等同,追求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就是追求二者价值上的等同——“价值”是把握刑罚的存在及其力度的关键词。黑格尔在论述“实在的契约”以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过程中,阐释了“价值”的概念,并且认为此种意义上的“价值”可以适用于刑法领域。实在的契约,是与形式的契约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中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又在这种放弃中取得了对方的所有权,如互易契约;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中,仅有一方取得或者放弃所有权,如赠与契约。在实在契约中,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永恒同一的东西,即自在地在契约中存在的而与外在物相区别的所有权,它使得当事人双方都内在地保持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永恒同一的东西就是价值。契约的对象尽管在性质上和外形上千差万别,在价值上却是彼此相等的。价值是物的普遍物”。⑨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84 页。民事损害赔偿的情形下,如果被损害的物被毁灭或者根本无法恢复原状,那么基于物之间存在的永恒同一,即价值,就必须取代物的外在性状。因为民事上对物的外在的侵害,只是一种对所有权的形式上的侵害,它并不会侵害到物的内在。将此种意义上的“价值”引申到刑法领域,便意味着不同的外在的强制之间——不论是作为第一强制的犯罪还是作为第二强制的刑罚——也具有一种永恒同一,即都表现为一种侵害。例如,从外在形态上来讲,作为犯罪的盗窃和抢劫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同,而作为刑罚的罚金刑和监禁刑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如果从普遍物、永恒同一的角度上来看,这些强制之间的差异就可以转化为侵害程度上的差异,即“从侵害这种它们普遍的性质看来,彼此之间是可以比较的”。⑩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6 页。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是一种侵害,刑罚则是对侵害的侵害,因此,二者都表现为侵害。
正是基于犯罪与刑罚之间在价值上的等同,刑罚便摆脱了外在性状上的限制,并且获得了以有限的刑罚对抗无限的犯罪的可能。
二、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实质上是矫正刑论
黑格尔的上述主张表明,他的刑罚目的理论至少形似报应刑论。然而,这种形似只是一种偶然,他的理论实质上偏离了报应刑论,走向了矫正刑论。
(一)刑罚实践首要的是维护法律的有效性,而非一味追求报应
在黑格尔看来,法必须并且必然走向现实、走向定在,“法首先以实定法的形式而达到定在……法律就是法,即原来是自在的法,现在被制定为法律”,⑪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4 页、第227 页。因此,对法的侵害就转变为对现实法律的侵害,“在国家这一客观性领域中,判断的法乃是对合乎法律的或不合乎法律的东西的判断,是对现行法的判断,而且它限于最浅近的意义,即局限于知道什么是合法的”⑫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34-135 页。。因此,法——通过对侵害自己的犯罪的否定——所达至的与自身的和解、彰显其有效性和必然性,在实定法形式中,就表现为法律通过刑罚来证明或者显示自己的有效性,刑罚主要在于维护法律的有效性。
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并不必然表现出一种报应性的目的取向。
首先,维护法律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坚持罪刑法定,与报应无必然联系。
如果法律规定,对于盗窃行为最低处以拘役刑、最高处以15年有期徒刑,那么就不得以其他理由对盗窃行为人处以管制或者无期徒刑等刑罚。反之,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某一行为是犯罪,那么行为人便不构成对法的侵害,进而对其实施的惩罚便会成为侵害自由的第一种强制,以致丧失正当性。但是,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属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与刑罚目的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该原则不仅为许多报应刑论者所主张,亦为许多威慑论者尤其是一般威慑论者所强调。如果罪刑法定原则必定只属于报应刑的内容,那么刑罚目的理论中的报应刑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区别就会淡化许多。⑬在形式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与刑罚报应性的目的追求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只有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能够受到处罚,这表达了刑罚的被动性;凡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必定要受到处罚,这表达刑罚的必然性;凡法律规定犯罪的量刑幅度,犯罪行为就应在相应的范围内受处罚,这表达了刑罚的相应性,等等。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与刑罚的报应性相等同,否则报应刑与其他刑罚理论之间的争论就会转化为是否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争论,如此的话,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的争议就没有太大意义。应当从内容上理解报应刑论与其他惩罚理论之间的区别,如多数人认为,刑法关于对累犯应从重处罚的规定,实际上是预防刑论而不是报应刑论的要求,等等。依法定罪、处刑,更适合作为一种规范惩罚的方式,而非惩罚的目的。
其次,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存在度的限定,不要求彻底贯彻特定目的。
在法的适用过程中,由于法要进入并非由概念所规定的领域,因此,对于实践中的犯罪和刑罚的评定,法的概念只能够定下一般的界限。这便意味着,该界限内的任何程度的犯罪与刑罚都属于对法的侵害的相应否定,而且并不会使不法成为有效的,也不会使刑罚转为新的侵害。另外,理性本身就承认偶然性、矛盾和假象等,因此,“仅仅存在着实际适用的问题,即反正要作出规定和裁决,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在界限之内)都行”。⑭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3 页。这种界限上的规定,表现在法律中便是相对不确定刑的规定。法律对于现实中所要求的最终的判决结论,并不会作出规定,而是将这种作出结论的权力或者义务交给法官,法律仅仅限定法官在刑罚的最高和最低限度之间作出裁判。黑格尔认为法官的意志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意志,但他并未要求法官一定要坚持基于报应的目的作出最后的裁判。⑮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7 页。由此,法官在法律所规定的限度内作出了裁判,就已经符合法律、符合法的概念的规定性,其作出的裁判便不违背公正的要求。
最后,维护法律的有效性,更注重形式上的普遍性,而非内容上的合理性。
黑格尔指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被通过就意味着它得到了该国公民的理性认可,他所违犯的法律就是他自己的法,所以按照他当初的自由意志,他已经预设了他必须自己处罚自己,惩罚是罪犯理性的要求,甚至是罪犯的“一项权利”。⑯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 页。因此,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法律,只要得到通过,都可视为是公民自由意志的表现,是法的概念的体现,法得到了尊重。有学者指出,普通公民在理性上根本无法保证国家实际上是合理的,也无法保证其在对法律秩序表示认同时是在以普遍的观点影响普遍之物,普通公民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对此表示相信。⑰[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 页。对此,或许较为符合黑格尔思想的解释是:国家和法律的正当性,并非在于它完全源自绝对的理性,而更多地在于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法的概念必然要走向现实,并不是等到法律的形式和内容都完美以后才走向现实,而只是要求法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普遍性。从历史进程的角度上来说,合乎理性的东西总是会在适用中夹杂着非理性的东西,法典的发展只能表现为越来越合乎理性,而不能表现为保持其绝对完整和完美。“对任何一部法典都可以求其更好,不用多少反思就可以作出这一主张,因为我们对最好、最高、最美的,还可以想到更好、更高、更美的”。⑱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3 页。由此,不能够基于法律的不合理而反对适用法律,法律存在不合理之处乃一种必然,必须按照法律的本来面目接受法律。因此,暂且不论追求报应的刑罚是否是绝对正当的完美刑罚,而即便如此,当基于某种原因,法律以一种威慑或者矫正等目的而制定并要求如此适用时,或者法律反映出了威慑或者矫正的目的或思想时,只要这种法律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得到了维持,那么很难说追求非报应目的的法律在当时一定是不正当的。
(二)维护法律的有效性,最终表现为矫正罪犯
法律好似一池清水,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就如同维护池水的清洁性。犯罪对法律的侵害,就类似于废料对池水的污染;用刑罚否定犯罪,进而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就相当于用清洁设施净化受污染的水,进而维护池水的清洁性。池水若要恢复其本有的清洁,就得净化所有受到污染的水,直至好像水没有受到污染。与之相应,法律若要维护其有效性,就应当消除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一切不利影响,直至相当于犯罪没有发生过———除了彰显法的有效性。
由此,对于维护法律的有效性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去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如何去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首先,可以前瞻式地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犯罪所造成的侵害不仅仅是对单一个体的侵害,而是对普遍物的侵害,是对整个社会的侵害。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抛开法律以及法官意志的因素不谈,能够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主体,主要应该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实质上是指人们以一种无机的方式来表达其意见或者意志。黑格尔高度评价了公共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公共舆论不仅包含着现实界的真正需要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以及整个国家制度、立法和国家普遍情况的真实内容和结果。这一切都采取常识的形式”。⑲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332 页。公共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形式上的公共性,它是社会中人们拥有的形式上之主观自由的集中表现。因此,即便公共舆论中夹杂着错误与非理性,但对于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来说,它却是有效并且强有力的。
在内容上,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现实侵害,第二个方面是指犯罪给社会所造成的危险。第一方面的内容较为容易理解,因为对社会的现实侵害本身就意味着给社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第二方面的内容则需要进一步阐释。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社会中的侵害所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的观念、意识。如果一种行为不被一个社会认为是具有侵害性的,即使该行为在其他社会中被认为是犯罪,此行为在该社会中也具有合法正当性。从这个角度讲,犯罪的危害表现为对社会的观念和意识的影响。因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伴随着客观行为的消失而被消除,更重要的是消除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观念、意识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而这种不利影响也就包括了给社会所造成的危险,因为危险意味着对社会观念、意识造成一定的强制,以致使行为人或行为体被迫改变初衷,进而克制或者限制某种行为自由。由此,“对市民社会的危险性就成为它的严重性的一个规定,或者也是它的质的规定之一”。⑳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8 页。在这句话中,“它”指的是犯罪。
评定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无关于刑罚是否应具有报应目的。犯罪的发生,虽然会激发许多人的报复情感,但是公共舆论并非必然具有或者并非完全具有报应目的导向。公共舆论的内容是复杂的、不稳定的,其间夹杂着的目的也很有可能是多样的。鉴于评定的内容包括行为的危险性,并且涉及行为对社会意识、观念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此可以发现刑罚的预防元素。黑格尔强调行为是衡量犯罪与量刑的依据,但行为不可能脱离行为人而完全单独地抽象存在,行为是“意志作为主观的或者道德的意志表现于外……包含……单个人的希求”。㉑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3 页、第116 页。当一个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并给社会造成客观损害时,假定他的行为对社会意识、观念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某一定值A,那么如果该行为人在短时间内第十次在相同的条件下以相同的行为并给社会造成相同的外在损害时,他的第十次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势必会大于A。然而,第十次行为所造成的超出A 的那部分不利影响,与前几次行为或者与通过前几次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或人身危险性等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在评定的结果上,也可以找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应刑所要求的罪刑均衡性的主张。同样的行为,仅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会获得不同方式的对待,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反映在刑罚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罪行什么时候被发现,等等。在社会稳定时期,犯罪可以被视为是自然冲动的产物,而在社会不稳定时期,则必须通过惩罚犯罪来树立示范,㉒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9 页。“罪行是假象的实存,它们会在更大或更小程度上得到否认”。㉓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228 页。
其次,可以以矫正罪犯的方式消除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犯罪终究是虚无的,刑罚应当否定这种虚无,法的概念必然要现实化。既然犯罪的危害在于其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只有彻底地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刑罚才能够完成自身使命。然而,这种影响的消除,并非仅仅象征性地通过刑罚来否定性地评价犯罪、强加给罪犯外在痛苦。诚如黑格尔所言,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强迫“不仅必须被扬弃,就是说,这样一种行为的内在无效性不仅要以消极的方式加以展示,而且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加以报复(针对这种行为,必须使合理性、普遍性和对等性的形式生效。)”。㉔[德]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10 卷):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1808-1816)》,张东辉、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8 页。黑格尔虽然使用了“报复”一词,但根据前述其关于报复的定义,报复实质表现为对事物内在同一性的追求。黑格尔赋予报复的意义是:使得被罪犯“损害的对等性又被重新确立起来……使普遍的东西生效并得以完成”。㉕同前注㉔,黑格尔书,第338-339 页。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犯罪之所以不法,是因为它使得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均遭破坏,㉖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95 页、第105 页。因此,“损害的对等性的确立”以及“普遍的东西的生效和完成”必须从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来综合考虑。
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论及的是法的不同面向,并不对应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后果——相对于客观行为后果,更重要的是行为人是否尊重法。无犯意的不法行为人虽然也可能造成客观损害,虽然否定了对方在主观上所认为的法,但他的行为并不应受惩罚,因为他尊重普遍的法,没有违法的意志存在。欺诈行为人应当受罚,他肯定了对方所认为的法,但没有尊重普遍的法;欺诈行为实质是一种表面上尊重法,实质上否定法的行为。在犯罪中,普遍的法以及对方所认为的法都没有被尊重,法被全然否定。㉗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94-96 页。因此,罪犯对法的态度,对于消除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至关重要,“罪犯的定在的意志必须受到影响,这一要求与如下实际相关:惩罚一定要给罪犯留下印象,否则,他的定在的意志就不会受到它的侵害”。㉘See Jean-Christophe Merle, Ide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translated by Joseph J. Kom inkiew icz, Jean-Christophe Merle, Frances Brown, Ge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1.黑格尔十分强调刑罚应当“影响罪犯的意志”,甚至对待死刑问题时亦是如此。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不惜放弃刑罚的等价性而要求杀人犯必须被处以极刑,“生命是人的定在的整个范围……刑罚不能仅仅存在于一种价值中……只能在于剥夺杀人者的生命”。㉙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6-107 页。然而,之后,在《法哲学讲演录》中他又认为:“某些情况下,谋杀的发生是为了被判处死刑。谋杀犯这么做是出于厌世、出于蔑视生命,甚至是在一种宗教的意义上……因而,死刑并不能够影响他,因为他已决意抛弃生命,由此结果便是:监禁刑取代生命刑以影响罪犯的意志。”㉚See Jean-Christophe Merle, Ide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translated by Joseph J. Kominkiewicz, Jean-Christophe Merle, Frances Brown, Ge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33.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写成于1821年,而其《法哲学讲演录》写成于1824年至1825年。行为源于意志,一旦罪犯的意志受到了彻底、有效的影响,自然就不会有进一步的侵害行为发生,而一旦这一点得到证实,其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就被消除。消除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即消除侵害),实际上是要消除罪犯的定在的侵害意志,而且只有在意志层面上消除侵害,犯罪对于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才有可能彻底被消除,否则侵害意志的存在便会向行为提出实施侵害行为的要求,而这无疑是对社会的危险或者威胁。
刑罚以消除罪犯的侵害意志为任务,这意味着刑罚不再并且不可能仅仅与罪犯的行为本身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同一行为,基于行为人主观意志的不同,甚至是人格、性格上的不同,便会使得因行为所遭受到的惩罚出现差异。一个意志软弱、犹豫不决但谋杀成功的人,与一个意志坚定、欲望强烈但谋杀未遂的人相比,究竟哪一个人实际受到的惩罚会更加严厉呢?恐怕谋杀未遂的人会遭受更多的强制,因为他的意志更难受到影响。很难认为以影响罪犯的意志为导向的惩罚是一种报应目的取向的惩罚。影响罪犯的意志,意味着使行为人不敢或者不愿意犯罪,这实质上是属于特殊预防的范畴。㉛不容忽视的是,预防理论的适用在逻辑上不能够避免刑及无辜以及有罪不罚的现象发生,而黑格尔坚决反对此种意义上的预防理论。在他看来,刑及无辜意味着刑罚成为了第一种强制,是对法的侵害,是犯罪;而现实社会即使再稳定,也不可能放纵犯罪而不罚,否则会使犯罪被肯定为合法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为了被判处死刑而谋杀的场合,为何“影响罪犯的意志”会比剥夺谋杀犯的生命更重要,以至于罪犯不能轻易地被处以死刑,而其他谋杀场合谋杀犯则很有可能必须被判处死刑呢?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或许意味着,与生命相比,更重要的是承认或者彰显法的有效性。如果应了谋杀犯的期望而判处其死刑,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罪犯的特殊的不法意志得到了承认;而如果罪犯的不法意志受到了影响,则不法的虚无就有可能被消除,法的有效性就有可能得到彰显。黑格尔的这句话或许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依据:“对着自由这一更高领域面前,生命已非必要。”㉜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29 页。
“影响罪犯的意志”的特殊预防包括威慑与矫正,该两者对于法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在“威慑”情形下,罪犯的意志只是外在地被消除,他主观上仍潜藏着不法意志,他是被迫甚至承认可能拒绝承认法的有效性,是附条件地遵守法,并不是尊重法,亦即他仍然潜在地威胁着社会;而“矫正”情形下,罪犯是完全尊重法、无条件地遵守法律,他的侵害意志已经完全地被消除。法的必然性表明它最终要在主观面向和客观面向上彻底地彰显自身的有效性,这也意味着对于罪犯意志的影响,不能仅仅停留在威慑层面,更应达至矫正的境地。
由此,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中的刑罚最终导向的应当是对罪犯的矫正,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应定位于矫正刑论。
三、黑格尔刑罚目的理论的当代意义
矫正刑论与矫正性刑罚措施曾经盛行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然而,当前的刑罚目的理论领域,矫正刑论饱受诟病、综合刑论颇受欢迎;有很多人持刑事制裁几乎不具有矫正的价值的观点。㉝David E. Duffee and Edward R. Maguire(ed), Criminal Justic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Hall, 2007. p81.对此,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可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对综合刑论的质疑
现代关于刑罚的意义与目的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不同形式的综合刑论学说,它们均以报应、预防为基础,将报应与一般预防或者报应与特殊预防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然而,综合刑论虽然注意到了贯彻报应刑论或者预防刑论所可能产生的弊病,却无视报应与预防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的矛盾对立关系。报应刑论是一种“回顾式”的刑罚理论,真正的报应刑论只注重罪犯的所作所为,而不论其再犯危险性以及潜在罪犯的犯罪可能性。预防刑论则是一种“前瞻式”的刑罚理论,预防刑论注重罪犯的再犯危险性或者潜在罪犯的犯罪可能性,但并不排斥对罪犯所犯罪行的审视———即便仅具有手段性的意义。在逻辑上,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只注重罪犯的罪行”又“不仅仅考虑罪犯的罪行”,报应与预防在刑罚目的的同一层次上无法调和。
根据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如果仅仅单纯地考虑报应、预防或者报应兼预防,任何一种刑罚理论都应当遭到摒弃。“如果把犯罪及其扬弃(随后被规定为刑罚)视为仅仅是一般祸害,于是单单因为已有另一个祸害存在,就要采用这一祸害,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认为是合理的……问题既不仅仅在于恶,也不在于这个或者那个善,而肯定地在于不法和正义。”㉞同前注②,黑格尔书,第101 页。刑罚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追求,而不是围绕着报应与预防来寻求简单的折衷。
(二)矫正刑论的提倡
矫正刑论所遭受的质疑与批判,大多是基于矫正刑在运用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致矫正目的难以实现。然而,实践上的困难难以成为否定矫正论的充足理由,它仅仅能够证明当下还不具备全面实施矫正措施的条件。没有证据表明罪犯不可能被矫正,相反,可以找到通过惩罚来促进罪犯转变意志的例子。㉟邱兴隆主编:《比较刑罚:刑罚基本理论专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 页。如同不能因为暂时无法实现蓝图而选择放弃,基于当前无法全面贯彻矫正刑论而抨击它,这并不合理。矫正刑论所面临的真正责难应当是来源于理论层面:“‘矫正’的目的虽然看起来足够高尚,但实际上只是试图把人们塑造成我们认为他应当成为的样子,这就侵犯了它们作为自主地决定他们想成为哪类人的存在者的权利。”㊱[美]詹姆斯·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美]斯图亚特·雷切尔斯修订,杨宗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 页。
矫正刑论如果真如上述批判所言,自然应予以断然否定,然而,完全可以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矫正。矫正,并非以大家都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模式为导向,并非仅仅是把罪犯看作应使其变成无害的有害动物,而只是使每个人都尊重法、遵守法律。㊲有学者基于黑格尔关于矫正说的分析而认为,黑格尔对矫正理论持批判态度(See Jean-Christophe Merle, Ide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translated by Joseph J.Kom inkiewicz, Jean-Christophe Merle, Frances Brown, Ge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35.)。黑格尔确实曾经指出:“关于祸害的这种浅近性格,在有关刑罚的各种不同理论中,如预防说、儆戒说、威吓说、矫正说等,都被假定为首要的东西;而刑罚所产生的东西,也同样肤浅地被规定为善。但是问题……肯定地在于不法和正义。如果采取了上述肤浅的观点,就会把对正义的客观考察搁置一边。”但是,黑格尔所针对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祸害与矫正,反对将犯罪与刑罚视为一种单纯的祸害,反对当时存在的矫正说——如从善与恶的角度而不是从不法与正义的角度看待矫正,而非批判矫正本身。黑格尔指出:“关于作为现象的刑罚、刑罚与特种意识的关系,以及刑罚对人的表象所产生的结果(儆戒、矫正,等等)的种种考虑,固然应当在适当场合,尤其是在考虑到刑罚方式时,作为本质问题来考察。但是,所有这些考虑,都以假定刑罚是自在自为地正义的这一点为基础。”同前注②,参见黑格尔书,第101-102 页。每个人都有自主决定想成为何种人、如何生活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否则便是一种对自由的侵犯。法并不注重人应当以何种形式具体存在——它为道德所关切,法更关涉人存在本身,“法是把仅仅作为一般自由存在者的人当做对象的。法意味着每个个人都被他人当做一个自由存在者加以尊重和对待”。㊳同前注㉔,黑格尔书,第327 页。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是有理性的、自由的存在,单个人身上蕴含着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普遍性。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是不理性的,这种行为是虚假自由的表现,是虚无的,它在否定他人的同时也导致了对自身甚至所有人的否定。基于法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社会有责任帮助每一个人——包括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都过上一种理性的自由的生活,否则等同于没有把他当人对待。因此,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办法凭借自身的努力恢复真正的理性的自由的人,社会应当通过矫正等方式帮助他,这既是对他负责,也是对其他人负责的表现,在这种意义上,矫正性的惩罚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理性要求一种合法的举止”,㊴同前注㉔,黑格尔书,第327 页。矫正刑论亦未要求更多。作为一种探究刑罚目的的理论,矫正刑论是合适的。黑格尔的刑罚目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矫正罪犯之于刑罚的重要性,为矫正刑论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彰显了刑罚的人性关怀与理性追求,学界应重视该理论而不是将其边缘化。